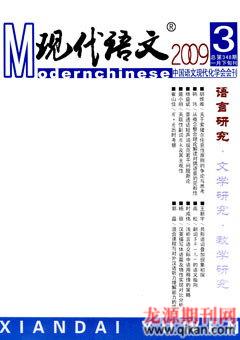不宜将“连及”视为修辞格
罗献中
摘要:现当代一些关于古汉语的著作将“连及”视为修辞格,这是一种不妥的做法。“连及”是古汉语中尚未成熟的一种表达方式,它不合逻辑、文理不通,已被淘汰。笔者认为,将其视为修辞,是缺乏道理的。
关键词:古汉语连及修辞语法逻辑
现当代一些研究古汉语或介绍古汉语知识的著作中,大都设有关于古汉语修辞的章节。在这些著作的修辞章节辛,一般都将“连及”列入了修辞格的范畴。笔者认为,将“连及”视为修辞格,是一种欠妥的做法。
什么叫“连及”呢?所谓“连及”,就是“连类而及”的缩语,又叫连文、连言、并言、兼言、并及、并称等,是古汉语中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现象。“连及”这种表达方式主要出现在上古语言中,其特点是:在叙述一个人(或物)时,若有同类的或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人(或物),就将二者一并举出。此特点正如清代学者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卷六中所言:“古人之文,多连类及之,因其一并及其一。”“连及”表达法在上古语言中的使用情况非常普遍,试举几例:
(1)《礼记·玉藻》:“(凶年)大夫不得造车马。”
车是可“造”之物,而马是不可“造”之物。只因车、马同为交通工具,属同类之物,故叙述时由车及马,将两者并称。
(2)《尚书·禹贡》:“江汉朝宗于海。”
长江入海,而汉江并不入海。只因汉江入长江,故并称江汉入海。
(3)《论语·宪问》:“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躬稼”本是稷之事,因禹曾亲自治水,与稷同为明君,故禹稷并称。
《孟子·离娄下》:“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
与上反:“三过家门而不入”者是禹,连及叙述到稷。)
(4)《孟子·告子下》:“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
“善哭其夫”者是杞梁之妻,因华周和杞梁均为齐臣,都在攻莒时战死,故将二者并提。
(5)《左传·昭公三年》:“昔文襄之霸也,其务不烦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五岁而朝,有事而会,不协而盟。”
实际称霸者是晋文公,向诸侯发号施令者也是文公。只因襄公是文公之子,又能继父业,故父子并提,连及叙述到襄公。
(6)《史记·李斯列传》:“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声也。”
乐声只能快“耳”,不能快“目”,因目与耳同为感觉器官,故连带举出。
《三国志·魏志·明帝纪》:“炫耀后园,建承露之盘,斯诚快耳目之观。”
与上反:“建承露之盘”只能“快目”,不能“悦耳”。
从上引诸例之中,不难看出“连及”表达法的“庐山真面目”。概括地说,古汉语中“连类而及”这种表达法是不合逻辑、不合情理的表达方式,非常容易产生一些逻辑和语法等方面的问题。第一,搭配不当,文理不通。如例(1)“车”可造,“马”岂可造?再如例(6)乐声可快“耳”,岂能快“目”?第二,混淆事实,是非不清。如例(3)“躬稼”本稷事而非禹事,却说“禹稷躬稼”;再如例(4)“善哭”本为杞梁妻而非华周妻,却说成两人所为。总之,“连及”表达方式所举的两人、两物或两事有实有虚,虚实难辨;人们若没有相关知识就不知其真正所指,很容易被误导,认为两者均为实指,或者认为文义费解。所以,“连及”实际上是一种缺乏逻辑、文理不通的表达方式,是不符合语言表达要求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语法学家黎锦熙先生就曾指出:“古人此例,不足训也。”(《比较文法》)
语言中任何一种表达方式的出现和使用,都要受到语言内在规律的制约和考验。语言规律要求表达方式中的语法和逻辑紧密结合,都经得起分析。换言之,任何一种表达方式的存在,都要经得起语言规律的考验,否则就会在语言的发展中,逐步失去合法的地位而被语言本身所淘汰。“连及”在古汉语史上的“生存”轨迹也正好证明了这一点。考察“连及”在古汉语中的使用状况可知,这种表达方式主要存在于先秦、两汉及魏晋时期(上古),隋唐(中古)以后便逐渐“销声匿迹”了。其消失的原因应该是语言规律对语法与逻辑相结合的要求日益严格,它由于不合逻辑、语法不通,从而失去了生存的理由。当初它之所以能够出现,主要是由于古代语言的文法尚为疏略,尚未完善;古人在行文时语法观念淡薄和逻辑意识不强。
也许有人认为,“连及”的表达方式与“偏义复词”的构词方式颇为相似;“偏义复词”可以在语言中使用,那么“连及”也应该得到认可。其实,两者是形似而实异。“偏义复词”是一种约定俗成、结构固定的双音词,具有一定的词汇意义,含义明确,一般不含歧义,不会使人误解。如《史记·吴王刘濞列传》:“擅兵而别,多他利害”,其中“利害”显然偏指“害”;诸葛亮《出师表》:“陟罚臧否,不宜异同”,其中“异同”显然偏指“异”;如此等等。这些词语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都不会产生歧义。现代汉语中同样有此现象,如“国家”,人们皆知其义是偏指“国”而不是兼指“国”与“家”;“窗户”,人们也皆知其义偏指“窗”而不是兼指“窗”与“户”。而“连及”则不同,它通常只是一种临时的连结,没有固定的词汇意义,含义不确定,容易使人产生误解,或令人费解,如上举诸例。所以,“偏义复词”的使用,古往今来,未曾断绝;而“连类而及”却早已在汉语史上“寿终正寝”。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种文理不通、逻辑不周、已被淘汰的表达方式,在现当代一些书籍中却被视为“修辞格”(就连一些权威著作也未能例外)。如现代著名学者杨树达的《汉文文言修辞学》一书中就列有“连及”的条目,书中所举之例甚多,也包括本文所举的例(1)至例(5);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杨剑桥著)以及其它一些出版社关于古汉语知识的工具书也将“连及”列入修辞类条目中。一些语文类杂志发表的文章中也持同样的观点,如郑州大学《语文知识》刊发的《“鲧禹决渎”怎么解》(1992年第8期)一文中说:“课本注者忽视了古汉语中的一种语言现象,就是古人行文中常会使用的‘连及修辞法。实际上,‘鲧禹决渎是运用了连及修辞,韩非子本意只在述‘禹决渎,而连及了鲧。”这些观点或做法都是不够妥当的。
一些学者为何将“连及”视为修辞格呢?其理由一般是认为“连及”这种表达方式在古文中有一定的“作用”和“效果”,主要是可以使古文中的词语凑足音节,使之读来上口,从而增强表达效果。如复旦版《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对“连及”的解释是:“指古人行文时为凑足音节、增强表达效果而增加字词,所增字词的意义与其前或其后的字词相同或相类。”其中即包含了对“连及”的“作用”和“效果”的认定。其它书中也有类似的解说。这种理由其实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古汉语中为补足语句音节所用的衬音词,一般为虚词而非实词。由于虚词无实意,衬音时不会“干扰”句意;而实词有实意,若用来“衬音”,同时也会“干扰”句意。“连及”表达法中所增加的词皆为实词(一般是名词),势必要“抚乱视听”,改变句意。另外,“衬音”说只能针对单音词而言,双音词并不存在“衬音”的需要,如例(4)。所以,将“连及”表达法的“作用”和“效果”解释为“衬音”“增强表达效果”,是缺乏道理的。事实上,如上所析,“连及”只是古人语言中尚未成熟、尚不严密的一种表达方式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修辞手段。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修辞本身的含义和功用这个角度,来说明为什么不能将“连及”视为修辞格。所谓“修辞”,就是“修饰文字词句,运用各种表现方式,使语言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现代汉语词典》)关于修辞的功用,陈望道所著的《修辞学发凡》中有精辟的论断,认为修辞学“最大的功用是在使人对语言文字有灵活正确的了解。”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商务印书馆)中更有细致的阐述:“修辞学的功用,可以从理论和实用两个方面来看。从理论上看,修辞学可以帮助我们揭示人类的语言之迷,阐明人类的认识活动,而且具有美学价值。从实用角度看,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即运用于说和写;另一方面可以提高理解语言的能力,即运用于听和读。”就连上面提及的复旦版《实用古汉语知识宝典》也认为修辞是“利用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多种语言手段来调整、修饰语言,以取得较好表达效果的一种语言活动。”而“连及”这种表达方式所产生的“作用”和“效果”恰好与修辞的功用是相悖的,与修辞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由此可见,“连及”有什么“资格”进入修辞格的行列呢?它有什么修辞效果呢?所以,将“连及”视为修辞格是明显不合宜的,是没有道理的。
“连类而及在逻辑上失之疏略,乃是语言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现象。”(引自《语文学习》1983年2期《“适耳目之观”浅说》)总而言之,“连及”是古人一种不好的、不宜提倡的、应该摒弃的语言习惯。我们虽然不必苛责古人的语言习惯,但也不能将古人语言中的这种糟粕视为精华。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郭康松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