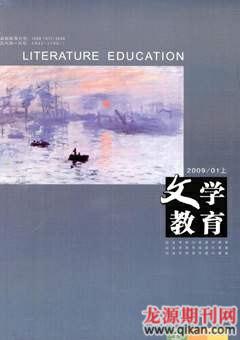试论中国现当代女性创作的理性化路程
女性,作为一个空洞的能指,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一种寄生的状态。在伦理道德中,她只是一种规范的标志;在经济秩序中,她是男人的依附;在文化层次上,她只是一个被命名者。在如此压抑的状态下,“女性所能够书写的并不是另外一种历史,而是一切已然成文的历史的无意识,是一切统治结构为了证明自身的天经地义,完美无缺而必须压抑藏匿、掩盖和抹煞的东西。”[1]
当历史跨入20世纪,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让妇女的地位一步步得到了提升,女性创作也逐渐走向了成熟。而这里所说的理性化路程则代表着女性内心精神状态由“外”走向“内”。这让我们感受到了作品中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内心价值意识由激进、感性走向理性、内省状态的过程。
一、男权主导意识动摇的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西方妇女解放的思潮,中国妇女也扛起了自我解放的责任,而同样在中国,男权在文化理念建立上的先行一步,带来了男性文化的中心主义和女性介入的艰难。这让妇女一直处于一种被动存在形式下。
对于男权文化的中心主义,马克斯·舍勒在《女性运动的意义》中有所分析:
长期以来,在确定文化目的时,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法权的性格特点和女性的独立参与都没有得到承认,所以,统治我们文化的价值、使命的目的都是男性的,而且是特殊的男性的,在这种制度中起来斗争的女人不得不先接受男性的特点。
女性在男性这座大山的压制下,存在了过多的不平等。历史上的女性运动在把自己的身份由被动转化为主动时遇到了困境,于是当世界的潮流要求与男权力量进行的较量中,女性以其张扬的个性,颠覆传统意识,并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但巨大的诱惑和压力往往威胁着女性独立性需求。其主要的限制因素有:
1、男权体系的抑制性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意识形态,一直把女性置于被动、附属的状态。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有三种常见的程式——才子佳人、诱奸故事、社会解放——体现了典型的男权意识,不管是哪种程式,都给予女人以弱小、温柔的、被男人统治、需要男人统治的来解放她们的依附于男人的形象。这样的文学让男人成为话语的主体和历史的主体,女性只是失去自我的依附者,她们丧失了自我的价值体系,最终变成“物”——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
而如此现状,在女性创作中,往往体现了两方面的意识区别。一是女性形象表现为独立意识的觉醒。二是女性往往对男性主体有出于“本能”的仇视和抵制心理。当五四新文化过后,男权权威的影响仍时刻左右妇女的思维习惯与行为顾及,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女性作家笔下的男性形象也因此被置于反动、卑劣的消极形象。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主要作家是丁玲,与传统的女性不同,丁玲的早期作品中的女性都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形态。她们大胆的尝试,第一次体验作为“人”的尊严,这时期的女性有如刚出笼的鸟,对于新生活的选择具有主动性,而反封建的潮流赋予她们爱与被爱的权利,但在这种“自由恋爱”的过程中往往形成了“情爱诱捕”模式,这时的男性意味着权利、压抑、冷漠、自私。当女性对未来生活抱有巨大希望时,男性的爱情炮弹给新思想的女性以沉重的打击,让这些刚从藩篱中走出来的女性又坠入了痛苦的深渊,值得肯定的是,这一时期的女性文本一方面陷入挣扎的困境,一方面仍怀着勇气直面自己所选择的人生,而此刻支持她们的是要求自由、平等的梦想,虽然男性带给她们的创伤将成为无法逝去的记忆。
2、女性自身思想的滞后性
“对于20世纪的女性而言,历史和文化的语境都决定着她们必然要受到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这种影响在决定她们的意识的同时也决定了她们的无意识。”[3]而这种无意识的心态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文化规范的内化。譬如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凌吉士一见钟情,她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亲吻到凌吉士的嘴唇,但她终于还是抑制住了,认为这都不是一个正经女人所能够做起来的。在她们的面前,有一条伦理道德的警戒线,当她们想要勇敢地跨出这条线,奔向新生活时,她们的内化作用迫使她们不时地往回看甚至有可能退回到原起点。
3、社会现实的纷繁性
譬如《阿毛姑娘》中的阿毛,她不满自己的生存状态可又没有办法加以摆脱,她向往都市的生活却又没有获得这种生活的途径,阿毛最终落落寡欢,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都市环境的诱惑,使女性无法找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平衡,造成了迷失。在五四初期的女性作家中也往往都看到一些女性形象受以上因素制约,而看到他们前进过程中的悲剧,不管是外在还是自身因素的影响,当时作家在建构其叙述体系中的女性形象时,还是带有自觉的冲动和感性的执著,即使满身伤痕。
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个性解放主题,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对现代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女性从几千年的封建礼教牢笼中摆脱出来,追求个性解放的自由,一方面体现了女性争取平等权利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也标志着真正现代意义上女性形象的出现。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会发现:小说的主角往往是由女性担任,但同样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则是女性获得了个性觉醒后找不到个性成长出路的悲剧命运。而这种命运的决定权除了外界影响因素外,新兴女性的道德束缚和冲动意识也影响着当时女性作品的发展。
二、女性反抗意识的成熟和母性职责的回归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创伤,80年代初的女性文学更多的是显示一种抗争意识,当“女性话语”的建立,让她们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时,这种意识也由激进走向了平和。
张洁的《方舟》无疑是那个时代具有象征性的文本。张洁在《方舟》中塑造了梁倩、柳泉和曹荆华三个独立女性的形象。在她们的身上均体现出非常强烈的性别意识,甚至可以说是对男性的沉重的批判意识,她们是一群婚姻的失败者,他们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史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曹荆华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党权威的父亲和因此失去生活保障的妹妹,嫁给了自己下放地的森林工人;柳泉因为留英的“间谍分子”父亲,和造反派小头目结合;而梁倩则因为有一个位高权重的父亲,使婚姻成为了别人利用的工具。如果说历史的悲剧带给她们不幸的婚姻,那么也可以说正是不幸的婚姻给予了她们女性的觉醒意识。这种觉醒的意识一旦产生,就带有很强烈的批判情结,从而形成了一种女性自我中心主义,她们有她们的理念和情感模式。
如在张洁的笔下,这些女性和一般的女性有一定的区别,“生孩子,睡觉,居家过日子”,她们都不行。这是她们自我形成的认识体系。张洁试图竭力强调的女性意识让女性脱离了身为女性的这一事实。当她们面对这社会的歧视时往往显得心力憔悴,但她们仍有坚定的意志,只是这种坚定的意志中包含着一种无比悲壮的色彩。
“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得到和尚未得到的权利;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不论是为了女人所受过的、种种不能言说或可以言说的苦楚;不论是为了女人已经实现或尚未实现的追求……每个女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这一句祝辞,为了自己干上一杯!”[4]
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女性抗争是把她们自身建立在与男性完全公平的状态下,甚至抛弃了生命本题活动的特殊性别价值。在这里我们是看到了饱经沧桑的女性在无力的强烈嘶叫。相对于五四时期的女性,她们仍在走不断抗争的老路,越走越彻底。但同时也反映了女性自身思想上的某种局限,因此显现出来的愤世嫉俗和激进态度。
随后王安忆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则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细腻与理性、沉稳与宽容。她开始让女性得到了一次回归。她们同样要面对情感的不幸,当《小城之恋》中那个近于憨直的女孩子,在性爱力的驱策下,不可遏止的原始生命的冲动,以及伴随的内在焦虑和罪恶感时,她在贪欲和罪恶感的忏悔中苦苦挣扎。但当我们在小说中最后看到了女人母性责任的承担时,我们意识到了母性的伟大与崇高,但这份伟大与崇高是建立在道德传统和反叛中执行的(非婚生育)。此刻的女性少了一份情感的热烈跳跃,而是在母性中找到一份先天存在的冷静与责任。
作家意识到了女性不仅仅是要取得自己的独立空间,同时母性责任的承担是无法逃避的,当我们看女人在爱的炼狱中涅槃以自我的牺牲为代价的悲剧精神时,在深层意义上我们应该意识到不是女性如何摆脱情欲所酿制的生命难局与永恒困境,而是去研究女性生命本体及命运。
此刻,我们看到了更为理性的女性在经历了热烈情欲的骚动与洗涤后,达到的从未有过的生命和谐。面对婚姻、家庭,女性的“心静下来了”。
正如王安忆自己曾说把自己的“一个女人的故事”称为“一个什么故事也没有发生的故事”,她把女主人公对爱情故事的宿命和虚无情绪里,暗示着一种女人命定里的沮丧,又从这沮丧里延伸出女人打破伊甸园的天真而走向成熟的希望。
三、“无名”状态下的女性个体意识
长期以来,女人一方面竭力跻身于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试图用男人的目光或超出性别偏见的目光来看待和描述世界;另一方面却又为自身的种种局限、束缚困扰的骚动不安,想求得一种终极的释然,为此而不断地去批判男权中心的种种不合理,表达身为女人的不幸、苦恼、愤慨、意愿和向往。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当代文学由80年代的“共名”状态转向了“无名”文化状态,“无名”指的是“在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宏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已经无法拢住整个时代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文化思潮和观念只能反映时代的一部分主题,却不能达到一种共名的状态。”[6]因此作者进入了一种“个人化写作”,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个人感受转化为独特的审美形态并表达出来。
90年代的女性作家也放下了“代表全体女性发言”的集体主义性别立场,退回到个人感受世界的立场,从而反观整个社会。不难发现她们具有了从自我宣泄到自我隐匿转变的过程。
在动乱、纷繁的社会里,王安忆敏锐地从民间文化信息中挖拾一种记忆的碎片。王安忆的《长恨歌》以个人记忆的方式描写了上海市民的生活场景,在较小的社会空间里仍然创造了一个有声有色的都市市民世界,虽然作品中并不拒绝重大的历史事件,在宏大历史与叙事的景片裂缝处,女性写作显露出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为男性话语所遮蔽,或始终为男性叙述所无视的女性生存经验。
可以说90年代女性写作实践时,强调了其“文化立场”而非“性别立场”,她们从文字的游戏和喧哗中呈现出自己的精神反叛,或踽踽独行于无声处书写沉默千年的女性生命体验。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女性个体形象出现代替了女性集体时代的共鸣。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人”非“类”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演绎着自己人生的悲欢离合、人性的美丑善恶。
在中国现当代的女性小说中,我们看到了许多哭泣的女性,同时也看到了不少微笑的女性,女性从束缚走向独立后伴随着是情感的理性化过程。相信,女性之笔不仅仅可以描绘有意义的图画,也能给我们展现女性自身更和谐的画面。
参考文献:
[1]孟悦 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郑州:河南出版社,2004:4。
[2](德)马克斯·舍勒.罗悌伦等译.资本主义的未来[M].上海:三联书店,1998。
[3]胡慧群.他者的潜在性抑制——论丁玲前期小说的女性生存处境[J].中国女性主义,2005年春(总第3期)。
[4]张洁.方舟[C].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
[5]王绯.女人:在神秘巨大的性爱力面前——王安忆“三恋”的女性分析[J]. 当代文学评论1988(3)。
[6]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李子诚,男,云南楚雄师范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学教学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