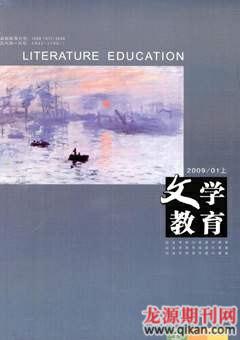由《吉姆爷》中译本看小说翻译叙述视角的传译
李 珂
一、序言
文学翻译中,译者不仅要在内容层面上与原文建立对等,也要反映原文中通过语体等形式特征体现的修辞、美学功能。根据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每一篇叙事都由两部分组成:故事和话语,即叙事的内容和叙事表达、传达内容的方式。现代小说更关注小说叙事的形式技巧,而形式技巧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便是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视角在叙事学中指事件被见证、报道和判断的立足点。小说叙述者主要使用一种视角叙述的同时,往往会对视角进行多样化的调节,如暂时使用人物视角、运用摄像式的旁观视角等以配合小说主题并取得一定的叙事效果。小说译者应区分故事的叙述声音和叙事视角,辨析视角的转换调节,并予以准确传达。本文试结合康拉德小说《吉姆爷》(Lord Jim)讨论小说翻译中的叙述视角问题。
《吉姆爷》(1900)可称是英国文学中一部突出的现代主义作品。小说打破了按时间顺序交代故事来龙去脉的传统小说叙事,“采用前后穿插多次往复的叙述方式”。[1]叙述视角方面也体现了新的尝试。整个小说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一至四章)为全知叙述,在决定吉姆人生命运的关键时刻,全面展示吉姆的思想、情感、动机与性格,使读者直接看到主儿公的内心深处。第二部分(五至三十章)运用有限叙述视角,以马洛作为好奇者探测疑云的方式展开。读者看到一个旁观者的客观印象和判断,而未真正深入吉姆本人的精神世界。第三部分(三十六至四十五章)通过给马洛的信转述了吉姆最终选择的过程。
二、全知叙述视角
《吉姆爷》以倒叙开篇,采用全知视角,全知叙述者用自己的眼光叙事和观察故事世界及人物内心。如小说第一段:He was an inch,perhaps two,under six feet, powerfully built……His voice was deep,loud,and his manner displayed a kind of dogged self-assertion which had nothing aggressive in it.It seemed a necessity,and it was directed apparently as much at himself as at anybody else.He was spotlessly neat,appareled in immaculate white from shoes to hat. [2]
浦译:他差一两英寸就到了六英尺,身量儿十分魁梧……他的声音深沉、洪亮,举止中表现出一种我行我素的固执,但没有一点咄咄逼人的张狂。这种态度好像是必不可少的,显而易见,对人对己都得这样。他真是整洁得纤尘不染,从鞋子到帽子上上下下一身雪白。[3]
熊译:他差个一两寸不到六英尺,体格健壮……他的声音低沉、响亮,他那样子表现出一种顽固的自负,但并不咄咄逼人。他好像不得不如此,而且他显然对自己同对别人都是那样。他整洁得一尘不染,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雪白。[4]
从叙述学的角度,“全知叙述者在一个超然于人物和事件之外的全局的角度叙说”。[5]他全知全能,视野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原文以第三人称描述吉姆的概况,隐含了全知叙述者的存在,并通过“a kind of dogged self-assertion”,“nothing aggressive”,“in immaculate white”流露了叙述者对吉姆较客观的评价。两译文也以“一种我行我素的固执”、“一种顽固的自负”、“并不咄咄逼人”等较忠实地再现了原文,未添加译者的主观评判色彩。同时,原文除第三句,其它句子的主位都是“he”或“his voice”。功能语言学中,“主位既是句子的第一个成分,也是叙述者组织信息的出发点”。[6]在主位一一述位结构中,主位通常是最突出的成分,说明谈话的题目。主位组织也是语篇发展最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某些情况下,语篇中一系列相关的所指往往用作主位,并被前景化和突出。因此,原文第一段便暗示了聚焦对象“he”,但未提及其姓名。中文语篇较少用代词,但两译文都未按中文行文习惯,而以“他”多次充当句子主位,这某种程度上符合原文全知叙述的特点。对“It seemed a necessity……”一句的处理上,两译文有差异。浦译使用“这种态度”为主位对应“It”,与原文一致,并补充说明前一句的“his manner”;后半句“and it was directed……anybody else”本是较客观的现象描述,浦译“显而易见,对人对己都得这样”则变为叙述者的主观评判,因而与原文不符。熊译仍以“他”为句子主位,保持了译文句子主位一致,构成放射型主位推进模式,但有悖于原文;后半句“而且他显然对自己同对别人都是那样”则达到了对原文的忠实传译。
全知叙述者“可以毫无限制地深入任何人物的内心,对其思想感情、细微的意识都可提供信息,还可以同时了解在不同的地点发生的几件事情”,[7]从而使读者对人物有一个更好的把握。如:Afterwards,when his keen perception of the Intolerable drove him away for good from seaports and white men,even into the virgin forest,the Malays of the jungle village, [8]
蒲译:后来,他痛切地感受到了一种无法忍受的力量,这种感受便把他永远逐出了海港和白人圈子,甚至赶进了原始森林,与莽林村落的马来人为伍。[9]
熊译:后来,他对不堪忍受的重负那敏锐的感知力驱使着他永远离开了海港和白种人,甚至把他赶到了原始森林里。[10]
这里,叙述者进一步显示其全知全能的便利述说吉姆的过去。蒲译将“keen perception”处理为“痛切地感受到了”,传达了人物的心理情感变化;熊译处理为“那敏锐的感知力”则倾向于对人物固有特点或能力的揭示。由此反映了两译文虽对全知视角叙事进行了一定的传译,但对语言的隐含意义有不同的揭示。再者,蒲译采用了“逐出”一词,添加了“与莽林村落的马来人为伍”,使译文具有较浓厚的贬斥色彩,而这是原文全知叙述未曾体现的。
三、人物叙述视角
《吉姆爷》第四章引入马洛这个人物,很多事件便通过他的视觉、听觉和心理进行观察和感知。从第五章到第三十五章,叙述以马洛的口吻进行,意味着由全知叙述视角转为人物有限视角。通过马洛与吉姆的接触以及马洛与他人的交谈,作者从不同层面向读者展现了完整的吉姆,揭示了吉姆的本性。这就需要译者细心辨察注意叙述视角的变化,才能准确传达人物感知事物的角度、方式和过程。如:The examination of the only man able and willing to face it was beating futilely round the well-known fact,and the play of questions upon it was as instructive as the tapping with a hammer on an iron box,were the object to find out what's inside….…You can't expect the constituted authorities to inquire into the state of a man's soul--or is it only of his liver? [11]
蒲译:对唯一的一个能够而且愿意正视这个问题的人的讯问总是在众所周知的事实上兜圈子,毫无用处,针对它进行的那种诘问游戏的作用等于用锤子敲打一只铁箱,目的是想发现里面装的是什么……你不能指望任命的官方人士去查问一个人的灵魂的情况——否则那不完全成了他的肝气情况了吗?[12]
熊译:对唯一能够而且愿意到场的那个人的审问,老是无聊地围着那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兜圈子,翻来覆去的提问就像是要知道一只铁箱里边装着什么,却老拿锤子敲它的外边一样……你不能指望这样组成的权威去探查一个人的灵魂所处的状态——或者说仅仅是他的肝脏的状态![13]
作者安排马洛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述说他出席法庭对吉姆的审问,并从马洛的角度评价这种审问毫无意义,对社会道德标准提出质疑,从而为揭示吉姆的善良本性作了铺垫。“futilely”显然是叙述者对审问行为的总体评价,蒲译以“毫无用处”单独译出,改变了原句形式,但叙述者对审问的批判得以强调,并与后文“诘问游戏”相呼应。熊译将此处理成副词“无聊地”,保留了原文形式,但与原文意思欠符合;而且熊译也能体现“the play of questions”对法庭审问的讽刺批判意味。此外,两译文对“or is it only of his liver?”的处理完全不同。从语篇衔接与连贯的角度分析,事件的经历者和讲述者马洛由批判审问行为转向了指责审问法官的无能。蒲译的“否则那不完全成了他的肝气情况了吗?”略显突兀,似脱离了上下文语意。熊译的“或者说仅仅是他的肝脏的状态!”把这种法官的探查能力从较深层的灵魂降至更肤浅的“肝脏”,突出了对他们的藐视。再如:The red of his fair, sunburnt complexion deepened suddenly under the down of his cheeks……His ears became intensely crimson and even the clear blue of his eyes was darkened many shades by the rush of blood to his head. His lips pouted a little trembling as though he had been on the point of bursting into tears.[14]
蒲译:他那白皙的久经日晒的面部的红色突然在面颊的绒毛下面加深了……他的耳朵变得绯红,甚至他那双明澈的蓝眼睛由于血冲到脑袋上而深沉了许多。他的嘴唇有点撅,哆嗦着,仿佛他就要大哭一场似的。[15]
熊译:他那被太阳晒脱了皮的白皙面孔的红润在颧骨的绒毛下突然加深了……他的耳朵更红得厉害,就连他那晴朗的蓝眼睛也因为涌上头部的血液而暗淡了许多。他的嘴唇微微撅起抖着,好像眼泪就要流出来了。[16]
这段描写仍采取马洛的视角,叙述了马洛同吉姆的首次正面接触。第一人称叙事有助于缩短人物世界与叙述者和读者世界的距离。通过马洛的视线读者仿佛也在近距离注视着吉姆。熊译取“红润”对应原文的“The red”欠妥,不符合被太阳晒脱了皮的面孔的肤色。再者,“the clear blue of his eyes was darkened”在熊译中是“暗淡了”,与原文中人物的视觉印象不一致。选段传达的重点不仅是吉姆给人的感性印象,还透视了他当时的复杂情感状态。如“as though he had been on the point of bursting into tears”熊译转换的“好像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基本合乎原意,但无法表达吉姆当时内心的强烈情感。蒲译“仿佛他就要大哭一场似的”更好地传译了对吉姆内心的洞察。作为人物叙述者,马洛的视野是有限的,他可以描述所见所闻,但对其他人物的内心,只能从他们的眼神言行等进行揣测,用诸如“仿佛”、“看来”的话语。但熊译增添“他狂热地希望用这种方式能为自己做某种辩白”,违背了人物视角的有限叙述。因此,在人物视角叙述模式下,人物的心理状态常常是通过语言形式或语篇特征暗示的,通过人物眼光所作的人物、场景等描写实为人物心理的外化。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所以译者应当把握折射人物心理的语言、语篇特征,并准确地予以传递。
作者通过借用故事中人物马洛的视角以第一人称叙述,使人物的经历、思想和感受被前景化,使读者逐渐进入人物的世界,直接感受人物的认知和情感。同时,任何一部作品都某种程度上渗透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因此叙述视角的巧妙安排有助于实现阅读中作者、叙述者、其它角色与读者的交流对话。这其中也偶尔出现全知叙述者的声音,第八章:Marlow paused to put new life into his expiring cheroot,seemed to forget all about the story,and abruptly began again……He paused again to wait for an encouraging remark,perhaps,but nobody spoke; only the host,as if reluctantly performing a duty,murmured……[17]
蒲译:马洛停下来给他那奄奄一息的方头雪茄注入了生机,似乎吧故事完全丢在脑后,然后又猝不及防地开始了……他又停下来,也许要等着听一句鼓励话;可是没人吱声;只是主人好像是勉强尽尽责任,喃喃地说……[18]
熊译:马罗停了停,又吸了吸他那快要灭了的方形雪茄烟,让它重新燃起来,他似乎完全忘了这故事了,却又突然重新开了腔……他又停了停,也许是等待一声鼓励的话吧,但谁也没开口;只有主人,仿佛很不情愿地履行着一种职责似的,喃喃地说……[19]
作者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使读者从马洛回忆中的过去的世界暂时转向他回忆时的外部客观的背景,将他讲述时的状态与听众的反应形成对比,折射了吉姆在那个人性冷漠、麻木,深不可测的世界中经受的种种压抑煎熬,进一步激起读者对吉姆的同情。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蕴涵深刻,译者理应最大限度地忠实传译。形式上,两译文都传译了原文的全知视角叙述,体现了视角的转换。内容上,选段第一句“Marlow paused to put new life into his expiring cheroot”可视为隐喻,暗示当时听众无动于衷、对吉姆的事兴趣减退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能表现了马洛讲述时的投入,他完全陷于回忆中而近乎忘了手中的烟。蒲译取“马洛停下来给他那奄奄一息的方头雪茄注入了生机”,采用了直译法,基本对应于原句的形式和双重隐喻效果。熊译取“马罗停了停,又吸了吸他那快要灭了的方形雪茄烟”,此意译仅描述了吸烟动作,对隐喻的传译则有所欠缺。这就要求小说译者在翻译时特别留意并再现人物视角叙述语篇中的视角变更现象。因为这种语言特点不仅透射人物的感觉、心理和行为等特点,也隐含着作者对于叙述文本中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的评价。
四、结语
叙述视角模式影响小说作为叙述语篇的形式特点并体现一定的作者意图。把握了小说的叙述视角,读者才能更好地理解人物、叙述事件和叙述情景等语篇构成因素间的关系,更好地领会作者的意图和作品的主题。就本文探讨的问题而言,小说译者应尽力分析原文语篇的形式特征,尤其是把握原文的叙述视角模式,根据叙述视角的特点把握语篇意义并予以传递,使译文符合原文叙述视角的叙述特点及视角变更体现的意图性,准确反映人物的感知范围、心理状况和意识形态,从而在语义、语用和语篇各层次上全面再现原文。
参考文献:
[1]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142.
[2][8][11][14][17]Joseph Conrad. Lord Jim.Oversea Publishing House, 1998.1,2,43,57,76.
[3][9][12][15][18]约瑟夫·康拉德著,蒲隆译[T].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1,2,44,58,74.
[4][10][13][16][19]约瑟夫·康拉德著,熊蕾译[T].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2,39,51,64.
[5][7]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94,109.
[6]胡壮麟.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2.
李珂,女,安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