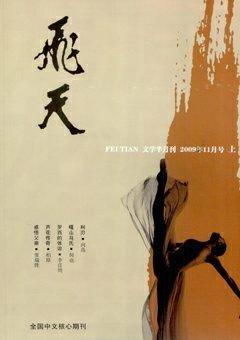生命理想的诗意表达
唐 澜 晏 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新文学”的开创者从单纯地把目光投向国外,借鉴西方文学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于西方文学走向的文学创作方式转向于中国土壤,在富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氛围与乡土气息中探索中国新文学体制的建构与完善,诗化小说就是其中的一种。废名是诗化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和沈从文在对传统小说自觉而大胆的变异中,使诗化小说成为一种新的小说样式并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废名的田园小说、沈从文的湘西小说在凄惨悲凉的现实农村寻找温情与诗意,极力在笔下表现农村美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乡风民俗,纯真、善良、友爱、无私的人伦道德。他们在深深地眷念和追怀情绪中,用诗般的语言、灵动的意象、高远的意境,刻画出了一系列诗意盎然的少女形象。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为我们呈现的国民劣根性形象,老舍笔下的北京市民形象,茅盾所塑造的资本家形象等等。这些形象以其启蒙与救赎性,民族与地域性等特征而独特存在。而沈从文、废名为我们贡献了一系列女性诗化形象,大自然之子的她们淳朴、单纯、飞扬飘逸的形象成为中国文学人物长廊里不可缺少的典型。
郑振铎曾评价《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一花一木,一桥一水,乃至园中丫头的一颦一笑,他都不曾忽略过去……而家庭生活、女性的琐屑心理,便成了他最擅长描写的目标。为了对于女性有了那么精密的注意,故写来便活活泼泼,口吻如生。”[1]其实运用它来评价废名、沈从文也是适用的。他们最善于摹写女性复杂而微妙的内心世界。女性的思春,在他们笔下写得天真浪漫;女性的嗔怒,在他们笔下也是灿若桃花。
废名并不丰富的作品中,最能代表其创作风格的是《竹林的故事》《桃园》《桥》等小说,而这些小说都着墨于女性的性格抒写,如三姑娘、琴子、细竹,因为这些少女形象的刻画,小说才会更显生动、跳跃。沈从文的小说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以描述湘西人生形式为主的乡土小说;一是揭示城市被“阉割”生活的都市小说。都市小说只是作为陪衬湘西美好人性而存在,而湘西小说里写得最好的小说皆塑造了女性角色。评论家陈国恩就说:“通观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他所勾勒的自然人性系统呈现了一个金字塔形状,处在顶尖的是纯情少女翠翠、三三、夭夭等,她们代表着圣洁的美,透着神性。”[2]所以,我们不难发现,从少女的诗意形象的分析入手,是打开废名、沈从文内心世界最合适的切入点。他们都怀着无限的爱心去表达更符合人类的形而上的人性发展,构建一个美好的理想的乡土世界,他们把审美理想寄予在这群乡土精灵上——集纳了自然山水、古老民俗、世故人情中最优美的成分,身上体现出天真、纯朴、热情的诗意性格的女性。
以废名的黄梅县、沈从文的沅水流域为原型的乡土世界是诗意的存在,那里自然风光秀丽、群山环绕、绿叶遮蔽、依山傍水,是诗一般的世界。因此,废名、沈从文笔下的女性与本土文化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一旦割裂便会显出种种乖戾来。她们的生命不是回归自然的生命,而是生命本身就是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沈从文、废名将他们笔下的女性都置于自己所熟悉的故乡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于是这些女性便在自然清新之气,潺湲流水中孕育而出,成为自然之子。
废名将女性置于大自然的茫茫竹海、高山密林中。《竹林的故事》写道:“出城一条河,过河西走,坎脚下有一簇竹林,竹林里露出一重茅屋,茅屋两边是菜园。”[3]三姑娘就是在这种清新秀美的环境中生活。老程晚间回来,从荷包里掏出红头线给三姑娘,妈妈烫好酒,三姑娘摆好酒杯。老程实在用不着下酒菜,对着三姑娘慢慢地喝了。这是一种普通老百姓的从天知命、安居乐俗的人生态度,外界繁华的喧哗与油腻的富贵无法影响他们的生活。这造就了三姑娘心地纯洁、宁静,有礼有节,与充满寂静美的自然融洽无间的性格。
沈从文在《边城》一开头就给我们描绘了“茶峒”这个小山城:“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的鱼不计其数。”[4]这片青山绿水环绕的小山城,是《边城》整个故事发生的场地,也是翠翠成长的地方,“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晒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4]翠翠生下来便无父母,可以说是以青山为父,以绿水为母,成长于青翠竹篁中,吸取大自然山水灵气。在人情事理上,遵循着大自然的安排,从万山的和谐亲密中体会到了男女之爱。翠翠情窦初开,喜欢上了傩送,这一切都是那样自然,未含半点杂质。他们在陌生环境中总是孤独者,只有回到本土文化中,才如鱼得水。
但废名笔下的少女形象和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却也有所不同——因为两位作家的生命理想是不尽相同的。废名的人生观受佛教的影响颇深,因此在作品中往往表现一种禅境,他笔下的少女,除了清纯、自然外,更多了一份才情。
《桥》绝大多数篇幅是小林、琴子和细竹的闲散自由的生活:玩耍的快乐、玩灯影、看鬼火的情绪,唱命画等等,这些故事充满了童趣,我们分明从中感受到单纯的宁静的生命跃动,童心的乐趣与甜蜜。小说为我们塑造了琴子、细竹两个卓尔不群的才女形象。她们锦心绣口,文思飞扬,她们不但能够吟诗作对,更难得的是她们有一种聪慧而灵动的情思,这种情思,在与小林的碰撞中时时发出璀璨夺目的光辉。小林曾给细竹讲自己雨中游历的经历,细竹就给小林画了一幅画,“小小的一张纸,几根雨线,一个女子打了一把伞”,这是一种诗的回应。她们说出的话里,如“想象的雨不湿人”,“月亮是仙人的坟墓”等等,无不透露着诗情。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则是纯然的——没有文化知识界入的本然生命形态。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中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他的小说里有温顺娇乖、多情执著的“边城”精灵翠翠;天真纯洁、好奇任性的“碾房”女儿三三;单纯质朴、浑然不觉的小童养媳萧萧;美丽善良、机敏无畏的黑中俏夭夭……每个女性都成了一种诗意的存在,她们生长在风俗淳美、人心善良的湘西世界,未受商业金钱势利侵蚀,行为举止较少受到世俗约束,她们没有算计人的阴毒招法,带着本真性格生存。沈从文把现实生活的重压从她们身上卸下,让她们符合自然的健康地生长。她们的单纯如稚童般透明,她们只有天真、清纯、飞扬飘逸的诗的品格,这样才能承托沈从文的健康的人生形式的理想。
那么,废名、沈从文对这一系列“女性”的诗意化叙述为了什么呢?笔者认为需从两方面去考虑:一是对文学体式的一种探索,力图用一种全新的叙述视角来完善文学的体制;二是历史大变动的血的现实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再是一个人类的适意生存的空间,他们只好趋于诗意表达来弥补这现实带来的缺陷,可以说是对现实的一种“温情”反抗,同时也是对人类“诗意栖居”的期待。
尽管他们对城市人群的堕落有过不满、批判,但这是一种叙事策略,为反衬乡村美好人性而存在的。他们在大多数作家认为愚昧无知、麻木不仁的乡村,发现了诗性与纯美,热衷于表现不受近代城市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束的原始古朴的人生的审美理想,这也正是他们所开创的诗化小说在现代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上独特存在的原因。
【参考文献】
[1]林锦鸿.红楼梦与女性美[J].红楼梦研究,1988,(3).
[2]陈国恩.浪漫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J].学习与探索,2005,(4).
[3]冯文炳.桥·桃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222.
[4]沈从文.沈从文作品精选[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242,244.
(作者简介:唐澜,四川文理学院助教;晏青,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