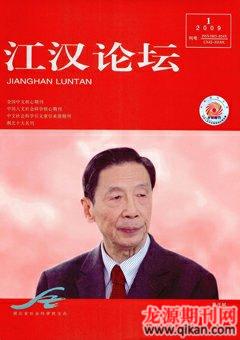饱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
梁桂莲 刘川鄂
摘要:张执浩的诗歌写作凝聚着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他对生活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梦想“在远方”到“继续下潜”进入生活内部的转变。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写作也经历了从逃离生活——融入生活——深入生活的变化。张执浩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意,同时也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理解和认识。他凭借着对生活的热情,将诗歌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现生活中的欢喜,也抚摸生活中的疼痛,温暖,饱含着生命的痛与爱。
关键词:张执浩;诗歌艺术;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1-0110-05
抒情是诗歌最重要的品质。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诗缘情而生”的论述,并形成了抒情言志的诗歌传统。新诗在其发展过程中,在抒情之外积极探索诗歌的叙事性和戏剧化等可能,其审美特征已不限于抒情,但不可否认,抒情仍然是诗歌内在生命力的体现和所在。“诗无论进步到如何程度,抒情不会和诗绝缘,除非人类的情感根本绝灭。”①当代诗歌经历了关注宏大叙事,为政治、历史歌功颂德而政治抒情诗和表达人类集体经历,表达对生命、理性的尊重而呐喊的朦胧诗后,诗歌进入到更个人化的抒情时代。这种抒情不同于以往诗歌的浮泛空洞的呐喊,也不同于其他诗歌的刻意求工,而更显自然天成,更关注个人生命的内在真实感受。这就是诗人从非日常的、精神性的集体高度转向日常写作呈现的自然、随意、亲切的抒情特色。
张执浩的诗歌写作凝聚着对生活的认识和发现。他对生活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梦想“在远方”到“继续下潜”进入生活内部的转变。与此相应的是,他的写作也经历了从逃离生活——融入生活——深入生活的变化。张执浩在《从写作的激情到生活的热情》中指出,重新回到写作的激情意味着重新返回日常生活的现场。张执浩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诗意,同时也在诗歌中表达自己对生活,对美的理解和认识。他凭借着对生活的热情,将诗歌的触角伸展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发现生活中的欢喜,也抚摸生活中的疼痛,温暖,饱含着生命的痛与爱。诗人在生活的磨练中体会生活的原始素朴之美以及人对生命、时间的刻骨铭心的疼痛。他执着地在生活、生命中体味着诗意,这种诗意不是故作呻吟之声,也不是矫揉造作之态,是包含着真实生命体验的睿智之思。张执浩的写作就是这样一种缘于生活、生命的书写,把生活与抒情结合起来,用爱来抚慰生活,超越生活,又丰富了生活的内在,达到了艺术与生命的完美统一。
一、生活的抒情
很多评论家都称张执浩是“本色诗人”,这可能是因为张执浩专注于描绘日常生活中的俗事俗物,不加以任何美化和修饰,还生活以具体琐碎的面貌。于坚曾说:“汉语的写作方向潜在着一种来自语言本质中的‘升华化诗意化的倾向。作家往往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语言往美的有价值的方向去运用”,而“我宁愿我的写作仅仅是一种语言的记录,于什么美或丑无关”②。张执浩也说,在经过生活的反复磨打之后认清了生活的真实面容:它不是透明的,也不是温情的,甚至不是污浊的,它仅仅是本真的。张执浩的诗歌写作去除了以往诗歌的雕琢、装饰、崇高和优美的外衣,而还生命于琐碎、具体、本原的真实面貌。
张执浩对生活的理解经历了逃离——融入——深入的转变。张执浩在开始写作时对生活采取了逃离的姿态,他用一种假想的美好生活来替代琐碎、庸常的生活。他在对春天、女孩、苹果、蜻蜓进行歌唱、赞美的时候,在书斋里用冥想、梦幻替代出门旅行的时候,他所谓的生活是一种远方意义上的梦想中的生活,并非 “原汁原味”。甜蜜、美好而没有接近生活的本质,它是梦想抵达的高度。因此诗人在早期诗歌和早期的小说中将生活灌注了一种真、善、美的理想,并反复吟诵。在作家眼中,“三个小女孩和一只雏鸡”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美丽图景;“糖纸”的颜色是生命和青春的绚丽多彩;“糖纸的甜蜜”是全世界人类的甜蜜;“蜻蜓”的飞行是我们集体的梦想。这是诗人“灵魂中形同虚设的一幕”。诗人在自己假想的生活中做着甜蜜而温柔的梦,现实的残酷和无奈在梦想中逃遁得无影无踪。张执浩这时期的写作饱含着激情,激情让他具有“一梦到底”的毅力,也让他敢于“在火上生火”,向高处攀升……然而,这种全力以赴的歌唱热情并没能持续很久。诗人很快从梦想的天堂跌落到现实的大地,开始接受真实的生活。
由此诗人看到了生活中真实的一面。撕开生活丰富、美好、温暖的表象,内蕴更多的是残酷和无奈,虚伪和欺骗。女教师发现“她年轻,但有人比她更年轻/ 还有人使用更猩红的唇膏表达/生活的勇气;还有一双更假的眼睛/要与她分享这新的一日”(《女教师的早晨》)。残酷的生活打破了诗人的白日梦,诗人清醒地看见:“昔日的春天,昔日的繁花”,“如今只残留一截断壁、三两根枯枝”(《倒塌的花架》);昔日的甜蜜的小女孩如今已变得“少年老成”,而以前的梦想现在是“掘地三尺,我也不能让好梦成真”。张执浩在与生活面对面之后,看到了生活的不完美和残缺,但他仍然倔强地“要与美为伴”,要“排出内心的积怨”,做一个生活的歌者。他相信诗具有一种能改变生活并使生活履行它许诺过但落空了的东西的力量。他就是怀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去写作、生活,让生活充满诗意,让写作抚慰生活。但是诗人很快发现,这种高于生活的美是脆弱而易损的,它并没有永久的保质期。他说:“在战栗的桥身上,我不是生活者/更像是生活的敌人。”(《长途卡车上的猪》)生活教会诗人认识到了生活的琐碎、具体,不得不重新面对生活承担生活。诗人也由梦想生活转变为体认生活:“我曾笑过,笑这些雪片一般的报纸/笑这些笑话,这些奇闻轶事/现在看来,它们就发生在我的生活里/不是身边,而是内部。”(《一张晚报的早晨》)诗人意识到,作为一个人,是无法逃离具体而实在的生活现场的,只有进入生活才能做到审美性的超越,简单的否认和盲目的逃避导致的只能是梦想的落空和写作的空洞。张执浩不断调整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努力使自己的写作与自己的日常生活保持着一种对应关系。他希望他的诗歌能说出常识,具有一种本真性,因为这比发现真理更重要,也更艰难,更需要勇气。
一般而言,作家总是喜欢关注重大的事件,喜欢探寻哲学或者是真理,以显示“不同”,“每个人都试图找到一条引人注目的路,既不是为了深邃的思想,也不是为了求索,而只是为了硬挤入一种特殊的差异性”③,但是诗歌更需要的是“回到内心”表达那些普通的事物和朴素的情感。诗人开始反思生活,并对自我进行无情的解剖。诗人在诗歌中质疑到:“我是不是在高音区徘徊久了,被晚风/吹空了内在的激情;或者,必然是/低音区积水,内心是一片沼泽地。”(《变声期》)通过反省,他认识到诗人、诗歌与生活的关系不是俯视,也不是仰视,而是平起平坐。一个优秀的诗歌写作者必然是一个深入生活,并且与生活平起平坐的人,他有勇气和力量直面生活,体会生活的充实,也正视生命的虚无,把永无止境的劳作当作神灵的奖赏而非处罚,并加以领受。诗人由此返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场,积极地融入日常,在生活内部做匀速位移。诗人说:“内心里有一片牧场,但没有/今夜的羊群;内心里有爱,但没有/受爱者:内心里有一张嘴,但没有/力气说出‘内心。”(《拔》)这时候,生活再也不是一种梦想和白日梦,而是带给诗人切肤之痛的真切实在。
由此诗人在深入生活中发现:平凡普通的生活中也蕴藏着美,更有一种亲切、朴素之美。这种美一直存在,只是它需要进入生活去挖掘、打捞。张执浩看到了诗歌与生活的合一性,并不是非此即彼,背道而驰的,诗歌就蕴涵在平凡的日常里面,从具体细小的物事中体现出来。诗人从一棵白菜、一块红布、一碗米、一瓢水等具体的物事中挖掘出它们平淡而朴素的诗情,细小、精致而又不嫌花哨。诗人说:“要有足够的耐心为土豆削皮/我一再要求自己,要敢于将日子过得热气腾涌/细小的、些微的、缺乏味精的生活/足够的承受力将带来足够的/欢乐:不哭,也很少笑。”(《足够的》)诗人感叹:“亲爱的生活,你把我磨练得无情无义,/也将我击打得麻木不仁。”诗人明白对生活不仅是面对而且更是一种承担,只有让写作与生活发生了“关系”,展示了生活的难度和困境,写作才具有人性的温度,具备贴己感,能够直指人心。正如张执浩在写给《平行》文学网站的那段文字:“所谓平行,首先是与生活保持一种恰如其分的对等关系,既是毅然反抗,又是当然承担;既从容,又紧张;既明知无望,又矢志前行。”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就是这样“对等”而又“平行”,既相互交叉渗透,又相互抵触超越。
于坚说:“诗歌已经到达那片隐藏在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底下的个人心灵的大海。”④而张执浩也经历了“写作的激情到生活的热情”,认识到写作就是在“内心的工地”不断地开掘勘探,而不是在高空架云梯,丰富的内心才可能成为写作的工地,诗歌就成了不断挖掘、开采情感的勘探者,诗人就像是一个在工地上忙碌的工作者。张执浩的诗歌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契合了当下凡世俗人的生存状态和审美取向,拉近了诗歌与读者的距离。他从生活中发现诗意,也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在生活中学会倾听,唱出了心中最真实的悸动和震颤,给人以温暖和信心。
二、生命的疼痛与抚摸
张执浩的诗歌写作蕴涵着一种生命的疼痛感,很多评论家也认为读张执浩的诗歌有流泪的冲动。这种疼痛感不仅缘于身体的具体的痛感,更是体悟到内心灵魂最深处的颤栗和悸动。张执浩的诗歌有一种直指人的灵魂最深处的东西。他的诗歌经常是“语言沉浸在血里/到了半夜,你闻到了自己嘴里的血腥味”(《岁末诗章》),诗人对时间、生命有一种刻骨的疼痛,他感受到时间的流逝、生命的消殒,以及人在命运面前的虚无和无助,由此引发了对存在的哲思性的思考。他诗歌的这种对生命、时间的形而上思考是与生活的具体物事结合在一起的,温暖、及物而又给人以震撼。
诗人首先意识到的是身体上的具体的疼痛。身体的疼痛是最显在的,这种痛感也是最容易表白的。诗人这样描写牙疼:“我曾经拜访过牙医,让他/在我的龋齿里填充多余的疼。”(《体力活》)牙疼是身体表面的疼痛,具体细微,让人烦扰。诗人不仅确切感知疼痛的所在,也感知到疼的声音。在《内心的工地》中诗人形象地描写了关节之疼:“‘到处都是疼!他抚摸着风湿的关节/听见骨头里面传过来一阵劈劈啪啪的/断裂声,仿佛大风折断树枝。”诗人从疼痛的部位写到疼痛的声音,尖锐,刻骨。这既是关节的疼痛之声,同时也是时间对人反复捶打的声音。诗人不仅发现了生命中的痛感,还发现了“疼”的颜色是“碜白”的,发现“疼”在自己体内行走的隐约的脚步。疼痛在诗人的笔下就具有了一种可视、可触、可听的质感,与人的生命、生活体贴相连,不可分割。但诗人并没有停留在抚摸把玩身体的疼痛上,而是经由这种具体的身体之疼上升到生命之疼和生活之疼的形而上思考,并借此反抗肉体。肉体的疼痛更深刻地来源于生命的疼痛。它为认识生命之疼、生活之苦提供了一个契机。
生活是琐碎的,生命是疼痛的。每个人都得经过时间的敲打,最终达到对生命的敬畏。诗人撕开自己疼痛的伤疤,在诗歌中反抗时光的无情和生命的无常。诗人写到:“我想用回忆解开青春的死结/我想与时光步调一致/用一只梦的容器交换前程的虚无。”(《吹着》)诗人还发现命运瞬息万变、不可把握的性质,人对此则无能为力。诗人说:“我想打捞命运,付出了/高代价,雇佣了鲸鱼,却被它拖进了/地狱。”(《内心的工地》)诗人的写作始于疼痛,而他自己则更像是一个铁匠,在疼痛的神经上创造。“在成为一把刀子前/ 在铁匠的脑海里,疼痛/已经发生,并且难以扼制。”(《在成为一把刀子之前》)张执浩在母亲去世之后,更是深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破碎性,他一次次地深情回忆母亲,一次次地让自己面对巨大的悲痛,感受生命的疼痛和时间的创伤。张执浩的诗歌里有大量的关于疼痛的语句:“我退出来,让时间喊‘疼!/哦我陷得太深,如同血液里的血液,/也像是海洋中的水滴。”(《拔》)时间已经与疼痛合而为一,不分彼此。时间流逝,生命在历经岁月的涤荡之后留下千疮百孔。“早年的一根刺埋进了晚年的肉体/如今,我疼。/我的呻吟缘于无知岁月里的一段梦境”,诗人又进一步确认到“是的,我疼,我疼于老之将至”。诗人遏止不住地喊叫着疼,这种痛感缘于岁月、时间给人带来的创伤和灼痛。诗人在与时间面对面的交流中,深深感到生命在时间面前的无奈。时光之刺扎进了肉体,始于一个孩子的长大并贯穿一生。“所以,我的疼/始于一个孩子埋在体内深处的懊悔/他不该长大,更不该成人/所以,我的疼贯穿着漫长的一生/而回去是不可能的。”(《大于一》组诗)诗人把具体的身体的疼痛赋予了一种形而上的生命内在的体验,深入到了骨髓和血脉。作家林白敏锐地发现了张执浩诗歌中的这种与生活相关的痛感,她说:“张执浩的诗中盛满了生命的爱与痛”,“这种痛感不是纸上的疼痛,也不是一种遥远的疼痛,不是‘俄罗斯的暴风雪。读张执浩的诗,你会明确知道他身在何处。他的痛感是从我们生活经验出发的,跟我们的身体、身边的事物有摩擦。他的疼痛感是可以传达到我们的血肉里的。”她引用张执浩的诗句:“我知道大海的苦胆早已为此碎裂/我挤着自己所剩无几的甘美之心/潜下去,直至心碎。”(《继续下潜》)
诗人不仅在诗歌中反复诉说疼痛,还反复地用“衰老”来表达时光的无情和对命运的捉弄。“在皱纹里。在风中。/在一个人的节日。/未及展开的青春与老年相遇。”(《哆嗦》)衰老是人不想面对的现实,却不得不去面对。“他拒绝了所有的梦境,惟独留下一张白纸/他从不书写,但始终在读:/‘您怎能指望我爱上这老人的世界?”衰老是时间带给人的不可磨灭的印迹,它在让人面对身体的溃败的时候体验到深刻的精神的疲乏与无力,甚至直接导致人对生活的虚无理解。因此,承认衰老,面对生命的不可挽回的消逝,对人来说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力量。“现在他虽然老得不够彻底,虽然/面对货郎手中的小圆镜时,难免恍惚/把镜子里面的老人误认成了别人”。张执浩发现了时光对人无情的剥蚀,感慨生命像忘川之水一样不可重复,因此,他的这种对生命、时光的描写就灌注了一种刻骨的温情,出之于生命的疼与痛。既深刻体验疼痛,又在疼痛中反复书写,达到对生命的一种哲思体验。
三、隐喻的表达方式
中国文化的特质之一就是“诗化”,“诗化”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隐喻的使用。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隐喻不仅是作为一种妙笔生花的描述手段存在的,而且是作为一种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存在的⑤。隐喻是无所不在的,它已经渗透到人类语言的方方面面。离开了隐喻,人类就失去了把握世界的工具。
在文学史上,隐喻有过分夸大过度滥用的弊病。在90年代的写作中,于坚等人针对诗歌隐喻的过度泛滥和只对历史、命运、玄学等抽象问题的关注,在“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两大阵营的交锋中,提出了“拒绝隐喻”的命题。从本质上说,要拒绝隐喻就会从根本上抽空了语言活动的内容,陷入了拒绝语言的迷宫。于坚曾在《拒绝隐喻》中宣称:“在今天,诗是对隐喻的拒绝。”其实于坚的“拒绝隐喻”意在恢复日常的知识,以当下的、具体的、直白的、可感的口语进入诗歌的神殿,寻找新的意义、命名和肯定,在词与物、现实与欲望、生活与思想之间建立新型关系。与此相应的是“回到常识”的口号,“回到常识”,首先意味着要清除覆盖在词语层面上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尘垢,使人有能力回到事物和生命本身的最基本状态,有能力动作。在诗歌中,隐喻不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诗歌方式,是诗人理解社会、文化、历史的方式,是诗人与世界之间的隐含的沟通和默契。因此,于坚的“拒绝隐喻”更准确地说是拒绝语言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沉淀,还语言以自然清新的面貌。从这个角度说,人类的文化活动不可能脱离隐喻。“隐喻是诗的基础,也是诗性语言的根柢,‘没有隐喻就没有诗。没有广义的隐喻,也就没有诗性语言”⑥。
张执浩是一个精于隐喻的作家,正如我们说他是一个精于语言的作家一样。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隐喻不仅是修辞学意义上的,更是诗学意义上的。“诗学意义上的隐喻结构,是更高层次上的智性创造的艺术认知模式。它是探索和表现人类复杂微妙的生命和精神的秘密形式,是本真而深刻的艺术感知的形式”⑦。在语言的使用中,每个人都无法避开隐喻,拒绝隐喻也就是拒绝了语言,而这是不可想象的。“隐喻并非仅仅是一种修辞或陈述,并非局限于逻辑的领域,一种认识上的解释性的手段,即某种东西取代了本来所指的东西,或说某种东西使另外的东西得到理解。它自身是一种结构性的力。诗与思并不仅仅是通过它,通过隐喻去思某种东西,诗与思正是从这儿发生的”⑧,隐喻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与现实也是不可分割的。隐喻不仅是修辞手段和诗歌技巧,更是诗歌结构方式和诗性思维方式。柯勒律治也认为:“想象的最终实现将要采取语言的形式,而艺术想象的实施过程,也就是隐喻的过程。通过隐喻,词语建构了一个来自它们自己范围内的现实。一个隐喻自身就是一种思想。人们就生活在隐喻的世界里。而隐喻又是世界的隐喻。”⑨因此隐喻是语言的特性,它本身是人类本质特性的体现,是人类使世界符号化即文化的创造过程,也是人类活动的根基。它充满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止表现于我们的语言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张执浩善用隐喻,而不是单纯地为语言增加所谓的文化或者是意识形态的内涵。隐喻意在言词间造成一种“事物和意义相似性的辉煌映射”。张执浩诗歌中的隐喻是从事物本身出发的,缘自事物的本性,直接抵达人的内心。在张执浩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小美女”、“小女孩”、“蜻蜓”、“春天”等词,这些词语在诗歌中表达的是美丽、真诚、纯洁、甜蜜的象征,并不是被刻意标示出的一个与现实对峙的特例,它只是诗人对生活的一种抒情性的表达。在《高原上的野花》中诗人说:“我愿意为任何人生养如此众多的小美女/我愿意将我的祖国搬迁到/这里,在这里,我愿意/做一个永不愤世嫉俗的人/像那条来历不明的小溪/我愿意终日涕泪横流,以此表达/我真的愿意/做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父亲。”我们说一首诗的隐喻结构是一个意象系统,同样,在这首诗里,我们能看到张执浩惯用的诗歌意象系统。这里的“小美女”与诗人一系列诗作中的“女孩”、“女婴”具有内在精神上的一致性,都是指向一种纯洁、美好的事物,是与生活实在相连、和谐共处的。“祖国”意指诗人“内心的工地”,他要把内心投注在这里,建立精神的家园,实现心灵的栖居。“来历不明的小溪”和“涕泪横流”紧密呼应,是诗人缘自内心的“亲密的泪水”;“披头散发的老父亲”我们可以看成是诗人在经历了岁月的洗礼之后,从一个将生活理想化的人成为一个与生活平行的人,不牵系于外物,不执着于妄念,通脱畅达。在《体力活》里,诗人这样写到:“我曾经拜访过牙医,让他/在我的龋齿里填充多余的疼。”“牙医”隐喻生活,而“多余的疼”则意指诗人不想也不愿意承担却不得不承担的琐碎、平庸和淡淡的悲凉、痛苦,是时间对诗人的击打和磨练。张执浩用这些平常的词语表达了生活的真实感受,既不刻意伪饰,也不故作姿态,顺手拈来,贴切自然,温暖贴心。在张执浩的诗歌中,“每个隐喻都是一首小型的诗,而一首诗则是一个巨大的、连续的、持久的隐喻”⑩。张执浩对语言的把握,得力于他对生活的感受和触摸。他的每一个隐喻,看似平常,但都是一次对新的意义关系的发现和创造。他把词语从既定的语法修辞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和意义。因此,“诗的语言是这样一种语言,追求自由和超越,不断创造新的意义。诗性语言,是语言的欢乐,是存在的欢乐。诗的语言使思和意义从约定俗成的语言规范和强制中解救了出来,语言在语言的活动中获得了一种超验性”{11}。
四、含蓄、韵致的语言
张执浩的语言充满了诗意,具有很强的情感渗透的力量。诗人是由语言构成的,诗人的自身构建必须从语言开始。诗人以他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存在于诗歌文本里,语言是他或她外显的气质。个性化、独特化的语言方式是他作为诗人存在的必要条件。马尔克斯有一段关于小说语言的对话:“对我来说,文学就是那表面上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东西(一个形容词),就是最细小的细节,就是一个形容词和一个韵律,形容词是一个作家和另一个作家区别的标志。我酷爱词语,喜欢不同的作家使用不同的词语。”{12}马尔克斯虽然说的是小说语言,但并不局限于小说,它同样适用于诗歌写作,诗人更应该在语言中建立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
张执浩是一个精于语言的作家,他的语言除去了那些涂饰,但却具有自然的鲜活的力量,能够直接温暖人心。他的语言新鲜、自然而又具有生活的气息。“比燕子更轻巧而透明的飞/六月的蜻蜓/运输阳光的飞机”(《蜻蜓》),诗人把“蜻蜓”比作“运输阳光的飞机”,一个小小的物事,因为诗人用充满爱的目光来看,就成了纯洁、温暖的象征,洋溢着美好的诗意。这种诗意是诗人情感审美的结果,它不同于那种冷漠的直白书写。同样,在《油菜花》中诗人写到:“油菜花。我想在夜幕中辨认/谁是把泥土揉成了黄金的人”。油菜花的金黄让诗人联想起黄金,自然、贴切,毫不伪饰,毫不矫情,活跃在简单自然的诗句中,平淡中渗透着诗意。这是诗人建立的理想、自然、美好的境界,它不受世俗生活的污染和破坏,空灵、美好。而要建立这种理想的诗一般的生活,则只有从精神上努力,要靠情感、想象、幻想和爱,这才能实现人类“诗意地栖居”。而“情感本身才是人们全部生存赖以建立的基础,人必须通过活生生的个体的灵性去感受世界,而不是通过理性逻辑去分析认知世界,诗与情感结为姐妹,诗是人心灵具有的行为方式”{13}。张执浩的语言具有一种情感的力量,这源自他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的笔下,这些语言因为有了诗人热情的灌注而变得鲜活、生动。在他的笔下,石头会“互相倾轧,像盲目的仇恨”《采石场之夜》,蚂蚁在“大地深处散步”《一列老式火车》,蛇会在“无意间触动了/自己晾在枝叶间的外套”《蛇与蛇皮》,张执浩用比喻、拟人等多种手法写人、写物,生动活泼,在平常之中见出诗意,传达了诗人内心的美好情怀。这既是诗人对生活、世界的审美方式,也是诗人心灵的诗意境界的表现。诗人甚至在怀念逝去的故人的时候,语言也是纯净的,没有歇斯底里的泪水充斥,却自然洋溢着一种深深的缅怀:“一年了,我计划着怎样架上纸飞机去你的国家旅行/我想出现在你调配室的荧屏里/我还计划养一些蜻蜓,把它们训练成/为你复仇的斗士,总之,我计划去做一回你。”含蓄、节制地用一些诗人惯用的意象和人们熟识的事物,用梦想的方式表达了对故友的怀念,干净、纯粹、明亮而不失真情。
90年代后张执浩由诗入小说,“坚守纯诗的艺术规范和个人化的写作立场,把纯诗和个体的精神元素注入他的小说,扩大了他小说的诗意空间,增强了他小说的表现功能,自有其独到的韵律和色调”{14},实现了诗性写作。张执浩不仅追求诗歌语言的优美,就是在小说中我们也能时刻感到他语言的诗味,而这正是张执浩写作的一个主要特征。语言诗化的实现一是语言的流畅自然,在语言中营造意境。如上面所说的乡土田园风光的描绘,作家不在于表达某种清晰、明确的意思,只是为了组织语言以实现一种诗化境界,流畅诗意的语言表现的是乡村静谧、和谐的氛围。二是运用丰富的想象、比喻,产生一种出其不意的新鲜刺激,从而制造一种诗意的效果。张执浩善于把不同的事物组合起来,加以想象性组接和比喻运用,产生一种新奇的效果。张执浩在《倒塌的花架》中这样写道:“从前是春天,花架是平步青云的梯子/从前是百花,歌声是招风换雨的布匹”,如果说把“花架”比作梯子还不算很新奇的话,把“歌声”比作“布匹”就是作家充分利用想象的结果。“春天不过是一桶倾倒的油漆/风的刷子使万物变得干净而轻盈”《不化的雪》,春天的万紫千红和油漆所具有的五颜六色的色彩具有相似之处,自然贴切中又透着新意。作者还充分发挥想象“收藏雪花”,雪花本来是极易融化不具有收藏的特征,但是诗人利用背离常规的语词组合,突破一般的语法规则,在变异中实现了诗意,增强了语言的表达力。再就是作家主观内心的诗意。诗人都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诗人写小说会不断地将诗歌中的意境、情绪带进小说中,追求小说诗意的情境。这种诗意情境正是作家所要追求的,它可以抵抗世俗中的污浊和无奈。因此这也是作家主观情绪的反映。作家的内心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世界,蕴藏着他对美的发现,诗意的开掘。作家内心的诗化是实现语言诗化和文本诗化的前提和源泉。
张执浩的诗歌体现了一种对人生命的现实关怀的情怀和一种爱的力量。他以诗人的眼光来面对生活,对具体而微的事物充满了爱心和感动。诗人耿占春指出:“在一些九十年代重要的诗人作品中‘明显地增加了日常的情境与情节,增加了戏剧化与对话性。这样的诗人是注意力的给予者。它显示了诗人的好胃口,要及时地消化掉从现实世界中冒出来的一切非诗意之物”{15}。张执浩正是凭借着自己对生活、生命的热爱来消化、体味这些平凡中的事物的。在他的眼中,一粒米、一碗水都闪烁着诗意的光辉,生活处处显示出了它美好的一面,只是我们缺少了发现和注视。在时下放逐激情和温情的写作中,张执浩对诗歌的本真追求,对爱和美的发现、探寻,是对于人心人情的理解和抚慰。这可能就是张执浩作品中的诗歌精神,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写作精神。“诗歌精神”应该是一种朦胧的向上的超越力量,一种神圣的音调,一种苦厄中怀着希望的信念,一种对人类和大自然的眷恋和爱,它也是一种批判的力量。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是“精神乌托邦”的属地。
注释:
① 沈奇、王荣编《台湾诗论精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② 于坚:《棕皮手记》,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121页。
③ 《没有什么可以给青年诗人的忠告——聂鲁达访谈录》,见潞潞主编《面对面——外国著名诗人访谈、演说》,北京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④ 参见陈旭光编《快餐馆里的冷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
⑤ 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⑥ 马大康、胡勇:《从原始隐喻到诗性隐喻》,《学术月刊》2005年第5期。
⑦ 姜耕玉:《当代诗的隐喻结构》,《诗探索》1996年第2期。
⑧ 耿占春:《隐喻》,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⑨ 转引自李诠林《吕赫若小说文本的文化隐喻功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⑩ 保罗·利科尔:《言语的力量:科学与诗歌》,《二十世纪美学经典文本》第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页。
{11} 张瑞德:《〈隐喻〉:诗学新论》,《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2} 转引自郝雨《跨文体写作与诗化小说》,《理论与创作》2003年第1期。
{13}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文集》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页。
{14} 昌切:《惜名的张执浩》,《文学世界》1998年第2期。
{15} 耿占春:《群岛上的谈话》,《90年代实力诗人诗选》,漓江出版社1995年版,第311页。
作者简介:梁桂莲,女,1981年生,湖北当阳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湖北武汉,430079;刘川鄂,男,1961年生,重庆人,文学博士,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