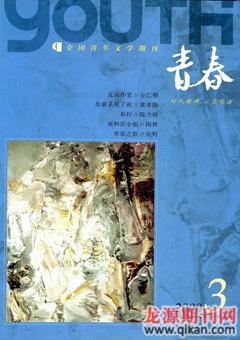青春之歌
吴 野
方之的《青春》之梦
粉碎四人帮,中国文学开始第二个春天。
早春二月,大批年轻人从广阔的天地走来,带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迎接新生活的欲望。他们中间,有为数不少的人渴望着将心中的话在笔头上像泉水般喷涌出来,谱写人生,奉献社会。新的文学杂志呼之欲出,适逢其时地提供了他们奋身的舞台。
著名作家方之以及下放在淮阴的斯群和其它文联同仁回到南京,他和斯群一道以敏锐的感觉,呼吁在南京办一个青年们渴求的文学月刊。文革前上海曾有一个培植文学青年的《萌芽》,受到欢迎,该刊物已停办。南京创办,则为全国第一家。方之患着严重的肺心病,气喘吁吁地到处呼吁:“办《萌芽》,办《萌芽》!”,
南京市委非常支持这个想法,刊物从刊物起名开始,呱呱落地的婴儿应当有一个寓意深远、特别是广受青年欢迎的名字。斯群带着编辑部的同志在大江南北工厂学校到处征求意见。一共收集了上百个刊物名称。都不错,提议的人都有道理,真是箩里挑花,越挑越花。对于《青春》这个刊名,起初有人不同意,认为俗了一些,有点像牙膏的牌子,但大多数人都说好。青春是人生最美的年华呀!最后,斯群一锤定音:《青春》。问到什么理由?人生最宝贵的就是青春呀。经南京市委批示,1979年10月创办《青春》文学月刊,由斯群担任主编。
《青春》的封面是有特色的。试刊号取青春女子的形象,青春的火,在燃烧,充满激情。定下这个基调以后,每期均采用少女形象,有一期用了前线歌舞团舞蹈演员的跃动舞姿,居然有一两个读者对于封面上露出了手膀有意见,个别人的意见毕竟代表不了大多数,大多数人喜欢,就是《青春》的倾向,不断展示的少女形象形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我非常荣幸地接到斯群的调令,参加筹办。编辑部在鼓楼检阅台,两层楼,水泥钢筋建筑。夏秋之交的南京是出名的火炉天气,这碉堡式的建筑则是火炉中的火炉。曾传炬等同志都打着赤膊,穿一条短裤衩。由于文学长期处于断层状态,稿件需要一篇一篇组织,工作量很大。方之躺在简易的钢丝床上,一面咳嗽,一面看稿,我不由得想起与这位南京文学青年的良师益友相处的难忘日子。
六十年代,我们参加文联组织的活动。方之负责小说组,我们时常见到。他不事修饰,总是那一身蓝色的衣装,出口就是淳朴的口头语。因为“探求者”的事被打成右派以后,话不多,其实,他是很能说的,没有事就在南京郊区跑,我到栖霞、六合、江宁,好多农村干部都说方之是他们熟识的朋友。只要听到新鲜的谚语、俗语、歇后语、,马上就记下来。以至于他的作品,脱口就是老南京话。方之的小说,除了立意、人物个性等好多方面的成就,语言犹有强烈的特色。在方之去世两周年,叶至诚在《青春》上专门撰文评论方之作品的语言特色。他十分赞赏《出山》的开头,“小王村远近闻名,就因为:穷”。又借主人公王如海父亲的口,代表他接受群众意见参加选举,从侧面表现这个主人公形象:“如海和我一样,是个粗胚,只会撑船、放鸭、捞鱼、盘泥巴,从来没有当过干部。千根骨子撑把伞,还望众人抬举”;还用南京郊区的土话写王如海拒绝女儿的个人要求:“你跟我说,是嘴上抹石灰,白说”,听其声如见其人,真像是农民在和你对话,又像方之的声音。在讨论稿件的间隙,方之也会讲一些个人的事情,比如,省里出于关心曾经打算把陆文夫调南京,方之调苏州。这两位作家坚决不同意,因为作家离不开自己的生活基地,尤其是语言环境。如果真的那么办,就比如让鱼离开水,树的根被拔出了土。方之说到这里,又来了一句南京话:“那真是‘哄嘛!”,(哄,就是闹笑话的意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我坐在一边揣想,如果真的让他们互调,用拔苗的办法帮助生长,中国文坛就没有了陆文夫,也没有方之,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呢?
初稿、二稿、三稿,排版、印刷、在各大报刊上发广告…… 杂志试刊号进度向前推移,方之的病情也在加重。无情的病魔甚至于有意抢在方之的前面,他没有见到亲手修改的稿件变成铅字;他不知道,试刊号会受到那么强烈的欢迎,发行量高达十六万份。
方之在重病中。这个刚强的人被病魔击倒了。但是,他志犹未尽,壮心未已。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处于最好的创作环境,和方之有着相同经历的作家都争分夺秒,譜写力作。方之届于中年,正在炉火纯青,胸怀着文学壮志。青年时期,他以“岁交春”、“出山”等作品步上了创作的高峰,进入新时期以后,他又以“内奸”等新作瞩目于国内文坛,获得了1979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获奖时他已去世。在思想解放运动的论坛上,这个身体羸弱的人,以战士的风姿迎战极左的余毒,倡导“防癌文学”。在医院,无论清醒时还是睡梦里,他的心还在系念着文学。在他的书案上堆着厚厚的稿纸,那是他宏伟的写作计划。有一次,发过高烧之后,极度无力。听说陈白尘先生来访,居然爬起来,撑着病体下床,现场的人都感到惊愕。
方之的家就在我的对窗户。儿子韩东是当今很受青年欢迎的作家。他的《扎根》,写一个叫老陶的干部全家五口下放到江苏省当年贫困地区淮阴“扎根”。他不愿意虚耗光阴,在农村造屋,学习栽培和饲养,搞好与当地群众关系、鼓励妻子做“赤脚医生”,但是命运最后还是把他连根拔起的故事。这部小说是以他的家,自然也包括方之的遭遇。作品获得了第二届世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另一个儿子李潮原来也是我们青春杂志的编辑。小说写得好。有一篇《奔向太阳岛》,写知识青年下乡以及回城,人的价值认识。其中有一段,写介绍对象时,主人公対女孩子的外貌不甚满意,准备在陪她参观动物园以后即分手。当别人津津有味地观看蛇吃小鸡的时候,女孩子不堪这种缺乏人性的场面而晕倒。反映了她的善良的人品。小说很有才气。方之如果健在,当十分慰藉。可惜,他又没有见到。
我真希望这个把生命献给文学事业的人能看到理想已经万紫千红。
《青春》,为无名者铺路,作家的摇篮
编辑部二十多双眼睛一起望着斯群主编。她拿起电话筒:“是邮局发行科吗?”。这个电话,是在讯问第一期杂志发行数字。可是,这个电话在青春的历史上是一个值得记载的重要事件。青春杂志正式向全国发行,数字是一个测试,测试“为无名者铺路”的方针是否迎合时代潮流,以及试刊以后杂志在青年中的关爱程度,是青春走向未来的一根标志线。大家的眼睛盯着她,她也很担心,试刊发行量大,那只是零售数字,毕竟是试刊,第一期是长期征订数,如果办得不好,读者是不认账的。当时,大家都像儿子即将诞生,候在产房外打听消息那种心情。
突然,主编提高了语调:“有那么多吗?”,得到对方又一次肯定以后,这位新四军时期的老干部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大半年下来,她一直带着大家焖头编稿,现在,取下眼镜来敞怀大笑。“第一期32万份”,她向大家转告这个都在期盼着的好消息。然后,把这个喜讯向南京市委分管文教的书记周伯蕃作了汇报。周书记,是一个满腹经纶,通晓马列理论的学者,他在各种场合纵谈解放思想,得到南京市文化界的敬重。青春创刊,他在各方面都给予热情的支持。
大批读者来信。那时候,没有青春偶像剧,没有当今荧屏上风流倜儅人物故事。有的只是人生追求。一位长白山深山里的青年说,文化大革命让我们荒废了青春,这是我一生中最不甘心的事。这么多年以来,他已经对于文学失望,读到青春以后,他仿佛找回了自己的青春。他是用卖鸡蛋的钱来订杂志的。有位读者反映,他们那儿在排队购买青春。更多的读者则表示,拿起笔来,写自己的生活,也来作一个文学摇篮里的梦。
邮政局的同志加大了工作量,每天要抗一大麻袋的稿件。
日本一位广告发行人闻讯来南京,愿意每期免费印制封面封底彩色画页,被我们婉言拒绝。
只要发现一篇好稿,一个新人,立刻溅出一片欢喜。我们尤其高兴的是,当代最优秀的文学青年都往这里投稿。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梁晓声在青春发表处女作《今夜有暴风雪》,以后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作家张平(现为山西省副省长)发表处女作《姐姐》获得全国文学奖。贾平凹发表了最初的小说《纺车声声》。姜天民《第九个售货亭》被拍成电视剧。本省本市不少文学青年从青春走向全国。著名作家王蒙为青春的读者长篇连载理论《当你拿起笔》,陆文夫、高晓声都为青年撰写辅导文章。编辑杨光中至今保存着上百篇著名作家的亲笔来信。由于大家的支持,青春最高发行量达到65万份。
《青春》甫一诞生便受到欢迎,有办刊宗旨切合时运,抓住机遇的因素,更需要扎扎实实的案头工作。
斯群长期担任宣传部门领导,以严格、严励、严密的作风办刊。青春在她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些好的作风。比如,每稿必复。其中,文笔尚欠火候,但已崭露苗头者,专门请上门,找一个招待所,通过办学习班的形式,面对面地改稿。每天有数百上千的来稿,做到件件有回音是不容易的。编辑复信,人手不够,专门聘请一些业余作者帮助回信。有些作者将这些信保留多年,上门来找编辑回忆初出茅庐时的情景。
编辑部严格规定,投稿者必须在35岁以下。当时文学刊物不多,年轻人与成熟的作家竞争,发表的机会自然受到影响。我们把35岁作为青年作者的保护线,这一方文学园地就成了萌芽之圃。周梅森《明天一定再来》、黄蓓佳《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王安忆《当长笛SOIO的时候》、梁左《中学时代的朋友》、董会平的《寻找》及其续篇发表以后,收到读者热烈欢迎。著名作家苏童的处女作《第八个铜像》乍一发表便显示了他出类拔萃的才华。
编辑部禁止编辑与其它刊物专业作家交换作品,互相发表。不允许编辑在上班时间搞创作,更不允许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作品。
参与思想解放,鼓励争鸣作品。发表《杜鹃啼归》男主人公的爱情选择,引出了社会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挑战》写男女主人公邂逅在寝舱时情欲与理智复杂的矛盾,在读者中有较大轰动。刊物连续发表五篇不同观点文章,展开更为开阔的思考。
为了奖掖作者,于创刊初创之时(80年)设立“青春文学奖”。光阴荏苒,当年的获奖者已经成了今天读者们都很熟悉的大名家。
青春杂志热情地对待初学写作的年轻人。北京市有一位女作者,叫赵泽华。她在文革中逃避坏人的追逐,被火车压断了一条腿。她很消沉,几乎想到了绝路。一天,她受到了一封很长的信,遒劲的毛笔笔迹,热情地为她的人生做着指点,她很感动。通过一段往来,他得悉这位编辑名叫邢煕坤。在邢老的带动下,青年女编辑梁晴也和赵泽华交上了朋友。并邀请她到南京来,陪着她游览中山陵、玄武湖。以后,邢老专程上北京了解她的工作情况。在整个社会的帮助下,她终于在北京的一家专门面向残疾人的文学刊物就职,以自己的经历出版了《生命坚持》一书。
青春杂志,除了正常编稿,经常搞大型活动。有一次,我们想到《世说新语》,那种超短型的纪实文章真实、短小,是大众化的好文体。便用这种形式表现新的内容举行全国范围的大赛。第一期,由我们编辑部人员化名写,让读者参考。然后正式征稿,发动全国文学青年写。每人限写三篇。结果,有两千五百人参赛,七千五百件,我们整整装订了一百本。评奖的时候,争论很激烈,因为篇篇来自于生活,从各个角度反映时代,可以说,都是好作品。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八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举行诗歌大赛,庆祝仪式在雨花台举行,电视台现场拍摄,还与江苏省文艺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本诗集。
诗歌是属于青年的。大量诗稿来自于学校、军营、企业,诗情澎湃,使杂志充满了青春朝气。我们编印了 “诗歌专号”还编印了“小说专号”“微型纪实文学专号”、《纪实文学专号》和《处女作专号》《大学生专号》等。随着青年作家的成长,他们需要较大容量的文学平台。于是,我们除了《青春月刊》以外,应时出版了以发表中长篇作品为主的大型刊物《青春丛刊》。南京市上上下下都夸赞说,在斯群主编的带领下,青春编辑部同志们共同写出了一篇好文章。
青春的副产品,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建了一座“青春楼”。地处闹中取静的兰园。建筑质量很好,整体浇注,二十多人,每人一套。建成的时候,自发登楼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以今日而论,单位自建住房不足为奇。但是,这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由我们自己出资建造,之前几乎没有听说过。为这件事,好几家报纸都做了宣传。对于知识分子说来,是一声新鲜的福音。“青春楼”的名声不胫而走。“青春楼”里住着梁晴、孙景生等好几位青年作家。在周梅森、韩东他们家里,每天深夜你都可以听到电脑键盘有节有奏的敲击声。那时候,电脑刚刚时兴,286型,他们就用这种简陋的电脑写出了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
青春杂志庐山笔会
难忘那一场雨,汩汩流淌的雨,像三叠泉的瀑布,没有个止境。这场雨温润地流在年轻作者的心头。
他们是幸福的。徐乃建、丁宏昌、李潮、沈泰来、吴倩等青年作者,刚刚发表作品,露出文学苗头,就邀请他们上庐山,举行笔会。编辑部特意邀请了前辈作家同行,从中山码头上船开始,艾煊、高晓声、陆文夫、顾尔谭这些文学大家就不时与青年作者切磋写作,春雨润物细无声地给予指导。我记得,艾老问我们喜欢读谁的著作。年轻人思想超前,说喜欢海明威的多一些,《老人与海》,确实是名篇。也有人喜欢萨特、喜欢……问到我,我喜欢萧洛霍夫。我觉得萧洛霍夫生活底子厚实,人物个性非常鲜明,故事也好看。我的观点可能落伍了,但艾老点点头。
雨,伴随着我们的旅途,一直把我们送上山,上山以后,天还是没完没了地落着。冷雨并没有浇灭我们的情绪。那时候的作者老实,笔会会风很正。除了写稿,就是听课。晚上跳跳舞,完毕。不像现在一些青年作家,出发之前就声明,笔会上只是吃吃玩玩,绝不动笔。有一个作家精通易经,他宣传一个理论,说走运走运,运气来自于“走”。哪儿发请柬去哪儿,别人开会他还未到,别人会未结束,他已拎着礼品打道回府。我们那一批作者,董会平的小说《寻找》发表以后,在年轻人中间反响很大,许多人来信希望他继续寻找,找出新的主题。丁宏昌整天皱着眉头,在改他的一篇反映知识青年进城以后境况的作品。写成的作品立时送到老作家的房间审阅。
庐山上的雨,随云而走。云来,雨来。云去便是晴天。我们游览了庐林湖、仙人洞等景点。美庐,是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别墅。艾老读得书多,说毛泽东来这里,一口就说这是大王八住的地方。毛主席把“美”这个字一笔一划地拆开,“美”,这个字果然是大王八三个字。进到院子里,园中种着各种花草,那真是奇花异草,我们都不认识。艾老一一道出花草的名字。我这才悟到,艾老的文笔细腻精致,知识宽泛,不能不让人佩服。联想到我们一些青年作家,写到田野的景色,总是以“田野上生长着不知名的小花”一笔带过。
在庐山上碰到一些名人。南大中文系教授程千帆和他的妻子沈祖棻。以程老的声望,完全可以以公费出差的名义,在山上小住。但程老用刚刚出版的一本书的稿费自付。
我们还碰到白桦、梁信。梁信是《红色娘子军》《怒海轻骑》等电影的作者。白桦在庐山大会堂作报告,很精彩。他那部《今夜星光灿烂》受到批评,说把伤员的腿用一个特写,血淋淋的有人性论的味道。他就反驳这位同志,说你也曾在部队待过,哪一场战争不流血?在一个大的战役之前,第一桩事便是挖坑,以便掩埋敌人的尸体,也要掩埋我们自己战士的遗体。他曾参加攻打襄阳城的战斗,桥被炸断,遗体堆积如山。战士们前赴后继,踏着遗体冲锋,最后的胜利总是用战士们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在《今夜星光灿烂》中,还有一个情节也受到批评。李秀明扮演的女主角作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婚礼上凤冠霞披,十分好看。批评者认为,贫农的女儿怎么能向往封建色彩的打扮。白桦又举了一位红军团长在延安的故事。这位团长三十多岁,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米脂县的姑娘。米脂是公认出美人的地方,这位团长总算完成了人生大事。可是,姑娘提出婚礼上坐轿,团长要骑大花马,身上披红挂彩。团长也答应了。结婚那一天,部队首长萧克前来制止。团长在马上恭恭手说:“司令员,人家姑娘家一辈子就这一点心愿,你就成全我们吧!”。萧克笑了笑,策马而去。不久,这位新婚不久的红军团长牺牲在战场上,浪漫色彩的婚礼故事伴随着他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庐山笔会上,白桦虽然讲电影创作,但对我们青春的小说作者很有启发。
披风戴雪为纸忙
杂志的发行量大固然是好事,发行量太大却变成了难事。
第一期便达到32万份,以后,月发行量不断攀升,每个月四五十万份,(最高一期达到65万),需要好几十吨纸,一节货车车皮,南京市所有文化用品商店库存加起来也不够。只得请市委出面向省报、市报借,借到了新华日报主编樊发源的头上。一期接一期,他们也喊吃不消。省报市报有国家批的计划用纸份额,我们是新情况,编外。好比计划生育意外生了个黑孩子,这个孩子又胖又壮,食量来得个大,奶妈都发慌。编辑部同志们都自觉地把纸张当成最重要的任务,一见面就问,你有没有纸头的路子?
事业是大家的,责任也由大家分担。
搞纸去!搞纸去!纸张是杂志的救命粮。
斯群主编于是向老朋友们诉苦,请他们给予支持。雨花主编顾尔谭很干脆:“你们大胆办,如果真要断顿,用我们的纸,我们共存亡!”。著名画家亚明和斯群是新四军的战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线索,他在轻工部有一位战友,也是新四军的,全国用纸单位都经他的手批。
我们就带着亚明的便条,还带着一幅亚明的画上北京。这位老处长叫王克勤,在战争中负过伤,走路一瘸一拐的。那时的干部都很廉洁,没有行贿受贿之说。几十吨、上百吨,批到哪个厂,我们就到那个厂去取货。福建南平纸厂、湖南岳阳纸厂、江西纸厂我们都是老客户。王克勤有一个藏画的喜好。我到他那儿去的时候,他递给我一个册页。亚明已经把扉页画好。王克勤熟悉我们江苏新金陵画派,除了傅抱石已去世,每一次见他的面,他就把册页递过来,向宋文治、钱松喦、魏紫煕等大师求画。当时,著名画家的作品还没有走向市场,这些令人尊敬的艺术家听说我们的困难,个个帮我们尽义务,一页一页画下去,绘的都是精品。
文化市场渐渐繁荣,到轻工部要纸的单位越来越多,有时候王处长批的条子也不管用了。我们只得再找途径。
这天副主编李锡焕问我,出一趟远差有没有困难?他告诉我,斯群在南化认识一个工人,家在东北,很能干,南化公司许多东北业务都找他办。李锡焕让我和他一道上东北去搞纸。我表示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说到困难,编辑部的困难自然是应当放在前面的,我二话没说就买了两张火车票。
春节刚过,许多人家还沉浸在节日的气氛里,我们冒雪出发。车窗外,沿途都是雪白的雾淞,到东北以后才知道什么叫冬天。岑参描写北方的雪,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名句。这是诗,夸张了的。长白山的雪,没有席子大,但大的是一朵朵白玉兰,小一些的是棉桃,有时,天上没有下,山洼里大风一刮,树林里呼哨声响成一片,碎琼乱玉满天飞,也是一场横飞的雪。我穿了两层大衣,冷风还是前胸后背乱鉆针。可敬那林区的老太太,七八十岁,依然在路边上笃缝纫机,为顾客做衣服。
这趟东北之行,市领导很重视,特地让我到轻工局内部购买了十只南京特产钟山牌手表,这种表,26元一只,又批了一车大桥牌自行车的计划。这两种东西都是南京特产,很受欢迎。
我和同伴到吉林以后,这个同志家里有急事,给了我几个东北造纸厂的关系人地址,让我放了单飞。
松花江畔,长白山下,在塞外度过了两个多月。我到过中朝边境的图门,时逢枯水季节,中朝之间被冰层联通,随时可以跨到边境线以外,没有一个人愿意过去。朝鲜的山上都用石块镶着巨大的朝鲜文口号,估计是金日成万岁之类。电视里只有一个女播音员读稿子,偶有文艺节目,还是血海、卖花姑娘老节目。我们延边朝鲜族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每天有歌舞节目表演。他们生活安适,衣食无忧。鲜族人喜欢吸烟,火车上男的女的,几乎人人卷烟叶。女乘务员用流畅的汉语,然后再用朝语介绍路程。招待所睡炕,十来米长的大炕,七八个人睡一起。我来到全国产量最大的石砚造纸厂,看到整棵树通过传送带去化纸浆,甚为可惜。回南京以后,只要见到空白纸片,一定节约使用。又到好几家县级的小造纸厂,但都没有批到计划用纸。
时间久了,纸张还没有下落,心里的压力很大。孤独的时候,马上就看见编辑部同志们皱着眉头问着我:纸头!纸头!纸头!我那位南化朋友帮我出主意:纸头搞不到,在东北搞木头,回到江苏再换纸也一样。打电话回编辑部请示,主编说那也好,我就再上吉林敦化林场。
小时候,听一个顺口溜:东北三大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其实,东北的森林是更值价的宝。可惜,从日本人占领时便开始滥砍滥伐,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火车、汽车视线之内,已看不到一棵一个人合抱的大树。二十多年前,在林区里找木头也不容易。(如今国家林业部采取禁止随意滥伐等保护措施,情况已大大改观。)那一次东北之行,我总算找到敦化林场,对方答应用南京的大桥牌自行车换他们一车原木。
两个多月以后回到南京,杜鹃花染红了玄武湖畔,春天的意思已经很浓了。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扩大,不再需要向有关部门批条子办纸张了。但东北之行在我的人生中是一段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