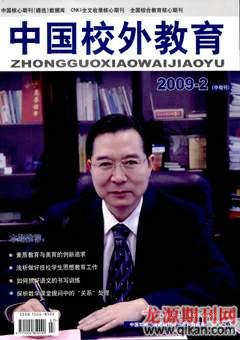季红真文学批评初探
封 燕
【摘 要】做为一名当代文学评论家,季红真的评论通常是与具体的作家作品紧密结合,发掘每一位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并从宏观的角度将作家及其创作纳入到整个当代文学思潮中,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身为一名女性批评家,女性作家和文本中的女性形象始终是她研究的切入点,而且与她开阔的批评视野一脉相承。
【关键词】季红真 文学批评 批评家
季红真从事文学批评的源头,是在大学时代。在她读大学二年级时,张洁的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季红真参与了这次论争,在《读书》杂志上署名禾子发表了《爱情、婚姻及其他》一文,从此走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此后,她文思泉涌,相继在《文艺报》、《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多家报刊发表论文多篇,其中十几篇被中国人民大学资料社复印。
与其他年轻的批评家一样,季红真初入批评界就表现出了充分的自信与坚定:一开始,她就致力于扬弃批评惰性,寻找批评自身的位置。这与当时批评界兴起的对审美批评复归的潮流是一致的。当时的中国文坛,文学批评不景气的局面已存在很长时期,这与批评家的不能独立思考和失去主体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进入新时期后,这一点引起更多批评家的注意,特别是一批年轻批评家的注意。季红真近年来的一系列文学批评的活动,就属于这一文学批评寻求的整体。
与一些批评家所擅长的,对于某一局部现象的条分缕析不同,季红真是以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把握开始其批评工作的,从而以对文学全貌的稳健描述创造了她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最能体现她这种批评风格的,当属《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一文。该文为季红真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其批评的切入点选择为新时期小说基本主题的转变。在浩瀚纷繁的材料中,通过对新时期全部文学现象进行扒梳筛选,运用她在理论方面的有效积累,从中总结出最能体现实质的规律:“社会生活中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开始的变化,推动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入,思想落点的转移,形成了小说主题的阶段性演变。两大主题阶段:社会政治的批判—民族文化的思考,主题的分化与艺术的自觉。”
本着这种文学批评的宏观整体感,在《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之后,季红真又相继推出了一些篇幅较长、视野开阔的论文。在《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文中,她将中国近年来的小说创作视为整体。通过对这一复杂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的整体把握,概括出富有规律性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将其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关系予以了详细的论述。在此后的两篇长文《文化“寻根”与当代文学》、《朦胧的古典精神—“寻根”后小说谈》中,季红真文学批评的宏观整体感再次得到了体现。她不仅认识到“寻根文学”是新时期文学中一个集大成的文学思潮,而且对其给予中国当代文学格局的深刻影响,进行了宏观的把握,认识到在其影响下,“中国当代文学格局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不仅在这个潮头中充任中坚的一披中青年作家,衔接起无四以来新文学的多个传统,顺应着20世纪世界文学的美学潮汛。而且,也带来了理论、批评格局的整体性变化”。
季红真的这种批评风格不仅体现在上述这些长篇宏论中,还表现在她的作家作品论里。她的作家作品论,也既是基于自己审美感觉的选择,又与对思潮宏观描述相适应。值得注意的是:她不仅将单个作家的创作视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且将当代作家的创作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把握,这样就有了建立在彼此参照、对比的整体高度。这种将批评对象放置于整个文学发展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对比的批评实践,能够鲜明地显示出批评对象的独特之处,从而迅速切入内核。这种比较的观念一直存在于季红真文学批评中。如论阿城时,就将他与同时代的作家汪曾祺、贾平凹进行了比较,认为他们虽然都坚持以中国古代哲学为基础的审美态度,且都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达到了“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境界。但是阿城与他们是不同的,除了载体选择的明显差异外,他更倾向于对现实的超越,达到对世界人生整体的哲学了悟。运用比较方法得出的这些结论无疑更具有说服力,而批评者的整体观念与历史文化意识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为使文学批评摆脱千篇一律的缺陷,季红真总是极力寻求每个作家的独特之处,努力完成批评的更新,而正是这种对于批评对象独特性的深刻挖掘,使她对作家艺术性的把握往往十分独到而精确。她这样评价莫言的作品:“如歌如画,如剪接奇妙的电影,如音响嘈杂的现代音乐—繁多的意象与痛苦纷扰的情绪,都以原子裂变般的冲击力,震荡得人们头晕目眩。”这是她眼中阿城的创作风格:“像一支支旋律平缓而沉积着世代平凡人生的内容的古老谣曲,平和中引发着普遍的审美共鸣。”她注意到汪曾祺的作品里隐匿着一种深厚的意蕴,它“并无实体却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贯注于人物性格、故事情节;挈领着整体的美学风格,形成其创作的基本格调”。她归纳张承志的创作风格为:“粗犷强悍的的气势,绚丽凝重的色彩,丰富沉实的底蕴,在壮美的风格中,悸动大生命的真欢乐与真痛苦。”
在季红真的批评观念中,始终掘弃作简单而抽象的结论,而是注重综合性的多方面的考察。她注意从各个侧面观察事物,因而其批评是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如她对汪曾祺笔下人物性格的复杂内涵就有独到而准确的把握,像写身为小知识分子的高鹏,“他饱读诗书,性情耿介方正,不苟合于世。”但由于环境的窘迫压抑,以致“性情孤僻急躁”,有着“近于偏狭的自尊”。“古典文化给予这个人物‘贫贱不移,清高耿介的品性,但生逢动荡的年代,他的性格只有变得越来越封闭。”正是对批评对象有了这样综合性的把握,她才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这些传统文化与生活铸就的性格,代表了汪曾祺小说现实主义的水平。”
回顾季红真的文学批评之路,可以看到:她从初入评论界就显示了清醒的超越意识,并以自身的努力,完成了从社会的批评到美学批评的过程。她已逐步找到了大文化的视角,注重整体的文化背景(从物质生存方式到精神生存方式)对文学整体发展的影响。这种由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识导致的对于历史的整体思考,正是季红真美学批评予人以深刻印象的重要原因。而文学批评的这种历史文化大背景,也正是季红真在其文学批评中所竭力追求的境界,她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表明:影响几代批评家进行创造性劳动的批评贯性开始减弱,基于文学自身特性的审美批评受到了重视,这对于改善文学批评自身处境是颇有益处的。虽然出于种种原因,近年来已无缘见到季红真的文学批评作品,但是她曾做出的这种可贵的探求与取得的成就,是不会消逝于人们脑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