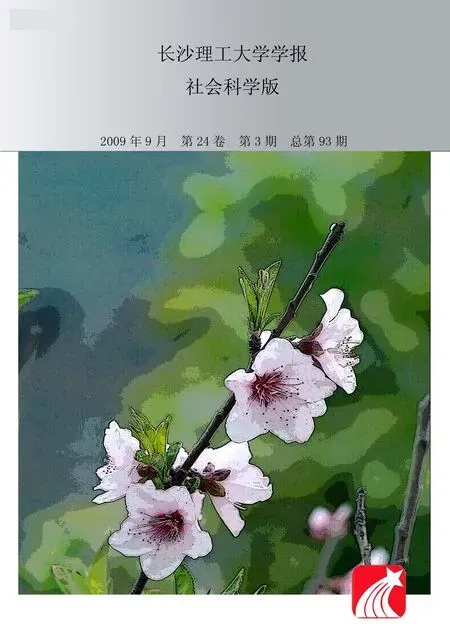千古沉冤须昭雪
——为温庭筠的人品翻案
万文武
(武汉市电影公司,湖北 武汉 430015)
温庭筠的人品,自从两《唐书》给他贴上“薄行无检幅”的标签后,千余年来,为世訾謷。“温氏似但为一潦倒失意、有才无行之文士”,温词“不过逐弦吹之音所制之侧辞艳曲”。①可见对温氏人品的认识,不仅影响到对温氏之人格,更影响到对其词的解读与评价。 温庭筠果真是无行的文人么? 在论及他人品之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温庭筠所生活的时代。
温庭筠约生于唐宪宗而殁于唐懿宗之世,中经穆、敬、文、武、宣五个皇帝,约半个多世纪。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指出:“唐之宦官,其势十倍于汉、宋。”②当年刘蕡就曾愤怒地给文宗上书指出:“忠贤无腹心之寄,阍寺持废立之权。”③此其一。其次是方镇的跋扈。“政刑不由乎天子,攻伐必自于诸侯。”④而最坏的是宦官与外藩的勾结,朝臣的鲜廉寡耻,以至“逆党私人奔走京国,贿赂行于朝廷,皆为张皇贼势以劝姑息,嚣张不辑,乱其成谋也。”⑤朝廷为这三股邪恶势力所把持,“此自取其灭亡也。”⑥所幸唐之当时“回纥、吐蕃唯以侵略为志,浸淫之而自敝,亦无刘渊、石勒之雄心,斯以幸存而已矣。使如宋也,三虏迭乗以压境,岂能待一迀再迀三迀而后亡哉!”⑦可见坚持统一还是割据分裂,坚持打击阴腐势力,制止内外勾结,还是与阴腐势力互为奥援,以助长凶熖?这就是整个晚唐政治斗争的焦点;也就是区分当时进步与反动的分水岭。裴度、李德裕因为坚持统一、打击宦官,无疑代表着进步势力;而“恃阴腐为奥援者”⑧的牛党则反之。看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进步与否,这样的大是大非是不能不问清楚的。温庭筠作为一个白丁,未能跻身于政治的上层,在当年牛李斗争当中,还不够入派的资格,但他的政治观点、思想感情,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李党”。其实李德裕无党,这从他重用牛党中的许多要员就可见。史书上所谓的“牛李之争”,只不过是牛党在尽力排除朝中的进步人士而已。不问大是大非同等地称之为“党”,这是糊涂观点!温庭筠早年从裴度游,中间曾一度为文宗的太子永的亲信。太子永被害后,温庭筠又倾向于李德裕。纵观他所亲近的,都是中国历史上已有了定评的先进人物。反之,他对于黑暗势力的几度拉拢决不听命。王夫之说,“故君子之观人于早也,持其所习者以为衡,视其师友,视其交游,视其习尚;未尝无失,而失者终鲜。”⑨从他一生的行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温庭筠在晚唐是进步的。我以为这一点,正是他的词中为什么总是极度相思而又甘守寂寞的基调。他之所以穷愁潦倒,终至“以窜死”,完全不是因为他“士行尘杂”,而恰恰是因为他坚持进步立场,为腐朽黑暗势力排斥的必然结果。
这里试举出几件直接关系温庭筠政治生命的重大事件,来看一看温庭筠的立场和政治表现。
一、第一次贬谪
大中十三年,即李德裕贬死在海南的第九个年头,温庭筠因与宰相令狐绹政见不合,也被贬随州。
最初,令狐绹和温庭筠都曾受知于李德裕;从令狐绹秘密授意温庭筠为他写《菩薩蛮》以密进宣宗的情况来分析,温庭筠可能因这层关系而住在令狐相府,并为令狐绹视为腹心。但温庭筠的政见倾向于李德裕,是以他 “身在曹营心在汉”,纵与之日事游宴,而思想感情却是非常孤独苦闷的。这点,对于理解温庭筠的词至为重要。由于温庭筠坚持进步立场而又锐意进取,丝毫不掩盖其鲠介之个性;而令狐绹此时,腐化堕落至极,所以他对于令狐绹常持批评态度并予以揭露之,这样,温庭筠之最后被令狐绹赶走。借用现代的话讲:这是路线斗争,时人不能抹煞其正义性,是以只能以“恃才傲物”毁之。但温庭筠之才华又已博得了皇帝宣宗的喜爱,而宣宗既为太监所立,自己又苦于拗不过阴腐势力,所以在听命贬谪温庭筠时,只好既称为贬谪,却又破天荒地给一个落第的白衣秀才“释褐”,安排官职,还特地为之下了一道充满着爱怜的贬谪诏书。这确实如张采田说的:“实为创例”!诏书肯定了他有千里马那样的不可羁勒的才能。并且承认:这次把温庭筠贬下去,等于是把屈原贬到了湘江;把贾谊放到了长沙。我们的学者称飞卿词之所以没有寄托,就是因为他没有屈原那样的人品,而身当其时的宣宗,却偏偏要在诏书中将飞卿比之为屈原,这真是极大的幽默!诏书最后语重心长地叮嘱他:只要他肯放弃进步立场,回到他们这边来,他们是一定会像汉文帝之看重贾谊那样,委以重任的。这样的诏书,应该说“皇恩浩荡”,富有诱人的感召力量!如果温庭筠没有坚强的政治信念,没有忠贞操守的政治品德,真的是一个“无特操”的堕落文人,他早就拜倒在他们的脚下,感激涕零了。然而,他却公然抗旨,不到指定的贬所随州,而偏偏要跑到襄阳去投令狐绹的政敌、属于“李党”的徐商,政治立场又是何等的鲜明,其行动又是何等的果敢!令狐绹和宣宗对于异己的政策是:“但有罪莫舍,有阙莫填,自无遗类矣!”他岂有不知?所以他清醒地表示:“苟无直道,将委穷途”,“敢叹朝饥,诚甘夕死”!⑩对如此皇恩而弃之不頋,只因为不是“直道”,这难道不能算是“富贵不能淫”吗?比起李宗闵、元稹、牛僧孺、令狐绹、白敏中等当朝之衮衮诸公,无此条件而卑躬屈膝地以阴腐为奥援而取高位的,温庭筠真个是人间之矫矫者了。
温庭筠不仅在权贵的取舍上如此,在经济上他也是耿介不拔的。他的宗亲温造、温璋父子“积聚财货”,非常富有。我们在温庭筠的诗文中,未见他有一句阿谀之辞,反倒有明确地表白:“浪言辉棣蕚,无所托葭莩。乔木能求友,危巢莫嚇雏。”他不以这样的兄弟为光荣,鄙视他们是守着腐鼠的猫头鹰,而他则是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練实不食”,立场界线是多么清楚!
二、第二次贬谪
咸通三年,温庭筠因徐商他调,失去了依托,遂由江陵东归,路过当时身为淮南节度使令狐绹的驻地扬州。这时温庭筠已穷到“处默无衾,徒然夜叹;修龄绝米,安事晨炊”的地步。他明知令狐绹在这里为藩镇大吏,以他们过去的私交,去“打打秋风”以救燃眉之急,似无不可。然而他却根本不去理他。令狐绹为此如雷暴跳,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这才发生了史书上说的“丐钱扬子院,夜醉,为逻卒击折其齿”,迄今犹为人所乐于称道的“风流罪案”。一个小小的逻卒而已,在封建社会,怎敢当街辱殴朝廷九品命官,以至有意破相!这分明是令狐绹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搞的一次阴谋。此人极善于运用奸计。例如当他的赃行被舍人刘紫微揭发后,他略施小计,反倒把刘紫微搞得身败名裂。他此时身为藩镇大帅,对付一个来到了他手掌心里的穷途末吏,无须大的动作,只一个小小卒子也足以对付的了;尔又其奈我何?
有的教授说:“丐钱扬子院”是因为温庭筠穷极无聊,只好写些曲子到妓院去卖几个小钱。是他的行为不检,所以才弄得身败名裂!这是书生论政。 殊不知“扬子院”不是行院,而是盐铁院。有史乘可证。
《太平广记·胡媚儿》载:“唐贞元中……有度支两税纲,自扬子院,部轻货数十车至。”“部”,押运也。“两支”即盐与铁也。可见扬子院中所储者并非妓女而是当时朝廷专利的盐与铁。当然,这是“小说”。再看《资治通鉴》卷237第1632页:“吏部尚书盐铁转运使李巽,奏郴州司马程异,吏才明辨,请以扬子留后,上许之。” 文下特地注明:“扬州扬子县,自大历以来,盐铁转运使置巡院于此,故置留后。”再如《旧唐书·懿宗纪》载:“咸通三年五月,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天子召见。……以磻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院专督海运。”至于《新唐书·列传》第74页“班宏传”:“扬子院,盐铁转运之委戴也。”则说得更直截了当。再如李廷先所著之《唐代扬州史考》第159页:“扬州为东南地区盐的集散地,设置巡院,专督办盐事。”不仅扬州巡院称“院”。如《旧唐书·柳仲郢传》:“尝感李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无禄仕者。仲郢领盐铁时,取德裕兄子从质为推官,知苏州院事,令以禄利赡南宅。”可见各地盐铁皆称“院”。那么温庭筠为什么要大闹扬子院,而令孤绹又这么恨他呢?据李廷光《唐代扬州史考》载:“安史之乱爆发后,扬州设立淮南节度使,盐铁转运使亦常驻扬州,或径由淮南节度使兼任,总掌东南八道财富,为国家赋税主要来源。”可见令孤绹此时,是淮南节度使兼任盐铁转运使。盐铁专卖是个肥缺。宋洪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载:“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州为一而蜀次之也。”以在京为宰相时尚且“货贿盈门”之令狐绹而当此“尽斡利权”之肥缺,那真是得其所哉,能不大贪而特贪吗?《资治通鉴》对他之政绩如何没有记载,却记下了令狐绹前任的王播:“盐铁使王播,自淮南入朝,力图大用,所献银器以千计,绫绢以十万计。”这些是他作为“羡余”献出的,那么他自己所得呢?自然远不止此“余”数!在唐史中,王播尚不以贪名,令狐绹在淮南是如何的贪墨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以温庭筠之个性,当他路经扬州,如果知道了令狐绹有什么劣迹,未有不“闹”的。《旧唐书·本传》称他“乞索于扬子院”。“乞索”是讨要。讨什么?要什么?其真实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不会是讨钱。因为要讨钱直接去谒见令狐绹,既不失礼,又得实惠,岂不是两全其美吗?如《唐摭言》中说的诗人张祜:“赵公令狐绹镇淮扬,祜尝予狎宴。”温庭筠与令狐绹的关系,过于张祜,而他却“久不刺谒”,这四个字就已写出了令狐绹的恼火!更何况他又从而大闹之,这“闹”可谓大有文章!因为小民的“讲理”,在政府就往往是“闹事”。是不是温庭筠知道了令狐绹的一些赃证,而被其殴打夺毁之呢?惜乎史书不载,但温庭筠之与这位“尽斡利权”的大人物之泾渭不合的强硬态度,则是显而易见的。如此矛盾,这才有本传中说的:“醉而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之事。新旧《唐书》,一说“逻卒”,一说“虞候”,莫衷一是。但无论怎样,温庭筠这时朝廷也委任以县尉之职,同属司法部们,纵触宵禁,何致非要“败面折齿”,予此奇耻大辱?在晚唐,虞候是军中执法的长官。一个“犯宵禁”的人,自有地方治安管理,而温庭筠又不是军人,何致要劳动军事执法长官?这分明是身为边镇大帅的令狐绹以私人的军事力量挟嫌折辱以泄私愤之故。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温庭筠这才告到了京师的执政者们那里,如他在《上裴相公启》中所说的:“岂期杜挚相倾,臧仓见嫉。守土者(令狐绹)以忘情积恶,当权者(杨收)以承意中伤。直视孤危,横相陵阻(以“败面折齿”之陵而阻之,“阻”的到底是什么?)。绝飞驰(上诉)之路,塞饮啄之途。射血有冤,叫天无路。此乃通人见悯,多士具闻(当时是很多人知道真相的)。徒共兴嗟,靡能昭雪”。杜挚是三国时魏人,曾求过丘俭,这是指令狐绹曾求过温庭筠的,不记恩还反过来陷害他,是为“忘情”,而臧仓则是战国鲁平公的嬖人,这也就是指令狐绹不过是宣宗的嬖人,他这里就把这个事件的主谋令狐绹与其门徒杨收勾结为奸,指得非常的明白了。由于牛党势太大,公卿无人敢管。时正为宰相的杨收,又是令狐绹的得意门生,同时在中央主持盐铁事务,两个贪墨之徒,在经济上自有勾结,处于同一利益集团,是以这才科了温庭筠一个“薄行无检幅”的罪名,把他贬为方城尉。温庭筠的好友纪唐夫在《送温庭筠尉方城》一诗中就说:“凤凰诏下虽承命,鹦鹉才高却累身”,用的是曹操假手黄祖谋杀弥衡的故事,隐射了温庭筠这次被贬的关键之所在。
三、为何“屡试不中”?
开成三年,宫廷内发生了一次残酷的抢夺储位的斗争。当时的太子是文宗的长子永,而且品德优良,据兵部尚书王起撰的册谥太子为“庄恪”的哀册文看,这位太子永的人格和品行是:“蕴才游艺,玉裕金相。……尊师重傅,养德含聪。畏驰道而不绝,问寝门而益恭。招贤警戒,齿胄谦冲,冀日跻于三善,奉天慈于九重。汉庄好学,既显于外;魏丕能文,方循于内。美不二于颜过,嘉得三于鲤退。”
这些话因为是给死人做文章,自然有溢美的成分。但王起是太子侍读,当深知太子的为人;而他本人,又是众人眼里的“当代仲尼”。《北梦琐言》载:“王文懿公起,三任镇节,敡历省寺,赠太尉。文宗颇重之,……画仪形于便殿。师友目之曰:‘当代仲尼’。”那么出自于他笔下的这些话,其可信程度应当很高。也许正是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储君,才为把持朝政的宦官所不允许,故与杨妃勾而谋害致死了!温庭筠与太子永是好朋友,他在《太子西池二首》中就曾标榜过:“莫信张公子,窗间断暗期。”《汉书》记载:“富平侯张放始爱幸,成帝出为微行,与同辇执辔入内禁中,设饮燕之会,引满举白,谈笑大噱。”显然,温庭筠在这里是把自己比作张放,以隐喻自己和皇太子之亲密关系的。对于皇太子永的屈死,温庭筠不仅不顾生命的危险,当时就写下了许多深情而悲愤的诗,如《庄恪太子挽歌词二首》、《洞户二十二韵》、《雍台歌》、《生禖屏风歌》、《题望苑驿》、《太子西池二首》,还写了《四皓》,明确地说:“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真有紫芝翁”。在《庄恪太挽歌词》中又说“商公下汉庭”,都是用的汉高祖听信戚姬的谗言,欲换太子的典故,以说明太子永的死,正是杨妃的陷害。而且他还深情地写了《舞衣曲》,把自己比作陪同太子游宴的富平侯,而把太子永则尊之为秦王李世民,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圣主唐太宗。这就足见他对于太子永的评价与期许。在南衙北司对于太子永的废黜与否斗争得正激烈、也就是文宗动摇的时候,他作为太子永的亲信,也一定承受着重大的压力。因为只要他站出来指诬罔为“确证”,从而假手文宗以除掉太子永,这对于北司自是最为有利的了。作为交易,他此时要中试甚至做官又有何难?然而温庭筠顶住了种种的威胁和利诱,并勇于直面血淋淋的事实而写出了像上面举出的那些诗,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后来他向朋友袁郊、苗绅、李逸和淮南李仆射表达心态时说:“赋分知前定,寒心畏厚诬。”“积毁方销骨,微瑕惧掩瑜。”“欲就欺人事,何能逭鬼诛!”从此处就知道他顶住了多大的压力。他表达出的是对于太子永无限低迴掩抑的爱护心情。“定非笼外鸟,真是殼中蝉”,他是明知自己这样做的命运,并且清醒地等待着他们随时来捉拿他归案。他以这种必死的决心,表示了对太子永的忠诚与坚持正义的大无畏的气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虽荐名居第二,终被黜落罢举,就很好理解了。他之所以没有惨死,这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因为杨妃在谋害了太子永后,还未站住脚,她自己也就跟着被另一拨太监们搞下了台,而新上任的宰相恰好又是温庭筠的父执李德裕。而李德裕又是最讨厌宦官的。只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温庭筠才免除了一场杀身之祸,遑问考试!第二年,他之所以托疾不试,也是还处在这一阴影之下。
可惜武宗谢世,宣宗上台,李德裕被贬,令狐绹、白敏中等这些曾为李德裕所提拔的大人物,马上反戈一击,以更左的手段,作为向牛党和阴腐势力投靠的代价,先后皆取得了相位。温庭筠在此时却偏偏要顶着这几股黑暗势力汇合成的巨大逆流,站出来为处在下流的李德裕大唱赞歌。他在《题李相公敕赐屏风》中吟道:“丰沛曾为社稷臣,赐书名画墨犹新;几人同保山河誓,独自栖栖九陌尘。”这与他在《中书令裴公挽歌词》中颂裴度“萧何社稷臣”是一样的。他不仅歌颂他是“社稷臣”,而且笔锋所向,直指朝廷。他敢于“愤容凌鼎镬,公议动朝廷”,不怕“干时”而道“自孤”。这又是何等的才识与胆略!别说“薄行无检幅”的文人办不到,就是当时多少名流,甚至还有为历史歌颂至今的人物,不也多投靠阴腐势力以取将相去了吗?有比较才有鉴别,当此之时,“先君之骨未寒,太尉之逐已亟,环唐之廷,无有一人焉昌言以伸其忠勋者,岂徒无为之援哉?白敏中之徒且攘臂而夺相位,崔(潭峻)杨(嗣复)牛(僧孺)李(宗闵)抑引领以望内迁”,大家都忙着投靠竖宦以求进身之时,唯独温庭筠这一个不屈服于邪恶的硬汉,却冷冷地表示:“胁肩难黾俛”,对这些丑类装不出笑脸,也弯不下腰来。为此他明知下场不好,但他作好了准备:“宁甘半菽”,“不薄生刍”,不是龙门不跳,无妨“鱼服自囚拘”。他的“名宦不进,坎壈终身”,充满了堂堂正气,傲骨凛然!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政治品质。当年进士及第,是要由宰相批准的,而此时正是白敏中、令狐绹为相,在牛党主持的考试中,他还想能及第吗?唯有大闹之以泄愤而已。“耿介非持禄,优游是奍贤”,正是他冰清玉洁的精神境界。这样的人,是很难想象他会是一个“薄行无检幅”的小人的!在晚唐那样个黑暗的政治压力下,不论等待他的是如太子永的绞索还是如李德裕的长枷,他都表现得镇定自若,畅言无忌。试问:没有对于自己政治信仰无比坚定的人,能办得到吗?正因为令狐绹、白敏中这些小人当政,所以他才“为当塗者所薄”。冰炭之不同器,这不足为他羞,反而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四、怎样的“无行”?
温庭筠潦倒一生,好不容易在约五十五岁的时候,牛党下台,徐商为相,他这才当上了一名小小的从六品上的国子助教。职务虽清闲,但在晚唐“贿赂充塞于天下”之际,而又重进士出身之时,这却也是一个肥缺。据《北梦琐言》记载,当时卖一个经业举人是十万贯。《旧唐书·令狐滈传》说令狐父子“每当贡闱登第”,“货贿盈门”,“喧然如市” ,“白日之下,见金而不见人”!而且当时的社会普遍皆黑,“虽贤者固不能保其清洁,特以未败露而不章,实不可问也!”然而奇怪的是,历史上却未见多少评论家敢说令狐父子及这些“贤者”们无行!
到了温庭筠“主秋试”了,如果根据某些史籍记载的,说温庭筠在考试时 “以文为货”,那么当他一旦得到了这样个主秋试可以“货文”而大捞特捞的机会,岂不是要比那些为史书称赞的相爷、御史、贤者们更滥污吗?但奇怪的是,像他这样一个“薄于行,无检幅”的堕落文人,对于前人和社会上的这一套“濳规则”却大大的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他不仅锐意改革,尽蠲积弊,真正做到了为国家民族选拔那些“识略精微,堪裨教化”的人才,而且还敢于把他选中的人的文章张榜公布于众,以昭告于天下!其透明度之高,迄今也难能!甚至不妨这样说,自开科取士以来,没有像他这样做的《唐才子传》八记载:“(邵)谒,咸通七年抵京师,隶国子。时温庭筠主试,悯擢寒苦,乃榜揭诗三十余篇,以振公道。”《全唐诗话》也说:“温飞卿任太常博士,主秋试,涛与卫丹张却等诗赋皆榜于都堂。”值得注意的,这里明确说他“悯擢寒苦”。他敢于得罪高门显阀的权贵和大商富贾的豪门,硬是要将那些真正有才而无权无势的人选拔出来。为了“以振公道”,抵抗这些压力,所以他这才把选拔出来的人之文才公之于众,让天下的人都来监督鉴定,“以明无私”!无怪他敢于放言:“韶光如见借,寒谷变风烟!”这样看来,他岂止是大诗人、大词人,更难得的他还是一位大政治家!像他这样英明出色的政治措施,改革了积年弊习,改变了组织成分,使能者居官,贤者当道,消除了像刘蕡说的“灭亡之道”,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可惜他毕竟只是一个微末的学官,这样敢于逆潮流而作的结果,只能是连他自己的从六品的前程也断送了。但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他的这一篇闪耀着圣洁之光芒的至文:
“榜国子监
右前进士所纳诗篇等,识略精微,堪裨教化;声词激切,曲备风谣。标题命篇,时所难著。灯烛之下,雄词卓然。诚宜牓示众人,不敢独专华藻。并仰牓出,以明无私。仍请申堂,并牓礼部。咸通七年十月六日,试官温庭筠牓。”
孔子说:“君子坦荡荡”,温庭筠将当之而无愧。他的这一举动,在贿赂公行的晚唐,诚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壮举。他使一切的丑类自惭形秽!可想而知,他的这种越格的行为,事前事后会遭到来自上层社会各方面多大的压力,他之终于放榜了,要作出多么艰巨的斗争!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轻薄荡子能有这样雄伟的胆识与魄力?更不能相信一个专事狭邪之行的堕落文人会有这样冰清玉洁的情操?所以鲁迅先生说:“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事实是只有以振兴国家民族为己任的人,他在选人和用人时,才会“不敢独专华藻”(而我们至今还有评论家说温庭筠的诗词是梁陈宫体,似乎是专于华藻而没有思想寄托的),而去公布这些“堪裨教化”的精微卓识;才能于激切的声词之中发现“时所难著”的忧国忧民之士;只有唯贤是选,他才能赏识“雄词卓然”而不是“见金不见人”;也只有大公无私的人,他才敢于“并仰榜出”向黑暗势力挑战“以振公道”。王夫之说过:“唐之乱,贿赂充塞于天下为之耳。凡三百余年,自卢怀慎、张九龄、裴休而外,唐之能饰簠簋以自立于金帛之外者无有。”然而,温庭筠却办到了!这就是温庭筠人格的光辉最伟大之处。可惜的是,晚唐之世,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更不允许他的存在,是以“会商罢,杨收疾之,遂废卒!”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温庭筠使杨收辈“疾之”而“遂废”以“卒”,这是必然的。这不是温庭筠个人的命运,而是时代的命运。那些以为温庭筠只不过是一潦倒无行的文人,他的诗词里绝对没有忠爱之思、家国之戚的论调近于诬罔!吴小如先生说:“一向被称为‘艳科’之祖的温庭筠竟连一句露骨的色情描写也没有,”有的只是对他描写的对象的“尊重和同情”。以此律唐宋之词,试问有几人当得!
五、群魔乱舞 丑者钟馗
温庭筠除了有一个爱狭邪之行的风流罪名之外,据说他长得丑,因而还有一个“温钟馗”的恶谥。
温庭筠丑不丑,不得而知。按说辩论一个人的相貌是没有意义的。然而正如《水浒》一百另八个的混名都标志着各自的个性和特征一样,研究“温钟馗”这个混名,当也有助于我们对于温庭筠人格的了解。
钟馗的故事始于唐玄宗,距温庭筠不到一百年,所以这是唐本朝的一个新典,相信唐人是不会用错的。宋沈括《梦溪笔谈》载有钟馗的服饰,并没有说他的相貌。玄宗的《批》所谓“因图异状”,也只是说画下捉鬼的这一奇异的状况,何况“异”亦与丑无涉。而主旨在“烈士除妖,实须称奖”,为的是“岁暮驱除,可宜遍识,以祛邪魅,益静妖氛。”以此衡之,那么“温钟馗”出现在这时,其意义就只能是 “以祛邪魅,益静妖氛。”唐玄宗在感激之余,不可能丑化钟馗是显然易见的了。
再从“温钟馗”这一称号来看,它最初见于《北梦琐言》。《北梦琐言》的作者孙光宪生于公元896年,卒于公元968,晚于飞卿不过26年,他说:“薛侍郎昭纬气貎昏浊,杜紫微唇厚,温庭筠号‘温钟馗’,不称才也。”这里除了杜指的是形之姸丑外,薛指的是神,温指的是才,语意非常清楚,并非皆言其丑。若飞卿很丑,他为什么不说“其貎寢也”,而要说“不称才也”呢?查温庭筠之为人,史书所记一为“凭才傲物,多犯忌讳”,又说他“文多刺时,复傲毁朝士”,说他“恃才诡激,为当塗者所薄”,从未及其姸丑。对于晚唐那样一个黑暗社会,他凭着一身傲骨,八叉之才,敢于把“万岁”当成“簿尉之流”,敢于耻笑当朝一品的“相国无学”,甚至为了捣乱等同金融交易市场的考场,居然敢在试官置于“簾前”独照的情况下,居然仍给八人作了枪手,还最先交卷退出考场。他敢于恃才诡激,凭才傲物,敢于文多刺时,屡犯忌讳,敢于傲毁朝士,无所畏惧,在这样一群鬼物中,他真个是像钟馗那样,将这些鬼物戏弄于手掌口吻之间,这是多么高大的形象!当塗者,也就是把社会搞得如此黑暗,以至有那样多的“忌讳”怕刺,怕揭露,为他们所薄,那不正是很了不起的吗?他们“薄”的愈狠,说明温庭筠刺的也就愈深、愈中要害,因而说明他的思想愈敏锐,形象愈益高大。温庭筠最后“以窜终”,并且祸及子孙,就足见他对于晚唐统治阶级的攻击是多么的深刻尖锐,所以“当塗者”们才恨得这么狠!可惜历史上只留下了他“文多刺时”的罪状,却不见“刺时”之罪证,大约也是不敢让它见阳光,遂付之一炬了。给他取一个“温钟馗”之名,若以唐玄宗的立场论,显然是“爱称”,而不是丑化;即令是后来出于主流社会对他的丑化,也正好是暴露了鬼物们对于他的恐惧心理,暴露出了两者鲜明对立的立场。从这“钟馗”的名字里,为我们形象地塑造了一位愤世忧民而敢于抨击鬼蜮世界的真正战士。
其实,新旧《唐书》以及其它著作把温庭筠丑化为“士行尘杂,不修边幅”、“薄于行,无检幅”,不外乎说他与贵胄们“酣醉终日”,“蒲饮狎眤”。那么试看史籍说的与他交游的那些贵胄,最坏的莫过于令狐滈了,其劣迹连偏袒牛党的司马光也无法掩饰,据《资治通鉴》说:“左拾遗刘蜕上言:‘滈专家无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权。’起居郎张云言:‘滈,父绹……由滈纳贿,陷父于恶。……人号“白衣宰相”’。”他岂止是衙内,直接就是相公!然而他不仅没有温庭筠这些罪名,反而做了大官!再说“饮宴”,在唐朝的上层社会,那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被认为高雅的行为。是以有唐一代,以诗词咏酒宴歌舞的篇什,真个是汗牛充楝。《资治通鉴》卷250载:唐懿宗李漼“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馀,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曲江,昆明、灞浐、南宫、北苑、昭应、咸阳,所欲游幸即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乐、饮食、幄帟,诸王立马以备陪从。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十馀万人,所费不可胜纪。”请看看,温庭筠之于李漼,那简直判若云泥!可怜温庭筠连他们这些基本的条件都没有,却反而因此“累年不第”,这说得通吗?
以上仅举此几点,即可见加在温庭筠头上的罪名,而且一直沿袭至今,是多么的可笑亦复可悲!对于这样一粒久为封建尘埃所掩没的璀璨明珠,我们今日之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当然都有责任拭而出之,使之成为我们民族一份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注释]
①叶嘉莹:《迦陵论词丛稿》第1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②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6第929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③④⑥《旧唐书》《刘蕡传》卷190下第5064页。中华书局1986年5月湖北第二次印刷版。
⑤《读通鉴论》卷26第931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⑦《读通鉴论》卷26第934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⑧《读通鉴论》卷26第918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⑨《读通鉴论·宣宗三》卷26第943页)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
⑩温庭筠《上宰相启二首》《温飞卿诗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一版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