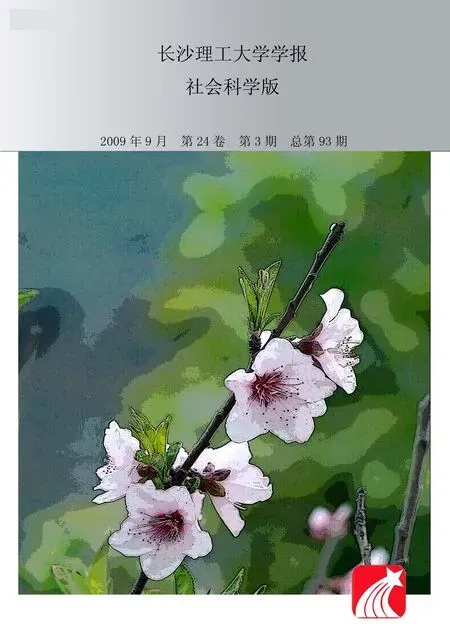知识溢出、风险分担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基于农民工“群团流动”的经济解释
刘祚祥, 胡跃红
(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4)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在此期间,约有2亿农民成功地转换成为其他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仍在转换着的农民约1亿左右,他们的职业、身份以及生活方式尚在改变之中。那么,导致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农民职业转换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流动为什么采取了“群团”的形式?农民工群团流动的组织形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何实质性的影响?本文以改革过程中的真实事件为基础,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原理,对此作出经济解释。
一、农民工“群团流动”案例:桂林酸菜与惠州制鞋厂商
桂林人喜欢吃酸菜,特别是酸笋子、酸豆角、酸辣椒、酸芥菜、酸榨菜等。在前桂林陆军学院的斜对面,有一个不起眼的住宅小区,名叫“同心园”,自从1993年,湖南武冈市的第一批做酸菜的农民开始租赁这里的住房后,这个小区就成为桂林酸菜的主要加工基地。这里聚集了30多家酸菜制作加工销售商,这些人全部来自湖南武冈市的头堂乡,而且还沾亲带故。到2007年的时候,他们占有了桂林酸菜市场中40%的份额。2007年3月,当地街道借口酸菜制作污染环境,将他们遣散到桂林的北村与红太阳小区等地,这个酸菜加工基地才不再存在。这个案例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农民流动及其非农转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结构的演变机理以及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这个酸菜加工销售团体的开拓者是武冈头堂乡农民毛政立。因为其老兄在原来的桂林陆军学院任职,凭借着这种关系,1989年毛政立从武冈来到桂林,辗转再三。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桂林的农产品市场中有人在卖酸菜,决定试一试。武冈农村泡酸菜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技术比较成熟。他首先泡酸豆角,因为这种酸菜加工的时间比较短,而且对于技术的要求不高。在第一批酸菜上市的时候,他发现卖酸菜的利润非常可观,一年下来,赚了差不多2万元, 是当时在武冈务农收入的4~6倍。1990年他的大妹夫、表姐夫、还有一位堂弟随他一起到桂林卖酸菜,这几个人在桂林很自然地与毛政立住在一块,交流泡酸菜的技术、分析酸菜市场的行情。就这样他们在桂林的酸菜市场站住了脚。曾祥光与徐桂云夫妇是另一案例。他们在桂林酸菜市场有点名气,2007年他们加工并卖出5万斤酸笋子、3万斤酸辣椒、4万斤酸豆角、4000斤酸姜、4万斤酸芥菜,同时还倒卖了4万斤酸榨菜。这对夫妻是1991年到桂林的,当时曾祥光23岁,初中毕业;徐桂云20岁,小学毕业文化。因为曾祥光是毛政立的妹夫,在曾祥光的母亲即毛政立岳母的干预下,1991年春节刚过,这对在武冈穷得实在没有办法的新婚夫妇随着姐夫来到了这个以前都没听说过的城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由此可见,农民在选择到城市中打工的时候,与他们所能够获取的信息紧密相关,农民的非农转移是农民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的选择。
那么,他们对于生产技术、销售、市场的相关知识是如何获得的呢?以曾祥光夫妇为例。以家庭为单位的泡酸、卖酸在家庭内部是有分工的:白天,丈夫去原料供应市场买原材料,妻子则在市场设点、卖酸菜;晚上,回家后一起加工。原材料的选择、酸菜的制作以及客户的管理等知识,他们是在实践中一步步积累起来的。例如,在水的选择上,刚到桂林时,泡酸用的是来自漓江的自来水,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地下水泡的酸菜质量要好很多,而市场份额与质量有很大的关系,于是,边实践边改进,他们的技术基本上能满足桂林人的口感与喜好。所以,“干中学”是这些农民进入城市获取知识的主要手段,而且这些技术在这个圈子中是公开的,从而降低了信息的传递成本,提高了知识的溢出效应。
广东惠州吉隆制鞋厂商的演变则是农民非农转移中群团现象的另一个典型案例。上个世纪80年代中晚期,受沿海开放的影响,湖南省武冈市石羊乡200余受过初中级教育的青年人,聚集到了惠州吉隆等地的制鞋厂。在生产过程中,他们通过“干中学”的方式,逐步掌握了鞋子生产流程中的各道工艺。陈立煌、曾和平是其中的佼佼者。陈立煌是曾和平的妹夫,也是武冈第一职业中专87届兽医班的同学。1989年在家乡做兽医没有门道的他们迫于生计的压力,便结伴而行,随着风起云涌的“民工潮”来到了惠州制鞋厂。他们受过高中教育并掌握了一些美术基础,通过工作中的知识积累,掌握了从“打模”到“模具设计”等主要技术,成为了制鞋厂的技术骨干。1997年陈立煌便与曾和平联合办厂,生产凉鞋。
10年过去了,陈立煌与曾和平都已独立门户,事业兴旺。到2007年陈立煌的年纯收入已达500多万元,曾和平也获得了100万左右的收入。现在聚集在惠州吉隆的武冈制鞋厂商约有20多家,武冈从业人员约有5 000多人,由于老乡之间在技术、信息、资金之间的合作成本较低,武冈人开设的制鞋厂的竞争力提高,逐步在当地占据主导地位。
二、农民工“群团流动”的制度基础及其经济效应
农民非农转移过程中所形成的“民工潮”是我国农民在城乡二元化背景下自发形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是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制度创新。在30年来的改革历程中,对中国农村影响深远的主要有家庭承包制、“民工潮”以及免征农业税。家庭承包制与免征农业税的实质是修改与重构农民、农村集体与国家的农地产权合约。农村家庭承包制,“以它最简单而又最完善的形式来说,是等于用租地的办法将土地界定为私产”[1],这项制度安排使农民获得了支配自身的劳动力和支配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权力,界定了农户的私有财产权与农民自身的人力资本产权边界,从而为民营企业的产生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合约安排,只规定了农民对国家与集体的义务,而没有表达出国家与集体对农户的责任,农户从政府手中获得土地耕种权是以不损害政府和集体的既有利益为前提的,政府当时与农户缔结合约时,除了将农地的耕种权赋予农户以外,其他权利基本上保留了下来,从而使国家、集体与农户三者之间的权、责、利很不对称。这种权、责、利不对称的结果就是农民负担加重、乡村负债高筑、农村公共产品严重短缺,在加上农业的小农户经营规模、兼业化生产方式以及传统的农产品定价方式,使农业成为中国产业中最无利可图的一种产业。
另一方面,家庭承包制界定了农民的人力资本产权,使农民可以在既有的约束条件下进行理性选择,因此,农村劳动力的配置就成为农民基于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过程。在现代社会,不同产业因为其分工程度与生产规模不同,导致不同产业中相同要素的边际生产能力不同,从而决定了相同生产要素的价格偏离,在套利机制的作用下,要素从低价位的产业向较高产业流动,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市场价格,这是一价定律。由于现代生产与服务业是建立在高度分工与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因此,生产要素在市场的作用下,将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现代生产与服务部门流动。在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在分工程度高的现代生产与服务部门的边际生产效率要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因此,传统农业中的劳动力有向现代产业转移的趋势,在劳动力所有者可以自由支配其劳动力的前提下,只要农民的非农活动所带来的收益高于农业生产的收益与流动成本,农业劳动力的非农转移就可能变为现实。随着农民搜寻工作的成本下降,从事非农生产的比较利益将进一步突出,于是劳动力转移将变得更加频繁。
改革之初,农民获得了土地耕种权及自由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但其手中的货币资产与非货币资产非常短缺,几乎没有储蓄,也不能将土地资本化,所能够依凭的就是其自身的人力资本。作为风险规避者的农民如何跨出这艰难的第一步呢?关键是在预期收益一定的条件下,怎样才能将外出打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并在此过程中完成知识的转化。因此,需要一个风险分担机制与一个低成本的学习机制,而农民外出过程所结成的“群团”组织,正好具有这样两种功能。农民工的“群团流动”事实上就是农民以血缘、地缘或者业缘为基础,采取“群团”的方式结伴外出,是中国农民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组织创新。这种外出的“群团”现象伴随着整个农民的非农转移过程,由于结伴外出的农民是熟人,由此组成的熟人圈子能够低成本地交换打工的信息、学习相关的技术以及分担打工中面临的各种风险。即使在农民获得了相应的知识,掌握了相关技术以后,进入创业阶段,流动中的群团组织仍然是他们获取生产要素、进行技术交易、分享市场信息的主要依托。这是因为基于社区信用的群团组织,不但降低了农民之间的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非农知识的传播、技术的学习。
农民非农过程中基于血缘、地缘结伴而成的“群团流动”组织,不但节约了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农民之间的知识交流与风险分担。具有不同知识的人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机制,并因此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免费的礼物”,它表明技术与知识具有人类共同财富的特征[2]。知识溢出效应是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利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不耗费知识获取者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不计入行为人的学习成本,事实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共同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副产品”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相互学习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我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源泉。
三、农民工“群团流动”的内在机理与社区信用拓展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伴随着农民的非农转移,而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离土不离乡”阶段与“外出打工创业”阶段。在“离土不离乡”的转移阶段,其关键是技术与企业管理性知识的获取。这种技术性知识是如何获取的呢?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是在比较封闭的社区中一代一代遗传下来的,知识的传播与扩散都很慢,而且在长期的经验积累与试验中,其知识形态基本上处在一种均衡状态,从而导致我国农村社会发展十分缓慢。但是,农村工业化对于世代务农的农民来说,除了资本的积累以外,关键的是技术。在商品短缺时代,那些有经商传统的地区,凭借历代累积的商业知识,对某种商品市场具有很强的敏感性,问题的关键是生产。产品如何生产呢?最便宜的方法就是模仿,当时遍布全国的“假冒”、“三无”产品是我国局部地区农村工业化初期的产物,农民依靠着人情关系从城市中聘请退休的老工人、工程师来指导,生产市场中紧缺的产品[3]。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积累了工业技术、工业管理及其工艺流程方面的知识,再加上农民的经商传统,于是农民企业家与农村工人这种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了。由此所构成的乡镇企业成为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中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的是技术人员从城市到农村的流动,尽管这种流动的数量不大,但对于改变我国农民的知识结构与提高农民的素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从事后的效果来看,一个乡镇企业,就是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干中学”成为我国农民成为现代产业工人的主要途经。基于熟人圈子的社区信用是乡镇企业赖以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我国农民非农转移进入“外出打工创业阶段”的时候,农民所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风险分担与知识转换。当我国农村流动人口在进入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所受的正规教育程度不高,又没有相关的非农工作经验,他们在进城前的人力资本积累总体上是不丰富的,不但存在如何将原来的人力资本转移到新环境下的可用的人力资本的问题,而且还存在一个在非农过程中学习新技术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与家人,还要支付获得新知识的费用。因此,农民必须找到低成本更新自己知识的途径与组织方式[4]。基于血缘、地缘与业缘而结合产生的农民群体,在共同的生产过程中会形成一种相互学习机制,并因此产生“知识溢出”效应,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知识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免费的礼物”。掌握了一定的工艺技术与市场信息的农民,在不同空间范围与周围群体发生互动与交流,一方面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另一方面加快了知识在不同群体之间的传播,而熟人圈子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组织形式。熟人圈子能够将不同的个人、群体、产业和区域有效地连接起来,促进历史的延续性、建立共同的信任关系、构建共同的信息交换平台。
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模型化了共同学习过程中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果是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利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不耗费知识获取者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不计入行为人的学习成本,事实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共同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副产品”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相互学习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是我国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源泉。由此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人力资本转移与积累由以下四个阶段组成:农村社区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在新环境下的外部延伸——“干中学”所累积的人力资本增量——人力资本存量与增量的融合。而这四个阶段中所需达到的目的,又必须依托于农民的“群团流动”方式。
农村社区所积累的社会资本如何在新的区域得以拓展,也就是农村社区信用是如何拓展的问题,是研究我国农民非农转移过程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国农村社区组织是以家庭为中心所构建的人情圈子。从1978年到现在,乡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改变了原有社区生活的组织结构,农户家庭的生产性功能重新处于决定性地位。在农村社会这个圈子中,家庭作为第一圈,担负起农民的生产、培育后代等全面复杂的功能,而农民社区生活的第二圈,则由亲属间、邻里间、乡村间的联系所取代。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事实上确认了农民对于其财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从根本上否定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导致了家族系统、家族文化与家族信用的复归,这些内容构成了农民赖以生存的社会资本的存量,也成为农民走进市场的重要资源。一方面,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经济生存状态在经济发展中逐步被打破,乡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户通过协作获取自身短缺生产要素的能力,成为决定其经济地位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社会联系广度、经济能力强弱等资源条件在农民家庭间的分布不平衡,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了富裕程度有明显差别的阶层。在社会资本稀缺、社会信用缺失、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普通农户要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特别是要在传统的种植业之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就需要从具有资源优势的家族成员方面获得支持。亲属关系和家族渊源等社会资本在我国转型期中成为了弥合阶层差别、分享发展机会和利益的重要渠道。乡村经济发展的这种客观要求,成为促使农民有意识增进亲属间、家族成员间联系的内在动力。
在传统的农村社区积累的社会资本是如何延伸到陌生的城市的呢?农村社区信用的空间转移与拓展,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与农民非农过程中的“群团流动”相伴产生的。与托达罗模型中农户在迁移过程中的盲目性不同,中国转型期中的农户的迁移是非盲目性的,因为农民的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他们的社会关系来实现的,在他们作出进城打工的决策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有比较真实的信息作为其决策基础的。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流动的组织问题与其社会资本有着更密切的联系。“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组织特征”课题组把劳动力外出中“外地亲友帮助联系”、“本地外出民工介绍”和“跟随他人一道外出”三种情形定义为外出民工的自组织形式,依靠这种自组织形式成功流动的占总流动人数的75%[5]。由于这种自组织形式占据了迁移方式的主导地位,所以一个村子里外出的劳动力常常有着相同的目的地,甚至是同一就业单位或相同的行业;相应的,民工第一次外出,大多数倾向于几人同行,在共同的迁移过程中,相互交流的学习过程增加了迁移者的情感,累积了新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我国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群团现象,事实上是我国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匮乏,单个的迁移者所面临的风险很大,群体组织可以规避知识匮乏的风险。例如,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结伴外出的乡里乡亲往往共同租住民房,分摊房租,形成小型聚居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地缘为核心的聚居区。这样传统社区的社会资本就延伸到了新的居住区。
四、结论与启示
1.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民工“群团流动”现象是我国农民的既有约束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现象。农民工流动过程中以血缘、地缘或者业缘为基础,采取“群团”的方式结伴外出,既节约了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过程中的信息成本,又分担了他们转移过程中的风险,而且增加了知识的溢出与扩散几率,是中国农民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组织创新。这种创新建立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之上,是农民基于成本与收益所作的理性权衡的结果。对该组织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在制度起源与知识交易的问题上,农民工“群团流动”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研究案例。
2.农民非农过程中基于血缘、地缘结伴而成的“群团流动”组织,不但节约了交易费用,而且有利于农民之间的知识交流产生知识溢出效应。知识溢出效应是一个人的行为对另一个人利益所产生的效果,而这种效果并不耗费知识获取者的人力、物力、财力,即不计入行为人的学习成本,事实上,具有不同知识结构的人在共同劳动中所获得的知识是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这种“副产品”的存在,导致了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对于这个问题的剖析,将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新经济增长理论,据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质就是新知识的流入与普及,而“群团流动”则是一种低成本的知识传递与学习机制。
3.农民工“群团流动”的经济组织方式,不但降低了农民转移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分担了转移农民所面临的各种风险,而且为农村社区中所累积的社区信用向异地转移提供了渠道。在社会资本稀缺、社会信用缺失、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普通农户要在经济活动中取得成功,特别是要在传统的种植业之外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就需要从具有资源优势的家族成员方面获得支持。亲属关系和家族渊源等社会资本在我国转型期中成为了弥合阶层差别、分享发展机会和利益的重要渠道。农村社区的信用资源转移,就是通过“群团流动”的经济组织予以实现的,这种现象的存在,为优化我国的城市化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4.在劳动力市场上,就业机会是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函数。这里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主要包括获取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较强的承担风险能力,以及对于各种职业的适应能力。而对于从农村社会走出来的农民来说,其社会资本存量是由他所生存的社区决定的。一旦迁移者在异地获得了第一个工作岗位并因此停留下来,他就会结交一些打工的朋友,还会认识一些城里人,他的社会关系网络就随之扩大了。这种以社会资本存量为核心的熟人圈子,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五常.再论中国(增订本)[M].北京:花千树出版社,2002.
[2]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2003.
[3]胡必亮.关系共同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朱锡庆.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6).
[5]蔡昉.民生经济学——“三农”与就业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