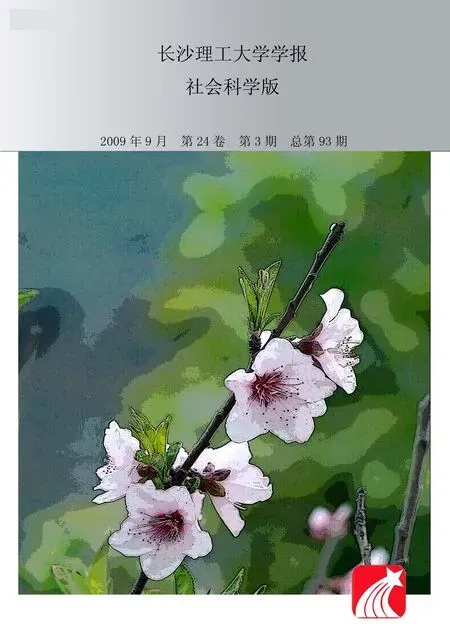“和”之源与“和同之辨”
左亚文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和”的词源考释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和谐,这个人类为之追求的价值目标,它不是从“同一”或“一致”中而来,而是从“差异”或“对立”中而来。例如,只有不同的声音相和调,才能产生美妙的音乐;只有不同的味道相配合,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只有不同的要素相结合,才能创造出新的事物。
声音之和。从史料看,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已认识到这个道理。在商周的甲骨文和金文中,“和”字作“龢”,从龠,禾声。《说文》释为:“龢,调也。”“龢”属于形声兼会意字。“龠,乐之竹管,三孔以和众声也。”[1]“龢”字的左部就是古代竹管乐器的象形写法,它本身就生动形象地表达了“声音之和”的发生是不同音素按照音乐规律相互配合、协调的结果。“和五音以悦耳。”五音者,宫商角徵羽也。要创作一首优美的乐曲,不仅需要运用“五音”这些不同的音阶作为创作的元素,而且根据音乐的节奏、韵律、情感、意境的需要,将音素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调和配合,才能形成悦耳之声。
据古文献记载,我国早在黄帝时期,就开始制礼作乐,后继的帝王均重视音乐的教化作用。《尚书》记录了舜帝曾命夔对贵族子弟进行乐教活动。“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这里的“八音”,是指用八种不同材料作成的乐器,包括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至周代,古文献所记载的这八个种类的乐器已达七十多种,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乐器体系。至商周时,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奏乐歌咏已成为贵族阶级政治统治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因而大大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之和不再是单一乐器的演奏,而是多种器乐的合奏,同时有歌舞相伴,形成了诗、歌、声、舞多种艺术形式相配合的高层次的“声音之和”。而且,乐与人相谐共鸣,让人受到熏陶和感染,使人的个性和情操达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中和之境,乃至进入“神人以和”、“天人合一”的至极状态。这样,音乐不仅给人们以美的享受,而且收到了寓教于乐的效果。
饮食之和。在古代金文中,“龢”通“盉”。《说文》:“盉,调味也。” 盉者,本为调和水酒之器具,意为饮食之调和。古人对饮食之和多有论列。《诗·商颂·烈祖》:“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尚书·说命》:“若作和羹,尔唯梅盐。”对于“和羹”,《郑笺》释:“和羹者,五味调,腥热得节,食之于人,性安和。”在郑玄看来,和羹,不仅能使五味和调,食之悦口,而且能使人性情平和,利于养心。成汤时名相伊尹以和羹之道说政,对于饮食调和之事有精妙之论。他说:“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后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不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吕氏春秋·本味》)史载,伊尹乃庖厨出身,他以自己的特殊经验向君主讲述烹饪调和之事,循循善诱地启发君主谨行治国为政的和谐之道,可谓用心良苦,耐人寻味。
在众多的自然、人事中,存在着普遍的“差异之和”、“对立之和”的现象。除声音之和、饮食之和外,还有嘉禾之和、文彩之和、四时之和,物象之和、牝牡雌雄之和、君臣之和、夫妇之和、朋友之和等等。这些都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千百次地碰到的现象和经验的事实,正是在这样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人们逐渐地懂得了“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国语·周语》)的道理,并得出了“和而不同”的结论。
礼义之和。但是,要使这种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由现象的观察进到社会的实践,方能深刻把握“和”的本质内涵。大凡对于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观察和经验只是认识的起点,只有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特别是在创造性地构建和谐对象性存在包括和谐之物、和谐之事、和谐之美的过程中,人们才可能真正地从世界的本质、本源和本体上体认到和谐的深邃意蕴。
中国古代圣哲所关注所亲历的主要是社会政治和管理实践。这种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与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相比,具有更为显著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特征。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首先依赖于所改造的客观物质对象,并且必须遵循客观对象自身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当然也离不开一定的客观环境条件,但是归根结底,环境条件也是人们创造活动的产物。因此,和谐之道在社会实践中的实现更能显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和谐实践的主体更能深切感悟和认识到和谐之道的奥妙和重要之所在,因而亦更能激发起人们创造和谐、崇尚和谐和维护和谐的热情和使命感。和西方的哲学家不同,中国的哲人尤其是儒家一般不脱离政治实践,他们的理论直接地就是为当时的治国理政服务的,不少人进出于朝野之间,兼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实践中,思想家们将和谐的感性经验认识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古代哲人们对于礼义之和的创制和认识上。
礼义之和与声音之和、饮食之和有所不同。后者虽为人所创,但它从广义上讲,属于人化自然。《庄子·齐物论》中对自然界中的“天簌”、“地簌”、“人籁”有十分生动的描绘。“地籁则众窍是也”,风吹众窍,发出不同的声音,此为“地籁”。但众窍的产生,风的流动,风吹众窍而发出声音,这一切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庄子从老子天道自然无为的观点出发,认为这一切都是由“咸其自取”的“天籁”所为,而“天籁”本质上就是自然。“人籁则比竹是也”,比竹为箫,不会自动发出声音,须赖人的吹奏。但人吹奏竹箫与自然界风吹众窍相似,只是人利用了自然界现成的材料制作出人工产品,并创造性模拟自然界发出悦耳的音乐,因而本质上属于“人化自然”。饮食之和与此同类。而礼义之和则全然是人类创造的一种制度性和精神性的产物。
“礼”在古代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复合概念,举凡政治法律制度、伦理道德规范、日常风俗习惯、社会等级秩序、价值评判标准、审美意识情趣、思想心理观念等等一切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内容,都包含在“礼”的范畴之中。用现代的话讲,“礼”是包括思想道德在内的精神文明和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政治文明的统一。因此,“礼”对社会生活和个人行为的规范是无所不在的。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而一定社会关系形成和维护必须以一定的道德规范和政治法律制度作保障,这就是“礼义”和“礼制”的必要性。对此,古人有十分深刻的认识。“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则也。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礼记·丧服四制》)“非礼无能节事天地神也,非礼无能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昏姻、疏数之交也。”(《礼记·哀公问》)这里把“礼”提升到了经天义地、合乎阴阳四时的高度,这一方面说明了“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通过正反的比较论证了“礼”之所以生的客观根据及其规律性。
“礼”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就是和谐,即社会规范的合理、社会生活的有序和社会关系的协调。和谐则是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五辅》)这里列举的八个方面,既涵盖了社会关系的基本方面,又指明了如何处理这些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而它的最终目标指向则是社会的和谐。用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主张的这种构建社会和谐的方法是符合系统论的层次性原则和结构性原则的。实际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及至可以预见到的未来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绝对消除在社会财富、权力、知识、职业、名誉等资源占有上所造成的等级区分,也不可能消除在这些资源分配上所必然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这种社会现实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也是合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任何从善良的道德观念或理性原则出发,企图借助外部强制的力量人为消除这种社会分层和利益矛盾的做法,实践证明只能造成更大的社会矛盾和更严重的社会冲突,甚至将社会推进灾难和痛苦的深渊。
因此,欲寻求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顺应社会系统的层次性和结构性规律,因势利导,以合理、有度的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护适应当时历史发展的等级结构和社会秩序,并以此来调节社会各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当然,一个社会的矛盾冲突有时要运用强制的力量来加以解决,但强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达致社会的和谐。解决社会冲突的最佳手段是运用和谐的方法来化解矛盾,乃至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者在讲“礼”时,所注重的是其礼义、礼仪等内在和外在的教化功能,崇尚的是其尊尊亲亲的和谐境界,强调的是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宽广和包容的气度,期望的是“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客观价值目标。
礼义之和的理念和实践是中国古代留传给后世的一笔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贡献给世界历史的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这样的思想理念和历史实践何以产生在中国而不可能产生在西方,是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形复杂而又相对封闭的独特的地理环境中,从原始氏族到阶级国家的过渡,虽然征伐战争不可避免,但更多地采用的是和平、和缓、和谈的方式。当时崛起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华夏部族面对周围众多的其他部族,简单地用“斗”的方式是难以服众的,只有主要用“和”的方式即以德服人的方式、协商的方式、结盟的方式,才能建立和维持部族共同体或部族联盟。即使对于那些叛逆的部族使用武力予以征讨,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俘获人口、财富,而是为建立统一的“帝国”而拓展势力范围。夏代正式建国后,这种部族结盟以君主统治下的诸候分封制形式得以保存,像西方奴隶社会那种将战争中的异族俘虏大批贬为奴隶的现象极少出现。同时,在这一历史变革的过程中,由于较多地保留了原来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于那些从事生产劳动的广大民众从来没有把他们当作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史料记载中那些最早的统治者几乎都认识到“民”的重要历史作用。我国早在尧舜时代,就产生了“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的民本主义思想。在我国古代社会,自天子以至庶人,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依然存在,但是,除各级统治者之外的士农工商,都属于“民”的范畴,在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等级”是相同的。在我国没有产生像古希腊城邦奴隶制国家、古代印度和日本那样由出生决定并由社会分工所固定化的社会阶层,这种扁平化的社会结构是滋生具有高度普遍意义的和谐观念与和谐精神的独特的社会历史土壤。
中国古代的“礼义之和”作为那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既是一种思想理念,又是一种历史实践。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在这种思想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历史实践,而历史实践又不断检验和提升着这种思想理念。正是在这种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循环往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哲人对于“和”的认识深入到了本质的层次,对于“和”的本质内涵、特征以及如何达到“和”的方法,都获得了较为丰富和深刻的认识。循着认识的必由之路,对“和”的认知将随着实践的推进上升到概念的本体阶段。
二、“和同之辨”的本体升华
将“和”从日常语言提炼为哲学范畴、从感性认识跃升到理性认识,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从已有的史料来看,直到西周,那个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们才在总结生活实践经验以及天文、医术、军事、农业发明等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政治上兴废得失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和谐的思想理念,用以解释社会现象乃至宇宙万物。
史伯的“他和说”与“专同”。明确地把和谐思想提升到哲学本体高度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史伯是西周末年太史,他鉴于西周无所挽回的衰颓之势,从分析周朝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入手,最后从哲学上概括出了“和”、“同”的概念,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重要命题。他在回答周为何必然衰败时指出: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以食兆民,取经入以食万官,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天夺之明,将无弊,得乎?(《国语·郑语》)
史伯关于“和同”的论述不仅用“和”的观点来解释宇宙万象,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证“和”的合理性和普适性,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一普遍性的哲学命题;而且把“和”与“同”相比较,强调了“和实生物”与“同则不继”在本质上的对立性。
“和”作为多样性的统一和差异要素的有机结合,它以扬弃的形式包含差异和对立于自身之内,将这些差异和对立的要素通过“和调”而形成新的和合体。这就是所谓“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的道理。而“同”则是相同要素的机械相加,由于缺乏异质要素的参与和驱动,因而必然处于停滞、僵死的状态。这就是所谓“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的涵义。所以,在哲学上,“和”与“同”是根本对立的一对范畴,“和”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状态的辩证范畴,而“同”则是形而上学思维在认识上的一种表现。但是,“和”并不绝对排斥“同”,而是把“同”与“不同”作为事物的内在构成环节包含在它自身之中,从而形成新的和谐统一体。
如果从“和”的辩证发展轨迹来看,史伯主要从“他和”的角度论述了“和”的本体内蕴以及“和”、“同”的本质区别。“和”是“以他平他”的结果,即是说,“和”中包含了“他物”,是不同“他物”和调、统一的产物。就“和”中包含的诸多不同的“他物”来讲,它们因彼此不同,故互为“他物”。一物是“他物”的“他物”,而“他物”则是此一物的“他物”,它们之间因有其内在关联而结合在一起,又因其内在的结合而彼此成为“他物”。然不同“他物”的结合,并非量的堆积,而是新质的突现和新事物的诞生。
史伯作为那个时代智慧博学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分析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的基础上,从本体论上提炼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哲学命题,深刻地揭示了“和”通过“以他平他”而产生的内在机理,从而使“和”的哲学思想得以奠定。同时,史伯把“他和说”与“专同”相对待,在思想史上,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和同之辨”,为廓清“和”、“同”在哲学上的分立打下了基础。
晏婴的“否和说”与“同一”。史伯之后,齐国政治家晏婴从“可”与“否”的对立统一关系继续深化了“和同之辨”。史载:
齐候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
在“和”与“同”的对立上,晏婴与史伯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和”是包含了差异和对立的统一,是具体的同一,有如“和羹”;而“同”则是排斥差异和对立的抽象的同一,有如“以水济水”。但晏婴和史伯有所不同的是,在如何达到“和”的问题上,所强调的是对立两个方面的互补互济的作用。如君臣的关系就是这样。在治国决策时,君主认为可行的,必定有不可行的地方,当臣子的责任是及时提出这些不可行的地方,以便使君主的决策更加完善;同样,君主认为不可行的,必定有可行的地方,当臣子的责任就是及时提出这些可行的地方,以便使君主的考虑更加周全。这里,晏婴提出了“可”与“否”的对立统一和互补互济的关系问题。除此之外,晏婴还提出清与浊、疾与徐、哀与乐、刚与柔、济与泄、成与去、不及与过等十数对矛盾,着重论述了它们之间相反相济的关系。晏婴的这些思想在继承史伯“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多样性的异质要素如何通过对立面的互补互济的作用而实现“和”的结果,从而更深入地揭示了创生“和”的本质规律和内在机制。
孔子的“人和说”与“同和”。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一生以宣扬“中和之道”为己任,为和谐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和”与“同”的关系上,孔子更多地注重的是“人和”,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从当时的时代实际需要出发,孔子不是把对“和”的阐扬放在哲学本体论上,而是将其具体化为处世之道和君子之德,使之成为社会实践和人生践履的方法论原则。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庸·第十章》)
无论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是在人格修养上,孔子都强调培养“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君子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所谓“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指坚持自己的原则,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同时,善于尊重和团结各种不同的人,不搞结党营私,不搞宗派主义。在个人的人格修养上,所谓“和而不同”、“和而不流”,是指君子要具备宽广的气度、宽容的雅量、宽宏的胸襟,同时又能坚守自己的节操,具有独立不倚的精神品性。而小人“同而不和”,是指那些利欲熏心之辈为谋取一己私利而结成小团体或小宗派。这些人以利益为标准来处理人际关系,来划分派别派系,利益成为他们结合的唯一共同点,不能带来利益的人都成为他们排斥的对象。因此,小人的“同”是建立在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上的“同”,是各自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同”,因而是缺乏诚信基础的经不起任何时间考验的“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君子之所以能团结一切人,是因为他有“仁者爱人”之心,故尔能超越个人利益,施爱于一切人。小人因束缚于个人名利,因而不可能真正去爱他人,与人相和。君子取和以去同,小人取同以去和,前者谓之“和同”,后者谓之“同和”,二者的价值取向,可谓大不相同。
诚然,君子与小人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实际生活中,君子可能变成小人,小人可能变成君子。儒家主张人性本善,每一个人都具备成为君子的秉赋,只要你加强修养,涵养善性,就能达到目的。孔子在人性修养和人际关系上的“和而不同”说以及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不过是给人们提出了一个做人的标准和价值的准则。
因此,孔子的“和同之辨”在哲学上主要表现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它把前人在这个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进一步引入到个人生活和人性修养的领域,既使之具体化了,又使之获得了人本学的升华。
孔子之后,“和”的思想延绵不绝,代代相传,但“和同之辨”不再成为理论热点。主要原因一是由于“和同之辨”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取得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已成为一个勿庸争辩的问题;二是先秦之后,大一统的寡头君主专制建立起来了,像晏婴一样敢干向君主“献其否”以表明政治异见的环境条件已不复存在。所以,自秦以降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统治过程中,思想和政治、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严重的“悖反”现象。一方面,思想家和政治家继续大谈“和而不同”之道,“和”的思想得到了发扬光大;但另一方面,当涉及到现实政治的时候,特别是当触及到最高统治者的政治主张时,这些思想家和政治家就再也没有他们先辈们的那种勇气了,即便某些正直之士敢干叛逆“犯颜”,也必然落个“口未言而身先死”的下场。历史是现实之镜。历史一再昭示我们,“和”是天地之正道,“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就社会发展来说,和则顺,不和则乱;和则进,不和则退;和则兴,不和则衰。但理论认识是一回事,能否付诸实践又是另一回事。要解决两千多年来就一直存在的理论和实践、思想和政治的脱节和“悖反”,就必须营造能够使二者真正结合的制度环境,就必须创建能够使各种“和而不同”的要素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就必须从社会中彻底消除与“和”相对立的各种形式的“专同”和“专一”的专制遗毒。如果说,在二千多年君主专制的社会中,君权的“专同”还有其历史合理性的话,那么,在现代民主政治特别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中,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上的“专同”,都已完全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当今日之中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重提“和”的思想时,从源头上探寻“和”的产生以及“和同之辨”的源流,并对其进行现代的阐释,乃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逻辑必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参考文献]
[1]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199.
[2]郑涵.中国的和文化意识[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
[3]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谐文化与和谐广东”论坛[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