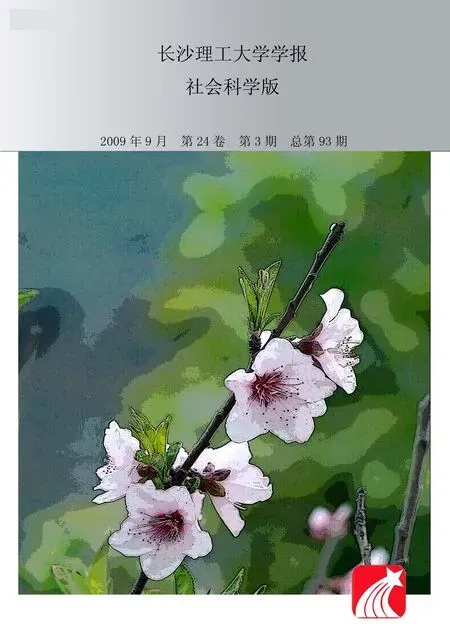政治、经济和文化多维关系解读
——兼论和谐社会构建
韩美群, 宋 州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经济、政治和文化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然而,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上,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有些人通常从经济决定论的角度简单理解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认为全部社会的基础是经济活动,政治、文化只是经济活动的结果;有人根据列宁提出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1]的观点,指出政治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有人根据西方文化形态史学家所提出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因素,而经济、政治只是社会发展的表面现象的观点,断言文化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的决定作用。从总体上看,这些认识都具有片面的性质。
一
经济对政治和文化具有决定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原理。19世纪中期,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创立“新唯物主义”时,主要面临着发展唯物主义,从历史领域里驱逐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科学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任务。当时,无论是像费尔巴哈那样的唯物主义者,还是像黑格尔那样的辩证法大师,一旦他们进入历史领域,企图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时,总是试图从精神或意识入手,来说明历史的事变和社会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满足人们吃、喝、住等物质需要的经济活动是低俗的、不值一提的。例如,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2]黑格尔则明确地提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创造主”,认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指导者的理性的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3]在黑格尔看来,粗糙的物质和物质活动恰恰是要予以“扬弃”的,只有通过“扬弃”这种“感性的对象”,才能把握作为其内在灵魂的“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在积极参与社会实践的斗争中,逐渐认识到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性质和不合理性,于是,毅然反叛黑格尔以及一切旧哲学,开始从一个新的但又是最基本最简单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历史的本质。这就是从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最基本的物质生产劳动入手,来解剖社会的结构,分析社会的内在矛盾。这种研究,使他们揭示了一个历来被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这就是“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4]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严格意义的政治活动、文化活动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因此,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经济始终是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政治、文化虽然可以以巨大的力量反作用于经济,但它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却最终要由经济来决定。如果离开人类的经济生产和物质生活来抽象谈论人类的精神,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不切实际的空谈阔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基本思想。
二
社会的运行是多维辩证的。从实现和保障社会发展的手段来看,政治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首要作用。如前所述,在终极的意义上,经济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因,一切政治、文化活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然而,经济利益的实现既然需要通过政治才能体现和维护,那么在一定时期当运用单纯的经济手段很难实现和维护经济利益时,依靠政治的力量来加以解决就具有了决定的意义。1921年初,当托洛茨基在党内挑起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的争论时,列宁提出了著名的政治“占首位”的论断。列宁曾指出,“最重大的、‘决定性的’阶级利益只有通过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具体说来,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5]这在无产阶级未夺取或未巩固政权之前,无疑是对的。但是,在夺取并巩固了政权之后,政治还能继续起“决定作用”吗?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列宁是辩证论者。他一方面坚持经济的基础作用,甚至说“今后最好的政治就是少谈政治”;另一方面,针对托洛茨基在工会问题上否定党的领导和国家管理的危险做法,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对此,列宁作了具体的论证:“因为问题只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产任务。”列宁还特别指出:“自然,我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希望我们少搞些政治,多搞些经济。但是不难理解,要实现这种愿望,就必须不发生政治上的危险和政治上的错误。”[6]在实行了新经济政策之后,在党的工作重心已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之后,列宁提出坚持党的领导这一不可动摇的政治路线,具有关系党和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首要意义。因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实践活动中,即在确定的经济前提条件下,政治往往起着首要的决定性作用。
三
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存在和发展一刻也离不开有意识的人的活动,社会的存在都毫无例外地打上了意识的烙印。从文化学的观点来看,文化作为“观念的表征”和“时代的活的灵魂”,是蕴涵于社会历史之中的内在动因。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一些近现代学者关注的比较多。如中国早期的文化民族主义,强调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指出中国应用人类需要的精神力量去开创新时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出“文化霸权”理论已为人熟知。葛兰西承袭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历史的人。但不同的是葛兰西特别强调人的创造性、人的意志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人能创造自己的个性、创造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具体的意志,也就是在实践上把抽象的愿望或生存动机加到用以实现这种意志的具体手段上去”。[7]葛兰西把人的集体意志提到了空前的高度,正是基于此,文化被放在了人类生活的最显要位置。后来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这一思想,提出文化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指出一个缺少文化核心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一个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这样的国家终将分裂。至于当代西方的文化形态史学观,则明确地把那种内隐于社会深层的文化观念或文化模式,作为评判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域生存方式和发展状况的标准,并把它看作是推动这个民族和地域文明变迁的内在根据。对于这些思想,有人认为他们忽视了经济的基础作用,所以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但如果仔细探究这些思想的本质,就会发现其中不无可取之处,如从具体民族、具体时代特点和实际应用的角度来看,文化或民族精神在特定时候也可以推动社会的发展,起重要作用。因此,简单地断定这些观点属于历史唯心主义是肤浅的。由于文化是一个或几个民族在广大地域历经长远历史逐渐孕育而成的产物,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广泛涵盖性,它对人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又是持久有力的。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命脉,是其生存之源,发展之本。由于文化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文化在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占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
四
从社会历史运行的具体过程来看,经济、政治和文化三者交互作用、耦合互动、有机统一。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指出马克思和他在早期著作中之所以没有过多论及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和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当时的任务要求他们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经济基础的作用上面,所以,他们主要是从基本的经济事实出发,引出政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这在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是必要的。但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忽视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就容易给人造成误解,以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经济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并就社会历史创造活动过程中诸因素的相互作用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恩格斯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8]首先,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一定的政治是一定经济的反映。相对而言,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当着政治文化上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基础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9]其次,经济与文化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共生共长的关系。一般来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文化发展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在一定条件下,文化会反过来对经济起决定的作用。再次,政治与文化之间是互为前提、互相作用的,政治受经济的制约,又要以一定的文化为根基。文化与政治同属上层建筑,文化是一定政治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一方面政治的构建要以文化为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一定的政治又对文化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总之,经济、政治和文化作为社会结构的三个不同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它们在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五
多维度全方位理解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促进社会进步与和谐发展,正确认识和处理繁杂的国际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国内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来说,正确处理社会结构的多维关系事关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化。这三个方面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而且它们相互渗透和相互促进,只有三者协调发展和相互促进,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诚然,在现阶段,我们必须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所决定的。但是,抓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政治为代价,从一个极端滑到另一个极端。现在,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淡漠政治,提出政治应该为经济“让路”、政治是多余的等等,这些主张和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不是相互排斥的,我们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要把政治建设放到次要位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10]另外,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的发展,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政治建设的落脚点,对于促进社会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上相对落后的民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在文化上演奏“第一提琴”,引领世界文化潮流。从经济实力上讲,我国还不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但我国的先进文化建设与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相比,却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只要我们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一切优秀文化传统,博采世界各国文化之长,就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民族先进文化,使中华文化再现辉煌。
就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来看,正确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关国家的安全和对外关系的成败。首先,世界各国政治舞台上的较量越来越表现为以经济、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斗争,因此,经济手段也就成为了实现国家政治目的重要方式,即国际经济活动日益具有政治化趋势。如在中美关系中,最惠国待遇本来是一个纯经济贸易问题,但在1989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中却被高度政治化,将它同所谓的中国人权、民族、宗教等问题联系起来,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斗争的主要焦点。当前,有些人看不清国际经济的政治化趋势,宣扬经济的非政治性,在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的同时,提出全盘照搬西方现成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不顾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趋向以及我国的实际,这对我国社会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因此,在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过程中,对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图谋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能就经济讲经济,还要善于把握经济中的政治问题,从而维护国家安全。
当前,文化广泛渗透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作用越来越综合化。文化是构成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因素,是凝聚人心的黏合剂,据此,有的学者提出文化国力的概念,[11]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所谓文化国力,是指综合国力中的文化力,它是与综合国力系统中的经济力、政治力等因素相对而言的。在国际政治舞台的较量过程中,随着经济因素的地位逐渐上升,文化因素也随之上升。在新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都有赖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进步程度。在当今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下,文化国力的重要作用也得到普遍的认同,这正是西方学者提出文化扩张、文化外交、文化霸权的一大背景。因此,加强我国文化国力的建设,也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407.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58.
[3]黑格尔. 历史哲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46.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776.
[5]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333.
[6]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2.407.408.410.
[7][意]安东尼奥·葛兰西. 狱中札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45.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696.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326.
[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