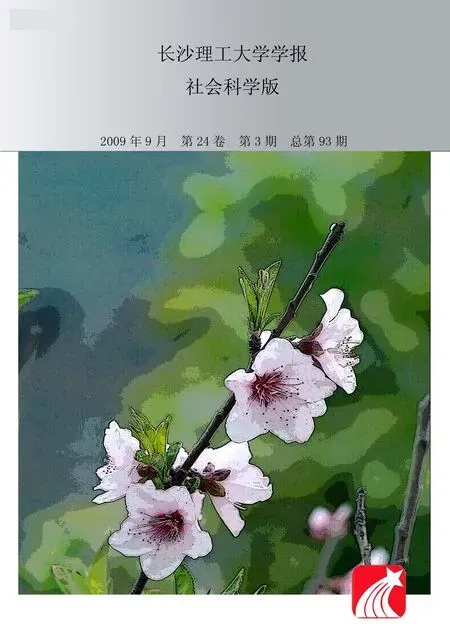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
汪东发
(广东海洋大学 文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88)
当陆志韦、闻一多、徐志摩等觉悟到诗的形式缺乏,开始为新诗构造“诗的躯壳”时,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另一些觉悟者开始了他们要住的诗的世界的寻求,致力于探索新诗的艺术表现,将象征主义诗艺引入新诗。两者都是针对着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但又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着眼于新诗的自由散漫、形式缺乏;后者是着眼于新诗过于“明白清楚”,艺术表现粗浅直露。闻一多、徐志摩等标识着郭沫若时代①的诗学深度,李金发等则是戴望舒时代的先行者。这两个诗人群的诗学探索,影响所及,形成了1920年代诗坛的两大诗歌流派,新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整体上推进了现代新诗的发展。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将1917~1927年的新诗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但按而不表,后来(1936)在《新诗的进步》一文中作过公正评价,他同意一位朋友的说法,也认为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一派比一派强,“新诗是在进步着的”②。
1925年李金发的出现,无疑是新诗坛的一大新异景观。
李金发(1900~1976),原名李权兴,笔名有李淑良、李金发等,广东梅县人,1919年秋至1925年5月留学法国,专习雕塑,其间醉心于法国象征派诗歌。他的新诗创作开始于1920年,1923年集成《微雨》和《食客与凶年》两个诗集,后来都寄给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周作人,“望他‘一经品题,身价十倍’”,周作人复信称“这种诗是国内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③。1925年,李金发的《弃妇》、《心愿》、《时之表现》等诗在《雨丝》刊出,这年11月他的第一部诗集《微雨》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也是新诗史上第一部象征主义诗集。《食客与凶年》则迟至1927年才由北新书局出版。这两本诗集“印刷的耽搁”,李金发在其第三本诗集《为幸福而歌》的《弁言》里说“所有诗兴都因之打消,后除作本集稿子外,简直一年来没动笔作诗”④,热情锐减。后来李金发诗作很少,1942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异国情调》是他的一部诗文合集,诗的分量有限。
李金发的《微雨》虽出版于1925年,但集中作品,包括他的《食客与凶年》和《为幸福而歌》两部诗集中的作品,都作于1920~1924年,尤以1923年所作为多。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大体和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诗人的创作同步,与闻一多作《红烛》篇什、与徐志摩感情“无关栏”地写诗、与郭沫若写完《女神》写《星空》及冰心写《繁星》和《春水》也大体同步。这就难怪接到李金发旅欧诗作的周作人会称之为“国内诗坛所无,别开生面的作品”,李金发诗作与这些诗人诗作相比,差异是惊人的。
李金发说:“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⑤他的诗歌创作对于“自己的世界”的表现,集中在爱的苦痛与幻灭、生之忧愁和凄苦、心之孤寂与悲哀,有“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怖”(《琴的哀》)。
“我们散步在死草上,/悲愤纠缠在膝下。//粉红之记忆,/如道旁朽兽,发出奇臭,//遍布在小城里,/扰醒了无数酣睡。”(李金发《夜之歌》)
“衰老的裙裾发出哀吟,/徜徉在丘墓之侧,/永无热泪,/点滴在草地/为世界之装饰。”(李金发《弃妇》)
“如残阳溅/ 血在我们/ 脚上,//生命便是/ 死神唇边/的笑。”(李金发《有感》)
“我们折了灵魂的花,/所以痛哭在暗室里。/窗外的阳光不能晒干/我们的眼泪,惟把清晨的薄雾/吹散了呵,我真羞怯,夜鸠在那里唱,/把你的琴来我将全盘之不幸诉给他,/使他游行时到处宣布。”(李金发《不幸》)
“生命便是死神唇边的笑”,这就是李金发式的极为恐怖和哀戚的生命感悟,一份比较经典的哀怨、绝望、颓废而且神秘的“现代”情绪,一曲心灵哀歌。他的诗是这样,甚至“他的雕刻都满是人类作呻吟或苦楚的状态,令人见之如入鬼魅之窟”⑥。虽然此前的新诗中并不缺乏极富“象征”意味的作品,如沈尹默的《月夜》和《三弦》,周作人的《小河》,郭沫若的《女神》,等,但与李金发诗作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李金发“有意的讲究用比喻”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⑦,是“流动的,多元的,变异的,神秘的,个性化,天才化的,不是如普通的诗,可以一目了然的”⑧;以“人生的悲哀”为基本主题,“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绪”⑨,他尽情表现“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⑩,“文字不照寻常习惯安排”,“行文朦胧恍惚骤难了解”还“有感伤与颓废的色彩”“富于异国情调”。
周作人称赞李金发,是对“象征”(他说就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兴”)和“融合”的提倡和强调。1926年他为刘半农的《扬鞭集》作序时说过:
“我觉得新诗的成就上有一种趋势恐怕很是重要,这便是一种融化。不瞒大家说,新诗本来也是从模仿来的,它的进化是在于模仿与独创之消长,近来中国的诗似乎有渐近于独创的模样,这就是我所谓的融化。……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觉得所谓‘兴’最有意思,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中国的文学革命是古典主义(不是拟古主义)的影响,一切作品都像是一个玻璃球,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没有一点儿朦胧,因此也似乎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正当的道路恐怕还是浪漫主义,——凡诗差不多无不是浪漫主义的,而象征实在是其精意。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新诗如往这一路去,融合便可成功,真正的中国新诗也就可以产生出来了。”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中最早称李金发为“诗怪”,奉为“中国抒情诗第一人”,朱自清后来也肯定说:“李金发先生等的象征诗兴起了。他们不注重形式而注重词的色彩与声音。他们要充分发挥词的暗示的力量;一面创造新鲜的隐喻,一面参用文言的虚字,使读者不致滑过一个词去。他们是在向精细的地方发展。”
但“作诗的时候从没有预备怕人家难懂,只求发泄尽胸中的诗意就是”,声言“我绝对不能跟人家一样,以诗来写革命思想,来煽动罢工流血,我的诗是个人灵感的纪录表,是个人陶醉后引吭的高歌,我不能希望人人能了解”的李金发,他的诗引起争议、引起“微雨冲击波”是必然的。主张“作诗如作文”,要求诗要写得“明白清楚”的胡适说“看不懂而必须注解的诗”是“笨谜”;梁实秋认为“笨谜”的出现是因为模仿所谓象征主义的诗,很偏激地说“是人就得说人话,人话以明白清楚为第一要义”;任钧则认为“无视民众只为自己”“把诗写得非常晦涩暧昧”是新诗发展的歧途。可以说,将死亡和悲哀、神秘和幻梦带进新诗,李金发带给诗坛的怪异感差不多等同于“狼来了”的恐惧感。他“凄迷奇幻”的抒情品格,使得自己的诗作自降生那天起就备受指责,以至于很长时间人们都不愿承认他对诗坛的贡献。其实李金发何尝不是开一代诗风的诗人,尽管他既引进了象征派同时又败坏了象征派的名声。
李金发之后,王独清(1898~1940)凭吊或陶醉在《圣母像前》(1926年版),穆木天(1900~1971)怀揣凄苦的《旅心》(1927年版),冯乃超(1901~1983)举着惝恍的《红纱灯》(1928年版),加入了象征派的合唱。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都是1926、1927年回国参加创造社活动的由浪漫主义走向象征主义的青年诗人,诗风相近,但与郭沫若、田汉、成仿吾等风格差异较大,史称“后期创造社三诗人”。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评价说“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轮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豪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托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力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无疑是很中肯的。
“我从Cafe’中出来,/身上添了/中酒的/疲乏,/我不知道/向哪一处走去,才是我底/暂时的住家……/啊,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我从Cafe’中出来,/在带着醉/无言地/独走,/我底心内/感着一种,要失了故园的浪人底哀愁……/啊,冷静的街衢,/黄昏,细雨!”(王独清《我从Cafe’中出来……》)
王独清的“歌唱”有两种主要动机,“第一是对于过去的没落的贵族的世界的凭吊;第二是对于现在的都市生活之颓废的享乐的陶醉与悲哀”,感伤情调深浓,有象征主义的尝试,也有浪漫主义的影响,并无多少晦涩之作。这首诗就是朱自清说的“显胜于晦”的。同样兼具有浪漫派和象征派风格的穆木天和冯乃超,比起李金发来,他们的感伤的哀吟也要明朗一些,不如李金发那般凄迷和沉哀。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濛濛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古钟 飘散 在水波之皎皎
古钟 飘散 在灰绿的 白杨之梢
古钟 飘散 在风声之萧萧
——月影 逍遥 逍遥——
古钟 飘散 在白云之飘飘
一缕 一缕 的 腥香
水滨 枯草 荒径的 近旁
——先年的悲哀 永久的 憧憬 新觞——
听 一声 一声的 荒凉
从古钟 飘荡 飘荡 不知哪里 朦胧之乡
古钟 消散 入 丝动的 游烟
古钟 寂蛰 入 睡水的 微波 潺潺
古钟 寂蛰 入 淡淡的 远远的 云山
古钟 飘流 入 茫茫 四海 之间
——暝暝的 先年 永远的欢乐 辛酸
软软的 古钟 飞荡随 月光之波
软软的 古钟 绪绪的 入 带带之银河
——呀 远远的 古钟 反响 古乡之歌
渺渺的 古钟 反映出 故乡之歌
远远的 古钟 入 苍茫之乡 无何
听 残朽的 古钟 在灰黄的 谷中
入 无限之 茫茫 散淡 玲珑
枯叶 衰草 随 呆呆之 北风
听 千声 万声——朦胧 朦胧——
荒唐 茫茫 败废的 永远的 故乡 之 钟声
听 黄昏之深谷中(穆木天《苍白的钟声》)
穆木天比较注重诗的音乐性和形式感,这首诗“托情幽微远渺”,以散词断句传达诗人对荒郊迷蒙凄怆的钟声的感受,“声”感鲜明强烈,声韵及词的断续承继有一种奇妙的“拟钟声”效果,诗情与诗形也契合得很好。
冯乃超歌吟“现实的哀怨”“伤痛的心碎”,也有相对明快的节奏和清晰的情绪流。
“我看得在幻影之中/苍白的微光颤动/一朵枯凋无力的蔷薇/深深吻着过去的残梦//我听得在微风之中/破琴的古调——琮琮/一条干涸无水的河床/紧紧抱着沉默的虚空//我嗅得在空谷之中/馥郁的兰香沉重/一个晶莹玉琢的美人/无端地飘到我的心胸”。(冯乃超《现在》)
李金发是将法国象征诗的手法介绍到中国诗里来的“第一个人”,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此外,冯至、戴望舒、梁宗岱、胡也频、姚篷子、邵洵美、于赓虞、石民、侯汝华、林英强等也受这一思潮的影响或直接取法于法国象征派而从事诗歌创作,1920年代中后期,象征主义诗歌创作成一时潮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
感伤的象征诗的兴起或者说象征诗派的出现,既是新诗自身发展的结果,即初期新诗的粗陋直露导致的反叛与超越的艺术演变要求,也与时代社会生活和外来文学影响有着密切关系。形式缺乏、技术幼稚的初期新诗,自己为自己培植了两股“反动”力量,这就是格律诗派和象征诗派。前者主要致力于“形式建设”方面的诗美创制,后者主要致力于丰富新诗的艺术表现,都是期望实现新诗的“艺术化”。从“时代”影响来看,五四运动过后、尤其是“五卅”以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革命低潮期,苦闷、彷徨、感伤、悲哀、寂寞的时代情绪或者说“时代病”代替了革命的呐喊和浪漫的抒怀,时代感伤风盛,正如饶孟侃所说“差不多现在写过新诗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染着一点感伤的余味”。从文学传统的影响来看,五四时期西方象征主义、表象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就被译介到中国,而李金发、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则直接深吸着“异国的薰香”,接触并接受了20世纪初风靡世界的象征主义艺术,开始他们最初的模仿和借鉴。李金发就坦承自己是“受鲍特莱尔与威尔伦的影响而作诗的”。
李金发的象征派诗艺引入,正如他在《食客与凶年·自跋》中所说,原本是想把中西“两家所有,试为沟通”的,但自己的创作实践却并未很好地实现这一意图。他的诗生硬、晦涩、过分欧化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诗情过于凄迷沉哀。在李金发诗作诗风影响下形成的象征诗派,他们“深吸异国的熏香更多于借鉴中国民族的传统”,“歧路的教训和尝试的经验同时呈给了新诗的殿堂”,也一直声名不佳。但李金发们的诗艺引入,给当时的诗坛带来了一股新异的诗风,丰富了新诗的艺术表现和艺术品格,对中国新诗艺术发展的积极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他们的诗学探索,其经验与教训,是戴望舒时代诗学传统的重要构成。
[注释]
① 笔者的“新诗四时代论”认为,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1917~1923年左右),中经郭沫若时代(1919~1932年左右)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1925~1937年左右)的掘进,至艾青时代(1932~1949年左右)走向综合。可参见拙著《新诗四时代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3。
② 朱自清:《新诗杂话·新诗的进步》,作家书屋,1947。
③ 李金发:《异国情调·从周作人谈到“文人无行”》,商务印书馆,1942。
④ 李金发:《为幸福而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⑤ 华林(李金发):《烈火》,原载1928年《美育》1期,转引自孙玉石《象征派诗选·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9页。
⑥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原载《美育》2期(1928),转引自《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⑦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
⑧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
⑨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
⑩ 黄参岛:《〈微雨〉及其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