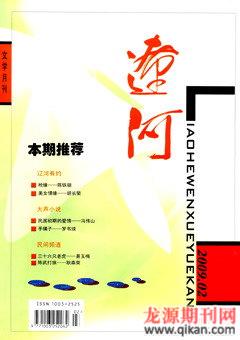我愿意把一切都给了你
林海文竹
初秋的菜园子,并不萧索。明媚的丽日晴空下,茄子枝上挂着最后一批果实,那颜色愈发的深紫了。辣椒枝叶间也尚纷披着不少尖红的小辣椒,在风中微微摇荡着,似串串红绿相间的风铃。叶蔓已趋向枯黄的芸豆架子上,几株牵牛正缠绕攀爬,蓝盈盈、粉艳艳的花儿在晨风中竞相开放,让这秋日的乡野并不显得颓凉,而是更显生命不息的勤勉与坚忍。
离村井不远的那片菜园里,那圈石砌的矮墙里,一片低矮的海蓬子花正在盛开。红的、黄的、紫的,烂漫的花们。像给那片小土地铺上一匹锦帛。帛上端坐着一位痴呆的老人,花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散荡在呆滞、黝黑的脸上。她每天早晨、黄昏,都要在这坐上一个时辰,风雨无阻。
一圈矮墙里,一个老人守着一地杂花,几株柳树,一座土坟,兀自坐着,这于村里人就像是地里春种秋收的庄稼,早已成丁习以为常的事。可是才见了几次的我,看着她独坐的背影,心里却总止不住要落下泪来。久未回老家,现在才知道,这位七十多岁的远房二娘已经老年痴呆好几年了。
年轻时她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女子。跟开私塾的爷爷颇读了些书,身材高挑匀称,油亮的长辫子,白净的满月脸,标致的五官,精致得体的自制衣饰,兰心慧质的灵巧能干。当年风流倜傥、退了军役一心务农的二大爷是很费了些心思、周折,才将她娶进门的。据我妈说:她进门那一天,远近有许多來看新娘子的姑娘回家后心酸地落下泪来:艳羡她的美。她的好,心酸自己这一辈子都不能有这样美的时刻。
日落西山,牛羊的叫声扯散了乡村的炊烟。穿戴干净、光鲜的年轻二娘怀抱才出生一个多月的馨香的儿子倚门而立,与门前菜园子里打点菜蔬做晚饭的邻家媳妇开心地逗笑、调侃。下地回来的年轻二大爷老远就奔过来,一把抱过可爱的儿子左亲一下,右亲一口,含笑地瞥了眼微笑的二娘,她就羞红了脸回家准备晚饭去了。他们的幸福、恩爱曾是村里人最可乐的笑谈。
可是,命运曼妙的脚步在这个人人艳羡的家里突然拐了个弯,亲亲的儿子一次病后出现了种种反常的迹象。那时她已怀了第二胎。她像受了惊无法安定下来的母鹿,惶惶地、心焦地抱着儿子四处求医问药。最终却不得不承认,儿子因为“有风”(医疗落后时民间的一种对新生儿特殊病种的说法),没有及时发现并治疗,已经病坏了脑子,异于常人了。
我妈说,当时在农村,因各方面落后,其实常有新生儿夭折或落下残疾的不幸发生。老人都会编各种迷信的理由安慰新母亲们:生下这样的孩子是冤孽、是轮回。大家心疼一场也就丢开心思,一样的过日子,再次生儿育女。
可是,二娘的悲剧就在于,她读过书,她不是一个完全愚昧迷信的农妇,她无法让那些自欺欺人的说法安抚自己一颗悲痛、无助的母亲的心。因大人的疏忽而导致儿子致残的事实,她无法原谅;长得白白胖胖、温软、可爱的儿子将是无论怎样成长,都不是一个正常人的现实。她无法接受!
那段日子,二娘几近崩溃的边缘。她紧紧地抱着憨憨的儿子,或整夜整夜无声地饮泣,或突然凄厉地放声号哭。如果不是她的婆婆求了当年懂医的我姥姥用土法熬了安胎药,由我尚未出阁的妈日日提了来给她灌下去,也许她腹中的孩子早流产了,说不定她从此心灰意冷、过早地结束自己及憨儿子的生命也未可知。可是,她腹中的孩子保住了,也许是那强烈地胎动牵引了她欲垮掉的意志。第二个孩子在七个多月时就早产了。再次为人母的责任让她不得不收拾一颗痛极的母亲的心,打起精神生活下去。
一开始,她把大儿子守得很严,不让别人看,不让别人有同情、嘲笑的眼神在孩子身上掠过。却总是把小儿子抱给别人看,不安地询问,让人帮忙观察一下,儿子的某些举动是否正常?什么是杯弓蛇影,什么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那时的她体会得最是刻骨铭心吧?
还好,二儿子是健康的。开心了会咯咯地笑,受委屈了会哇哇大哭,知道冷了要衣,饿了吃饭,会走路,会说话,会所有孩子应该会的事情。可是,二娘并不是很亲近他,却偏爱什么也不会的大儿子。
她用玉米皮编了许多垫子,天气好时,就在院子里铺上垫子,放上尿布,让大儿子坐在上面晒太阳。儿子除了吃吃地傻笑,“嗷嗷”地哭叫啥都不会。一双慘白的手,五指总是微曲着,见了人就要扑过来的样子,吓得小孩子从不敢在他身边玩,总是远远地避着。其实他除了坐着、躺着,连爬都不会。可是,人们还是受不了他在身边发出的瘆人的呜哇乱叫,那声音像极了被订了四掌,又困又饿又绝望的野兽发出的凄惨、尖利的号叫。
况且他是永远大小便失禁的,身上总带着令人作呕的骚臭味。虽然二娘准备了许多的尿布,不时给他换洗。可是他吃得太多了,排得也频繁。二娘又要家里家外的忙,无法保证他能永远清洁。下地回来的二娘洗一把手,先是给他换了尿布,擦净了身子,又端了水给他喝下去。他的白眼珠斜斜地转着,似笑非笑地呜呜叫着,有时用双手呼一下就掐住了二娘的脸,抓出几道淤痕,或是扯下一绺头发。二娘红了眼圈,拍抚着他,跟他说着话:乖,好孩子,着急了是不?娘来得晚了是不?宝贝口渴了,生气了……偶尔的,他也会被拍抚得安静下来,哼哼着用手抓了身边给他准备的几个布球,撕扯着玩去了。
二娘早已不复当年的秀美俊雅了,三十多岁已是满头华发,满脸皱纹,身体松垮、变形得不成样子。她和二大爷没有再生孩子。二大爷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一无是处、不能称作是“孩子”的孩子,会让二娘彻头彻尾地变了。除了干活、照顾孩子,二娘对什么都了无意趣。二大爷酗上了酒,爱上了赌博,习惯了骂天骂地骂一切,他每天像一头红了眼迷了性的斗牛,在街头田间游荡,无心干活,更不愿回家看到白痴的儿子,死灰朽木似的老婆。有天夜里,不知何因,竟失脚掉进沟崖里的积水里淹死了。
人们都可怜二娘的命苦,怪她放不下痴儿子,弄得日子不像日子,害得孩子亲爹没了,往后哪个男人愿意趟这烂摊子。甚至有人说还不如把那痴孩子弄死算了,养着也没啥意思,趁年轻早点打算自己往后的路,日子还长着呢。
二娘的神情更冷更木了,像极了一头没日没夜劳作的牲口,除了干活,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酷暑的午后,知了的叫声把空气喊得更炽热了,人们都躲在荫凉处酣睡,二娘趁此空闲去河里洗每天都少不了的大盆尿布;严冬,冷风刺得露在外边的肌肤刀割样生疼,二娘又砸开厚冰,去洗那洗不完的尿布。一日三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二十多年来,每顿饭,二娘都要先一口口地嚼了饭把大儿子喂饱了。从小到大,他不会自己嚼饭、吃饭。
二娘的心是苦的,牙也不争气地一块块脱落了。后来,一口烂牙嚼完两个大饼子,一小盆菜,总要用半个多小时才能把他喂完。二娘吃的永远是冷饭。我妈劝她:嫂子,你是家里的顶梁柱,先把自己照顾好了,吃完热饭再去喂他。二娘红了眼圈低了头,过好一会儿才低声说:妹子,他是不会说话的人……要是他啥也明白……我这心里,不想委屈了
他!
痴儿子不活动。吃得又多,长的便很“魁梧”,大圆脸,到了三十岁也没长胡子,没皱纹。二娘要搬动他已经很困难了,再不能经常背着他下地干活或去赶集“看”热闹了。小儿子一直是受冷落的,所以对娘及痴哥是愤恨的,根本不会去帮娘管他。
他三十岁那年的开春某一晚上,在睡梦中永远地去了,再不用亲亲的娘像照顾一个小婴儿一样照顾着他七十多公斤重的身体了。去看过的我妈说:痴了一辈子的傻小子,临走脸上的笑容,都像一个才生的小婴儿一样。二娘已不复年轻时的情绪不易自持,只是一直一直无声地流着泪,给他擦了最后一次身子,穿上新的衣服,打发了他上路。
后来把骨灰就埋在自家门前的菜园子里。留了一个上堆,立了块石条,二娘自己用凿子刻了几个字:宝新之墓——娘永远的乖孩子。那个春天,一有空闲,二娘就去河边捡石头,又在河边挖了几棵柳树苗栽在周围,二娘对我妈说:杨柳依依……此树易荣滋,无根亦可活……
二娘一人在坟边砌石头时,小儿子来了,闷声帮娘砌。二娘颤着声说:老二,莫怪娘,娘虽没大管顾你,可你……娘想让你大哥啥也不缺的……儿子用泥手背擦擦眼:娘,别说了,俺都知道……后来,生了孩子的二儿媳妇,弄了好看的海蓬子花种,帮二娘种在那上墙里,新媳妇说:娘,这草花年年发芽、年年开呢,俺大哥也住上新时代的花园房子了。
二娘帮小儿子把孩子带大送进小学后,去大儿子坟上的时间就多了起来,渐渐地便神志不清了。她每天都要把坟头上的土摸索一遍,雨雪天甚至找块塑料纸蒙在上头,而自己却光着头淋在那里。工作繁忙的儿子、媳妇也无暇顾及她。可我妈说:你二娘虽痴呆了,嘴角却挂着恬静的笑呢,她心里,也许倒不苦了……
牵着活泼、调皮的儿子的小手走在秋日的田野间,远远地看着二娘孤独的背影,我感谢自己手中握着的是满满的安恬与幸福。也许,对女人来说,有人以追求两情相悦的爱情为幸福,有人以追求衣食奢华的财富为幸福,有人以追求心灵的高远、清透为幸福,但对有些已为人母的女人来说,也许拥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孩子,哪怕只是一个很平凡的普通孩子,就是一种最基本、最可贵的幸福吧。
请幸运的人们,珍视眼下那些平淡事物所蕴涵的看不见的、却弥足珍贵的幸福一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