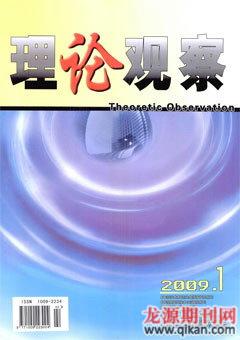当代中国政治的双重维度: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价值之探析
孙 庄
[摘要]一切社会在各种意义上都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中国帝国统治时期的政治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历史背景和内在逻辑,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不难找到传统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政府和政治的最直接的源头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革命过程中形成的政治设计和政治安排。所以只有把现实的中国政治放到传统文化与革命价值相互作用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考察,我们才能对当下的政治有更为真切地理解。
[关键词]中国政治;传统政治文化;革命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1—0032—02
“没有政治科学的历史无果;没有历史的政治科学无根。不探究过去,就不能准确地把握现在,更无法描绘未来的行动过程。”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文明是一个不断积累不断发展的过程。历史、现实、未来,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如集权制)、政治文化(官本位、父母官意识)、政治传统(人治传统)等均对当代中国的政府与政治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现实的政府与政治中均不难找到传统的痕迹和影子。所以只有面对未来,回溯历史,才能对现实的政治制度有更为真切地理解。
“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等于一只走兽蜕变而为飞禽。”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革过程中,中国的政治变迁最终选择了最彻底的变革方式——革命。这种致力于使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发生全面质变的革命思维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交织在一起的。在传统文化遗产与革命乌托邦理想的激烈交锋中,“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如果把传统中国的政治体系视为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系统,而把由革命时代创造的政治理念作为舶来品,两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由革命洪流造就的外来刺激与中国传统之间惊人的决裂和差异。
当代中国共产主义制度便是传统政治与革命主义相互作用的结晶。如何协调和保持二者之间的合理张力已成为当代中国政府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些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政治的本质。“它们是永久的和无法规避的,但是它们又允许不同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使人类得以在不同的取向之间进行选择和替换。”我们只有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在两者的相互关涉中寻找合适的平衡板和减震器,才能实现政治生活的良性均衡和稳定变革。
本文试图通过比较的方法展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革命价值之间的差异。以期借助对中国传统政治价值与革命思维的比较分析,获得对现实中国政治的准确理解。
1,政治权威中的精英主义和等级制——民众主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威构架基本上是精英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僚与平民之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泾渭分明的,并且按照人的身份差别区分官僚等级。其理论依据是,某些人由于自身良好的素质和品德并借助所受的教育而有权行使政治权力;那些德行有亏的人则理所当然的被安置在受统治的地位上。这在实践上便导致了精英和大众两个阶级构成的政体。与此相应的是全社会的权威等级结构,它构造了尊卑关系的复杂网络。这一权威结构与政治和经济的其他因素相结合,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分层体系。在移去了这种形式的政治等级制之后,支配亲缘关系和义务准则的高度复杂的社会关系结构便取而代之。这一体系把终极权力交给了宗法团体中辈分排列中最年长的男性,并将他下面的所有人置于一种等级制度中。它要求人们遵从比自己等级高的人,并指望来自比自己等级低的人的尊敬。但是,在“天演之公例”的革命者眼中,“大众参与是实现真正的社会和政治革命的唯一途径,组织起来的群众的支持将无往而不胜,精英统治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也会由于以少数人为基础而被削弱。”只有通过民众的民主经由伟大的革命才能转变为民众的专政。伟大的功业只可能来自巨大的磨难与牺牲,革命既包含着旧世界的毁灭又包含着新世界的诞生。民众主义将农民和儒家精英分离,将他们与政府隔离,并支持一种民众造反的长期传统。在劳苦大众受苦受难的万恶社会中,仇恨精英压迫的情绪与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新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与在农村根据地发动强烈导向大众动员和参与运动的战略结合在一起。我们所继承的最明显的遗产是权威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持续的紧张关系——在崇尚人人平等、共产主义价值观念的同时,它也保留了以前统治者的等级制度、精英价值,坚持对权威的无条件绝对服从。如何恰当处理精英主义和民众主义之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性问题。
2,和谐和秩序——动员与阶级斗争:传统的教化强调维护社会关系中的和谐,节制社会冲突的政治精髓,要求人民遵守秩序,保持安定,避免或压制对抗的表现。古老的中国不仅是一个农业官僚社会,而且也是一个家族制和根植于土地之上的社会。它以皇权统治作为规范秩序的道德核心,以儒家的三纲(忠、孝、节)作为社会秩序的原则。广泛的家庭系统是这个社会的基石,形成了妻子服从丈夫、青年服从老年、个人服从家庭、农民与兵士服从士大夫,整个社会服从皇权机构的社会秩序。而革命的核心价值观是斗争和动员。在革命时期,革命者坚信动员和斗争是革命的本质。因为它是一个受到威胁的少数人的运动,它受到敌对军事力量的包围,又处于一个不理解,不同情的社会环境包围中。军事型的道德准则——热情、英雄主义、牺牲和集体努力——具有很高的价值。最后到来的胜利是成功的政治动员的一个果实,这个动员是为了民族生存而在展开的战时斗争中形成的,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行政管理,而且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在革命价值观意识的引导下,社会渗透着阶级斗争,它们既是剥削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条件。要求公民积极而自愿的参加斗争,并公开向那些以自己的地位或行为来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发出挑战,坚持政治积极主义和斗争,就必须克服保持消极与保守的旧倾向。革命时代结束以后,官方强调的重点已不是对抗性的斗争,而是朝向现代化的积极主义。“安定团结”的口号代替了“敢于造反”的口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和奋斗目标。
3,“特定对象主义”——集体主义:在传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单位是亲缘单位,家庭或家族从一种忠于特定对象主义中得到明显的益处,这种忠诚感提倡排外和个人关系,而不是普遍和公共的关系,个人大多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对待效忠和责任问题,它创设了一种牺牲局外人利益、保护并有利于自己人的义务网络,忠于特定对象主义限制个人主义,同时也限制了更大团体的利益,它倾向于将小团体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私人团体的权威是实在性的权威,它们对个人的影响力是强大的,足以构成这一政治制度本身真正的竞争对手。甚至在革命时代“特定对象主义”还一
时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主流,如基于师生,同窗、同乡、婚姻、家庭等私人纽带的军事组织:军阀部队。在共产主义的伦理中,集体主义代替了忠于特定对象主义,以此作为忠诚和权威的决定因素。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无论在哪个级别上都高于团体内的构成分子:不管个人的联系和关系如何,忠诚的对象都是集体。这一原则要求献身于公共事业,自觉地克服将个人考虑置于集体之上的倾向。它坚持公共利益在所有生活领域都是最高权威,个人有义务维护和增进国家和公共利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仍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如何在不侵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更好地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换言之,对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如何协调处理个人权利和集体价值的关系已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必由之路。
4,“大中华中心主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链条上的一环:“在两千年中华帝国岁月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中,中国是世界闻名的中心和典范。”我国的古典文明、艺术和文字,以及社会价值系统,是其它国家公认的精神鼓舞及模仿对象。中国一词,就意味着中央之国,即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蛮夷文化总是被中国文化所吸收和制服的经历,使中国人断定中国文化一定真的优于其它文化。只是到了1895年以后,作为对甲午战败的一种反映,最终才放弃传统的华夏中心观念并且大规模的接受西方文化。“彼其所以变者,非好变也,时势为之也。”在接受共产主义世界革命观的革命者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预见的是一个既普遍又现代的社会,它将最终在全世界出现,并将建立在后工业化经济的基础上。这一学说就把革命斗争扩展到不仅包括中国,而且包括所有其它社会。中国人在接受了这一学说之后,便把他们的革命看成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认为阶级斗争的最终解决方式将涉及国际范围,而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它使现行的中国政治体制带上了一种与国际体制紧密相互联系的意义,这不是历史上的中国所具有的特征。后革命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在全球一体化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学会在不同的文明中分析、选择、借鉴、学习,使我国在世界各大文明的相互理解合作和和平交往中实现从革命时代向现代化社会的成功转型。
总之,一切社会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其过去历史的产物,现今的中国政治体制必然会带有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和革命主义的痕迹和烙印。在迈向多元治理民主社会的征程上,我们要建设具有民族性的现代国家政治体系就必须小心翼翼地对过去一缕缕的政治遗产进行折衷组合,只有这样才能有意识地创制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政治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