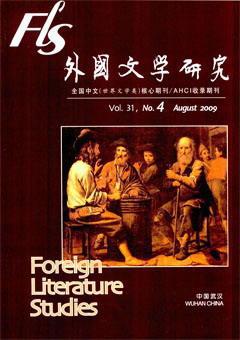现实的象征化与象征的现实化
张 杰
内容提要:在文艺学界,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通常被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法,然而,白银时代俄罗斯的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维·伊·伊凡诺夫却把两者有机地融合起来,提出了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本文以此为批评方法,深入剖析了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揭示该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的独特性,即“现实的象征化与象征的现实化”。这里现实的象征化是指酒神崇拜的现实反映,而象征的现实化则是由“合唱原则”来具体呈现的。论文最后指出,酒神崇拜的象征是相对稳定不变的深层宗教文化积淀,而“合唱原则”构成的现实则是极不稳定的表层社会现实生活,任何一部经典文学文本的现实性都会随着读者的阐释不断变化而逆向延伸。
关键词:维·伊·伊凡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
长期以来,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从批评方法来看,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往往被视为是迥然不同的两种方法,前者以作品反映的现实生活为依据,后者则更主要以主观的心灵感应及其表征为核心。然而,白银时代俄罗斯宗教文化批评理论家、诗人维亚切斯拉夫·伊凡诺维奇·伊凡诺夫则把它们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创立了一种独特的批评方法——“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该方法源于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探讨,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宗教底蕴发掘。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长篇小说——悲剧”(1914年)、“俄罗斯的面貌与面具: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体系研究”(1917年)等论文和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悲剧-神话-神秘论》(1932年)中,深入分析了《卡拉玛佐夫兄弟》、《群魔》和《罪与罚》等作品,充分论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的形式原则和“世界观原则”,归纳了它们作为悲剧小说的基本特征,力求梳理这些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以及人物与作者之间的思想联系,具体阐释了这些作品所蕴含的神话因素和宗教神秘论因素,表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
本文将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为具体实例,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努力阐明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批评的独特性,从而发掘该批评方法在文学文本分析中的特殊功用,同时也进一步开掘文学经典名著《卡拉玛佐夫兄弟》的可阐释空间,揭示其深刻内涵的复杂性,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一、现实的象征化:酒神崇拜
翻开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一幕幕19世纪俄罗斯社会的生动图景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以往的文学批评界在论及这部文学经典名著时,常常依据的批评理念是把文学看作为一种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评论界通常认为:“作家在小说中描写了卡拉玛佐夫家族成员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给周围的人带来的痛苦。这是农奴制改革后俄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反映出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和人们之间的畸形关系”(曹靖华505)。
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强调:“我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理解与我们的现实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完全不同。我的理想主义比他们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波格丹诺夫327)。在维·伊·伊凡诺夫看来,现实生活是由人们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层次的活动所构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反映的现实从表层上来看,无疑是19世纪后半期俄罗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但从深层次上来发掘,应该是人们长期以来的宗教文化活动在现今社会生活巾的积淀。这种积淀是源于“狄奥尼索斯(酒神)崇拜”与民间的狂欢活动。他坚信,狄奥尼索斯崇拜活动“始终贯穿于所有真正的宗教生活”(cm,TogMaqeB 14),甚至该活动先于人类语言的出现。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就是从宗教文化出发,把社会现实看作为是一种宗教文化活动在当今的象征化反映。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这种现实的象征化就是酒神崇拜的现实反映。
维·伊·伊凡诺夫的批评方法显然深受尼采的《悲剧的诞生》等论著思想的影响,但是在对酒神形象本身的认识上却迥异于这位德国学者。在尼采那里,狄奥尼索斯首先不足一种宗教和道德范畴内的现象,而是在此之外的一种心理现象和美学现象。可是,维·伊·伊凡诺夫则把它视为一种宗教范畴内的独特心理现象。酒神的癫狂状态其实是一种主体的泛化状态,主体与其他的“我”均不是客体,而成为另一群主体。酒神崇拜是一种精神宣泄,一种神圣的癫狂,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的认知方式。这种“精神普世运动”反映出文化的原始印迹,表明“超越个性”的个体群的经验的整体生成。众人在酒醉迷狂的情绪中彼此相遇,共同感知了上帝的存在。
在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处于“醉酒”的癫狂状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以主人公们对上帝的态度来区分和塑造人物形象的。父亲费多尔·巴甫洛维奇·卡拉玛佐夫是一个心中没有上帝的恶棍,因此他是一个丑恶畸形的灵魂。长子德米特里·卡拉玛佐夫是集“圣母玛丽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的人物,虽然他追求肉欲、生性粗暴残忍,但是他自己说道:“尽管我下贱卑劣……然而上帝啊,我到底是你的儿子”。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让德米特里在自我净化和自我完善中忏悔自己的罪过。次子伊凡·卡拉玛佐夫是个无神论者,他的叛逆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他为斯麦尔佳科夫弑父提供了思想依据,是思想上的凶手。伊凡的两个弟弟阿辽沙和斯麦尔佳科夫是两个性格迥然不同的人物,前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宗教理想人物的化身,后者则恰恰相反,是一个为了私利而背叛信仰的杀人恶魔。这一个个作为主体的人物精神宣泄、神圣的癫狂,从正反两个方面形成了一种“超越个性”的宗教文化氛围,创造了一种感知上帝的独特方式,反映了带有原始文化印记的“精神普世运动”。
在维·伊·伊凡诺夫那里,酒神崇拜应该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动,充满着欲望和自由。这显示出人对上帝的态度、人的创造欲或日创造冲动。狄奥尼索斯崇拜表征为“创造自由”的宗教隐喻,因此值得颂扬和赞美。这种自由既有环境的自由、氛围的宽松,各个主体间的绝对平等,同时也包含着每一主体精神的彻底放松和本性的真实袒露。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无论是恶魔还是圣徒,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均是积极的行动者,各自渴望着不同的自由,争取着平等的权利。这里既有儿子与父亲为女人的争斗,也有亲生儿子与私生子之间为权益的争斗,每个人的“为所欲为”其实都是对各自自由的追求。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把理想人物阿辽沙描绘得强大有力,相反展现出他的苍白无力,而父亲费多尔·卡拉玛佐夫和次子伊凡等也表现出性格强有力的一面。这便营造了酒神崇拜的“平等”、“宽松”、“自由”的话语语境。
在《卡拉玛佐夫兄弟》里,读者透过表层社会现实生活,能够感触到深层次的宗教文化象征,即狄奥尼索斯崇拜。这并非是一种神秘色彩浓重的宗教仪式,也不仅仅是表现为一场“精神普世运动”和创造自由的情感释放,而且更是一种独特的人类认知方式。读者可以从酒神崇拜的艺术表现过程中感受到,当时人们在接受“上帝的教诲”时是如何感知“真理”或
“真理”的各个侧面的。在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批评中,酒神形象实际上就是一种象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象征着一种思维的形式,一种综合了各种错综复杂矛盾因素的精神文化。
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表面上展示的是在19世纪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中各种灵魂畸形表现的现实生活图景,其实从深层次上发掘的是这一时期各种俄罗斯灵魂感知“上帝”的一幅宗教信仰图景,而这种图景体现了一种酒神崇拜的象征。
二、象征的现实化:合唱原则
维·伊·伊凡诺夫强调,艺术家的任何创作都不应是“天堂”与“尘世”的分离,象征主义艺术也不例外。他把象征视为以“尘世的、现实的”方式体现宗教思想的最佳途径。他在人类的文化史上寻找着自己的支持者,例如柏拉图、弗·索洛维约夫等以及俄国象征派诗人。维·伊·伊凡诺夫作为俄国象征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家,对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理论阐释是非常独特的。他不再像以勃留索夫为代表的俄国“老一代”象征派诗人那样,往往过于追求唯美主义,酷爱把心理体验投射到他们所否定的客观现实上,创造一种最为别出心裁的幻象世界。在他的“当代象征主义的两大本原”(1908年)、“象征主义的遗训”(1910年)和“关于象征主义的沉思”(1912年)等论著中,就鲜明地表现出俄国“年轻一代”象征派理论的“现实化”特征。
维·伊·伊凡诺夫所遵循的是歌德关于“象征”的认识,即象征的客观认识性。他从“现象”触及“本体”,把“事物”化为“神话”,从对象的实实在在的现实性触及它的内在隐蔽的现实性,从而揭示“存在的秘密”的现实意义。“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艺术激情在于:“运用象征认识每一现实,审视它们与最高的现实,也即现实之中更现实的现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维·伊·伊凡诺夫看来,象征的现实化是由“合唱原则”来加以实现的。“合唱原则”就是要求作者放弃自我浪漫主义的独自,应当适当地牺牲“自我”。为了“别人”,为了“聚和性”,作者就要把自我主体彻底融合在集体的“巨大的主体”之中。“聚和性”意味着一种爱,意味着“自我主体”在作为绝对现实性的“你”或“别人主体”之中的本性恢复。“聚和性是一种独特的结合,即结合于其中的所有个性都可以充分敞开,取得自我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别具一格的本质规定,取得自我完整俱在的创作自由的定位,这种自由使每一个性都成为一种说出来的、崭新的、对于所有人均需要的话语”。
如果细致分析长篇小说《卡拉玛佐夫兄弟》的艺术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合唱原则”是作家结构该部小说的主要艺术手段。小说的主要部分均是由一个个人物群体的“合唱”而组成的,尽管每个场合参与的人物众多,但是时间大都短暂。在小说作为引子的第l卷后,第2卷就展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集体“合唱”场景——佐西马长老修道室中的“不适当聚会”。这里集中了小说几乎全部的主要人物,读者可以在这个“合唱”中看到不同心灵交织的“乐章”,折射出社会现实的图景。第3卷则让读者更贴近每一个人物,在同一空间上感知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在第4卷里,作者继续分解了前面展开的各条情节线索,增添了不少插曲,使得费多尔·卡拉玛佐夫与他的儿子们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第5卷和第6卷在小说整体结构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作者把两个相互对立的人物伊凡与佐西马放置在了一起,构成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道德观、宗教观的相互碰撞,形成了复调的“合唱”。第7卷通过阿辽沙与格鲁申卡的对话,更是把现实主义的场景与宗教的、民间口头创作的象征融合了起来。第8章、第9章描绘了米佳和格鲁申卡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内心发生的激烈冲突与重大转折,直接由人物道德观念的重要变化反思了一些社会现实问题。第10卷一般被视为是作者有意识让读者放松的章节,为更好地阅读最后两卷做准备。小说第11又是由一系列零星的插曲组成,读者随着阿辽沙一起对格鲁申卡等人走访,表现了主人公们在老卡拉玛佐夫被杀到米佳被审判前的复杂心态的“合唱”乐谱。最后一卷更是借助审判这一场景,由复述检察官和律师的演说,与当时的司法制度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话语语境。
显然,从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出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象征的现实化是通过主人公的场景对话以及人物在他人意识中的活动等“合唱原则”来实现的。相对于“独自”的作品来说,“合唱原则”构成的艺术作I铺才具有不断的可阐释性,艺术作品的现实性才能够不停地延伸,才具有可持续性。维·伊·伊凡诺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象征艺术(狄奥尼索斯崇拜)、“合唱原则”等探讨,后来对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思想形成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象征与现实之间:文本现实性的逆向延伸
维·伊·伊凡诺夫的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批评的理论基石是古希腊文化与宗教的探究,这也是他用以考察一切人类文化与文学现象的出发点和主要参照。在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时,维·伊·伊凡诺夫不仅深入揭示了文本的现实性和象征性,而且还用实证的方法从源头上考察了酒神崇拜和希腊民间的狂欢活动。他甚至更正了考古学的传统观点,指出,酒神崇拜不是起源于居住在巴尔干半岛东部的色雷斯人,而是起源于希腊某些荒僻地区和岛屿的土著居民。
当然,作为象征主义的大师,维·伊·伊凡诺夫明确写道,“一切伟大的艺术成就都是以宗教为基础的,并且肩负着驱恶扬善的使命”。他认为,古希腊艺术与酒神崇拜等都体现了一般艺术与文化活动的本来真实涵义,“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就是要让整个现代艺术都应复归其本真意义,复归到其宗教根基上去。因此,他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文献辨析和一般考据上,而是采用“移情原则”,联系宗教心理与文化哲学背景进行考察,通过宗教的神秘体验来完成的,从而更为深入地阐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
在维·伊·伊凡诺夫看来,艺术的真实是“现实”与“象征”、“客观”与“主观”、“情感”与“宗教”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经典的文学文本才具有无限大的可阐释空间,读者才会有“说不尽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确实为维·伊·伊凡诺夫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批评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就反复强调:“我对现实(艺术中的)有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且被大多数人称之为几乎是荒诞的和特殊的事物,对于我来说,有时构成了现实的本质。事物的平凡性和对它的陈腐看法,依我看来,还不能算现实主义”(波格丹诺夫328-329)。
可以说,任何一部经典文学文本的现实性都具有两重性:小说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今天读者阐释作品的现实性。前者的现实性是非常有限的,仅限于小说反映的当时社会现实,对于《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说,就是19世纪农奴制改革后的俄罗斯社会现实。相反,读者阐释作品的现实性则足相对无限的,会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而逆向延伸。具体说来,不同时代的读者或者同一时代的读者,由于自身话语语境的迥异,对文学文本的现实性
认识是不一样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着的,而且越是经典的文学文本,其现实性的逆向发展变化就越大。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苏联文学批评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实性评价,可以以1956年为分界线,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除陀思妥耶犬斯基的几部早期作品以外,其创作中的现实性基本上是遭到否定的,其中包括《卡拉马佐夫兄弟》,而被肯定的是他的艺术表现成就。高尔基就曾称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恶毒的天才”(178)。所谓“恶毒”是就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创作的现实性而言的,所谓“天才”是指作家的艺术天才。因此那时很少有人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成是现实主义的大作家,而常常把他视为颓废主义作家。后一阶段是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75周年开始。当时,苏联文艺学界又重新展开了一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的大讨论,各主要报刊杂志几乎都发表了纪念文章。大家又都异口同声地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尊为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可以与托尔斯泰并驾齐驱。有人甚至把作家创作内容的复杂的矛盾性也看作是现实的真实反映。《真理报》就指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渗透着俄罗斯现实主义的传统的人道主义思想。
很显然,无论是前一阶段,还是后一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文本都是一样,但评论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一个颓废主义作家变成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这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现实性认识,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对作品的新理解而追加上去的吗?难道不是一种逆向发展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许还会不断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新现实性。
从共时的角度来比较,在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注重其创作与现实主义联系的批评者,往往把他本来纷繁复杂的艺术创作归入现实主义艺术的行列,称他是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大师。侧重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艺术关系的批评者,又坚持把他的创作纳人现代主义艺术的创作模式,以现代主义的批评眼光来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并把他当作现代主义艺术的开拓者。批评者们都试图从复杂的创作现象中理出一条由因果关系串联起来的纵向线索,并以此来阐明自己的结论。前者竭力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新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后者则要证明陀思妥耶夫斯的创作之所以是一种创新,就在于它摆脱了现实主义的羁绊转向了现代主义艺术。
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研究中,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批评界对这种现实性认识的逆向延伸。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其创作文本不可能再有任何改动,但是研究者的评价却在不断地变化着。与此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的现实性还在永远地延伸着。也许只要存在着文学批评,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还有认识价值,这种延伸就不可能停止。
这里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酒神崇拜的象征是相对稳定不变的深层宗教文化涵义,而“合唱原则”构成的现实则是极不稳定的表层社会现实生活。前者具有一定的超越性,无论后人怎样重新认识,都极少变化,而后者则由于局限于现实情感、认识水平和意识形态环境等因素,被后人不断重新阐释。因此,在“象征”与“现实”交织的艺术创作中,文本的现实性在逆向延伸着,而人类文明长期积淀而成的宗教文化象征却很难撼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