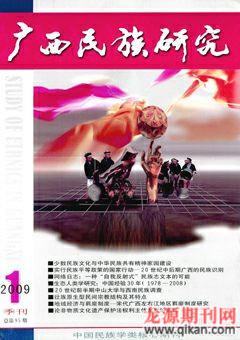宋自杞国索隐
【摘 要】自杞国是南宋时代西南的一个藩国,因贩马而强盛兴起来。本文资诸载籍,论述其的兴起、繁荣、消失以及与南宋的关系,并论述其国的主体族群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群体。
【关键词】自札国;南宋
【作 者】白耀天,广西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南宁,530021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10-009
Research on Ziqi state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Bai Yaotian
Abstract:Ziqi state is an attached state of southwest China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became strong through trading horses. This thesis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rise,Prosperity and disappearance of Ziqi state.
Key words:Ziqi state;Southern Song Dynasty
南宋时期,自杞国因与南宋政权买卖马匹,历史上曾活跃一时。可其来龙去脉,似亦隐晦不明。自杞国初在今贵州省境,其主体国人属于哪一族群,自来研究者关注不多,而论者多概而论之,所论似又与事实相距甚远。现略以论述,冀补阙遗。
一、自杞国凸显于历史舞台
《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之九三~九四》载宋徽宗政和三年(3年)三月二十九日“武经大夫新差权发遣广南西路都监权发遣宾州黄远奏状”:
自陛下登宝位以来,尤着意于南方,而夜郎、髦民一旦尽归王化,俾远人皆有蚁慕之心,故邕州管下右江化外之人咸欲款塞(纳款)归明,愿为王民焉……伏望朝廷早赐差,元(愿)陈献自杞等州。(令)邕州进士黄光日文并上隆州(治今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燕峒)黄辶尧等前来引接臣并管下首领前去赴广西经略司听便指挥。
宋徽宗览毕黄远的奏状,“诏令王觉与黄辶尧同共措置”,说明物落有声,黄远的请求得到了合情的处置。他管下的自杞州也成了宋朝的羁縻州之一。这是“自杞”一名首见于史籍记载。
靖康之变,北宋亡南宋立。建炎初(1127年),尚书户部郎中叶宗谔推荐“智谋深远、材术优良、备知峒丁情伪”而时为朝请郎广西经略司干办公事的邕管羁縻安平州(治今广西大新雷平镇)僚人李蒶出任广西左右两江提举峒丁公事。[1]李蒶上任后,奏议购买大理战马以解时急。宋高宗答应了,并命令他在邕州置“牧养务”,筹措买马事宜。[2]李蒶于是招募谙业人员,派遣他们带着盐、纟采经特磨道进入大理国招诱大理人带着马匹前来横山寨博易。然而,李蒶毕竟是僚人,“族既不同,其心必异”。他的主张,他的行为,即招来了宋朝官员们的忌妒、恐慌。绍兴四年(1134年)二月二十五日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奏说:“前广西提举买马李蒶差效用韦玉等十二人,厚斋盐、纟采入外国计置买马,虽一时逐急措置,然于边防未见其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必引慝边隙。”[3]明橐的话,代表了这些人的见解、理念以及朝廷的担忧。
建炎四年(1130年),南宋王朝藉李蒶与广西经略使许中意见不合将他免了。[4]李蒶官可免,战马却不能不买,诚如宋翰林学士朱震说的:“今日干戈未息,战马为急。桂林招买,势不可辍。”[5]因此,绍兴三年(1133年)正月二十六日,宋高宗“诏邕州置买马司”,收买产于大理国的合格战马。除了“招买特磨道等蕃马”外,买马司官又“差招马官前去罗殿国等处蕃蛮,别行招诱赴官收买”。[6]此一记载,道出了“自杞”仍然是默默无闻,不详此时“自杞”是否挣脱了黄远的辖属蕃篱?
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六月二十四日,知静江府方滋说:“广西买发纲马,多是西南诸蕃罗殿、自杞诸国蛮将马前来邕州横山寨,两平等量议定价值,从蛮所愿,或用纟采、帛,或用银、盐等物依彼处市价博易。”[7]从而,揭示了此时“自杞”在与南宋的马匹博易中已经可以与罗殿国等列齐观,不相上下了。这就是说,南宋在邕州设置买马司专买大理国产战马近三十年后,自杞方才摆脱羁绊,逐渐强大起来,以国称名,在诸蕃从大理国贩马来与南宋的博易中占有一定的份额。
自杞人“尤凶狡嗜利”,[8]既“皆长大勇健,凶悍善骑射,轻生好斗”,[9]又特会经商做生意。因此,他们以勇武开路,有利必钻,有利必求,以得利为满足。他们经商,是不失机会,不择手段,千方百计以营利为目的。淳熙四年(1177年)周去非《岭外代答》卷5《宜州买马》载: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10]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
罗殿甚迩(近)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宜人峻拒不去,帅司(广西经略司)为之量买三纲,[11]与之约曰:“以后不许此来!”
博马利大,罗殿国早就经营此项买卖,因此处处给刚上道的自杞人设卡为难,自然发生纷争。而南宋政权“政不欲近”,为巩固自己的边防,避开连近内地的宜州而定点于羁縻田州境内距邕州有七程的横山寨开设马市。[12]自杞人利近而行,不知南宋人的忌讳,可见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时他们走上贩马之路并没有多长时间。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记载淳熙三年(1176年)他斥自杞首领必程时说:“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国以此致富”。[13]此三十余年,是个约数,从淳熙三年(1176年)往上数,也就是绍兴十六年(1146年)左右。也就是说,自杞从绍兴十六年(1146年)左右开如涉足于贩马事宜,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不过十多年时间,而且多为罗殿国梗阻,规模不可能太大。
虽然绍兴(1131~1162年)中后期自杞人始行走上从大理国贩来马匹与南宋政权博易的道路,但是如同范成大指出的他们“尤凶狡嗜利”,具有商人的品格气质,扬长避短,变不利为有利,另僻蹊径进入邕州横山寨博马场,其路程尤近于罗殿国进入横山寨的路途八十程,[14]在博马中赢得了地利,赢得了先机。所以,乾道(1165~1173年)以后,自杞“岁有数千人至横山互市”。“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多至一千五百余匹”,占每年横山寨博易马匹总额的四分之三,垄断了横山寨的战马博易市场。[15]
自杞国在垄断横山寨战马博易市场的同时,国王阿谢的叔父阿已摄政有方,“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16]
阿谢、阿已,是见到记载的自杞国早期的王室成员。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
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允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余岁,阿已摄国事。自罗殿致书生,教之华言,教之字画。书诒田州黄谐,候问寒温之式,与中国不异。阿已摄事十七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17]
可是,范成大的《桂海虞虞衡志》却载道:
今其国王曰阿已,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多附之,至有精兵万骑。阿已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已犹举国听之。[18]
吴儆和范成大都是南宋淳熙(1174~1189年)初年或其后官于广西的南宋官员,但范成大为广西帅守,吴儆只是个邕州别驾。淳熙四年(1177年)春吴儆曾“被旨出塞市马”,直面自杞人,且曾庭斥自杞使者必程,其言或者较为可信。范成大作为广西经略安抚使,则是听人报告,视人书信,述说者或范氏自己无形中将阿谢、阿已二人谁王谁摄政、谁侄谁叔弄混了。
君臣一心,外财源源,淳熙(1174~1168年)前期,自杞“国益富,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僚至羁縻州洞境上”,成为“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之国”。[19]
自杞国富裕了,强大了,不仅侵占周邻,侵夺大理国盐池,压制罗殿国人,拦绝特磨道的马路,横刀砍杀南宋官兵;而且“请以乾贞为年号”,妄图脱离与南宋的藩属关系。邕州别驾吴儆在斥责其无知,犯了宋仁宗赵祯“庙讳”的同时,[20],对其使者必程威胁道:
汝国本一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余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余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卖马之路。[21]
自杞以商立国,以商致富,以商强大,而商业又是以与南宋博易马匹为主项目,绝断了该国的“卖马之路”,无异是扼住了其咽喉,令其国人生财无道,人穷财尽,国衰家败。所以,其使者必程不得不唯唯而退,放弃其不安分的痴想。
宝淘年(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蒙古兵二次从川西攻入云南,大理国灭。位于今滇、黔二省交界地区的自杞国自然成为蒙古兵东进广西必取之地。宝塘年(1258年)八月,蒙古兵因大理饥荒,军粮不足,“欲出交趾,自杞等处讨粮”。[22]此后,自杞国城即为蒙古兵所占领。为了充实粮草、便于运兵和后方安全,在云南的蒙古兵于进攻南宋的广西之前,既“在自杞管下莫贾墟造方仓一百七十八座”,修建“一丈有余”的大道直逼都泥江,又“兴兵打罗殿了”。[23]
罗殿国降了蒙古人,自杞人虽然国破却没有降服于蒙古人。据南宋前线统帅李曾伯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三日奏报称:“据谢济横山来报……及缴到自杞国王舟阝句并岑邈公状。此则不过欲坚来春市马之约。臣亦已许而报之。”[24]岑邈公为广西七源州(在今凌云县)壮族岑氏首领,曾为南宋刺探蒙古军情。舟阝句则为自杞国最后一个国王。过去范成大说自杞国有“精骑万计”,而吴儆则说自杞是“地广大,可敌广西一路胜兵十余万之国”,又经过了80多年的持续发展,不详其实力究竟如何,但以骑兵作为实力的自杞人在蒙古强兵压迫之下国破了,迂回辗转,仍然保有实力,仍然对南宋政权存着希望,冀想着通过市马重振国威,所以危难之际仍不忘于市马,不忘于坚定南宋政权“来春市马之约”。为了使南宋政权持续下去,他们尽其职责,随时向南宋报知云南蒙古军动向的信息。比如,李曾伯于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二十一日的《奏边事已动》即说,开庆元年七月十二日宋方谍探蒋方“申:初四日得自杞蛮主传来报,敌兵在今月初九日缚牌渡都泥江”,即是如此。
广西前线南宋军统帅李曾伯奏说:“敌兵犯广右(广西)已十旬。……近日两战,非不甚伟,然敌势猖獗终不能遏。其所入据俘获内,亦有罗殿鬼国诸蛮在焉。”[25]不仅 “罗殿鬼国”人参与蒙古人进攻广西,“爨簿”也参与其中。今湖南桑植县九万余白族人就是当年跟随兀良合台进攻南宋而流落于该地的“爨簿”的后裔。[26]但是,自杞人国破,没有降服于蒙古人。他们万骑飘忽,不详又落迹于哪里了?
二、自杞国疆域说略
周去非《岭外代答》卷9《蛮马》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罗殿、自杞、特磨岁以马来,皆贩之大理也。”由此或可以知道,大理国(治今云南大理市)产马,却没路径通南宋横山寨,因此由着罗殿、自杞二国及特磨道居中享受着贩马带来的厚利。
特磨道治今云南广南县,辖有今云南广南县、富宁县及今广西西林、隆林等地。有论者认为“今广西西部隆林、西林等地当已在其(指自杞国)囊中”,[27]似失偏颇。《元史》卷8《世祖纪五》载: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二月乙酉]宋福州团练使知特磨道事农士贵率知那寡州农天或、知阿吉州农昌成、知上林州农道贤,州县三十有七、户十万诣云南行中书省请降。
宋末元初的上林州,其地包有今广西田林县潞城以西的西林、隆林二县之地。入元以后,此一方域分立上林、安隆二寨。[28]
显然,自杞不能跨都泥江而过将今广西西林、隆林等地置于自己囊中,这是应当明确的。
特磨道与自杞,本无领土交连。建炎三年(1129年)提举左右江洞丁公事李蒶派人取道特磨道去大理国招诱战马来横山寨博易,径去径来,没有受到什么阻拦。所以,绍兴六年(1136年)五月,“富州侬内州侬郎宏报:大理国有马一千余匹,随马六千余人,象三头,见在侬内州,欲进发前来”。[29]同年六月四日,广西经略司也奏说:“招马效用谭昂去大理招马,经及八年,至去年九月内,满甘国王差摩诃菩俄托桑一行人斋机密文字与大理国王具章表匣,内差王与臣、杨贤明等官押象一头、马五百匹随昂前来,见在侬内佐部州驻扎,令昂先次斋牒申报。”[30]
绍兴八年(1138年)八月,为了扩大马匹来源,选取优良马匹,邕州提举买马司除循“旧法,于本路邕州横山寨招买特磨道等番马”外,又“差招马官前去罗殿等处蕃蛮,别行招诱赴官收买”。[31]大理国战马来到邕州横山寨博易,居中经手者多元化,激发了自杞人的“嗜利”。[32]后来,自杞国因博马发了大财,国富兵强,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特磨道在自杞之南,伏波铜柱之北,比年(连年)为自杞所梗,马不复至。”说明乾道(1165~1173年)末淳熙(1174~1189年)初,特磨道径通大理国的马道已经被自杞国断绝了。据《岭外代答》卷3《通道外夷》载,“特磨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墟,一程至最宁府(治今云南开远市),六程而至大理国矣”。特磨道马路被断,道出了此一时期自杞国的势力范围已经南下越过大理国的最宁府,进入今老挝,进入今柬埔寨。这也就是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所记载的自杞国鼎盛时疆域“西至海,亦与占城(在今越南南部)为邻”。
罗殿国见于史较早。《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载:“开成元年(836年),鬼主阿文谑簟;岵中(841~846年)封其别帅为罗殿王,世袭爵。其后,又封其别帅为滇王,皆髀也。”“鬼主”,就是世俗和精神信仰的领袖,这就是《新唐书》同传所说的“夷人尚鬼,谓主祭者为鬼主”。奉首领为“鬼主”,是彝族先人的习俗。所以,不论是“鬼主阿巍保还是“别帅罗殿王”或又一“别帅滇王”,都是今彝族的先人。
唐灭进入五代,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八月乙酉,“昆明大鬼主罗殿王、普露静王九部落各差使随髑逯莅酥荽淌匪纬化等一百五十三人来朝、贡方物”。[33]至北宋宣和六年(6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宋徽宗诏:“罗殿国王罗唯礼等入贡,并依五姓蕃例。”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四月二十七日,知静江府(治今广西桂林市)吕愿忠言:“罗殿国王罗部贡及西南蕃知矩州(治今贵阳市)忠燕节度使赵以盛入贡,进贡土产、名马、方物。”[34]
这些记载,揭示了罗殿国是彝族先人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鬼主”强大起来以后所建立的一个国家;揭示了罗殿国存国的绵远,自唐历五代、北宋、南宋,一直屹立于我国西南地区,与历代中央王朝保持着往来,保持着臣贡关系。
罗殿国是仅次于特磨道的第二个与南宋发生大宗战马交易的西南国家。但是,自从自杞国崛起之后,其在邕州横山寨的战马交易量日见减少。在乾道末淳熙初,“每岁横山市马二千余匹,自杞多至一千五百余匹”,[35]罗殿国在横山寨博马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就日见其少了。由于罗殿不是以贸易立国,交易份额的减少,并不影响该国的存在。不过,罗殿国在南宋后期毕竟不能存续下去了,这是因为蒙古兵进入云南灭掉了大理国,也东进灭掉了罗殿国。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9《奏边事及催调军马》载,开庆元年(1259年),“及敌人(指蒙古兵)攻打罗殿国,其国已拜降”。《可斋杂稿续稿后》卷9《奏边事已动》也载,“敌兵犯广右(广西)已十旬……近日两战非不甚伟,然敌势猖獗终不能遏。其所入据俘获内,亦有罗氏鬼国诸蛮在焉。”这似乎也在说明“拜降”于蒙古兵后的罗殿国人或者已经与蒙古军队一道攻打南宋了。
元无名氏《招捕总录·八番顺元》载:“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殿国主罗阿察、河中府方番主韦昌盛皆纳土来降。”《元史》卷61《地理志》载普定路,“今云南省言:罗甸即普里也,归附后改普定府,印信俱存。”元朝普定路,治今贵州安顺市,说明此前的罗殿国是以今贵州省安顺市为中心立国的。如此,则罗殿国的所在恰恰吻符于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指出的“罗在宜、融之西,邕之西北”这样的地望。[36]
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罗殿国“西与大理、自杞,东与黔南为邻”。大理国辖下的“于矢部”(今贵州省普安、盘县)东与罗殿国相接,罗殿国的西南部则与自杞国相邻。
《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之九三~九四》载,政和三年(3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远奏称率“邕州管下右江化外之人”归附宋朝,“元(愿)陈献自杞等州”,并引特磨道富州为例,要求宋徽宗“给赐官班、衣袄、印记”与其属下州洞首领,说明自杞是在黄远管内,即属“邕州管下右江化外之地”。其地当在那时西南番以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境内。
李曾伯《可斋杂稿续稿后》卷7《贴黄》载:“臣近得邕州报,溪洞路城州(治今广西田林县潞城)申:敌修路至都泥江。按地图,此江自大理、自杞、罗殿而出。未知所修路至某处。”这说明南宋后期西南三国都与都泥江连上了关系。究竟此三国各与都泥江哪一流段有关系?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邕州别驾吴儆“被旨出塞市马”。虽然他没亲历其国,却“目所亲睹”其人,并“分遣谍者图其道里远近、山川险易”。据他的《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所载,从横山寨去罗殿、自杞三国,到了泗城州(在今广西凌云县北、乐业县南),“稍折而东,历上、中、下思画州山僚境,渡都泥江,沿江而北,历幕州及诸山僚至顺唐府”,即可到达罗殿国。既然从泗城州要“稍折而东”,渡都泥江后又“沿江而北”,北去罗殿国所沿的“江”,不外是今北盘江。
显然,都泥江的主支流之一今北盘江流于罗殿国之境,而都泥江的另一主支流今南盘江则与大理、自杞二国连上了关系。
南盘江源于今云南省沾益。沾益,是大理国石城郡治所。南盘江向南绕至今云南开远市(大理国最宁府治所)折向东北流至今黔、桂边界与北盘江汇合形成红水河,即南宋时的都泥江。如此,则今南盘江的中上游在大理国境内,下游则为自杞国所在地。
《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去自杞国“自泗城州稍北出古宜县、古那县、龙塘山、安龙县、安龙州,渡都泥江,斗折而西,历上、中、下展州山僚、罗福州、雷闻岭、罗扶州至毗那自杞国”。“渡都泥江(今南盘江),斗折而西”,“历上、中、下展州山僚、罗福州、雷闻岭、罗扶州”始到自杞国,则自杞国城当在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西端的兴义县,因为再往西则为大理国属的“东爨乌蛮弥鹿等部所居”。[37]自杞国城在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县,也吻符于自杞国在南盘江下游贵州省境的地望。
方国瑜先生从途程情况考究,认为南宋横山寨达自杞国到大理国善阐府(今云南昆明市)的通道,与明朝刘文征天启《滇志》卷4《旅途志》所载的“由云南府四程至师宗州,四程至黄草霸,三程至安龙所,二程过河,又七程至田州”的交通线路相同,“两相对照”,从而得出“黄草霸(今兴义县)为古之自杞城”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方先生认为“安龙以东之贞丰、册亨,原属泗城州,清雍正年间始划归贵州,故渡河后四程始至自杞国界”,显然忘了时限。泗城州地跨过红水河,占有今贵州境内的罗甸、望漠、册亨、安龙等沿河地区,是明代时事,南宋时候泗城州何曾占有了这些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元一统志》虽已佚失,可是《永乐大典》卷8506宁字引有该书关于南宁府距罗殿国、距大理国、距自杞国程途略况的记载。方先生没有查对原引,却以赵万里所辑的《元一统志》为准,以致将南宁府“西北到罗殿蛮国一千七百三十里”讹成了“西北到罗殿蛮国一千三百八十里”,白费气力地进行力辩。[38]
北宋末,自杞州治今贵州省兴义县,南宋时自杞国城仍在今贵州省兴义县。但是,犹如自杞由州升国,其势力因博马而大发展,所以乾道末淳熙初既能够打压罗殿国,又能够将势力伸展南下强力阻断特磨道的买马路,垄断横山寨博马市场的交易,其国疆城已非昔日可比。因此,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自杞国在垄断横山寨博马市场以后,“国益富,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僚至羁縻州洞境上”,并将势力伸展南下,越过大理国的最宁府(治今云南开远市),使疆域“西至海,亦与占城(在今越南南部)为邻”。
自杞国人善于贩马牟利,也谙于骑马、纵捉马匹。范成大说,自杞人“胸至腰骈(并列)束麻索,以便乘马。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致有精骑万计”。[39]由于自杞国立足于建立“精骑”上,飘忽无挡,所以该国的疆域能够呈狭长形状,从贵州的兴义而西至海与占城为邻;能够在国城被蒙古人占领之后仍保有实力,不断地给南宋政权通报蒙古人的动态。他们纵骑由疆,最后也没有降于蒙古人,惟不详其由此而落迹于何处?
刘文征天启《滇志》卷4《旅途志》载:黄草霸(今贵州兴义县),“地实黔壤,昔普安陷于贼,州民群聚于此,庐焉”。是否是自杞人已经远离故土而去,城也空空,地也空空,因此普安州(治今贵州省盘县)的居民逃难时能够聚于黄草霸(今贵州兴义县)落户安居?
三、形体特征、风俗习惯,显示自杞人异于彝族先人
南宋绍兴中后期,因邕州横山寨买马,自杞始浮出历史层面。该国原初不大,人口也不多,却碰上了南宋与大理国进行马匹交易此一机遇,自大理国贩来马匹到横山寨与宋朝交易,居间获了厚利,由州升国,并成了富强之国。南宋淳熙间人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余匹,自杞多至一千五百余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雄于诸蛮。近岁稍稍侵夺大理盐池,及臣属化外诸蛮僚至羁縻州洞境上。”
乾道八年至淳熙元年(1172~1174年)官居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以官职所及,于其《桂海虞衡志》中记载了自杞国人的形体、性气特征和风俗习惯:
自杞本小蛮,尤凶狡嗜利。其卖马于横山,少拂意即拔刀向人,亦尝为所杀伤,邕管亦杀数蛮以相当,事乃已。
今其国主曰阿已,生三岁而立。其臣阿谢柄国,善抚其众,诸蛮多比附之,至有精骑万计。阿已年十七,阿谢乃归国政,阿已犹举国以听之。
诸蛮之至邕管卖马者,风声气习,大抵略同。
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腰弩箭諹,腋下佩皮箧,胸至腰骈足麻索,以便乘马。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刀长三尺,甚利。出自大理者尤奇。
性好洁。数人共饭,一盘中植一匕,置杯水其旁。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钞饭一哺许,搏之拌令圆净,始加之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每饭极少,饮酒亦只一杯,数咽始能尽,盖腰腹束于绳故也。食盐、矾、胡椒,不食彘肉。食已必刷齿,故常皓然。甚恶秽气,野次有秽,必坎而覆之。邕人每以此制其忿戾,投以秽器,辄跃马惊走。[41]
文中点明了自杞人的形貌特征是“深目长身”、“黑面白牙”。“长身”自是个子高;“深目”,就是眼框深凹。这似乎不是蒙古吉利亚人种的形貌特征。衬以“黑面白牙”,他们近乎是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阿拉伯人。“腋下佩皮箧”(qié,小箱子),似乎是古代阿拉伯人男子惯行的习俗。“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是游牧民族的长技,一般的农业民族或狩猪民族没有这样的高超技艺。以绳索在奔驰的马群中套取马匹,这也是阿拉伯人的习惯行为。
盐是食物调味品,世界上各人类群体都在使用,不足为奇,但在中国人的视角里,白矾或是媒染剂,或是净水剂,或是药物,并不是食物的调料。胡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是烹煮食物的调味品,但古代产于亚洲热带地方,在中国南方没有移植之前,它是昂贵的调味品,一般人家是不用或不常用的。自杞人“食盐、矾、胡椒”,道出他们不同于中国人的食物嗜好。“不食彘(zhì,猪)肉”,这是信教使然。佛教以不杀生为教徒“五戒”之一,倡导定时或不定时的禁忌荤腥,吃斋食素。“不食猪肉”的定性语,说明除了猪肉之外,自杞人还吃其它动物如鸡如羊如牛等类动物。很明显,他们信奉的是伊斯兰教,是西亚伊斯兰教的教徒。当时的占城(今越南南方)和以南的马来人有许多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
不用箸而用“匕”即汤匙之类的小勺子吃饭,不同于中国人传统使用的吃食工具。数人共饭仅用一匕,吃时搏饭捏圆置于匕上抛而入口,不让匕接触嘴唇,虽然强调他们讲究洁净,却也相异于中国人传统的吃食方式。
“食已必刷齿”,在古代,即使中国的皇家贵族也没有走到此一步。虽然元代郭钰《静思集》中的《郭恒惠牙刷得雪字》诗有“南州牙刷寄来日,去腻涤烦一金直”的句子,“牙刷”已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专有名词,然而“牙刷”被誉为可值“一金”,可知那个时候其极为难得,极为可贵,是自海外传入来的。明代,朝鲜人崔溥历游中国南北,其《漂海录》卷3载:
江南好冶容,男女皆带以镜奁、篦梳、刷牙等物。江北亦然,但不见带之者。[42]
“所谓‘刷牙,在明代又称‘刷牙舚子,简称‘牙子,其实就是‘牙刷。这是明人用来洁净、保护牙齿的一种工具。有些刷牙舚子,甚至还灌了香。所谓‘舚,俗称‘舚子,原本是一种用来刷头发使之光滑的毛刷。‘刷牙舚子就是从舚子变化而来,只是功能发生了改变,成为一种刷牙的工具”。[43]这说明,“牙刷”在中国作为社会人群的习常用品、习常用语,每天刷牙成为社会上某些阶层人们的习惯行为,始于元代,不过,“牙刷”一名迄于明代还没见定称。
牙是齿,齿是牙,本为一物,而且牙位于齿前,可是宋元及其前的人却以齿代牙,像马齿徒长、齐齿并列、令人不齿、教人齿冷、唇亡齿寒、齿亡舌存、齿剑膏镬、腐肉之齿利剑等。虽然“牙后慧”一词见于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但“牙后慧”成为“拾人牙慧”成语,却是在明朝以后。比如,南宋严羽《沧浪诗话·答吴景先书》说:“仆之诗辨,……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又如,明朝胡震亨《唐音癸签》32《集录》3载:“刘贡父滑稽渠率,王直方拾人唾涕。”清朝江藩《汉学师承记·江永》也说:“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这样一来,“拾人涕唾”、“拾人唾涕”、“拾人余唾”三成语就与“拾人牙慧”一个意思,即蹈袭人家的言论和认知,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可以说,“拾人牙慧”此一成语形成于后而后来者居上,在人们的言说和文章里基本取代了前三者。
明及明以前,汉文汉语涉于“牙齿”,多以“齿”代“牙”,无怪乎南宋时作为广南西路帅守的范成大谈到自杞人习俗时也不能免俗,说他们“食已必刷齿”。宋代,有着“食已必刷齿”此一追求洁净的习惯性行为的自杞人,显然不是传统的中国人,而是海外入居的外域人。
自杞人突出的性气特征是“尤凶狡嗜利”以及“少拂意,即拔刀向人”的粗暴横霸性格。“狡”是“狡诈奸滑”;“嗜”是“嗜好”。“尤凶狡嗜利”如同“逐什一之利”、“利市三倍”等,是历史上中国形容特会做生意、特会贸易经营的人的用语;是在西南诸国与宋的马匹交易中,“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匹,自杞多至一千五百匹,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44]的概括和脚注。“嗜好与俗殊酸咸”。[45]自杞人的“尤凶狡嗜利”,道出了他们在中国在周围各人类群体中的特殊性。此在当时居于中国西南的各土著群体中是不能比拟的。显然,自杞人是自海外的别的群体而来的。因为在他们立足之地的今贵州省兴义那地方,深居内地,丛山阻隔,既非贸易必通之道,在古代也没有什么热手的物资可作受欢迎的商品通流各地,从而形成他们那异于周围各土著群体的“尤凶狡嗜利”的性气特征。
由于自杞国人是北宋后期自海外入居于今贵州兴义的群体,不知不熟习汉语汉文。因此,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载:“自杞今王名阿谢,年十八,知书能华言,以淳熙三年(1176年)立,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允是。阿谢父死当立,生甫余岁,阿已摄国政。自罗殿致书生,教之华言,教之字画。尝贻书田州黄谐,候问寒温之式,与中国不异。”教授自杞小国王汉语汉文的必须向罗殿国聘请,让罗殿国书生来做教师,说明自杞人初于今贵州兴义立足,国人上上下下对汉语汉文素不相识,既生疏又感陌生。这在西南传统的各土著群体是不可能存在此种状况的。因为一国之中,自汉武帝设郡置县以后即逐渐濡染于中央王朝推行的“王化”,如同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或其前后唐朝中书令张九疑代唐玄宗拟就的给今川、黔、滇各地首领的信即《敕安南首领爨仁哲书》说的“卿等虽在僻远,各有部落,俱属国家,并识王化”。[46]“识王化”,自然包括汉语汉文在内。“耳濡目染,不学以能”。[47]比如,罗殿国见于唐、五代,他们国中就有许多谙熟于汉语汉文的“书生”,可资自杞的王室遴选。自杞人既然“尤凶狡嗜利”,长于商贾,流于四方,自然不会对汉语汉文如此生疏而陌生,不通于世务。他们既然对汉语汉文反常态地感生疏和陌生,由此或可以粗略知道,北宋后期自杞人方才从南方海外辗转进入今贵州兴义一地立足。
元朝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罗罗》载:
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革占,剜木为蹬,状如鱼口,微容足指。妇女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贱者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手面经年不洗。
有论者以此与范成大记载的自杞人风俗文化比较,认为其基本相同,因而认定自杞国为历史上彝族先人所建的国家,并引明朝田汝成在《炎徼纪闻》卷4中的言论以证其事。[48]此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觉得如此太不着底儿。
李京《云南志略》所载的“罗罗风俗”,除了“椎髻”、“徒跣”、“荷毡”、“带刀”、“少拂意即拔刀向人”似相类外,还有什么相同之处?而“椎髻”,是一“以锦缠椎髻”,一是“男子椎髻,摘去须髯,或髡其发”;“荷毡”,一是“戴笠荷毡”,一是“男女无贵贱皆披毡”;“带刀”,一是“背长刀”,“少拂意即拔刀向人”,一是“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间,一言不相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怎么就可以不究其底蕴而估定二者间相似相类呢?自杞“性好洁”,“食已必刷齿”,“甚恶秽气,野次有秽,必坎而覆之。邕人每以此制其忿戾,投以秽气,辄跃马惊走”,怎么可以跟“罗罗”人“手面经年不洗”放置于同一个层面上视为相类相同呢?就风俗而言,很明显自杞人与宋的罗殿、元的罗罗根本不属于同一人类群体。何况,自杞人“深目长身”、“黑面白牙”的形貌也与彝族先人的形体特征大不相符。
可怪的是明代田汝成《炎徼纪闻》卷4载“罗罗”的风俗,将范成大关于自杞人的记载与他自己或其他人的文字揉合在一起,分不清他所记的哪些是“罗罗”明代时候的习俗。
首先,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南江之外稍有名称者,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以道名。此皆成聚落,地皆近南诏。”而田汝成袭而不忠于原文却缀以己意,说道:“自罗殿东西,若自杞,若夜郎、鳎则以国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则以道名,皆罗罗之种也。”夜郎是汉代的国名,魇呛捍和隋朝的郡名,罗殿国是唐以后始出现,怎么可以齿齐平列?特磨道,宋代在自杞之南,是以僚人侬氏为首领,哪里又是 “罗罗之种”了?白衣九道也称为“九道白衣”,在特磨道的西南。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载: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延众镇右千牛卫将军张智常诱致九道白衣富雅州李聚明等内附。”延众镇,元丰七年(1084年)五月丁卯改为富州,归特磨道管辖。而宋代的“白衣九道”或“九道白衣”是指称泰掸群体的,又怎么可以将特磨道和白衣九道的人通指为“皆罗罗之种”?
其次,田氏所载的“罗罗风俗”,是以范成大记载的自杞国风俗为主,不求甚解地辑合明代一些关于“罗罗风俗”的记载,体现出来的并不完全是明、清时期彝族的风俗:
其人深目长身,黑面白齿;椎结跣餣,荷毡戴笠而行;腰束苇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长刀箭諹;富者以金钊约臂;悍而喜斗,修习攻击,雄尚气力;宽则以渔猎伐木为业,急则屠戮相寻,故其兵常为诸苗冠。谚云:“水西罗鬼,断头掉尾。”言其相应若率然也。
亦有文字,类蒙古书者。
坐无几席。与人食,饭一盘,水一盂,匕一枚。抄饭哺客,搏之若丸,以匕跃口。食巳,必涤噱(jué,口腔)刷齿以为洁。作酒盎而不缩(滤去酒渣),以芦管啐饮之。
男子则剃发而留髯;妇人束发,缠以青带。蒸报(与母辈及嫂等通奸)旁通,瞯而不恧(mù,惭愧)。
此中,范成大所记的“性好洁。数人共饭(几个人一同吃饭),一盘中置一匕,置杯水其旁。少长共匕而食,探匕于水,抄饭一哺许(用匙舀起一口大小的饭),搏之拌令圆净,始加匕上,跃以入口,盖不欲污匕妨他人”,变成了“坐无几席。与人食(招待客人吃饭),饭一盘,水一盂,匕一枚。抄饭哺客(用匙舀饭款待客人),搏若丸,以匕跃口”,就有点牛头不对马嘴的味儿,似乎像杜甫《彭衙门》一诗说的“小儿强解事,故索若李餐”了。而将自杞人“性好洁”随意变换成“坐无几席”,更其没有来由了。
至于能够显示出南宋时自杞人特殊的饮食习俗,如“食盐、矾、胡椒,不食彘肉”;特殊的“好洁”文化如“食已必刷齿,故常皓然。野次有秽,必坎而覆之。邕人每以此制其忿戾,投以秽气,辄跃马惊走”;以及他们“胸至腰骈束麻索,以便乘马”的装束习俗和“取马于群,但持长绳走前,掷马首络之,一投必中”的高超技能等,田氏则视之若无,一概不顾。自杞人这些优秀的文化,后来不详是随着自杞国亡而湮灭,还是自杞国灭人走他乡而远去,因史无记载而无从考索。不过,这些材料却揭示出了南宋时期的“自杞国”人不是明代的“罗罗”人。范成大作为南宋淳熙初年广西一路的帅守,总管与自杞国人的买马事宜,记载如是,诚难置疑。
清朝人檀萃钞旧书形成的《滇海虞衡志》卷13《志蛮》载,“于夷为贱种”的“白罗罗”“以革带系腰”。人死,“焚之于山,鸣金执旗招其魂,以竹裹絮置小篾笼悬床间如神主。五月二十三日列笼地上,割豚(杀猪)侑以酒食,诵夷经,罗拜以祭之”。“其难治者为黑罗罗。其俗男子挽发,以布带束之;耳圈双环,披毡佩刀。……在夷为贵种。凡土官、营长,皆黑罗罗也。……其富者,辄推为土司,雄制一方,耕其地者直呼为百姓。土司过必谒,奉茶烟必跪进,或献鸡、酒,或炮豚(烧猪),虽不食必供之;其极重,则具马镯。不然,即逐之。每曰:汝烧山吃水在我家,何敢抗我!……所居多为楼,楼下煤薰,黑逾黝漆,其光可鉴。扫地必择吉日,粪秽丛积,不俟日不敢拚除。”又“干罗罗”,“每食插箸(筷子)饭中,仰天而祝,以为报本”。这些记载都在说明,历史上在彝族中不论是列为“贵种”的黑彝还是列为“贱种”的白彝,一吃猪肉;二居室“黑逾黝漆”,“粪秽丛积,不俟日不敢拚除”;三用筷子吃饭,绝不类似于南宋时代自杞人以匕为食具。自杞人“食盐、矾、胡粉,不食彘肉”;“性好洁”,“食已必刷齿”,“甚恶秽气,野次(野外)有秽,必坎(挖洞)而覆之”:绝不类于罗罗人。如果说南宋的自杞人是彝族的先人是说不过去的。
自杞有“精兵万骑”,纵横驰聘。宋末元初,铁骑不知何处去,徒令后人叹春风。
参考文献:
[1](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M].[2]宋史.卷25.高宗纪[Z].[3]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二二之二一[Z].[4]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6[M].[5][29][30]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二二之二三[Z].[6][31]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二二之一九[Z].[7]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二二之二九[Z].[8][18][32][39][40][41](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28引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9][15][16][17][19][32][35][44](宋)吴儆.邕州化外诸国土俗记.粤西文载.卷36[C].[10]宋会要辑稿.第198册.蕃夷五之一二:“程无里堠。但晨发至夜,谓之一程。”西南山多路转,人走一天约五六十里。[11]岭外代答.卷5.马纲:“常纲马一纲五十匹,进马三十匹。每纲押纲官一员,将校五人,兽医一人,牵马士兵二十五人;进纲马则十五人,盖一人牵二马也。”[12]宋会要辑稿.第183册.兵二三之一一~一二[Z];岭外代答.卷5.宜州买马[M]。[13][20](宋)吴儆.竹洲集.卷1[M].转引自刘复生.自杞国考略[J].民族研究.1993,(5)。[14]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06.横山买马[M].[22](宋)李曾伯.贴黄.可斋杂稿续稿后.卷7[M].[23]李曾伯.奏边事及催调军马.可斋杂稿续稿后.卷9[M].[24]李曾伯.奏调军马及辞免观文殿学士.可斋杂稿续稿后.卷9[M].[25]李曾伯.奏边事已动.可斋杂稿续稿后.卷9[M].[26]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216.[27]刘复生.自杞国考略[J].民族研究.1993.(5).[28]元史.卷30.泰定帝本纪[Z].[33]旧五代史.卷34.明宗纪四[Z];新五代史.卷74.四夷附录第三[Z].[37]元史.卷61.地理志.广西路[Z].[38]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761~763.[42]葛振家点注.漂海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195.[43]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38.[45](唐)韩愈.酬卢云夫望州诗[M].[46](唐)张九龄.曲江集.卷12[M].[47]韩愈.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铭[M].[48]龙中.中国西南民族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03~206;侯绍庄.史继忠.翁家烈.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1:191~198;刘复生.自杞国考略[J].民族研究.1993(5);民族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432.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