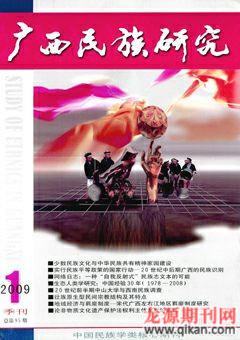黑衣壮:“我”的表述与建构
吕俊彪
一、问题的提出
从某种意义上讲,“黑衣壮”已成为继“刘三姐”之后壮族“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标识之一。不过,尽管被赋予“原始”、“原生态”、“古老而神秘”、壮族文化的“活化石”等诸多浪漫想象,享受着某种意义上的“诗意的人生”,并实现着所谓的“审美化生存”①,但“黑衣壮”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文化符号的出现,其实是一件相当晚近的事。1999年,在广西南宁市举办的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青年歌手黄春艳以一首动听的壮语歌曲《壮乡美》让世人见识了黑衣壮人独特的服饰和歌声。此后数年间,经过地方政府的精心包装和媒体化运作,“黑衣壮”迅速成为一个颇具竞争力的地方性文化品牌,并在国内娱乐圈掀起了一股“黑衣壮”文化热潮。②身着黑色的节日盛装、载歌载舞的少女,逐渐成为黑衣壮人的一种文化标识。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这场黑衣壮传统的发明运动当中,那些肚子里装着一大套黑衣壮历史、民间宗教和地方掌故的黑衣壮传统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道公,以及黑衣壮人的传统仪式,则在相当程度上被冷落了。③由此所引发的问题似乎就是,黑衣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群体?谁是黑衣壮文化的真正代表?黑衣壮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族群?他们通过何种方式来表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而更进一步的追问,则可能涉及到这样一些问题:族群认同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它的动因和基础又是什么?海力波的新著《道出真我——黑衣壮的人观与认同表征》(以下简称《道出真我》),试图超越以往黑衣壮研究中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取向,以主位视角和实在的田野工作,透过广西那坡县“文寨”黑衣壮的人观表述、族群认同以及当地文化表征的考察,探寻黑衣壮族群建构的历史踪迹和现实生活,展现黑衣壮人的生活世界。
二、黑衣壮:被想象的“我”
1999年以来,黑衣壮人以其“原生态的歌声、原始的舞蹈、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延绵千年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一些地方媒体关注的对象。这个“以黑为美”的族群,“带着‘不要问我从哪里来的另类魅力,向世人撩起了神秘的盖头。”④从某种意义上讲,“古朴、善良、浪漫”的黑衣壮人,正是经由现代媒体如此这般的“宣传”而广为人知。不过,海力波的研究表明,尽管黑衣壮村里的姑娘小伙子们通常会在传统干栏(房)的大门或者墙上贴上一些影视明星、流行歌星的招贴画,当地人的家里通常也会有电视机、影碟机等,一些人家甚至可以收看卫星电视,但是对于那些生活在类似于“文寨”这样一个2000年才有碎石路、最近几年才通电的村子里的黑衣壮人而言,他们对于外界的觉知仍然十分有限,而他们“神秘的”的社会生活,也鲜为外地人所知。这种情状,即使在交通、通讯条件已经变得比较便利,包括黑衣壮民歌在内的“那坡壮族民歌”入选2006年6月中国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Ⅱ—32)⑤,黑衣壮族群文化形象声名日隆的今日,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世人之于黑衣壮人的“了解”,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倚赖于媒体的宣传以及个人的想象,“神秘的”黑衣壮对于那他们而言,在较大程度上,乃是一个想象中的当代“异邦”。
成果与学者评介世代生活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自称为“敏”或者“布敏”的黑衣壮人,由于与外界的相对隔离,在服饰、婚姻制度、民间信仰、生计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呈现出与山下的“布央”⑥、汉人以及其他族群的某些差异。这些差异,似乎成就了黑衣壮人“原汁原味的族群习俗”,而其民风民俗也因此被一些人誉为壮族的“活化石”。⑦与此同时,由于生存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黑衣壮人则被一些从结果上考察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学者,描绘成一群“孤僻、寡闻、少欢、封闭”,“缺乏创新活力,墨守成规,满足于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普遍有惰性和排他性心理、缺乏进取心的“原始”族群。⑧从某种意义上讲,黑衣壮“原生态”文化的浪漫想象,以及黑衣壮“原始”、“落后”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基本定位,构成了黑衣壮这个当代“异邦”想象的重要内容。能歌善舞的、靓丽的黑衣壮少女与“孤僻、寡闻、少欢、封闭”的黑衣壮少年,似乎已成为主流媒体中的“黑衣壮文化”的典型代表。
对于黑衣壮人这种“异邦”式的当代想象,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后果。海力波认为,在浪漫主义的“原生态”的话语当中,黑衣壮人及其文化作为“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恰好可以弥补主流社会中已经缺失的美好品质;而在启蒙主义的“原始”话语中,黑衣壮人及其文化则恰恰承载着主流社会所力图摆脱的自身所具有的负面品性。但无论在哪一种话语之中,黑衣壮人始终是作为一种异己的“他者”而存在。⑨海氏的洞见,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黑衣壮的族群建构以及黑衣壮文化的再生产在当代得以顺利展开的深层社会原因。
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甚至于包括这种村落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在于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⑩对于黑衣壮人而言,问题的关键似乎还不止于此。事实上,黑衣壮人如何想象自己、建构自己,甚至比他们如何被别人想象更为重要。这样,进入黑衣壮人的生活世界,透过其社会生活的一些文化事象,探寻黑衣壮人的自我认知、自我建构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这大概是海力波写作《道出真我》的初衷。
三、“我”的表述
长期以来,“文寨”的黑衣壮,这个“穿黑衣”、“吃玉米”的族群,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在总体上被排斥在当地族群社会生活的主流之外,处于现代化的边缘。1990年代以前,这些住在崇山峻岭之中被“外面的人”污称为“黑衣崽”的黑衣壮人,不仅因为物质生活上的相对穷困而少与山外“吃大米”的“布央”、“布农”通婚,因为水田少不种水稻而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更由于生存环境相对封闭、服饰穿着习惯与主流社会相异而一度成为当局“除陋习,改服饰”的主要对象,其社会地位处在当地族群“差序格局”的最底层。
《道出真我》之于那坡县“文寨”黑衣壮人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一些与当地社会生活相关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沿革、人口分布、生计方式、生活周期等方面的内容,但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调查(研究)不同,海氏研究的着力点,主要放在“文寨”黑衣壮人的人观、族群认同与文化——政治实践之上。海氏的设想,大致是从观念与行动两个层面,展现黑衣壮人认识自我、建构自我的社会过程。
作为能力和行动的基础,以及自我观念与情感的重要表达方式,人观(personhood)是族群认同最深层、同时也是最隐晦的表达方式之一。《道出真我》把黑衣壮的人观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无疑是一个极好的选择。透过对黑衣壮人在其社会生活中展现出来的宇宙观、空间观、时间观的细致描述和分析,作者认为,以“好功德”作为自我核心观念的黑衣壮人,自认为在道德上具有其他族群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而这种优越性来自于他们对于“道法”、“秘法”的深入理解和圆满实践。[11]在海力波看来,“好功德”的道德观,对于“善好生活”的追求,对于“传魂”的焦虑,以及“魂、名、骨”三位一体的身体想象,构成了黑衣壮人的人观的核心内容。而借由信仰与仪式来达到“功德”上的圆满,实现肉体与灵魂在时间、空间秩序中的顺利循环,遂成为黑衣壮人自我认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也是黑衣壮文化自信心之所在。[12]
黑衣壮族群认同的表述,与当地人传统的人观、社会生活状况以及国家话语形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说“穿黑衣”、“吃玉米”、“住山上”是“布央”等其他族群的人对黑衣壮外在的族群特征的基本认定的话,那么,“好功能”、尽孝道、“讲文明礼貌”、知羞耻、懂“做人道理”等,则是“文寨”黑衣壮人的自我定位。尽管生态环境与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一直存在于黑衣壮人与“布央”人之间,但民国时期,“穿裙又穿裤”成为黑衣壮人区别于“穿裤不穿裙”的“布央”人的明显标志,而“布央”对黑衣壮人的排斥,也甚于汉族和其他族群的人。海力波认为,这种状况的存在,与1930年代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当地政府强迫黑衣壮人改装有着直接关系。为了追求所谓的现代化“新生活”,跻身于“现代国民”的行列,黑衣壮人的某些族群特征在无可奈何的情状之中被夷平了。1949年以后,通过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等官方媒体的宣传,以及升学、参军、“提干”(提拔干部)、户籍登记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落实,统一的壮族认同逐渐成为当地“布央”、“布敏”(黑衣壮)最为重要的族群认同方式。[13]在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当中,“布央”、“布敏”之间的族群界限有逐渐模糊之势,然而,黑衣壮人深层的族群意识并未因此而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