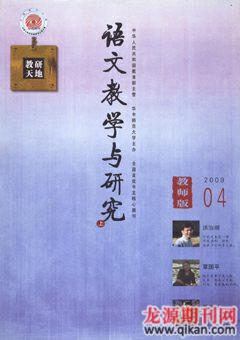《相见欢》的愁绪表达
李煜作为南唐后主,在被宋灭国之后,从一个“几曾识干戈”的风流皇帝沦为阶下囚,备受凌辱,每天以泪洗面,所以他后期的词作中抒发了深切的故国之思、亡国之恨。《相见欢》正是这些作品中的代表。
词人起笔就道“无言独上西楼”。“无言”二字活画出词人的愁苦神态,“独上”二字勾勒出作者孤身登楼的身影,孤独的词人默默无语,独自登上西楼。神态与动作的描写揭示了词人内心深处隐喻的多少不能倾诉的孤寂与凄婉啊!“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寥寥12个字,形象地描绘出了词人登楼所见之景。仰视天空,缺月如钩。“如钩”不仅写出月形,表明时令而且意味深长:那如钩的残月经历了无数次的阴晴圆缺,见证了人世间多少悲欢离合,今夜又怎能不勾起人的离愁别恨呢?俯视庭院,茂密的梧桐叶已被无情的秋风扫荡殆尽,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和几片残叶在秋风中瑟缩,怎能不“寂寞”情生!然而“寂寞”的又何止是梧桐?即使是凄惨秋色,也要被“锁”于这高墙深院之中,然而“锁”住的又何止是这满院秋色?落魄的人,孤寂的心,思乡的情,亡国的恨,都被这高墙深院禁锢起来,此景此情,“愁”何以堪?古典诗词中常借梧桐抒发内心的愁闷。温庭筠“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更漏子》);李清照“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声声慢》)。写雨中梧桐,最能表现诗人内心的愁苦。写缺月梧桐,则又是一番境界。苏轼的“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卜算子》)即是如此。缺月、梧桐、深院、清秋,这一切无不渲染出一份凄凉的境界,反映出词人内心的孤寂之情,为下片抒情做好铺垫。“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用丝喻愁,新颖而别致。前人以“丝”谐音“思”,用来比喻思念,如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就是大家熟悉的名句。李煜用“丝”来比喻“离愁”,别有一番新意。然而丝长可以剪断,丝乱可以整理,而那千丝万缕的“离愁”却是“剪不断,理还乱”。那么,这位昔日的南唐后主心中涌动的是怎样的离愁别绪呢?是追忆“红日已高三丈后,金炉次第添金兽,红锦地衣随步皱”(《浣溪沙》)的荣华富贵,是思恋“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破阵子》)的故国家园,还是悔失“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河山”(《破阵子》)的帝王江山?然而,时过境迁,如今的李煜已是亡国奴、阶下囚,荣华富贵已成过眼烟云,故国家园亦是不堪回首,帝王江山毁于一旦。阅历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经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折磨,这诸多的愁苦悲恨哽咽于词人的心头难以排遣。而今是尝尽愁滋味,而这滋味又怎一个愁字了得。“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紧承上句写出了李煜对愁的体验与感受。以滋味喻愁,而味在酸甜之外,它根植于人的内心深处,是一种独特而真切的感受。“别是”二字极佳,昔日唯我独尊的天子,如今成了阶下囚徒,备受屈辱,遍历愁苦,心头淤积的是思、是苦、是悔,还是恨……恐怕词人自己也难以说清,岂又是常人所能体会得到的呢?若是常人,倒可以嚎啕倾诉,而李煜不能。他是亡国之君,即使有满腹愁苦,也只能“无言独上西楼”,眼望残月如钩、梧桐清秋,将心头的哀愁、悲伤、痛苦、悔恨强压在心底。这种无言的哀伤更胜过痛哭流涕之悲。
在这首词中,李煜把自己的离愁别恨刻画得丝丝入扣,形象生动,真不愧是写愁情的高手。在他的另外一些词作中也有写愁的句子,最有名的两句应该是“离恨恰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前一句把愁比作春草,以远接天涯、绵绵无尽、无处不生的春草来比喻离别的愁恨,生动形象,自然贴切,以遍天下之春草,把人人心中所欲言而又不能言的东西,写得让人心里感受得到,眼里似乎也看得到,手里几乎还能触摸得到:春草一望无际,是离愁浩渺无边;春草尖细绵密,是离愁绵绵郁结;春草破土而萌,是离愁割之不尽……这是李煜以春草喻恨的名句,的确是传神之笔。后一句把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古代诗词中以水喻愁的佳句不少,但李煜的这一句最负盛名。不过,用水来比喻愁,李煜并不是第一个。李白曾经说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诗句。他在《金陵酒肆留别》中也曾用水来比喻离别的愁情:“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李白说别情的长短可以跟东流水比,别情能量长短吗?东流水虽然有长短但不能用尺子去量,诗人用不能丈量的别情与长得无法丈量的东流水作比,真是别出心裁。但李白的诗跟李煜的这一句一比,却比出了长短。因为李白的诗是在金陵(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写的,这个东流水指的是长江,而李煜的词是在汴京(今开封)被囚禁中写的,他的“一江春水”指的也是长江,李白是用眼前的景物作比,李煜的词是用远离自己的长江作比,长江成为怀念故国的一部分,这个比喻里就有怀念故国的深切感受,比李白的“别意”深厚多了。这是李白不如李煜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东流水”只能让人感受流水的方向,而“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有方向,而且还能让人想象出:滔滔滚滚的一江春水,波涛汹涌,奔流不息,而词人的离家之愁、故国之思、亡国之恨就如这一江春水无穷无尽、日夜奔腾。这两个人的愁情谁更深更浓也就比出了高下。
李煜之后,用水来比喻愁的诗家词家就越来越多了。北宋名臣寇准也曾用春水来写愁情。他说:“日暮汀洲一望时,柔情不断如春水。”(《夜度娘》)这里用春水比柔情,跟李白的句意相似,可以说是模仿李白,所以更不能与李煜的词句相比。欧阳修的“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秦观的“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江城子》),贺铸“漫将江水比闲愁,水尽江头愁不尽”:都用春水比闲愁,让人触目惊心。
这中间比较有名的是欧阳修的“离愁渐行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这两句很显然受了李煜的影响,把他用春草、春水喻愁的名句合二为一了,写出了离愁的绵延不绝。秦观的《江城子》中“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动,许多愁”也是写愁的名句,其实秦观的这一句也借用了李煜的创意,但不是照搬照抄,而是反用了他的意思,创造出更新的意境。“愁”是一种抽象的情感,可以用细丝乱麻比喻它的繁乱、无头无绪,用春草比喻它绵延不绝,用一江春水比喻它无穷无尽,但它又怎么能够流动呢?仔细品味一下,原来作者经历了这样一个化合过程:心中之愁——眼中之泪——江中之水,于是作者的“愁”就可以尽情流淌了,而且“满江都是泪”,说明作者的泪多、愁深。然而,浩荡春江即便日夜奔流,也还是“流不尽”词人眼中的泪、心中的愁。词人的泪之多、愁之深几乎难以言传,唯有神会,全凭你去想象了。
秦观几乎把愁写到极致,由南唐入宋的郑文宝后来在他的《柳枝词》中又翻新意,他说:“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你看,这“愁”不仅可以流淌,还可以用“船”来载了。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宋代写愁堪称愁绝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作中写愁的句子简直太多了。在她的笔下,“愁”这个抽象的感情概念,变成了无数鲜明、具体、可感的形象。“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愁”有了重量,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愁又似乎可以游走了,“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愁有了“雨打梧桐”似的声音,它能够从清晨到黄昏,又有了绵延不断的时间感。真是出神入化,处处都是绝妙之笔!
上面所说的这些愁,不论是如细丝乱麻、如春草春水,还是能流淌、有重量、可游走、有声音,但它总还是可以明确感受到的,并可以通过具体形象表达出来,而《相见欢》中的最后一句“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却是词人最质朴、最直白、最深沉的感叹,决非一个“愁”字所能概括!“别是一般滋味”,到底是什么滋味呢?它似乎不可捉摸,但又隐约感觉得到,似乎未曾经历,又似曾相识,说不清道不明。如果说上面的比喻是用有形的事物来比喻无形的情感,那么这一句就是用无形来比喻无形,而这种无形是词人难以说破、无法说破的情感,可见作者体验之深、愁情之苦。所以明代人沈际飞说道:七情所至,浅尝者说破,深尝者说不破。破之浅,不破之深。“别是”句妙。所以个人认为,前面品析了这么多写愁的词句,还是这一句格外的深挚浑厚,感人肺腑。
黄群芳,语文教师,现居湖北武汉。本文编校:艾永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