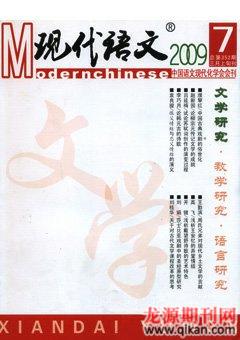言为心声,托物抒怀
摘 要:李商隐是唐代咏物诗大家,以写作“无题诗”而著称,其诗歌历来难解,早在元代元好问就发出过“独恨无人作郑笺”的喟叹。本论文探讨了李商隐咏物诗作的内容,他多将自己的家国之悲、身世之感寓托其中,形成诗作独特的感伤情调,与这种流荡于诗中的忧伤氛围相协调,使得李商隐的咏物诗中同时也具有了自己的独特的意象群。
关键词:咏物诗 李商隐 意象群 感伤
“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崔钰《哭李商隐》),这是对李商隐一生的总结概括,李商隐的一生,是坎坷不幸的一生,是惨淡寂寞的一生,也是忧郁的一生。他生活在唐帝国的后期,君主昏庸,宦竖跋扈,士大夫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狼狈为奸,而他自觉不自觉地卷入牛李党争。个人宦途的坎坷曲折,辛酸苦辣,生活上的辗转流离、饥寒交迫,使身处肉体精神夹缝当中的他,将自己的运命、感触,发为吟咏,形成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李商隐的诗作中几乎无不蕴藉着他自己特有的一种深微幽隐的情意,而且此种情意与他的身世遭际结合并有密切关系。
一
作为晚唐咏物诗大家,李商隐创作的咏物诗不少,归类的话可分为两类:无寄托的和有寄托的。前者几乎纯用白描,玩弄技巧炫耀才学,没有审美寓意,其长处也仅在刻画工细。李商隐的《牡丹》诗“锦帷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叶寄朝云。”这首诗句句用典作比,极力描摹牡丹的美艳,写出了牡丹的盛开、初放、摇动、光彩和香气。朱彝尊评:“八句八事,而一气涌出,不见折叠之迹。”何义门评:“非牡丹不足以当之。起联生气涌出,无复用事之迹。”令人赞赏的是诗人用典巧妙,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但给人的感觉也只是诗人在逞才使气。与《牡丹》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泪》诗,也是句句用典。这样的咏物诗在李商隐的诗作中所占的比重不大,而且历代的批评家们对单纯描写性的咏物诗评价也不高,认为格卑无远韵。李商隐的咏物诗大多是有寄托的,这部分诗作代表了他所处时代咏物诗的最高成就。
其实,李商隐美学思想就是主张有寄托的,“盖以徘徊胜境,顾慕佳辰,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谢河东公和诗启》)这也是对传统骚体美学的体认,他的咏物诗创作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朱鹤龄在《笺注李义山诗集》序中曾对此做过具体的阐释:
“《离骚》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遂为汉魏六朝乐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于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于婉娈,结深怨于蹇修,以叙其忠愤无聊、缠绵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后,阉人横暴,党祸蔓延。义山扼塞当途,沉沦记室。其身危,则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则庄语不可而漫语之。计莫若瑶台琼宇、歌筵舞榭之间,言之可无罪,而闻之者足以动。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皆有托。早已自下笺解矣。君故曰:义山之诗乃风人之绪音,屈宋之遗响。”
这段叙述同时也阐释了诗人大量创作咏物诗的原因:为避免动乱中的恐怖氛围,借咏物诗来较为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感慨;既可以将诗作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挂钩,又可以借诗来浇心中之块垒,借助“物”这层保护膜,不至于使诗作太张扬,同时又不违背诗人拯物济世的心愿,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诗人也能全身而退,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在义山的笔下,咏物诗有了丰富的内容:以物喻理,托物言志、因物抒愤、借物议政。这样的咏物诗占了李商隐诗作的绝大部分,这也符合了咏物诗鉴赏的审美标准:所谓有寄托的咏物诗,一体而兼有赋、比、兴,“咏物一体,就题言之,则赋也;就所以作诗言之,即兴也、比也。”(李重华《贞一斋诗说》)优秀的咏物诗,要做到“不即不离”,写物不仅要恰切无移,描摹其形态,更要着重寄托一己之情感,既要形似,更要神似,形神兼备。“咏物诗贵乎寄托缅缈,不黏不脱,得言外远神,斯为能乎。”(蒋冕《琼台诗话》卷四)己情、人情及物情,三者缺一不可,且互相贯通,这样的咏物诗才是真正的佳作,这种观点确实很中肯。
借物喻志是义山咏物诗作中最常用的手法之一。他的《初食荀呈座中》:“嫩箦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黄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荀在成为凌云美竹之前已告夭折,诗人由此想到自己受到摧残的峥嵘岁月,伤一己之不遇。
咏物的政治讽刺诗在其咏物诗中也有不少。例如《赋得鸡》:“稻梁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以斗鸡为喻,嘲讽了那伙贪婪好斗、排除异己、不肯尽忠国事、肆意独霸权位的官僚集团,实际上也影射了无休止的党争。同样的《蝶》、《嘲桃》、《题鹅》、《洞庭鱼》等作品也都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评。
《木兰》诗末联“瑶姬与神女,长短定何如”,表明诗人的政治态度,即不愿妄断人之长短是非。牛李党争中,李商隐处于尴尬的境地:令狐楚父子和王茂元对他来说,一为师门之谊,二为翁婿之情。身兼这两层关系而又处于誓不两立的朋党之争中,义山的委屈与苦衷自不待言。
封建时代的士大夫文人,抱定“学而优则仕”的信念,走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路子,在现实的铜墙铁壁面前撞的头破血流也“虽九死其犹未悔”,李商隐最初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有着盖世的才华和充分的自信,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通过干谒这条路寄希望于达官贵人来实现自己“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政治理想,但他面对的总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登安定城楼》)的局面,他忍辱负重地一次次向令狐父子表白心迹,希望他们能念及当年的情谊重新重用自己。
自始至终,李商隐都对未来充满了憧憬,每一次挫折后,心中都燃烧起新的希望,而每一次希望又都在残酷现实的面前无情破灭,于是既怀着对未来的无限热忱,又忍含着巨大的忧虑,诗人一生不懈的追求和事与愿违的结局,大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李商隐的一生,注定了是悲剧。“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有感》)这是诗人对自己一生坎坷经历的感慨,在这一声叹息中,又代表了封建时代多少有才华而又不得施展的知识分子的共同辛酸。
二
每一个咏物诗人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总是抓住这种事物的某些特征,作为突破口来表情达意。综合义山的咏物诗,会发现他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意象群。袁行霈先生指出:“诗的意象带有强烈的个性特点,最能见出诗人的风格。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建立了他个人的意象群。一个意象成功地创造出来以后,虽然可以被别的诗人沿用,但往往只在一个或几个诗人笔下才最有生命力。以至这种意象便和这一个或几个诗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诗人的化身。”(《中国诗歌艺术研究》)
《流莺》:“流莺飘荡复参差,度陌临流不自持。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风朝露夜阴晴里,万户千门开闭时。曾苦伤春不忍听,凤城何处有花枝?”诗人以流莺飘荡暗喻自己转徙幕府的生活,以流莺的婉转歌唱而佳期难得暗喻自己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更以流莺在京城长安无处可栖暗喻自己不能在朝廷里供职的遭遇,全诗暗喻连贯,层次递进,措辞婉曲,意境完整,使物态的细致刻画与情怀的深沉抒发巧妙得结合在一起。这首诗慨叹自己的怀才不遇比较得含蓄,在他著名的咏物代表作《咏蝉》诗中则直抒胸臆,书写愤激之情,这些都是咏物诗中的上乘之作,也都是诗人自身遭际和命运的对象化写照。
在晚唐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他所感应的是时代的衰飒氛围,是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园》)这一时代意识的体认,当他以黯淡的心态去反观眼前的这个世界时,他的观照中便带有了浓厚的悲剧色彩,笼罩在诗中的则是一层淡淡的哀思。《柳》诗言:“如何肯到中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野菊》诗:“己悲节物同寒燕,忍委芳心与暮蝉”,“儿时禁重露,实是怯残阳。”《落花》诗言:“肠断未忍扫,眼穿依欲稀。”写紫薇,“天涯地角同荣谢,岂要移根上苑栽。”从中可以看出,义山诗不是通过物的拼凑来直接塑造自己的意象世界,他总是杂碎着“象”的诸种状态,把意象处理得迷离惝惚,他所描写的不仅是一个物理的世界,更是一个心理的世界,有着对过去情感生活绚丽而惨淡的追怀,因此心理的波荡跳跃,形成了意象的迷离。
义山笔下的物,是诗人自己的象征,也是怜物怜己的悲歌。他写梅花,“匝路亭亭艳,非时裛裛香。素娥惟与月,青女不饶霜。……为谁早成秀,不待作芳年。”写杏花,“自明无月夜,强笑欲风天。”《槿花》诗:“殷鲜一相杂,啼笑两难分”,“回首问残照,残照更空虚。”《赠荷花》,“唯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映,翠减红衰愁煞人。”诗人正是通过这些物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他笔下的《题小松》:“桃李盛时虽寂寞,雪霜多后始青葱。……为谢西园车马客,定悲摇落尽成空。”《高松》:“有风传雅韵,无风试幽姿。”松树成为诗人形象的写照,诗人借它来表现自己的伟岸高直、壮志凌云、高标绝俗的精神境界,同时也抒发了自己坎坷孤独的寂寞心态。
唐以前只是诗人用来炫耀博奥、逞才使气的咏物诗,到了李商隐的笔下大放异彩,成为他诗作中极具个性与魅力的一部分。在他传于后世的近六百首诗中,咏物诗就有七十多首。从他所咏之物具有的共性和诗中流露的浓重的感伤情调,不难看出李商隐对人世间残缺事物有着独特的敏感和关注。其咏物诗风格也侧重于深蕴藻丽的一派,情感的抒发寄予言外之味和意境创新之中。正是通过这些事物,表达了他对一去不复返的大唐盛世的追忆,对自己空负才华而困顿蹇塞的命运的感伤,以及对生命的张扬和理想的讴歌。
(钟德玲 青岛 山东外贸职业学院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