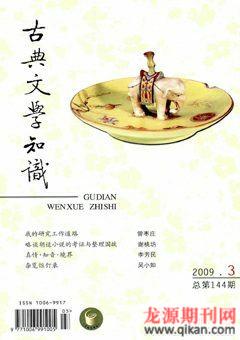梅心惊破,人间天上:以咏物手法写悼亡词
刘淑丽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易安词晚年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再注重居处精美物事的描画与铺叙,而是多直接的抒发,情感浓烈而不掩饰,伤痛之语往往直入人心,其感发性更强。造成这一巨变的原因,当然是她多舛的命运、被动经历的诸多变故,使她再也无法回到年轻时的优雅与小女人态。周围环境与内心的巨变,亦影响了易安词的创作。原来,典雅优美是有物质前提的。
这首词即是李清照晚年词作之一,最初见于《梅苑》卷一。建炎三年(1129)八月十八,赵明诚去世,此年冬,《梅苑》编成,故将此词收入。但是另有说法,认为此词应作于明诚去世后数年间,而现存的《梅苑》只是后人辑补本,也就是说,李清照的这首词有可能是后人辑补入的。这样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既然李清照在此词前有小序,云:“世人作梅词,下笔便俗。予试作一篇,乃知前言不妄耳。”明确说此是一首咏物词。而咏物之作,多数情况下,是咏眼前之物,方才有灵感与创作之佳思。以此来判断,则清照此词,最早应作于建炎四年(1130),即明诚去世之后的第一个春天,似乎更合情理些。当然,现在关于李清照作品的系年,绝大多数是合理的猜测,而无确切依据。
此时的清照,身在何处呢?建炎四年起的两三年间,清照奔波于浙东一带,此时大约是为颁金之事,追随高宗于浙东。《金石录后序》云:“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以一个五旬嫠妇,携金石器玩辗转奔波于数地,其处境之艰难、情怀之恶劣、情感之绝望,可想而知。所以,词的开篇即言:“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在李清照早年词作中,涉及闺房之物,往往不脱精美典雅浪漫之氛围,即使言及床帐,也是“朱樱斗帐掩流苏”(《浣溪沙》),华贵气派。如今,印入眼里的首先是藤床纸帐。藤床为何物?明高濂《遵生八笺》中的记载可为我们提供参考:“高尺二寸,长六尺五寸,用藤竹编之,勿用板,轻则童子易抬。上置椅圈靠背如镜架,后有撑放活动,以通高低。如醉卧偃仰观书并花下卧赏,俱妙。”(卷八)由上述之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藤床由藤竹编成,朴素简陋,而其尺二寸的高度,闲暇时日卧赏烟霞、花石尚可,若以此为卧具,未免简陋而不挡潮寒,尤其是江浙一带春日天气,湿冷逼人,最难将息。至于纸帐,虽然其上有时可画以梅花诸物,颇有几分清雅,但依然无法与“朱樱斗帐”相比。身居藤床纸帐之中,词人处境之清寒困蹇已不言自明。在藤床之上,纸帐之中,词人睁开眼,窗外,不知什么鸟,带着悠长婉转的鸣叫,从枝头滑过了,词人意识到了自己正身处异地他乡,再也不是“暖风帘幕”(《青玉案》)的“重门深院”(《怨王孙》)了。近来发生的太多事情,让她一时喘不过气来,眼睛刚刚睁开,忧愁烦闷就袭上心来,所以,词人发出“说不尽、无佳思”的叹息。“说不尽”之后,往往会接以愁啊恨啊之类的词,而此时的词人,却接以“无佳思”。为什么要用一个否定词来表达此际的心情呢?大约是所愁闷之事太多,不知从何说起了,只能以短短的一句否定,来圈定她的情绪范围;或者是,南渡前后发生的许许多多的变故,早已将她平静的生活彻底摧毁,如今,成天在奔波忧苦孤独惊吓中度过,包围着自己的,说不说都一样,都是这样一些负面的东西,所以,说不尽的,当然不是什么好的心情和思绪了,这也便有了“无佳思”的说法。无佳思,即情怀恶,就像她在另一首词中写的“断香残酒情怀恶”(《忆秦娥》)一样。这种恶劣的情怀显然不是年轻时闺房相思念远所萦绕的愁怨所能比拟的,这是一种真正处于悲苦境地所感受到的诸多苦难的集结。
虽然是赁屋而租,抑或是寄居在客栈,屋内陈设简陋,谈不上优雅,但熏香是有的,尽管比不上旧时“香冷金猊,被翻红浪”(《凤凰台上忆吹箫》)的气派。但是,此时的熏香又是什么样的呢?“沉香断续玉炉寒”。玉炉里虽然燃烧的是沉香,但此刻早已燃尽,而由于没有人添香续香,所以,炉中只剩下了灰烬,而不再是香烟袅绕了。不仅如此,玉炉里的香实际上早已燃尽,香炉里不仅没有热气,摸起来反而寒意逼人。江南的初春,屋里如果再没有熏香,那种清寒湿冷,可想而知。此处的“断续”,有的本子用“烟断”,似乎无法将香断而无人添香续香的意味表达得明显。沉香断续而无人添香,一方面类比了词人的心境,一方面也暗示了词人居处的清冷,无人问津。而“沉香断续玉炉寒”的外部世界,正与词人此刻的内心世界与感受达到了惊人的一致,所以,词人说:“伴我情怀如水。”所谓的“伴”,也便意味着玉炉香断而清冷湿寒的现状,与词人的情怀恰恰达成了同步;所谓“情怀如水”,绝不似“低头采莲子,莲子青如水”(《西洲曲》)的那种“如水”,那是表达了一种如水样碧绿的感觉。而此时的词人,那如水的情怀则是从温觉上而言,是说她的情怀,亦如断续的玉炉,清寒逼人。情怀到了如此冰冷的地步,那是怎样一种悲伤和绝望!可偏偏此时,不知是谁,吹起了《梅花三弄》的曲子,此前在词人心中蕴蓄的情绪,闻笛而被点醒,而惊心,而爆发,词人的情绪,就在笛声中稀里哗啦,溃不成军。
上片三句三组情景,逐层递进,词人起初恶劣的情绪,经过与外物的感应,益发消沉,终于在笛声中爆发。下片是更为强烈的抒发。与上片相似,下片亦是三组句子,每句前半部分是情景,后半部分是情感的表达。所不同的是,上片每句的外物与情感之间,它们的联系还是比较均衡的,也就是说,外物引发的情绪的波动不是太大,正如“伴我情怀如水”一样,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伴的同步的关系。而下片的情绪之强度,远大于外物的承载。也就是说,上片外物所激发的情绪积淀到了一定程度,使下片中的情绪稍微有外物的感发就会产生强烈的反应,甚至外界事物微小的动静,也能引发词人强烈的情绪波动。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吹下、千行泪。”小风疏雨,不比秋风秋雨,带来愁绪,春天的小风,应该是“吹面不寒杨柳风”那样的细致微醺,春天的疏雨,应该是似有似无“润物细无声”那样的轻柔欣喜,这样的小风疏雨本应给人带来春的风信,带来万物复苏的预言,而词人却在本应喜悦的春风春雨之前落泪了,不是一时的情绪失控掉下的几滴泪,而是有千行的泪。一个“又”字一个“千”字,透露了眼泪的多而不断。而“又吹下”,则意味着在小风疏雨之前,词人已经在落泪了,小风只是将她业已挂在脸上的泪吹落罢了,而这泪有千行万行,吹落了还会生出来,还会再被吹落。词人的眼泪才是真正令人惊心动魄的呢,比那笛声更加令人惊心!而不断的千行泪与断续的沉香,又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真可谓是未语泪先流。接下来,词人进一步说:“吹箫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倚?”直接说出了她这千行泪是为那个吹箫人而落。吹箫人为谁?源出典故。刘向《列仙传》“萧史”条载:“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凤鸣。居数年,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凤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为作凤女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焉。”吹箫人即指萧史,而此处,则是比喻词人的丈夫赵明诚。本来,萧史与弄玉是双宿双飞的,而此刻,吹箫人却独自去了,只剩下词人自己独自一人留在人间,孤凄痛苦自不待言。此处,又是一个“断”字——肠断。“肠断有谁同倚”一方面说明了词人如今的孤独寂寞,另一方面也透露出吹箫人未去之时两人常常同倚楼的情形,委婉诉说出了词人与丈夫往日的恩爱常人难比。愈是情感笃深,就愈是无法接受与适应单独生活的日子。词人的伤痛于此可见。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词人的任何一个日常行为都无法摆脱对往日美好生活的回忆,和对如今单栖独飞生活的无法承受:“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春日又来临了,爱梅的李清照,信步走到了梅树下,她本能地折下一枝梅花,但就是这一折梅间,她的心情又伤痛到了极点。就是梅花再美,也没有了一起赏梅之人,就是梅花插在发间,也没有了赏爱之人,就是想折一枝梅花相送,人间天上,到哪里去找那个要送的人呢?一枝梅花,何其微小,人间天上,又是何其浩瀚广远,它们之间是多么大的对比呀,可偏偏就是这么小的一枝梅花,找不到寄托之处!这样的凄苦,还有比之更大的吗?
为了表现深重的伤痛,词人充分运用了数字与对比。如“笛声三弄”与“多少春情意”;“一枝折得”与“人间天上”,这种数字与对比增强了表达的张力。此外,词人又几次用了否定句式,如“说不尽”、“无佳思”、“没个人堪寄”。甚至,词人在“断”字上的感觉亦值得注意,从香断到泪不断再到肠断,共同烘托出了一种心情。而且,这一词牌押的又是仄声韵,而且是开口很小的纸韵和寘韵(纸、寘通押),这些,都在形式上服务于词的内容的表达。
而从修辞上,词人也很注重整体氛围的营造。首先,还是回到藤床上来。白居易:“六尺白藤床,一茎青竹杖。风飘竹皮落,苔印鹤迹上。幽境与谁同,闲人自来往。”(《小台》)魏野:“藤床藤枕睡腾腾,软胜眠莎与曲肱。”(《谢王耿太傅见惠藤床王虞部见惠藤枕》)苏轼:“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借藤床与瓦枕,莫教孤负竹风凉。”“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纵笔》)苏辙:“清境不知三伏热,病身唯要一藤床。”(《环波亭》,《栾城集》卷五)张耒:“省门下马不读书,急扫藤床卧听雨。”(《曹辅》,《柯山集》卷二十七)晁补之:“清虚有物濯烦暑,藤床对月如对雨。”(《和王定国二首》,《鸡肋集》卷十三)曾丰:“公原自有长生道,藤床纸帐二十年。”(《寿广东提举韩判院》,《缘督集》卷四)以上所引,除白居易之外,其他都是宋人,大多是北宋时人。藤床在这些诗中的出现,大都与表现文人清贫的生活、恬澹的情怀有关。
再来看纸帐。唐释齐己:“沙泉带草堂,纸帐卷空床。”(《夏日草堂作》,《白莲集》卷一)王禹偁:“风揺纸帐灯花碎,日照冰壶漏水清。”(《夜长》,《小畜集》卷十)苏轼:“困眠得就纸帐暖,饱食未厌山蔬甘。”(《自金山放船至焦山》)“蒲团坐纸帐,自要观我身。”(《赠月长老》)苏辙:“岸帻携笻夜夜来,蒲团纸帐竹香台。直须觅取僧为伴,更为开庵劚草莱。”(《山房》,《栾城集》卷十)陈师道:“纸帐熏炉作小春,狸奴白牯对忘言。更无人问维摩诘,始是东坡不二门。”(《次韵苏公谒吿三首》其三,《后山集》卷八)宋僧道潜:“草堂早晚投君宿,纸帐蒲团不用收。”(《次韵李端叔题孔方平书斋壁》,《参寥子集》卷十一)宋毛滂:“蒲团纸帐两寂寞,独有老桧磨风霜。”(《立秋日破晓入山携枕簟睡于禅静庵中作诗一首》,《东堂集》卷二)宋李若水《睡觉》:“布衾纸帐饯残冬,老眼俄惊晓日红。”(《忠愍集》卷三)由上引唐宋诗中涉及的纸帐可以看出,纸帐属于清寒之物,常与蒲团之类同时出现,以此烘托主人清寒孤寂的生活与出世的情怀。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三载:“杜起莘自蜀入朝,不以家行,高庙闻其清修独处,甚爱之。一日,因得对褒谕曰:‘闻卿出局即蒲团纸帐,如一行脚僧,真难及也。”从上述宋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纸帐为当时仕宦阶层最简陋的随身装备之一,其朴素清寒程度可以比拟行脚僧。
此外,纸帐亦常与梅花相配,如赵信庵:“夜深梅印横窗月,纸帐魂清梦亦香。莫谓道人无一事,也随疏影伴寒光。”(《七言绝句》,宋陈景沂《全芳备祖集》前集卷一)刘后村:“瀑映梅花何所似,蚌胎蟾影浴寒江。梦回东阁频牵兴,吟到西湖始树降。雪屋恋香开纸帐,月窗怜影掩书。若将晋汉间人比,不是渊明却老庞。”(《全芳备祖集》前集卷一)因为同属清寒之物,所以梅与纸帐在格调与审美上给人的感觉比较相似,这一点宋人已经注意到了。宋林洪《山家清事》就专有“梅花纸帐”一条:“法用独床,旁植四黑漆柱,各挂以半锡瓶,插梅数枝。……用细白楮衾作帐罩之。”林洪还引朱敦儒词“道人还了鸳鸯债,纸帐梅花醉梦间”(《鹧鸪天》),来说明纸帐与梅花十分相称。周密《齐东野语》有“玉照堂梅品”,认为“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卷十五)。认为梅花为诗人宠物,一旦梅花入诗,“便觉有清意”。不仅如此,周密还“审其性情,思所以为奖护之策”,得出“花宜称、憎嫉、荣宠、屈辱四事总五十八条”,其中“花宜称凡二十六条”如下:“澹阴、晓日、薄寒、细雨、轻烟、佳月、夕阳、微雪、晚霞、珍禽、孤鹤、清溪、小桥、竹边、松下、明窗疏篱、苍崖、绿苔、铜瓶、纸帐、林间吹笛、膝上横琴、石枰下棊、扫雪煎茶、美人淡妆篸戴。”所谓“花宜称”,是指与梅花十分相配之景物。在周密所提到的二十六种景与物中,本词所涉及的就有晓日(朝眠)、薄寒(沉香断续玉炉寒)、细雨(疏雨)、纸帐、林间吹笛(笛声三弄,梅心惊破)等五种,可见,在本词中,虽然藤床、纸帐之类的物事可能真实地反映了词人当时的生活状态,但是,除此之外,词人善于以与梅相配之物与景入词的意向是较为明显的。
因此,上述景物作为梅之伴侣的出现,并不是偶然为之,而是体现了词人深细的修辞用心。这一点,如果不是对宋代相关物事在诗词中的运用习惯有所了解,大约是无法体味到的。明于此,我们到现在才真正了解,《孤雁儿》虽为李清照悼念丈夫之词,但在词的谋篇布局上,在词的修辞手法上,她仍然严格遵循了咏物之作不明言所咏之物,但事事与所咏之物相关这一规律,而且,清照的高明之处又在于她不泥着于所咏之物,而是在遵循咏物词基本规则的前提下宕开去,抒发了自己内心深重的伤痛之感,而使人读来以为只是悼亡,忽略了其咏物的色彩。至此,我们也明白了,清照词中小序颇为少见,何独本词前偏有小序。词人大约是通过小序告诉读者,这首词仍然是一首咏物词,而她对于“不俗”的追求,又使这首咏物词不同于绝大多数同类题材之作,因此,词前小序又不仅仅是在标明咏物词的特质,而是藉此使人明了本词的高出常人之处。以咏物方式写悼亡之情,高哉清照。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