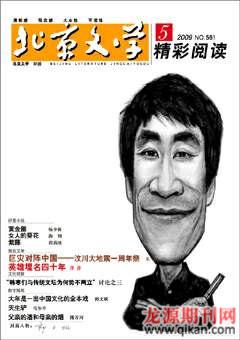鸡头
补 丁
王福因为抢了金水泉的鸡头吃,导致他爹被斗而死。从此,王福每年给金成送鸡头,金成每年给王福爹的坟扯草。这样已经22年了。王福给金成送鸡头到底要送多久呢?
8月21日,是王福刻骨铭心的日子。
秋风一扫,王福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年过四十的他荡漾在秋风中,浑身都充满了鸡的那种有点腥臭的味道。自13岁起,这种味道就一直伴随着他。但这种味道只有秋天才会聚拢,所以一到秋天,巴子营的鸡看王福都是怪怪的,王福眼里所放射出的杀气令它们老翻跟头。
一到8月初,王福都会买鸡,从1973年起,年年增加一只,今年已增加到22只了。买到鸡后,他用特制的笼子关了它们,像伺候老婆月子般精心。8月20日晚上,他用一根长竿挑了灯,让家人端来脸盆。青色的刀闪着幽光,在夜幕下飞起道道寒光,鸡头迸起来,又沉重跌下,血腥味便弥漫了整个巴子营。
鸡头被洗得干干净净,鸡嘴里的秽物也被掏得光光的,对着鸡头,王福脸上爬上的狰狞令家人不寒而栗。这时候,即使他的老母,也不敢丝毫打搅他。凝视一阵鸡头后,他将每年用来盛鸡头的篮子从房梁上解下,仔细地洗涮,篮子被洗得发白,他再上一层清漆,洁白的篮子装进洁净的鸡头,相得益彰。鸡头们都望着王福微笑,只等8月21日一到,就伴随他去完成一年一度的使命。
2005年的8月21日,王福起得很早。秋日的巴子营清晨凉凉的,几只叫不出名字的野鸡起得比王福还早,它们悠闲地在秋庄稼地里寻觅属于它们自己的东西。王福的到来影响了它们的宁静,它们扑扇着翅膀,怪叫几声,到别处去了。从村里转一圈回来,王福仔细地洗了脸,漱了口,换上崭新的衣服,来到了金成的家门口。金成家笼罩在一片薄雾之中,王福篮子的鸡头一个个直立,仿佛用手一拍就会飞起来。门楼上的琉璃瓦沐浴在阳光中,一点一点闪光。
“金书记,我送鸡头来了。”王福高声喊道。
隔壁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金成的儿子金水泉提着一把铁锨冲了出来:“王福,你有完没完?”
王福小心地回答:“又是8月21日呢,我只不过给金书记送鸡头来了。”
水泉拍拍铁锨把,“20多年了,你爹埋在地里都成灰了,我父亲千错万错,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你还想干啥?”
王福掂了掂篮子:“你看你看,大清早生什么气?我爹死了化作了灰,金书记还活着,只要他活着,我就得孝敬他。”
“你还不如杀了他。”水泉吼道。
“听听,听听,我怎么能做犯法的事?我是真心实意来看金书记的。”
水泉举起铁锨,身后苍老的声音喝住了他:“只要他有心,你就让他送,让他进来。”
王福进了屋,将一篮子鸡头倒在桌子上:“金书记,祝你活得千秋万代。”他恭敬地鞠了一躬,转身出门。
一声沉闷的响过后,鸡头都隔墙飞出了院子。王福一只一只将鸡头捡起来,数了数,还差一个。他拍了拍门:“金书记,还差一个,别的我都放在门口了。”
1972年,巴子营弥漫着一种饥馑,细细的尘土也在呻吟出一种饿音,小草懒得伸直身子,瘦成一把的羊缓慢地挪动着脚步。庄稼在疯长,干瘪的穗头连麻雀也不想光顾。开完三干会的金成斜披着衣服,口袋里塞着几个雪白的馒头,这是他节省下的,他可以想象出家人看到那几个馒头的喜悦,尤其是他的水泉,凭其中一小块馒头就能在巴子营孩子们中间树起威信。金成踩起的土跟在他身后,慢慢下落,几只苍蝇不时落在他的肩膀上,嗡嗡直叫,他扯下衣服一抖,一只馒头刺猬一样滚了出去,金成猛跑几步,拾起馒头,扑扑地吹掉上面的土,哼着《红灯记》插曲进了村。
他也闻到了村中因饥饿散发出的气息。
饥荒年并未消减人们“多快好省,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骑着自行车的县、公社两级干部也被这种热情感染,他们挥锨上阵,大战在平田整地现场。金成趿拉着鞋,拉着一辆架子车在奔跑,鞋底与脚板打起的声音很快引起一位县上干部的注意。
“穿这样的鞋能劳动?”
金成搓搓手:“没办法,老婆白天要战天斗地,晚上要点灯学习,没时间做。”
县上干部摇摇头,从自行车后座的一只挂包里掏出一双胶鞋:“试试,能不能穿上?”
金成不接,县上干部火了:“是怕腐蚀呢?还是怕拉拢呢?男人一双脚,保护不好如何干社会主义?”
金成只好接了,试试,合脚。县上干部指着金成那双鞋,对通讯员说:“带回去,进行阶级教育展览,让大家千万不要忘本。”
金成第一次穿胶鞋,因没衬鞋垫,脚板在鞋中滑动,一走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鞋面很快就没了本色。金成很心疼,待人家不注意时,脱了鞋,仔细磕掉土,包在衣服中。
县上干部在回大队吃饭的路上发现金成光着脚,问他为什么不穿胶鞋。他自豪地说:“留下在重要的场合穿,我的脚皮实着呢!”
为感谢县上干部的这种礼遇,金成杀了家中的一只鸡,鸡的香味很快就漫出,巴子营的男孩都聚拢在水泉家的门口,他们用鼻子嗅着香味,用手抓着香味,然后坐在地下,非常幸福地搓着手。大门吱呀一声开了,金水泉手捧着一只鸡头走了出来,一个男孩掏出口袋里的一只玻璃弹,对金水泉说:“给你这个弹子,让我们闻闻香好吗?”金水泉认真地说:“说好你们不能吃的。”男孩们都说:“我们只过个干瘾。”
孩子们闻鸡头时,金水泉又跑回院中,拿出那双胶鞋夸耀了一番,大马金刀坐在院门前的石头上,啃起了鸡头。胶鞋像两只老虎静卧着,黄黄的色彩很惹眼。水泉用舌头舔着鸡头,吮吸着,他的每一次动作,都刺激着王福。王福的喉咙在蠕动,他看到一点油渍沾在水泉的脸上,像颗痣般炫耀,他慢慢挪动脚步,悄声无息地行进,眼睛紧紧盯着水泉的手,看他把鸡头舔过来舔过去,就在水泉手中的鸡头离嘴的时候,他扑过去抢了鸡头,转身就跑。
金水泉被王福的举动惊得跳了一下,待他回过神来,王福已没了踪影。“我的鸡头!”他大叫一声,追了过去。“胶鞋。”跟着他的伙伴喊道。他转过身来,抓起两只胶鞋又追起来,两只鞋在他手里张牙舞爪,黄亮亮地,像两只死了的兔子。王福穿过田埂,奔过沟坎,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下坐下,尽情地啃咬着那只鸡头,他瞅着鸡头上小小的耳朵,用手拨了拨,小耳朵动了一下,他用舌头舔了舔,没什么味道,越来越近的叫喊声猛然使他惊醒,他张大嘴巴,揪住鸡头,两排牙竭力配合,一只鸡头很快成了碎骨头。
看着王福手中的一小堆骨头,金水泉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我的鸡头!”他扑上去揪住了王福的衣领,王福那只可怜的衣领像旗帜般飘了下来。“打,打!”跟随金水泉而来的伙伴们围住王福,殴打起来。王福护着他的手,任凭他们把拳头砸在他的头上,脚踢在他的腿上。待他们打累了,他望着留有余香的手指,一根一根吮吸起来。
将军般凯旋的金水泉发现手中提着的胶鞋帮上有了几点油渍,他明白这双鞋在他父亲心中的分量,他举起鞋,对着太阳看着,他盼着阳光能像水般把油渍吸收,但阳光下的油渍越发耀眼,他便抹起了眼泪。跟着他的伙伴一哄而散,他们比金水泉还怕金成,如果这事牵扯到他们,父母一年的劳动收入就会打折扣,他们没有必要令父母遭殃。
金水泉来到村外的河边,用青条石砌成的河刀削般对立着,河水笔直地往下淌。他找到人们打水的河台,把鞋伸到水中,用手使劲抠洗油渍。午后的出工哨响了,他母亲的叫唤声由远及近,炸雷般吼叫的父亲令他心惊胆战。他的手一松,那只鞋鱼般游到了河中,飘摇着往下冲去。他顺着河岸追起来,直到看不见它的踪影了,才停下脚步,午后秋庄稼的香味在他的嗅觉中一下子失去了原有的滋味。
平田整地大会战胜利结束,巴子营荡漾在一片喜庆中。县上决定在巴子营召开现场会,被树为典型的金成要在会上重点发言。
对金成和巴子营来说,这是难得的荣耀,金成的脚步轻快地飞驰在巴子营的土地上。他给老婆放了一天假,要她在一天之间绣一双鞋垫:“到那天,我要穿上县领导送的那双胶鞋,万人大会啊,要不是毛主席,我金家哪来的这种荣耀。”
“鞋掉进了水中。”他的老婆怯怯地说。问明了缘由,金成一屁股坐在地上,没有了胶鞋,他的荣耀就打了折扣。
左脚穿胶鞋右脚穿布鞋的金成跳跃在一片红海洋中,他佩戴着大红花,以农民特有的腔调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县上领导端坐在台前,有节制地鼓着掌,他在低头掸鞋上的灰尘时发现了金成脚上所穿的不同的鞋。
“为什么穿不一样的鞋?”
金成不知怎么回答,只好站在一边。“穿不一样的鞋的人革命立场是不坚定的。”县上领导气咻咻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金成一有空闲就削一块木头,免了一顿揍的金水泉也以高涨的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有点木工基础的金成画好了图样,一刀一刀地削着木头,当一个木鸡头呈现在眼前时,金水泉跳了起来。
“爹,您把这个鸡头涂上颜色,我挂在脖子上,天天就能闻到鸡肉的香味了。”
金成一巴掌拍到他的头上:“没出息的东西,烧火钳去。”
金水泉便拿了铁钳,伸到炉子里烧。炉子是用土坯砌的,几块质量不高的煤球在炉中发出暗红色的光,听金成的骂声又起,金水泉慌忙抽出火钳,拿给了金成。火钳头与木头相触,几声的蓝烟冒过,便没了动静。金成叹口气,索性蹲在了火炉边,边烧边烫,一个黑黑的小洞贼眉贼眼地在父子俩眼前晃动。
“去找根铁丝!”
金水泉翻腾了半天,没找到,便悄声细气地告诉金成。
“你有本事把胶鞋掉进水里让老子出丑,没本事找一根铁丝?”
“家里没有,我不能去偷吧。”
“榆树边上长倭瓜,能了你。去,把羊圈门上的铁丝抽一根来。”
铁丝穿进洞中,金成绕了一个圈,套在自己脖子上试了试。
“爹,您要戴这个么。”金水泉拍拍手:“你天天戴在脖子里,会更威风。”
“威风你妈个头。”金成斜披衣服出了门。
秋日的夜晚有点凉,巴子营人挤在大队的会议室中,谁也不知道今晚要开什么会。看着人到得差不多了,金成一拍桌子,喝令基干民兵将王福的爹押到斗争台上。
“为一只鸡头,让咱巴子营人丢脸啊,一只胶鞋是什么,那是巴子营人的荣耀,让我金成出丑,是让整个巴子营出丑,斗!”
拴有铁丝的鸡头挂在王福的脖子里,金成让金水泉上台揭露王福的丑恶嘴脸,“这,全是王福他爹教的,他就是不让咱贫下中农过好日子。”
“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论成分,我家可是三代贫农。”王福的爹争辩着。
金成一拍桌子:“还不老实,革命队伍里就不出坏人了?真是的。”
木鸡头晃动着,王福的爹耷拉着头,耳朵里传过的吵嚷声被风打湿,寒凉地贴在他的耳边,他紧紧攥着右手,左手的指头配合着弯曲成了一个鸡头,他努力地抬起了左胳膊,弯成鸡头的左手高傲地挥旋了一下,身子便歪歪地倒在地上。“鸡头。”他努力地哼出了最后一句话。埋葬了爹,王福坐在鸡舍前,一动不动,他妈泪眼婆娑,摇晃着儿子。“福娃,你爹走了,你可不能再傻了。”
王福咧了嘴,看着鸡舍里的那只母鸡无忧无虑地走动,他说:“妈,我要个鸡头。”
他妈一听鸡头,浑身哆嗦了一下:“娃,可不能再提鸡头了。”
“我就是要个鸡头。”王福站起来,狠命地踢了一下鸡舍,那只母鸡惊恐地叫起来。
等妈抓来鸡,王福把鸡翅膀反剪起来,母鸡在地下挣扎,“娃,杀了鸡,我家就没有买盐的鸡蛋了。”
“以后我家再不养鸡,”王福抢过他妈手中的菜刀,一刀就剁下了鸡头。没了头的鸡满院子飞转,王福仿佛又闻到了鸡肉的香味。
从来没有洗过东西的王福洗着鸡头,鸡头已被他洗得发白,他还是揉搓着,他不放过一根小小的茸毛。他的母亲站在旁边,不知儿子要做什么,只能默默流泪。洗好鸡头,王福又找出一只篮子,磕掉灰尘,在篮底垫上一层草,然后提了篮子出门。他走得很慢,秋虫在他脚下呻吟着,露了黄尖的草匍匐在地上,有点凉意的风吹起他单薄的衣服———那件已没有了领的衣服。
父亲坟前,他恭敬地跪下,弯曲着大拇指和中指,反复比划,最终,一个鸡头造型便出现了。他不禁佩服起父亲了,他临死前居然轻易地用手指弯出了鸡头造型。
在父亲坟前埋了鸡头,王福回到家中,将那只篮子吊到梁上。之后,巴子营大队增添了一位干活特别卖力的小社员。
1973年的8月21日清晨,王福将买来关了半月的一只鸡杀了,洗好鸡头后,他穿上了新衣服。母亲问他去做什么,他笑了笑,拉下了梁上的篮子,把麻纸打好的纸钱装好,径直到了父亲坟前。刚刚一年,父亲坟上的土还带着点新意。王福用手拨拉起几把土,塞住了坟左侧的一个洞。他拍拍篮子,篮里的鸡头跳动了一下,惊得一群麻雀没命地飞奔起来。
金成家的大门半开着,王福一进门,腿软了一下。看见院里奔跑的鸡,爹脖子上挂的那个木鸡头又展现在眼前,他双手端着篮子,恭恭敬敬进屋,放在了金成家的供桌上。
“金书记,我给你送鸡头来了。”
金成斜坐在凳子上,“你不怕我把鸡头再挂在你脖子里,像你爹一样批斗?”
“我怕。”王福小声答道。
“怕为啥要羞辱我,你当我不知道你肚里的那点小九九?”
王福低着头,用左脚轻轻踢着地下。金成掐灭了烟,“把篮子拿走,好好劳动,争取当个好社员。”
王福捧出鸡头,住桌上一放,提起篮子走了。金成叹口气,把鸡头扔给了狗。
1974年的8月21日泡在漾漾的雨中,金成靠在被窝上,隔着窗户看雨刷刷地往地下落,雨中传来的拍门声有点沉闷,金水泉跑去打开了门,王福顶着一头雨水进来,“金书记,我怕鸡头淋雨,用塑料包着,今年是两个,你看,一只公鸡头,一只母鸡头。”
金成挥挥手,王福走出了金家,没入了雨中。金水泉抓起桌上的一把菜刀,“你想干啥?”金成瞪了他一眼。
“我砍断他的腿,看他还送鸡头?”
金成长叹一声,“你砍断他的腿,他送的就不仅仅是鸡头了。”他拉开被窝,喃喃道:“又不是我有意的,你爹想不通爱死,我有啥办法?谁让你让我丢了荣耀。”金水泉问道:“爹,你说啥?”金成拉拉被窝,“只要我活着,他可能会年年送鸡头来,唉,人一辈子,何苦呢?权当每年让他供一回吧。记住,可再不敢惹祸了,在巴子营,活人讲究的是理数。”
金水泉把菜刀狠命地扔到了门外。
岁月就这样在王福每年送鸡头的行为中移动着,金成拄着拐杖,走进了2006年的夏天。巴子营雨意霏霏,连续几年的风调雨顺让地里的野草增添了不少,王福父亲的坟上绿意盎然“养儿子还要看老子死后啊。”金成用拐杖捣了捣王福爹的坟,他坐下来,一把一把扯着坟上的野草,“我已经扯了22年了,只要我死在8月21日前,你家王福的鸡头就再也没办法送给我了。我就不信,斗得过你,斗不过你儿子?”他抓过拐杖,将扯下来的一堆坟草打得七零八落,有几根草落在了他的头上,他用手扯着,仿佛他的头发都成了王福父亲坟上的草。
作者简介:
补丁,本名李学辉,男,生于1966年,甘肃武威人。当过教师、记者、编辑,现任武威市文联副主席、武威市作协主席,《西凉文学》主编。上世纪90年代步入文坛,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有作品被《小说月报》选载。曾获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出版有短篇小说集《1973年的三升谷子》《绝看》。中国作协会员、甘肃省文学院荣誉作家。
责任编辑 章德宁白连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