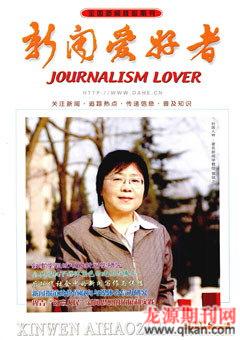简析中国音乐评论的现状
袁小娜
音乐评论是一个早就存在的人的审美评价活动,可以说自从诞生了人类的音乐,就伴生出对音乐事项进行评价活动的“音乐批评”。
追溯我国最早的音乐评论可以从先秦两汉的《礼记·乐记》、《乐论》算起,其中的评论言论信手即拾,诸如“《韶》尽美矣,又尽善也”、“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等,这些诗句真实而生动地传递出听乐者或描述或议论的现场信息,器乐、声乐无所不包。“唯乐不可以为伪”直到现在还在指导我们的创作思想,引起我们的审美共鸣。白居易的《琵琶行》应该就是一篇典型的诗词文体的音乐评论,其中的“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这些词语形象生动,闻者如临其境。也是今天我们的音乐评论中使用率极高的佳句。
什么样的文章算是乐评?似乎没有一个严格的界定。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秘书长明言给出的定义是:“音乐批评是以文学、哲学、美学、社会学、历史学、工艺形态学等单纯的或综合性的理性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现实事项与历史事项的一种理性建构活动。”从狭义上讲,就是指对音乐作品评论和音乐会评论。
在音乐艺术的传播过程中,作品原创、演绎再现和接受审美构成了不可或缺的三位一体。音乐评论家的任务是在音乐家和听众之间架起桥梁,但评论家面向的主要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是为听众解释音乐家的所作所为,为听众揭示音乐家创造成果的审美意蕴、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正像英国小说家爱德华·摩根·福斯特认为音乐评论的主要功能有二,其一,它能刺激我们的感官,使它变得更为敏锐,从而更易发现以往被我们所忽略了的音乐中的美感;其二,它能够纠正我们在听音乐时流于肤浅,或者满足于停留在仅仅见其华丽的表面上。因此,看一个国家或地区音乐修养和欣赏水平如何,只需看其主流媒体上的音乐评论是否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音乐事业没有哪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备受国际音乐界的关注,音乐演出市场空前繁荣,每年,无数国外艺术家、演出团体蜂拥而入,在中国观众有幸欣赏到世界一流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良莠不齐、泥沙俱下带来的影响。所以,面对演出市场的日益扩大、音乐需求的快速扩展,正确评价艺术的优劣,对音乐生态环境和音乐质量开展批评与监督,为音乐大众提高欣赏艺术能力的音乐评论,就显得更为重要。然而,我国目前的现状却是“缺乏高水平的音乐评论,缺乏高文化含量的音乐评论,缺乏带有批判意识的音乐评论。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音乐评论成为音乐界最贫瘠的地带之一,它常常在重要的音乐活动中缺席,常常在需要它讲话的时候失语,常常是一杯不热不烫的温吞水,常常是一株顺风摇摆的墙头草。”(梁茂春《呼唤新的音乐评论》)比起电影、文学、美术、体育、戏曲、娱乐等领域里的批评和评论都相当活跃的局面,音乐领域尤其是严肃音乐圈还保持着一种水泼不进的“和谐”平静。
不少音乐人士抱怨:中国没有音乐评论。其实音乐评论并非没有,在各音乐学院的学报以及文艺理论刊物中,音乐评论一直在很专业和很高层面上进行着。但是我们明白音乐家们的抱怨其实是指报纸上的音乐评论。在报纸上我们能看到的音乐家专访和音乐会报道,多是“引起轰动”、“爆满”、“精彩绝伦”之类的陈词滥调,满足于报流水账,而对采访者的艺术风格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对音乐演出活动的成败得失没有明确的评判,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常规性错误,让人看了不知所云、啼笑皆非、兴趣索然。
写音乐评论的人可分为三类:一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或曾经从事过专业音乐工作的;二是没有专业学习过,或仅是涉猎过;三是对音乐几乎是“门外汉”。一般情况下,后两种纯粹是出于对音乐的爱好和热情才走上乐评这条道的。他们大多在传媒领域跑音乐口,“文化乐评人”可能是对这个群体一个更准确的称谓。这就导致了近20年来构成“乐评人”主体的往往是搞中文、新闻、法律等文科专业或其他专业的,真正活跃在媒体上的出自专业院校的极少,形成音乐批评的生态失衡,谈感觉的太多,谈音乐本体的太少,谈技法的太少,这种情况会严重影响到中国大众音乐的发展。
评论人才匮乏是导致这种现状的原因之一。全国音乐院校很少有定位于音乐批评的培养方向,大部分学生的目标还是“学者型”。上世纪80年代还有一批学者对社会音乐活动颇为关注,但近年来则大部分专心于著书立说或者担任越来越多的教学任务而从评论界退场。音乐评论家应该是对音乐专业的各方面都有很深入的了解,而且还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其次,他还应该在媒体上占有一席之地,譬如一名记者或一名编辑。如果从音乐家这个角度讲,他们从小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学习器乐上,根本无暇涉猎与音乐评论相关的文史哲等学科知识,让他们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常常有一定的困难。当然,音乐家中也有少数写作高手,只是他们不可能整天出入音乐厅,忙着写评论。如果他们能在某个媒体上占有一席之地,或许就能改变“中国没有音乐评论”的抱怨。这就需要我国有条件建立音乐院校的,要尽快建立这个新的、重要的专业,从年轻的学生中培养出一代新的、杰出的音乐评论人才。
其次是媒体平台的缺失。刊登音乐评论文章的媒体平台可划分为三类:社会性报纸、音乐报刊和高校学报。社会性报纸给予主流音乐的版面是少之又少,可以说是“节约+慎重”,所报道的音乐会或音乐信息也呈豆腐干状大小。音乐报刊在中国屈指可数,如《音乐爱好者》、《人民音乐》、《爱乐》、《音乐周报》、《音乐生活》等以及像《爱乐者》、《大剧院之友》、《音乐厅之友》等之类的赠刊。而高校学报,曲高和寡、学术性强,受众面小,很少有即时性的音乐评论。在这种状况下,真正有质量有观点的音乐评论并不多见。而那些真正能写乐评的人却面临“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常常是在私下的场合或网络间发表言论或发帖子,这些不乏中肯和精彩的乐评,除了少量经过编辑大段删除、反复修改而成为较为“中性”的文章发表以外,“触及时弊”、“切中要害”的文章永远也上不了正规媒体的平台。在中国,缺少音乐评论的媒体平台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我们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法国的《费加罗报》,英国的《泰晤士报》、《独立报》等许多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以及电台、电视台,都毫不吝啬版面,设有固定专栏,每天都有音乐评论的文章与读者见面。所以,要想改观音乐评论的现状,就需要我们的报纸和音乐类杂志开辟专有的园地,并且能顶住风浪,长期坚持,这样就能吸引更多的读者和音乐爱好者,提高观众的鉴赏能力,由此还能进入一种良性循环,进一步激活演出市场,从而为观众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音乐演出。
再一方面,就是缺乏健康的音乐评论氛围。音乐创作和音乐批评是艺术发展道路上的两条辙、一根藤上的两个瓜。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好比放风筝,如果说风筝是音乐创作,那么线就是音乐批评,扯着线的目的是不让风筝掉下来,而是让它越飞越高。现在的状况是,我们的音乐批评对国外来的演出尚能说一些客观公正的观点,而对国内的演出提出批评,难度就大了,这就会涉及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解决这个问题,其一是作为评论者,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全面修养和专业素质,力求做到独立而又客观,言出由衷;其二,被评论者也需要有宽广的胸怀,只要是从艺术出发,只要是真情、真话,就应正确对待,而不要吹毛求疵,更不要大动肝火。其实,没有任何反应的演出才是最平淡、最没有价值的。职业音乐家在意的不应该是鲜花与掌声,而是媒体上的各类评论。在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柏林,那里的乐评家们犹如“音乐法官”,音乐评论俨然像“一纸判决”。当年小提琴家斯特恩的首场音乐会,《纽约时报》的一篇乐评,使他赌气出走整整一天;钢琴大家傅聪说自己“每场音乐会就像英雄就义”;帕瓦罗蒂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一个高音C破音,演出费被扣除后乐评给予恶评等,都说明音乐家们在媒体的压力之下,对自己的艺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可见,舆论的力量对于音乐家或者音乐大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和不可或缺。
音乐生活是一个大宇宙,音乐评论是其中的一个小宇宙。音乐评论的繁荣要依赖音乐大宇宙的整体繁荣——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音乐出版等的发展。希望我国在音乐评论方面能够做出新的努力,产生新的成果,与我国快速发展的音乐生活并驾齐驱,促成音乐大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也是乐评媒介所应担负的社会责任。
编校:杨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