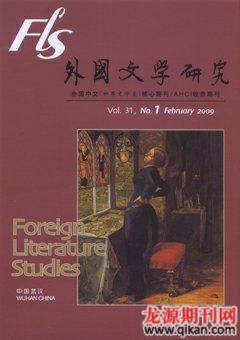伦理权威与宗教救赎:论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密友形象
杜 娟
内容提要:亨利·菲尔丁小说中的密友形象,不论是《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亚当斯牧师、《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先生,还是《阿米莉亚》中的哈里森博士,都凭借其高尚的个人道德引导着主人公的道德完善。这些形象的塑造其实暗含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意图:一是通过对他们多重身份的描写,揭示出密友形象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体系。而主人公被他们重新接纳的情节线索,则寓示了主人公美德有报的命运结局,即个人道德的社会认同。二是通过集中描写密友形象的道德状况,展示了美德在现实中软弱无力的际遇。在此基础上,作家提出了宗教对于人们道德困境的救赎功能。而他对宗教和道德关系的思考,则充分显示出菲尔丁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辩证思维。
关键词:亨利·菲尔丁密友形象
伦理权威宗教救赎
作为帮助主人公道德完善的重要角色,密友形象在菲尔丁笔下得到了浓墨重彩的生动描绘:不论是《约瑟夫·安德鲁斯》中的亚当斯牧师、《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先生,还是《阿米莉亚》中的哈里森博士,都凭借其高尚的个人道德引导着主人公的道德完善。在塑造这些次要人物时,菲尔丁对他们各自身份的设置颇具匠心,他们既是主人公的父亲代理人形象,又是作品中的伦理权威与道德法官,甚至是宗教劝诫者。在主人公道德完善的不同阶段,这些密友形象往往以截然不同的身份出场,大大影响了主人公的道德完善。本文即从他们的多重身份人手,力图揭示其中蕴含的叙事意图和道德内涵。
一
在密友的多重身份中,父亲代理人身份尤为重要。由于约瑟夫·安德鲁斯、汤姆·琼斯和比利·布思等主人公基本上都是些身份未明的人物,因此他们在自己的道德完善中,就急需一位父亲的替身,以便帮助他们从道德迷失的精神困境中警醒过来。而扮演了主人公父亲代理人身份的亚当斯牧师、奥尔华绥先生和哈里森博士,也的确以实际行动回应了主人公内心情感与道德诉求的双重渴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人物的父亲代理人身份,实际上是菲尔丁专为解决主人公的身份谜团而设。前文曾经说过,由于主人公的身份谜团大多与其家庭的破碎有关,因此他们在冒险经历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摆脱孤独、回归家庭的本能愿望——因为这样做可以凭借家庭的重建,去补偿他们起初对自己身份未明的痛苦。而亚当斯牧师、奥尔华绥先生和哈里森博士等人的出场,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人公内心的焦虑,同时也为他们的道德磨砺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关这些密友的作用,可参照“仁爱开始于家庭”这一古老的英国谚语,即意为只有当主人公首先获得了某种家庭温暖,其仁爱之心方能自然生成。若循此逻辑,那么当身份未明的主人公出场时,他们首先遇到的密友便成为了家庭的隐喻符号。菲尔丁对这类密友形象的书写,可谓直接贯彻了上述伦理思想。
在他笔下,几乎每一位主人公都有身边的密友充当父亲代理人角色,而他们也对主人公怀有家长般的特殊情感,并对推动主人公的道德完善提供了巨大帮助。如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亚当斯牧师要去伦敦刻印三本经义,不过当他遇见受伤的约瑟夫后,就陪护在主人公身边,还将自己口袋里的九先令三个半便士,全数尽供约瑟夫用。等约瑟夫伤愈后,亚当斯牧师又宁可自己步行前往伦敦,也要将所剩无几的钱财送给约瑟夫当路费。按他的话说,就是“无论什么行业的人,都应运用自己的才能免费解除贫穷和困苦”(The Adventuresof Joseph Andrews)。亚当斯牧师称呼约瑟夫和范妮为自己的儿女,还说“上帝交给他指教的堂区居民,他都当作儿女”。正是在这一父亲代理人的道德教化下,主人公约瑟夫才会时时刻刻以亚当斯牧师的教诲为道德准绳,后者实际上成了约瑟夫的道德监护人。至于《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先生,更是以菲尔丁的文坛保护人和赞助者拉尔夫·艾伦(Ralph Alien,1693-1764年)为原型。拉尔夫·艾伦曾任巴思邮政局长,尽管出身低微,却致力于改进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邮政制度,并因购买了一个价值巨大的采石场而变得极为富有,他不仅是一位慈善家,更是作家的庇护人。菲尔丁早在生前便得到过他的资助,在作家去世以后,艾伦还继续资助菲尔丁的孩子接受教育,并将自己的部分遗产转赠给了他的家人。由于这些缘故,菲尔丁才以极大的热情赋予了奥尔华绥先生令人景仰的高尚道德。在作品中,奥尔华绥先生虽然曾有过三个孩子,但他们都还在襁褓中就不幸夭折,更令人同情的是,他的妻子也先他离世,孤独的奥尔华绥先生只能和他的妹妹归隐乡间。正是这种亲情的匮乏,才促使奥尔华绥先生将琼斯和布利非视同己出。他不仅当了琼斯的教父,还按照自己的名字给琼斯起名为托马斯。作为一位心地善良,同时又继承了一笔可观遗产的好心人,奥尔华绥先生本身就具有乐于助人的高尚美德,他在周济别人时,“不但总设法不让世人知晓,甚至也不让受惠者本人察觉。他一向用‘借或是‘付给的名义,不说是‘赠与。尽管他在大量施舍,却总竭力用言语来冲淡他所做的好事”(《汤姆·琼斯》)。正是有这样一位集美德与财富一身的父亲代理人存在,才大大推动了主人公琼斯的道德完善。
同样的密友形象亦存在于菲尔丁的另一部作品《阿米莉亚》中——哈里森博士富有才识,比起主教来也毫不逊色,但他连一百磅的财产也没有,原因是他一半以上的收入都用于救济和布施了。作为主人公布思的密友,哈里森博士不仅在他陷入绝境时出手相助,更为主人公的道德完善和成长起到了监督和促进的作用。当布思和阿米莉亚的爱情看上去了无希望时,哈里森博士适时而出,他费尽唇舌才说服阿米莉亚的母亲同意两个年轻人结婚。即便后来另有一位富裕的求婚者温克沃思先生出现,哈里森博士也不顾阿米莉亚母亲的反对,极力促成了布思与阿米莉亚的结合,他也因此被布思称之为“忠诚而热心的朋友”(《阿米莉亚》)。如果仅从年龄上看,只比布思大两岁的哈里森博士似乎与父亲代理人的角色难以匹配,但他却以实际行动尽到了一个父亲代理人所能承担的全部责任。当阿米莉亚的母亲去世以后,哈里森博士在写给布思的信中,直接称呼两个年轻人是“我亲爱的孩子们”,并解释说“我现在将这样称呼你们,因为你们两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其他的父母亲了”(《阿米莉亚》)。事实上,他也的确成为了布思夫妇的保护者。在布思退伍以后,哈里森博士与布思夫妇一起居住在他的教区之中。这是一个牧歌式的田园社会,哈里森博士“把他所有的教区居民都当做自己的孩子对待,而他们则把他看成自己共同的父亲”(《阿米莉亚》),他也把“这座朴实无华的房屋称为地上的天堂”(《阿米莉亚》)。从中流露出来的家庭温暖与亲情,实际上成为了促进布思道德完善的重要推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尔丁在小说主人公的历史中,特意安排一些密友形象充当父亲代理人角色,本身就具有一种推动主人公成长的功能性叙事意图。换言之,密友形象的父亲代理人角色,其实是主人公实现自我道德完善的一个客观条件。假如没有这些人物的道德指引,琼斯等主人公就会在各自的冒险旅途中孤立无援,他们也无法感受到那些足以催生仁爱之心的家庭温暖。
二
需要强调的是,菲尔丁对于密友形象多重身份的设置,还体现了他对于人物个人道德的一种社会要求。除了父亲代理人角色之外,菲尔丁小说中的密友形象还充当了一个伦理权威的角色。比如亚当斯和哈里森博士都具有牧师身份,作为上帝在世俗社会的代言人,他们显然拥有足够的话语权力去判断世俗社会的道德善恶,同时也能依据每一个人的价值选择去裁定他们的道德状况。而这种伦理权威和道德仲裁者角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促进主人公道德完善的试金石。至于奥尔华绥先生,虽不是牧师出身,但他作为当地的保安官,却同样有权力去判断他人的道德状况。在《汤姆·琼斯》这部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奥尔华绥先生依据美德标准所做出的种种道德仲裁,因此可以说他和亚当斯牧师、哈里森博士一样,都充当了伦理权威的特定角色。
如果仅就菲尔丁小说的某种叙事模式而言,就会发现在主人公与其密友之间的情节线索中,故事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他们往往因误会或别人的挑唆而发生矛盾,作为父亲代理人和伦理仲裁者,密友会以驱赶或责备的方式对主人公进行某种惩罚,但随着主人公踏入冒险旅程和个人道德的渐趋完善,他们又会重新接纳主人公的回归。比如奥尔华绥先生误信人言,以为琼斯已道德堕落,无可救药,遂迫使主人公离家出走;哈里森博士也一度误会了布思,认为他已经变得虚荣奢侈,为了对其施加惩罚,博士亲手把主人公送进了监狱。当然,小说都会以大团圆的完满结局收场。在这一叙述模式中,密友形象作为父亲代理人和伦理仲裁者,其实代表了一种普世的社会道德。当他们以自己所坚守的这一道德体系去衡量主人公时,会发现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种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相分离的现象。比如琼斯的任性卤莽、布思的优柔寡断等品行,就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社会道德。而主人公的道德完善,其实就是一个个人道德向社会道德的回归过程。我们注意到,在菲尔丁小说主人公的道德完善历史中,诸如谨慎、自爱等个人美德的形成,往往都以他们付出自己的个性为代价。例如琼斯的成长历程即为典型一例。他从一个不谙世事的莽撞少年,成长为一个理智与情感兼备的道德圣徒,其间经历了无数的自我拷问与道德磨练,最终才重新获得了奥尔华绥先生的青睐。这就是说,在密友所代表的权威身份与主人公的道德完善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个冲突与磨合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实质,就是个人道德向社会道德的回归,也是菲尔丁美德有报伦理思想的一个具体表现,即主人公的道德完善终于得到了父亲代理人和伦理权威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美德有报指的就是主人公个人道德的社会认同。由此可见,菲尔丁之所以将密友设置为主人公的父亲代理人和伦理仲裁者角色,目的就在于为主人公的美德有报寻求一种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价值归宿。
在他看来,那些以追求个人美德为目标的道德主体,惟有将自己的道德历练融入一种普世的社会道德才会具有现实价值。小说中密友与主人公的矛盾冲突形象寓示了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某种分离局面,随着他们最终的和解,这种分离状况也以个人道德向社会道德的回归而宣告结束。这就是说,建立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体系,远比纯粹追求一种个人美德的历练更为重要。归根结底,个人道德必须建立在社会道德之上。菲尔丁这种注重社会利益和理性道德的伦理思想,不仅表明了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充分反映出他对于道德问题的一种深入思考,显然具有一种普世性价值。由于受到了沙夫茨伯里情感主义伦理学的深刻影响,菲尔丁在强调社会道德时格外看重个人的公众情感取向。前者在其伦理学著述中,曾将公众情感界定为“衡量一个行为或行为主体是否具有道德价值的根本标准”(转引自黄伟合)。而菲尔丁小说中的那些密友形象,又往往因其伦理仲裁者身份代表了这种公众情感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主人公被密友重新接纳的情节线索,本身就说明了公众情感对于道德主体的重要影响。因此菲尔丁对于密友形象的道德书写,便集中展现了他借助这些人物所代表的公众情感取向去重建社会道德的伦理诉求。
如果说密友形象代表了一种足堪垂范的普世性道德价值,那么菲尔丁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就必定会格外关注他们的道德状况。因为只有树立起一系列具有榜样意义的道德形象,小说主人公向社会道德的回归过程才能被赋予积极的社会意义。然而,这些密友形象在作品中所处的道德处境却耐人寻味,尽管他们都代表了崇高的社会美德,但在各自的人生境遇中却屡陷窘境。事实上,对密友道德困境的描绘在作品中占据了一定的篇幅。那么,该如何改变美德在现实中软弱无力的道德现状呢?菲尔丁所使用的方法,其实就是用宗教力量去弥补社会道德的危机。为说明这一问题,有必要首先了解一下密友形象的道德特性。
在菲尔丁笔下,主人公的密友尽管大都具有某些弱点,但就他们的道德本质而言,却仍足以担当起主人公的道德榜样。他们在性格方面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为天性朴拙。例如《安德鲁斯》中的亚当斯牧师“完全不知人情世故,很像是初到世界的孩子。他从来无欺骗人的意思,就以为别人也不骗他。他为人很慷慨,很讲交情,勇气尤为过人,纯粹简单就是他的特性”。作品中的细节最能说明亚当斯牧师的朴拙天性,这位外表严肃的道德君子,说起话来却极为夸张,言语之间总是能够流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比如当他得知约瑟夫的病情好转之后,便“将手指捻得劈啪作响(就像他平素那样),在房里转了两三个圈,欣喜若狂”。约瑟夫和范妮团聚,亚当斯“又在房间里跳过来,跳过去,欢天喜地”。很显然,这是一位朴拙到了近乎迂腐的道德君子,他对于别人的用意,永远只会从好的一面去理解。以己度人的结果,自然会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能够热心待人。也正是由于这一天性使然,亚当斯牧师才会屡屡遭人欺骗。若论朴拙迂腐,《阿米莉亚》中的哈里森博士比起亚当斯牧师也是不遑多让。他“在所有的场合,特别是有什么事情让他感动的时候,他总是用一种强烈和奇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在菲尔丁看来,哈里森博士的朴拙天性,有时甚至造成了他在识别力和判断力方面的匮乏。比如,“……博士很喜欢接受那位老先生粗俗的谄媚,看来是个容易被人愚弄的人”(《阿米莉亚》)。从自己所具有的这种朴拙天性出发,哈里森博士大力颂扬了布思夫妇的自然淳朴,他希望借此能够否定现存社会中道德关系的虚伪和荒谬。这就是说,不论亚当斯牧师还是哈里森博士,其实都希望能够重建一种淳朴自然的社会道德。问题是他们的努力究竟换回了怎样的结果?
《阿米莉亚》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在面对詹姆斯上校的贪婪欲望时,哈里森博士所能做的,不过是给他写了一封义正词严的匿名信而已。当这封信在化妆舞会上被人意外捡到后,哈里森博士甚至还遭到了别人的嘲笑。这就是说,哈里森博士由于对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在面对恶势力的破坏时,哈里森博士也毫无有力的应对措施。从这一人物近乎迂腐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所希望的社会道德关系,即那种自然淳朴的道德境界在人性的复杂面前显得何等无力。因此,哈里森博士从监狱中保释出布思以后,却并
未解决后者的苦难境地。由于对手勋爵和詹姆斯上尉的邪恶用心伪装得十分高明,以致连聪明的哈里森博士也一度被蒙在鼓里。哈里森博士企图向一位贵族举荐布思,谋求一个职位也被拒绝。对于布思夫妇的人生苦况,哈里森博士可谓是始料未及。而这种美德无力的状况,同样存在于《约瑟夫·安德鲁斯》和《汤姆·琼斯》中。亚当斯牧师对于布比夫人一众对约瑟夫和范妮的刁难、胁迫,只能用苍白的言语进行说教,表明自己的立场,还不如约瑟夫懂得自己抗争。而喜欢对世人进行道德说教的奥尔华绥先生,虽然认为“在尘世间,过一辈子清白、规矩的日子,也比荒淫、放荡要快乐得多”,但他却无力拯救业已走向堕落的珍妮等人物。这意味着作为主人公密友的哈里森博士和奥尔华绥先生等人,他们所向往的社会道德体系遭遇到了现实人性的严峻挑战。但对于菲尔丁而言,如实描绘出一种道德理想在现实社会中的尴尬境遇,并不代表要否定乃至放弃这一理想。恰恰相反,在亚当斯牧师、哈里森博士和奥尔华绥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勇气。尽管他们的道德理想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但其主张却仍是人们群起效仿的道德典范。问题在于该如何去解决这一美德无力的现实状况?在菲尔丁看来,若想改变这一道德现状,就必须借助宗教的救赎力量。换言之,对于社会道德的宗教救赎,其实成为了作家塑造密友这一道德典范形象的基本叙述策略。
在菲尔丁笔下,不论亚当斯牧师、哈里森博士,还是奥尔华绥先生,其实都有着极为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为人敬仰的伦理权威,即来自这种宗教特性。作为牧师,亚当斯和哈里森原本就是上帝在世俗社会中的代言人。而他们向主人公乃至其他人物所进行的宗教宣传,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是一种道德关怀。可以这样理解,当亚当斯和哈里森所代表的社会道德在现实社会中遭遇美德无力的尴尬时,他们往往凭借宣扬基督教教义的方式,为世人献上了虽不能至,但却要心向往之的道德境界。这一道德境界就是两位牧师对世人应当遵守的道德法则的规定,他们强调的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应然性,即人们在道德层面应当怎样。尽管这一伦理思想充满了具有宗教情怀的形而上学色彩,但却也不失为对美德无力的一种救赎手段。这意味着用宗教道德对世俗社会进行道德救赎,业已成为作家解决笔下人物道德困境的一个常见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深入观察这些密友的宗教宣传活动,就会发现他们对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解并不机械,而是要求世人必须通过道德实践,去回应基督教教义的道德规范。亚当斯牧师对此有着精辟说明,在他看来,“若是对良善有道德的人说道,‘尽管你为人清正,尽管你在世上始终谨守道德和善良原则,但是你不信宗教正宗,由于你缺乏信仰,将来是要惩罚你的?或者从相反方面说,一个教派在末日替那个恶棍祷告说,‘主呀,你的十诫,我虽然一条也未遵守过,但是我却条条相信,请你不要罚我吧!还有比这种教义带给社会的影响更坏吗?”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去贯彻上帝的道德教诲,那么即便他信奉上帝,也难以获得高尚道德。用保罗的话说,“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循律法”(《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作为道德的化身,上帝不会“逆着天理的首要原则及是非的起码概念行事”(《汤姆·琼斯》)。对于那些一味宣扬空洞教义、忽视道德实践的宗教流派,菲尔丁历来就深感厌恶。比如作为基督教一宗的卫理公会,由于宣称忠于《圣经》和历史上各项信经所阐明的教义,因而遭到了菲尔丁的严辞批判。在他笔下,卫理公会的教徒往往以伪君子形象出现,如《汤姆·琼斯》中的布利非,《阿米莉亚》中的一个卫理公会教徒,一方面对布思滔滔不绝地进行教导,另一方面却彻底查看了布思的每个口袋,拿走了他所能找到的全部财产。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菲尔丁在作品中对那些只知空谈教义的人物进行了严厉批判,但他却从未忽视宗教对于道德的巨大影响力。例如在《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中,当哈特弗利在监狱中自白时,就虔诚求助于上帝的“仁德和权柄”,希望藉此去摆脱尘世的烦恼。在他看来,彼岸世界“尽管人们认为那是虚幻的,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那确实是最悦目可喜的”。而《汤姆·琼斯》中的奥尔华绥先生,更是处处以基督教教义去教导主人公。在一次重病中,他以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嘱咐琼斯说:“孩子,我深深知道你的天性十分善良,你是慷慨和光明磊落的;如果这以外再加上稳健持重和笃信宗教,你就一定会幸福的。尽管前三种美德能够使你享受幸福,唯有后两者才能叫你的幸福持久下去”。宗教对于幸福的永恒保障功能,充分说明了它在人们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价值。此外,山中人亦明确提出过宗教高于道德的神圣价值,他认为尽管哲学使我们更加聪明,“但是基督教却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哲学使我们的心灵高尚而坚强,基督教却使我们温和、敦厚。前者使我们获得人类的赞美,后者使我们蒙受上天的垂爱。前者保障了我们暂时的幸福,而后者却保障了我们永恒的幸福”(《汤姆·琼斯》)。这就是说,倘若一个人不相信宗教,就会失去对某种绝对价值的信仰,从而形成相对主义的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显然会导致人们对自我天性的纵容——那些假借天性所求而犯下的不道德之事皆来源于此。试看《约瑟夫·安德鲁斯的经历》中威理森乡绅的观点,他在谈到自己参加的一个俱乐部时说:“这个俱乐部常出入的都是些有才学的年轻人。[……]这些人抛开所有教育得来的偏见,只遵从人类理智绝对正确的引导,寻求真理。这个指导,向他们显示了一个极古老、极简单的宇宙神性的信条的虚假,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替代的权力原则(Rule of Rights)——最为纯洁的道德”。可后来这些会友的所作所为说明,道德倘若离开宗教的监管,就会沦为天性的奴隶。有鉴于此,菲尔丁几乎在他的每一部作品中都着力宣扬了宗教的重要性。例如《汤姆·琼斯》中反复倡导的“仁爱”(charity)就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或主要原则,用《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中的话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在《阿米莉亚》中,赌棍鲁滨逊先生起初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和“无神论者”,尽管他并不绝对否认神的存在,但他却完全否认这世上有神意存在。就是这样一位不相信宗教的人,却在冥冥之中担任了神意的传达者,他在当铺偶遇穷途末路的阿米莉亚,“通过这件事情,我(指鲁滨逊——引者注)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上帝的手”。正是因为他对藏匿和更改遗嘱罪恶的揭露,才使布思夫妇脱离困境。至于主人公布思,也曾一度怀疑过宗教,尽管“他是个对宗教表示极为良好祝愿的人(因为他是个诚实的人),但他对宗教的概念是很淡薄的,而且是不确定的。说实话,他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但到最后他还是皈依了国教。从小说人物的信仰道路来看,菲尔丁在这部作品中的叙事态势其实就是由不信到信,主人公如何皈依宗教成为了小说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情节线索。
在《汤姆·琼斯》中,菲尔丁通过塑造屠瓦孔和斯奎尔这两个反面人物,生动描绘了宗
教和道德之间的复杂关系。精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哲学家斯奎尔,就相信人性具备一切崇高的德行,犯罪仅仅是违背了人之本性,因而“甚至把一切德行都看作只是理论问题”。由于这一看法将上帝逐出了道德领域,因而将人们的美德追求完全寄托在了个人的修行之上;至于神学家屠瓦孔,则认为自亚当以来,人类的心灵就成为了罪恶的渊薮,必须仰赖神的恩宠才能得到洗涤和拯救。这种否定人类主体性价值的神学思想,显然与斯奎尔针锋相对。那么,真理究竟掌握在哪一方手中?从这两位人物在作品中的道德处境来看,他们并未因自己的宗教和道德主张而得救,恰恰相反,他们各自的道德状况却足以警示世人,倘若缺少了宗教或者道德中的任何一环,人们都将堕入不道德的境地中去。菲尔丁对此评论说,这两位人物“要不是在建立各自的体系时,屠瓦孔过于轻视道德,斯奎尔过于轻视宗教,要不是他们二人都把善良的天性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就不会在书中被描绘成为嘲笑的目标了”。在小说结尾,斯奎尔临终写了封忏悔信,他替琼斯伸冤,为奥尔华绥先生重新接纳琼斯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而屠瓦孔却仍顽固不化。这样的结局其实回应了休谟《人性论》第一卷结论中的论断:“一般说来,宗教中的错误是危险的;哲学中的错误则仅仅是可笑而已”。在人们的道德追求中,宗教精神和道德实践其实缺一不可,而宗教精神更起到了维护道德的作用。
从主张道德修行的实践性到宣扬宗教精神,菲尔丁借助密友形象所传达的伦理思想,其实反映了自近代以来基督教的某种发展历史。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不论是路德、加尔文还是伊拉斯谟,都具有极为鲜明的人文主义观念,而他们反对偶像崇拜,主张以信徒个人修养为本的救赎说,以及否定天主教会的改革思想,均在英国社会留下了深重痕迹。菲尔丁极力宣扬的道德实践论,其实就是这一宗教改革运动的某种时代回音。从这个角度说,菲尔丁借助密友形象所传达的宗教思想,本身就融合了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的人文主义基因。前者鼓励人们相信神意和因果报应,主张只要在道德实践过程中顺从上帝的意旨,便会获得美德有报的圆满结局。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菲尔丁美德有报的伦理思想,其实带有很强的宿命论和预定论色彩。由于这一主张坚信上帝对人们的命运安排具有某种先验的合理性,从而传达出了在冥冥之中自有上帝神意存在的宗教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尔丁“美德有报”的传奇笔法,本身就印证了基督教的因果报应说。至于后者,则在基督教义之外,更看重人们的主体性价值,因为只有凭借自己的道德修行,才能借助上帝的神恩通达道德的完美境界。从这个意义上说,菲尔丁笔下的宗教与道德问题,其实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宗教为人类的道德追求提供了一个普世性的绝对价值,所有的美德追求即以这种绝对价值为旨归;而人类的道德追求必须凭借自己身体力行的道德实践,才能在神旨的感召下通达完善的道德境界。
综上所述,菲尔丁之所以在小说中塑造一些密友形象,其实暗含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意图:一是通过对他们多重身份的描写,揭示出密友形象所代表的社会道德体系。而主人公被他们重新接纳的情节线索,则寓示了一个主人公美德有报的命运结局,即个人道德的社会认同。二是通过集中描写密友形象的道德状况,展示了美德在现实中软弱无力的际遇。在此基础上,作家提出了宗教对于人们道德困境的救赎功能。而他对宗教和道德关系的思考,则充分显示出菲尔丁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辩证思维。
责任编辑:四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