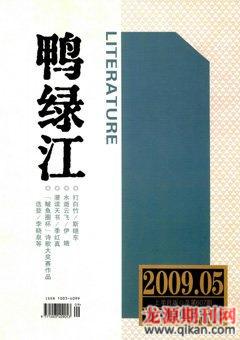打白竹
斯继东,1973年生,浙江嵊州人。中短篇小说散见《收获》《今天》(美国)《西湖》《青春》、《长江文艺》《安徽文学》《作品与争鸣》等纸刊及《他们》《黑蓝》《尚书屋》《中国新小说》等网刊。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嵊西乌带党首领裘文高,会同仙居郑万枝等,率义勇二百余人自仙居至嵊县白竹村宿营,筹划攻打嵊城。清军派管带刘庆林、哨官杨泰华率兵前往镇压。裘文高派部分人员身穿清军号衣,混入清营。然后内外夹攻,击毙刘、杨两头目和士兵共八人。清军败回县城,数日不开城门。
——《嵊县志》
有句老话,叫妻不如妾,妾不如偷。
老话一句是一句,不会错。我没老婆。一直没。之前没,之后也没。之前是不想娶,娶老婆干吗?我对我爹这样说。“娶老婆干吗?那你不娶老婆又想干吗?”我爹那个急啊,“你不为自己想,可你得为爹想,得为你爷爷想,得为你爷爷的爹爷爷的爷爷想,得为你的祖宗十八代想啊。”我爹一急,猴脸上就会绽出一根根青筋,多得就像我的祖宗十八代。可是,我爹的爹我爷爷的爷爷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又不认识他们。当然,我是认识我爹的。他看上去挺可怜,那一根根青筋把他的瘦猴脸搞得跟他的小腿肚似的。事实证明我不是捡来的,我的确是我爹生的。因为我也有张瘦猴脸,跟我爹那张就像印板印出来的一样。还好我的小腿肚没跟着脸像。我爹的小腿肚胀鼓鼓的,里面爬满了绿莹莹的蚯蚓,很丢人。出于同情,我在嘴上应承了我爹:“好的好的,娶一个就娶一个吧,又不是要阉掉做太监。”一样是出于同情,我在私底下替自己关了肚肠门。像我爹一样生个儿子,一把屎一把尿地养他,然后让他像我同情爹一样来同情我吗?除非把我的脑袋翻个面!我爹的确是死不瞑目啊。但终于还是瞑了,是我在合棺前给他瞑上的。在这之前,我咬了咬他的耳朵:爹啊,我没妻没妾,可我有很多相好。
我的确有很多相好。她们就像收镰后被遗弃的稻头,星罗棋布在白竹村周围的村堡里。赵宅的杨月桂、李庄的柳小满、张村的吴菊花、蔡家湾的李小娟、施家岙的施银钗、眠牛弄水库的孙水琴,当然还有甲秀坂的夏水荷。听听名字你就想象得出她们的模样,可她们的命都不好,按瞎子的说法是命硬克夫。作为仁义之地忠烈之乡的女人,她们只能老老实实在家守着死鬼男人的木主。就像寺庙里供奉的水果,男人们看在眼里,馋在心里,但是,万万动不得。我可没那么多讲究。既然菩萨不吃,那我还谦让什么。就只是伸伸手,梨、苹果、水蜜桃都到了我的嘴里。果然,梨很脆,苹果很香,水蜜桃都快熟透了。
但我也有我的禁忌。比如,白竹的赵二娥我就不碰,所谓兔子不吃窝边草;比如,今天吃了梨,苹果和水蜜桃什么的就得留到明天;再比如,这个村里找了杨月桂我就决不再找李月桂孙月桂什么的。
跟我爹一样,我也是个阉鸡的。所不同的,我爹半路出家,而我不是。我从小就干不了农活,碰到锄头柄就脚酸手软眼冒金星。我爹说,行行出状元,你就跟着我阉鸡吧,这是命。果然是命。没几天功夫,我爹在我跟前变得笨手笨脚了。于是我理所当然地就接过了爹的家当。我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块褡裢,平时就搭在肩上,一前一后晃荡着两个口袋,后面用来装铜钿,前面装阉鸡用的工具:一刀一钩一绳。刀很利,钩很长,绳子就是一根带活扣的棕丝,都是细得不能再细。老实说,这的确不是我爹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干得了的活。
天蒙蒙亮时,我已经踏着露水出现在村口。因为“阉”字不雅,老祖宗传下来时立了规矩,这门手艺是动手不动口的。其实根本用不着吆喝,我只要在村子里转上一圈,然后回到村口那棵大槐树下等着,生意自然上门。树下有现成的青石条。我点上烟。为什么所有村堡都会有这样一棵该死的大槐树呢?我想不明白,很多问题我都弄不明白,比如:为什么每个村都会有一个等着我的寡妇。每次我这样犯迷糊时,墙弄角就会准时闪出一个骚抖抖的女人和一只倒霉的公鸡。我把刀钩绳取出来咬到嘴里,再把褡裢翻个面铺到膝盖上,第一笔生意就接手了。鸡到了我的手上后忽然安静下来,装腔作势的挣扎变为乐颠颠的颤抖。这个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女人。我不急,一点都不。鸡一样,女人也一样。鸡爪已被布条缚住,就像门上了栓。我的大腿稍稍一用力就夹住了翅膀,那是她们的胳膊。这些肚脐下的绒毛就像衣裤鞋袜,只会妨碍我的活,当然得先除掉。我轻车熟路地找到了那个地方,对,就是这里。我的刀子早已经亮出来,就等着这一刻了,现在,我可要出手了。疼?开始时会有一点,之后就好了。忍一忍吧,我还没用钩子和绳子呢。太浅了,我还得深入一点,再深入一点。躺好了。你看我干吗?对,是带钩的,倒扎钩。快了,就快好了。我已经用上绳子了。现在感觉如何?舒服了吧?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完事后连伤口都不用包扎,怎么会疼呢?
爹,鸡干吗要阉啊?第一次干时我问我爹。阉了长膘。爹说。鸡阉了之后是公鸡还是母鸡啊?我又问。不是公鸡也不是母鸡。爹说。那是什么鸡?我再问。叫草鸡。爹说。那人要是阉了呢?我继续问。不男不女,就成了太监。爹终于直起了头,他干完了活,他又让一只公鸡变成了草鸡。干完活后爹的话多了起来:不知道太监吧?太监都很胖。当然,爹也没见过。太监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你要坐了龙庭才会有很多太监来服侍你。为什么皇帝老儿要让太监来服侍呢,因为皇帝有很多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全天下的美女都在那,能让男人来服侍吗?我要是皇帝,我也不放心啊。我爹说到这儿,我忍不住喊了出来:爹,我也要做皇帝。爹劈头给了我一巴掌:短棺材,你想造反啊,造反可是要杀头的!
前半场戏唱好,还有后半场。热水热茶,热酒热菜,当然还有热炕头热身子。唱后半场戏时,我一般就会讲一讲草鸡太监的闲话。她们都爱听这个,嘻嘻哈哈的,像添了道下酒菜,身体自然也更来劲了。但甲秀坂的夏水荷是个怪胎。她不爱听这个,她也不笑。你知道你说第几遍了吗?她板着脸。进门之前,她会递一块碱皂给我,把你那身臊洗洗吧。在床上时,我说,你上来吧。她说,我又不是婊子。第二天天不亮走之前,我会从褡裢中匀出一半的铜钿放在那个谁的床头柜上。铜钿叠起后细细长长的,有点扭,就像女人的腰身。有人会说多了少了,有人会装作没看见。总之两厢都喜欢。但夏水荷不。她像是跟铜钿有仇,抓起来就朝我身上砸,有多少砸多少。铜钿满地乱滚,我只得贼一样落荒而逃。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老话总是对的。但白竹村的炳汉老秀才说,天要变了。他懂一点三脚猫的星相。天怎么变得了?我白天阉我的鸡,晚上偷我的相好,天变不变关我什么事?但天的确有点要变的样子。先是听说广东有个叫孙大炮的跑去北京城找李中堂,要求搞个什么官当当,但中堂理都没理,孙大炮一怒之下就扯起了反旗,好像成立了个什么会,里里外外声势很大。后来绍兴府也跟着热闹起来。一个叫光汉子的混到安徽衙门里,杀了巡抚大人,还有一个半雌雄的女人舞刀弄枪的也跟着造起了反。我们嵊县也出了好几个人物,董龙岗的金发龙头,灵鹅村的牛大王竺绍康,廿八都的张伯歧,还有我们白竹村的裘文高,七党八会的,都跟绍兴那个汉子和女子有来往。但天到底还是没变。京城照旧坐着皇帝,造反依然要被杀头。据说孙大炮逃到了南洋,据说绍兴的女人被砍了头,据说光汉子的心肝被挖出来炒菜下了老酒。嵊县的几个头目也都遭了通缉,避走到了隔县外府。据说裘文高就一直躲在天台、仙居一带。
天没变,我却变了。有一天我忽然动起了娶老婆的念头。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我老了。我的脑子开始不管用了,我的鸡巴也不再是从前的鸡巴。颠三倒四的,有一次我居然把李小娟叫成了柳小满,还有一次我居然把吴菊花托我买的鞋样送给了施银钗,不对,可能是把柳小满叫成了李小娟,也可能是把施银钗的鞋样给了吴菊花,反正就那么回事。本来挺得心应手的一件事,现在让我觉出了烦。另外一个原因跟小铜匠有关。那天我跟他在开牌九时因为一点莫名其妙的事闹了起来。小铜匠理论不过我,就骂开了:你个腌■阉鸡佬,有什么可显摆的,老大年纪了怎么连个老婆也没混上。娶个老婆也算能耐?我挺恼,当时就在牌桌上搁了话:半个月内我娶回一个给你看看。
话搁下了,娶谁去呢?手指头扳过来扳过去,我就想到了夏水荷。这么多个相好中,就她怪胎。她不好好做我相好,难道是在盘算做我老婆?越想越觉得是这么回事。于是那天我连鸡都没阉就去了趟甲秀坂。
“你跑这寻我开心啊?”她上下瞧我,眼睛像个鸡毛掸子。
“说正事呢。”这回我有点急。
“你不就图个快活吗?你以为我不知道赵宅的杨月桂、李庄的柳小满、张村的吴菊花、蔡家湾的李小娟、施家岙的施银钗、眠牛弄水库的孙水琴——”她像我一样扳起了手指头。天。她二门不出的人,怎么知道得比我还清楚?
“行行行,算你说得对。可我烦了腻了厌了,我现在就想娶个老婆过日子,你倒说句肯还是不肯。”
这之后她说话变得扭扭捏捏起来。闹了半天,我明白了。她是肯的,但场面上只能装作不肯。所以我娶她,就得换一种方式。
“不就是抢吗?”我说。真是脱裤子放屁。
我找到独眼标时,他正在院子里和他的廿四结拜喝酒。大路碗里的老酒满腾腾的,一只热络络的狗只剩下了一副骨头。“那寡妇真愿意?强抢民女的事情可做勿得!”阿标开始有点犹豫。但他的弟兄们黄汤落肚听到有事做,都来了精神:“标哥,带上家伙吗?”我赶紧说,不用不用,女方是愿意的,去抢也只是做个样子。我知道阿标有一支过山龙,束了红绸,枪管有一人高,篷一铳,五里路会去。“又不是去杀人放火,带什么家伙?”阿标同意了。“那我也跟着去吧?”我问阿标。“你去干吗,你就在家等着做新郎倌吧。”阿标拍拍我的肩膀就带着弟兄们出发了。
后来的事,是谁都没料到的。中午时分,阿标他们回来了,没带回夏水荷,却一个个鼻青眼肿的。事后据阿标一位兄弟说,本来事情挺顺当的,夏水荷哭也哭了闹也闹了,终于在众人的围观中被塞上轿,眼看就要出村。谁知半路上却杀出了个程咬金。就是甲秀坂的武生,当时担任乡团团董的宋保兴。他横在大路口把轿子给拦下了:“小小一个白竹村,青天白日敢来撒野,当我们甲秀坂没人吗?”乡团一拥而上,双方就动起了手。阿标他们势单力薄,又手无寸铁,面对越聚越多的甲秀坂人,只好掷下花轿,狼狈而回。我真的没想到会闯出这么大的祸,早知这样,给我十个胆我也不会去找阿标的。我就上去劝阿标:“标哥,你消消气吧,都是我不好,我不要那女人了。”“什么女人?”阿标本来一声不吭地蹲着,这会儿忽然像伤铳野猪似的暴了起来:“这儿没你事,阉你的鸡去吧!现在,是我阿标跟宋保兴的事了。”
我知道阿标不是一个打落牙齿往肚里咽的人,我还知道阿标有一支过山龙,束了红绸,枪管有一人高,篷一铳,五里路会去。我一直担心闹出人命案,但蛮七蛮八的阿标却想出了一个文文气气的让宋保兴难过的法子。白竹和甲秀坂在甘霖和石璜中间,白竹人赶甘霖市得过甲秀坂,甲秀坂人赶石璜市得过白竹。第二天正好是石璜市日。近晌午时,阿标带上人在村口的路廊里设了伏。等甲秀坂人赶集回来,阿标是两只手捉蟹,来一个捉一个。捉到村里后,该吊的吊,该打的打,嘴强的还被沉了粪池。被捉的要问缘由啊,阿标答得干脆:去问宋保兴。当天夜里,两边都挺热闹。那边宋保兴家被村人围了个水泄不通,骂的骂,吵的吵,砸的砸,打的打,宋保兴光着屁股在街上过了一夜;这边阿标和他的廿四结拜扬眉吐气地喝了顿酒,吃了裘阿根家一只狗。恶气是出了,可事却越闹越大。第二天宋保兴去甘霖找了师傅赵诗高,赵诗高又去县城找了县令秦家穆。阿标遭了通缉,县令悬赏三百大洋,罪名是私通盗贼,图谋造反。差役来捉,阿标星夜逃出了白竹村。
造反,造反可是要杀头的。阿标哥被我害惨了。他老娘天天哭,哭着哭着就把眼睛给哭瞎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天天心惊胆战地捱在家里,等着差役来捉我。罪名是私通盗贼,图谋造反,跟阿标一样。这事因我而起,不捉我捉谁呢?我生了场大病,瘦猴脸更瘦了。因为我的缘故,周围村子里的公鸡耀武扬威了好一阵。本来它们在学会打鸣之前就得变成草鸡,现在倒好,它们都学着在半夜三更打起了鸣。但差役一直没有上门。
阿标逃走时背走了那支过山龙。我说过阿标不是一个掉落牙齿朝肚里咽的人。果然,那年麦黄时节,阿标背着过山龙回来了。阿标不是一个人,他带回了蟒蛇样的一大队人马。有多少人?曹操兵马八百万,想过一座独木桥,一个,两个,三个——黑压压的,数也数不过来。阿标扛着过山龙耀武扬威地走在最前面,之后是裘文高,裘文高之后是一个鲁智深,后面的人举五色旗,都穿了黑色对襟短衫,中间一个白底的“义”字,都扛了家伙,有五发套筒、土制双转筒两发头、独响枪和土铳,再后面队伍就有些七零八落,衣衫不整不说,操的武器是板叉、斧头、钩刀,锄镰钉耙,什么都有。据阿标讲,他逃出白竹后就去找了裘文高。他知道裘文高跟宋保兴是死对头,乌带党中“文高道卫”的陈道卫就是宋保兴杀的。果然文高对攻甲秀坂杀宋保兴很有兴趣,但他却是空口讲白话,手头连一兵一卒都没有,于是文高就带了阿标去找东阳九龙党的大开和尚。据阿标讲,大开和尚是个酒肉和尚,他力大无比,能“举臼当帽,掌磨作扇,捏竹如泡”,听到攻打号称浙东粮仓的嵊县县城他来了兴趣,可问题是他也刚刚吃了败仗,手头只剩下了十几个徒弟。据阿标讲,事情来得凑巧,当时正好仙居佬借道大盘山准备攻打东阳县城。文高和大开就去找仙居佬商量,但仙居佬对宋保兴和嵊县县城都没兴趣。七拉八扯的不知怎么就提到了嵊县绿营管带刘庆林,仙居佬忽然就来劲了。“刘庆林?我倒想去会会他!”原来仙居佬跟刘统领有渊源,以前两人一块儿带过兵,打下了半个台湾,阵是仙居佬排的,功劳却被刘统领独得了。于是仙居佬就放下东阳城来打嵊县城。据阿标讲,仙居佬的人马本来也没这么多,一路开过来,田坂里的人听说到嵊县去吃大户,都掷下了田稻,连烧炭佬也大钩刀拿着跟来了。据阿标讲,义军经南山八宿屋,夜驻蔡山湾,本来是计划第二天先吃掉甲秀坂然后攻打县城的。但那天早上,他们一马平川开到剡溪南岸,却出了点小问题。由于前几天发大水,江面上的木桥被冲毁了。没办法,只好原路折回,绕道石璜过白竹攻打甲秀坂。一来二去,等部队开进白竹,已是中午时分,只好驻下吃饭。文高在路上发了不少的狮象图,陆续有乌带党徒操着家伙从四方赶来,上于的张立民还扛来了一箩炸药,队伍又壮大了不少。文高当然不想把战场摆在家门口。队伍刚开进村,就发生了偷鸡摸狗的事,村里人都来找文高理论,文高很恼火,却又发作不得。正在这时,探子来报了,刘统领带着人马已经从甘霖开向甲秀坂,新昌的凌统领带部下也正在朝嵊县进发。在阿标家的院子里,文高与仙居佬发生了争执,文高主张速战速决,攻入甲秀坂,而仙居佬则主张就地布阵,以逸待劳。没人帮文高讲话,连阿标这样的外行也认为仙居佬到底是打过台湾的,行军布阵有一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于是,村前屋后的风水树、居家竹被砍倒了,村子里所有的桌椅、水车、稻桶都被搬了出来,所有的棉被都搜出来泡浸到了水里,祠堂、土地庙、沿村的房屋的墙壁都被凿开了,瓦屋顶被掀掉了,所有的铁锅都被挖出来做了盾牌。仙居佬随机应变、就地取材,布下了著名的“长蛇阵”和“蜂窝阵”。下午三点光景,刘统领骑着大白马,挥着指挥刀,带着队伍冲了上来,看看近了,仙居佬一声令下,枪声像锅底的竹节一样噼里啪啦响了起来。就这样,计划中的打甲秀坂变成了打白竹。
阿标说半个台湾都是仙居佬打下来的可能没吹牛。仙居佬后来又布了疑兵阵,用了火攻,把刘统领的队伍打了个披败溜风,刘统领本人也被砍下了脑袋。仗是打赢了,可白竹村却遭了殃。仙居佬带来的兵趁乱劫了财劫了色,裘阿根那把火也蔓延开来殃及了大半个村。一仗打下来,村堂变成了瓦砾堆,几个小脚老太婆逃勿及,也被烧死在里头。本来说好取了甲秀坂再攻嵊县城的,仙居佬得了刘统领报了私仇,借口攻打东阳城连夜开拔了。大开和尚死了几个徒弟又打不成嵊县城,也计划走。裘文高没报成仇,反倒引狼入室在家门口开了战场,很没脸面,只得跟着大开溜了。阿标本来挺兴高采烈的,像是立了头功。别人跑来告诉说,自家屋子被毁了,瞎眼老娘也被烧死了,这才清头过来,没命地向回跑。
仗打起来时,很多人都朝村外跑,我没跑。我目睹了打白竹的整个过程。阿标带着仙居佬入村时跟我打过招呼,“兄弟,我替你报仇来了。”报仇?我跟谁有仇啊?是宋保兴吗?好像不对。可我难道是个局外人吗?也不对啊。整桩事情,前因带后果,一环扣一环,不都是因我而起的吗?可我又做错了什么?我不就想娶一个寡妇吗?我为什么就不能娶一个老婆呢,人家不都有老婆吗?
打白竹是光绪三十三年秋天的事。那之后我就放弃了阉鸡这门手艺,重新握起了锄头柄,奇怪的是,碰到锄头柄后我脚不酸手不软眼也不冒金星了,我把我的一亩三分田拾掇得很地道。阿标被抓进去又放了出来,因为他疯了。他看见我总是呵呵地笑:“兄弟,我替你报仇来了。”裘文高一直逃亡在外,因为打白竹的事他成了全村人的仇人。他是个孝子,总记挂着家里的老娘,时不时潜回家探视,又不敢在家过夜,只得露宿野外。盛夏时为免蚊咬,他全身用沙覆盖,仅露朝天鼻眼,在沙滩过夜。为防不测,他还毁坏了自己的脸。但终于还是被告了密,于三十四年春被砍了头。世道反反复复的。先是宣统皇帝下了台,造反的孙大炮上了台,不叫皇帝叫总统了,县太爷也改叫知事,后来孙大炮不知怎么的就把位子让给了袁大头,袁大头不想叫总统又要叫皇帝,孙大炮就又起来造反。白竹村安安稳稳的,没人再对这些感兴趣。造反?造反总是要被杀头的。我也一直安安稳稳地呆在白竹村。春播秋收。我还养了一院子的鸡。公鸡,母鸡,但没有草鸡。我再也没起娶老婆的念头,我把我的那些个相好都给忘了。赵宅的杨月桂、李庄的柳小满、张村的吴菊花、蔡家湾的李小娟、施家岙的施银钗、眠牛弄水库的孙水琴。但我还是会想起甲秀坂的夏水荷。她后来嫁人了吗?她的日子过得咋样?当然,没人来告诉我这些。
有一年,村里来了一个年轻的阉鸡佬。他一进村就吆喝开了“阉鸡了阉鸡了——”听口音不像是本地人。像我一样,他在村口大槐树下的青石条上开始了他的生意。我有点兴奋地坐到了他的旁边。我没有看见那块熟悉的褡裢,替而代之的是一块皮革做的围裙,这让他看上去像个杀猪佬。他的嘴里叨了根烟,烟灰长长的,随时都会掉下来。鸡在他的手里死命挣扎。他没给鸡褪绒毛,直接就下刀子了,刀口很长,然后他把他的食指很愚蠢地伸了进去。
小子,鸡可不是这样阉的。我真想跟他说上这么一句。
但我没有。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