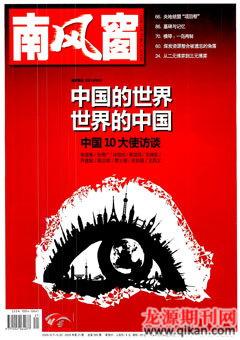中俄需要“人民外交”
田 磊
中俄之间政治上的互信是空前的,国家关系是历史最好水平,但民间的偏见还是很深的,民间感情需要花大力气培养。
俄罗斯是中国最强大的邻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苏联第一个与中国建交,至今,中俄关系历经60年风雨。60年与强邻为伴,甘苦交杂,不同时期的中俄关系中,总是伴随着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影子。在国际舞台上,中美俄三个大国之间的博弈和角逐从未间断。
从1965年进入外交部起,张德广开始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官生涯。其问,他先是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参赞,后又先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国驻俄罗斯大使、上海合作组织首任秘书长。
9月底,张德广在北京接受了本刊记者采访。在他的讲述中,40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最痛苦的经历是1991年苏联解体后,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的那场降旗仪式。“看着苏联的国旗缓缓降落,心里很难过。”张德广说,毕竟那是苏联,是共产党的国旗。更让他难以忘怀的是,苏联国旗降下后,一个原本关系很好的美国学者,当着他的面说:“苏联没了,下一个垮台的共产党国家就是你们中国,我们原来共同反对苏联,现在苏联倒了,中国对我们也就不重要了。”
如今,这些痛苦早已释怀,中国并没有像他那位美国朋友期待的那样垮台,而是在国家复兴的道路上,更加从容地角逐于大国舞台。
中俄民间互信待加强
《南风窗》:今年是中俄建交60周年,很多人都说,中俄两国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可是,对于大部分中国年轻人来说,对俄罗斯的陌生感比以前要强了,比如在中国的大城市里举办的中俄文化年,远没有“中美”、“中法”、“中英”等活动人气旺,而在俄罗斯国内,不少人对于中国人的态度似乎也并不十分友好,为什么会这样呢?
张德广:中俄关系发展了60年,风风雨雨、起伏不定,到今天这个建交60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中俄关系的亲历者,确实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其中就包括你提到的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认同。
到今天,毫无疑问,中俄之间政治上的互信是空前的,国家关系是历史最好水平,但这只是讲官方的、政治的关系,也可以包括经济的,经济现在是560多亿美元的贸易额。但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光是政府层面的信任是不够的。
现在中国人在俄罗斯做生意,经常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一些俄罗斯的强力部门,对中国人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偏见,比如,不少中国商人做生意比较有钱,但并不注意打扮,警察看到衣冠不整的中国商人就抓,当他们掏出护照时,他们根本不看,就说你这护照是假的,甚至拿过去就撕掉了。
所以说,民间的偏见还是很深的,民间感情需要花大力气培养,报纸上天天说中俄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这个友好需要切切实实地让老百姓去接触,去相互了解,没有这个层面的认同,只是政府在讲话,写个文件,是不行的,必须去落实这些东西,变成真正的友好。俄罗斯人见到我们中国人,会觉得亲近,我们见到俄罗斯人就认为是朋友,那样才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真正做到这一点,还差得很远,国家可能做到了,但人民这个层次,还是要通过各种途径开展交往,这样两国才能做到世代友好,这也符合两个相邻大国各自的国家利益。
《南风窗》: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吗?
张德广:建立互信的桥梁是首要的,现在中国主流社会对俄罗斯的了解,基本上是靠1950年代我们在建国初期派出的一批留学生,可现在他们也都七八十岁了,对俄罗斯的回忆还是那些苏联的老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等,这代人应该说是我们对俄罗斯了解的桥梁,但他们其实并不很了解今天的俄罗斯,俄罗斯油画、芭蕾舞、民间艺术等等都是我们所很不了解的。
而俄罗斯对我们的了解,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那一大批苏联专家撤回去之后,其实也没有什么桥梁了。一直到1982年,有一本《苏联百科辞典》,把它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双方学者有一些联系,到最近几年,学术方面的交往才多了起来。
现在国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加强民间交往主要是两个途径,一个是俄语年,一个是国家年,这些活动非常需要,填补了很多空白,但动员的社会层次、领域还不够,涵盖面还是太少。你想想俄罗斯人是1.4亿,中国人是13亿,仅仅靠几十次活动,真是沧海一粟,差得很远。
40年边界谈判
《南风窗》:中俄之间的边界谈判整整进行了40年,虽然最终达成了协议,完成了边界勘定,但不少国人认为,在边界谈判中,中国吃亏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德广:从1964到2004年,中俄花了40年时间,最终把所有边界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个好事,边界问题解决后,就排除了两国关系中最敏感的、爆发性的潜在问题,整个边界地区变成了和平的纽带,这对两国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两个国家来说,这是双边关系上的巨大成就。
至于说谁吃亏了,谁占便宜了,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比如黑龙江上、乌苏里江上那些岛屿,由于多少年变迁,很多位置跟以前都不一致了,俄罗斯人说是他们的,我们主张是我们的,争议很大,只能在国际法的框架内,通过友好协商,平等互利,通过互谅互让来解决。边界问题涉及很多历史沿革,世界版图变化很大,如果都去翻历史旧账的话,世界永无安宁之日了,并不符合各个国家的利益,如果因此而引起战争,或者长期紧张,是吃亏还是占便宜呢?这些都很难讲。中俄能够达成谅解,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是个好事情。
《南风窗》最近莫斯科的“灰色清关问题”似乎就是个不小的摩擦。7月莫斯科市政府以“违反环境卫生规定”为由强行关闭了切尔基佐沃市场,引起人们对灰色清关问题的广泛关注,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张德广:这个问题已经拖了10几年,我当外交部副部长的时候,实际上就提出来了,这其实是一种不规范的贸易方式,国际上不可能长期存在,关键是怎样解决,怎样软着陆,使双方的利益不至于受到损害,中国一直很关切,因为这涉及我们几十万人的就业,我们的商品出口等等,但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在这方面没有权力,或者说不应该这么做,他们的问题在于做法上不是很周到,执行部门出了问题,使中国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现在这个问题毕竟还是解决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外交部、商务部做了很多事情来保护中国商人的合法利益,俄罗斯政府也还是配合的。
双头鹰的复兴
《南风窗》:2000年普京在上台伊始认为,俄罗斯在近二三百年来第一次面临着沦为二三流国家的风险,经过普京近10年的执政,您认为俄罗斯发生了哪些变化?它的复兴之路走到哪一步了?
张德广: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10年是叶利钦执政,俄罗斯国内充满了权力斗
争、政治斗争,根本谈不上复兴,是一个经济、政治加速衰败的10年。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在这个过程中,国民经济被一些寡头垄断起来,特别是能源方面,先是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金融,之后开始对政治施加影响。
从2000年到2008年,是普京当总统--的8年,其间他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个是打击寡头,把经济大权特别是关乎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掌控到国家手里,不是简单的收归国有化的问题,而是打击他们,有违法犯罪的,投入监狱,借此来整顿经济秩序;第二个是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叶利钦时期,有些共和国,特别是民族共和国以及远东一些偏远地区声称,他们的议会可以制订法律,自治共和国和本州的法律,可以高于联邦的法律。这就等于在走向分裂了,普京一上台就着力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法律方面,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地方法律必须服从中央法律。从莫斯科到各共和国,中央法令一统到底,垂直的中央领导得到了强化。
这两项措施收到了实效,这8年来,应该说俄罗斯复苏的速度很快,但也有问题,经济复苏主要靠能源和资源,自身的科技能力、创新能力没有发挥出来。俄罗斯的科技创新能力实际上是很强的,在历史上,俄罗斯诞生了很多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航天、电子、军事工业都非常先进,但这些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仅仅依靠能源支撑起经济复苏。结果去年金融危机一发生,世界能源价格暴跌,俄罗斯经济就遭受了巨大冲击,原来外汇储备达到5000多亿美元,很可观,现在一下子用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俄罗斯经济发展和复苏的基础并没有打好,生产、创新的能力,市场机制的建设都还有很大差距,人均生活水平并没有很好的改善。
《南风窗》:俄罗斯的复兴会对中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俄罗斯习惯于将自己定位成西方国家,他们会更注重俄罗斯内政外交与西方的联系,把与西方的交往放在首位,只是在与西方国家产生矛盾,自身处于发展低谷时,才会转而修复与东方国家的关系,这种印象是一种误解还是确实存在?您在担任驻俄大使期间,曾与俄罗斯政治精英有过密切交往,在他们身上,您有这种切实感受吗?
张德广:俄罗斯国内从历史上就存在着两派,一种是所谓的西方派,一种是东方派,或者叫欧亚派,俄罗斯到底是欧洲国家还是欧亚国家,这是他们一个一直都达不成共识的问题,他们找不到俄罗斯的身份,我的理解,一个是跟地理位置有关系,地理位置横跨欧亚,但政治经济中心都在欧洲,文化属于东正教文化,也是西方文化传播过来的,所以他们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但从地理上、生存的硬件上,又大部分都在亚洲,比如现在经济最主要的支柱之一石油天然气郁在亚洲境内。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西方派一直说要回归欧洲,苏联时期俄国脱离欧洲了,没有按照欧洲的模式去发展,现在苏联解体了,他们要回去。多年来,包括普京都提过回归欧洲的问题。但很显然此路不通,回不去了,为什么呢?欧洲说你不足欧洲国家,或者说块头太大,回到欧洲,就把欧洲给搞坏了,欧洲装不下你。欧洲害怕俄罗斯,认为是个威胁。
另一派就说,冷战之前包括冷战时期到现在,我们跟欧洲的关系就是一种疙疙瘩瘩的关系。我们必须在东方寻找伙伴,特别是中国、日本、韩国,发展同这些亚洲国家的关系,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也做了一些工作,表示积极发展跟东方的关系。但到目前为止,就我的观察来看,他们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俄罗斯记者也喜欢问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中国外交官看来,这个问题很简单,东西方的关系都应该发展,我跟他们记者说,你首先不要把它看成是劣势,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分裂的俄罗斯,一个东方俄罗斯,一个西方俄罗斯,而应该是一个横跨亚欧的俄罗斯,从优势的方面来开拓自己的未来。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说明在制定国徽的时候,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就已经有了一种这样的思想,既要看着西方,又看着东方。
但后来,随着俄罗斯国内不断的政治动荡,各派的权力斗争,他们又都喜欢利用这个问题,有的强调欧洲,有的强调中国,把这个问题弄成势不两立的对立情形,现在也是,主张跟中国发生关系的人,会受到别人的攻击,主张跟西方主动发生关系的人,也会受到其他一些政治流派的攻击,高层政治家也许懂得双赢的思路,知道双方面都应该重视。到目前为止,就我观察,他们国内并没有形成一个很明显的占主流地位的共识。告别“结盟”
《南风窗》:现在有人建议中国应该跟俄罗斯结盟,这样才有实力对抗美国,您怎么看?
张德广:这个说法是不科学的,既不符合时代要求,也不符合中国外交政策理念。中国现在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这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是冷战时代,我们主张独立自主,同各个国家友好合作,特别是大国,比如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虽然有矛盾、摩擦,但合作是主要方面,共同利益是主要方面。
结盟这个外交形式,是在对抗的时代产生的,是两大军事集团,或者地区的或者全球的,严重对峙,势不两立的状态,尤其是战争状态下,有可能产生的,一些国家把结盟作为一种外交选项,来应对威胁,加强自己的地位,巩固自身安全。但如果世界处于现在这样一种全球化、多极化、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下,结盟就显得没有必要了,是一种很不明智的选择。
原有的一些结盟,比如北约,它是冷战时期产生的,到现在并没有取消,但它也正在谈论自身的改造。时代不同了,它没有对抗的目标了,现在不能再说俄罗斯是北约的对抗目标,既然是结盟的军事集团,那么,干嘛要结盟呢?它已经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所以现在北约面临着自我解释的问题,必须解释为什么还存在,宗旨、目标是什么?必须调整改造,不调整改造,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了。
如今,我们不赞成结盟,这个外交理念是非常清楚的。不能停留在想象的阶段,美国人一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搞他,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必要的。
《南风窗》:那么对于G2这个概念,您大约也认为是不科学的?
张德广:这个概念是美国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中美两国很大力量,合起来可以共同管理世界,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中美,这个观念跟我们的观念不同,温家宝总理在欧洲曾经批评过这个观点,说这是错误的,是不可行的,我完全同意。
中美两国不可能控制世界,管理世界,美国一家做不到这点,现在它拉上中国,可是中国根本没有这个理念,没有这个愿望和要求,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事情做好,世界的事情,我们的主张是让大家共同来做,我们不认为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能够把世界领导起来、统一起来,世界是复杂的,多样的,世界上的事情应该是大家来做,我们一向如此主张,我们并不会因为美国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好一些了,我们就说,好,我们两家联手管理世界,这是行不通的,马上就会有其他国家来反对,凭什么接受你们中美的领导呢?
他们现在甚至取个名字“中美国”合在一起,这是更加荒唐的事情,根本不合乎中国的外交理念,也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发展需要。当然,如果提出这个概念的初衷是强调大国的作用,中美两国很重要,在世界上应该承担符合自己国力的责任,我个人觉得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中美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美集团领导世界,那就很荒唐。
《南风窗》:但在现实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经济、政治地位确实在上升,您觉得中国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张德广: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平等的大国,现在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大同,不能算一个强国,富国,主要是我们的人均GDP还很低,国内经济发展质量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整,我们还是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夫,而不是说我们很了不起了,在国际上就可以怎样了。国际交往还是应该坚持韬光养晦,我们现在比以前可以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比如说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做的应该积极去做,但千万不能超越国力去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