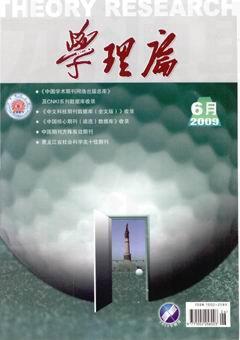走进中共党史创建史的史料之林
时 晨 衡朝阳
摘要:由于第一手文献史料缺乏,中共党史创建史研究困难重重。又因为不同时代有关回忆录资料的大量出现,导致中共党史创建时期一些重大历史研究抵牾很多。国内有关档案在1980年代逐步公开。但仍不足以解决中共党史创建史有关悬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中共创建史研究是巨大的推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根据中国、前苏联大量文献,特别是利用日本有关档案对中共党史创建史进行梳理,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其审慎的态度、求真的精神和新颖的观点都值得借鉴。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中共“一大”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3—0158—02
史学即史料学的说法固然走了极端,但史料的基础地位却得到了保障,就这一点来说,这一观点有它的积极意义,尤其对于纠正党史研究中存在的“以论带史”甚至是“以论代史”的偏颇更有其现实作用。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以下简称《成立史》)对我国中共创建史进一步研究的启发和推动作用应该主要体现在这一方面。
如著者所言,中共成立史尽管时间很短,研究成果却极其丰富,据石川祯浩不完全统计,以中共成立史为对象的专著就有二十多部,文章则有两千五百篇以上,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弄清中共成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或者说,大量的研究反而导致这样一个倾向,即轻易地相互借鉴,甚至以讹传讹”,因而“本书的描述总体上倾向于考证” [1],纠正基本的史实错误。
为此,作者大量运用第一手资料,对关于中共创建史的相公史料特别是回忆录进行细致而翔实的考证,在此基础上对许多结论提出质疑和纠正。作者利用的档案文献就包括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档案、日本内务省警保局档案、中共中央档案馆藏档案、俄国社会政治史档案馆(原俄国现代史资料保存中心)资料、俄罗斯解密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有关档案等,其他的资料,如日记、回忆录、当时的报刊,以及一些文献集等,可以说是竭尽所能,令国内的党史研究者都要叹为观止。正是在对大量资料比较、鉴别、考证的基础上,石川祯浩在《成立史》中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兹举几例:
一、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
这一说法突出在魏金斯基来华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已经就成立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商议,这个具体的商议时间是1920年初陈独秀在李大钊陪同下秘密离开北京赴天津途中。《成立史》追根求源,“南陈北李说”来自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的回忆,最早是1927年5月他在李大钊追悼大会上所做的演讲。而高一涵在此后不久发表的纪念李大钊的文章上其他内容与悼念演讲相同,独不再有陈独秀、李大钊相约建党说。而且,作者根据高一涵1920年2月13日从日本寄给胡适、陈独秀的信进一步证明,高回忆中所谓陈、李相约建党时他在北京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他当时是在日本。由于高一涵的不在场,他的回忆录就失去了真实性,“南陈北李说”从史实的角度也就失去了依据。
在否定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基础上,《成立史》再就魏金斯基第一次来华在北京与李大钊的接触进行考证,对李大钊当时和魏金斯基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的结论表示怀疑。这里,书中首先引用张国焘的回忆直接证明魏金斯基当时尚隐藏真实身份,他和李大钊之间没有进行什么初步的商谈,因为张当时正追随李大钊,因而他的回忆有一定参考价值,再根据原始档案——魏金斯基当时的报告,中间只提到了陈独秀,而没有出现李大钊,说明李大钊和魏金斯基当时仅仅是一般交流,不会进行到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样的讨论深度[1]。
在这里,对高一涵回忆录的考证和对张国焘回忆录的引用都体现了作者的审慎态度,正如书中所说:“本书中,有的部分当然不得不依据回忆录,但在论述时,将努力根据已公开的第一手资料对每个回忆录加以引证和纠正。”[1]对回忆录的考究和置疑,典型的例子在作者对于中共“一大”出席者人数的史料鉴别。
二、“一大”代表人数和名单
《成立史》追溯了中共“一大”代表人数在中国国内的研究历程:1927年1月中共有关人士发表了两篇文章,主张是11人,但没有姓名。建国以前给出代表姓名的回忆录是周佛海和陈潭秋,1927年周佛海发表《逃出赤都武汉》,列举了“一大”代表人名11人,加上忘记了姓名的济南代表2人,共13人;而陈潭秋则给出了和周佛海一致的11人名字,并明确了济南代表王尽美和邓恩铭的名字,“至此,出席中共‘一大的人数和成员基本上明确了。”但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一大”代表12人说,而到20世纪50年代,以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标志,12人说成为定论。书中认为,这与斯诺对毛泽东的那个采访,即《红星照耀中国》的发表有关,该书中毛泽东的回忆就认为“一大”代表是12人。由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的确立,“一大”代表“12人说”此后成为定论,影响了建国后的回忆录,以董必武——这个参加“一大”且一直未离开中国共产党的要人——为例,董必武的回忆录被给予很高的评价,事实是,他的回忆也是变化的。董必武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1956年一直认为“一大”代表是13人,直到1957年苏联移交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给中国,1959年中央档案馆把“一大”的相关文件俄文稿的译文拿来做鉴定时,董必武承认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同时放弃了他的13人说,同意12人说。然而问题随之而来,就是他本来确认的13个代表,谁该被剔除?李达、董必武等在回忆录中否定了包惠僧的代表资格,1969年毛泽东在党的“九大”的讲话关于12个“一大”代表也排除了包惠僧,这一问题成为定论,使得以后的回忆被扭曲。作者引用董必武的论述:“回忆那时的事,难于摆脱现在的思想意识,如果加上了现在的思想就不一定可靠”[1],指出,正是因为包括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刘仁静这样一些留在大陆的“一大”代表无法摆脱中共的思想意识,最可靠的原始文件又当作机密,导致回忆和研究的混乱。而事实上,作者认为,“一大”代表在中共“一大”的有关档案资料上都证明是12人,被排除的不是包惠僧,而是陈公博。作者依据张国焘、周佛海以及陈公博自己的文章,确认陈没有参加“一大”的嘉兴南湖会议,而关于“一大”的原始资料是在会议结束时写的,所以,推测陈公博被排除,比较包惠僧或是何叔衡更有说服力。
在关于上述“一大”代表人数和名单的研究中,作者刻意强调了政治思想意识对中共党史回忆录的影响,从而努力“要把中共成立史从后人评价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置于当时的环境中去,这就是本书的全部意图”[1],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对“一大”代表人数考证过程中,也对中国档案解密的滞后提出了疑义,中共“一大”的原始资料即俄文文件在中国一直被当作“秘密文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公开,而在此之前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在美国、俄国被发现和公开[1],这也是造成“一大”研究在很长时间里无法深入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一大”研究给我们启示主要在注意党史回忆录的政治风向标的话,《成立史》还对党史创建史研究中的以讹传讹甚至是谬误的层累叠加做了警示。
三、李大钊和《晨报副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晨报副刊》1919年4月开始刊登了很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翻译文章,“揭开了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序幕”。《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和李大钊的年谱都认为,李大钊参与了这个时期《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成立史》揭示,这个说法源于成纲1941年4月27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文章《李大钊同志抗日斗争史略》中所谓李大钊曾是晨报主任编辑的错误记述,后来发展到 “协助《晨报》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并进一步被夸大解释为“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原来《晨报》的旧人中,也有人写了记《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的奋斗生涯》这样的文章。”[1]事实上,作者以1916年9月5日《晨钟报》的《李守常启事》,说明李大钊仅仅担任《晨钟报》编辑主任20多天就辞职了,而《晨钟报》改名《晨报》后,李大钊虽有投稿,却“并没有原始资料能够证明李大钊直接参与了《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结合作者的考证在《晨报副刊》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渊泉”是《晨报》记者陈溥贤,而李大钊此间的文章多有和《晨报副刊》翻译的内容一致。这样,陈溥贤在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中介作用随着两人关系的进一步被揭示就很清楚了。至于两人的关系,结合陈和李大钊共同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回国同入《晨钟报》做编辑,推测两人的关系应该很亲密,作者甚至收罗梁漱溟的《回忆李大钊先生》中的一句话“我出寺门,路遇陈博生走来。他是福建人,与守常同主《晨钟报》笔政”,说明在李大钊牺牲后,陈还去停放李大钊遗体的寺庙,他们之间的联系在《晨钟报》以后应当一直存在,这就为了解李大钊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提供了清晰的解释,也给予陈溥贤应有的历史地位。
《成立史》还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具体时间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对张太雷1921年赴苏时的身份做了引人入胜的考证等等,都值得党史研究者和学习者一读。
历史研究是一种祛魅的过程,揭开层累的迷雾,回归真实的历史,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石川祯浩的《成立史》在史料的丛林中跋涉前行,他的研究态度和结论都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1][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313.
(责任编辑/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