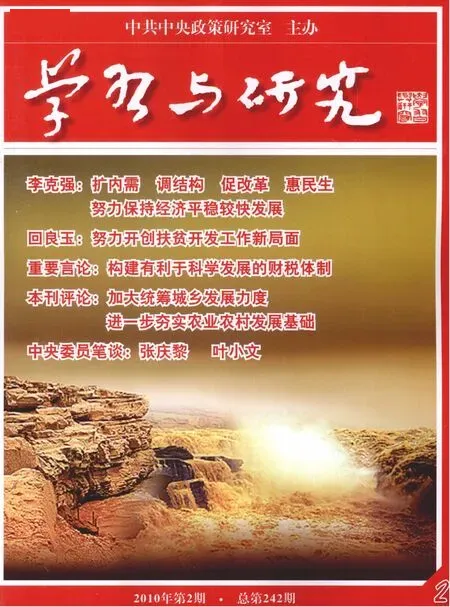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上)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初探(上)
葛荣晋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所蕴涵的“实心实学”思想,可以概括为:“本体工夫合一”的“实心”论,“实地用功”的“实功”论,“践履之实”的“实行”论,以及“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的“明德亲民”论。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是明清之际“实学”社会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
王阳明;心学;实心实学;明清社会思潮
本文试图超越中国明清以降的“理学研究范式”和近六十年的“两军对垒研究范式”,从“实学研究范式”的新视角,全面地诠释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从而揭示王阳明心学体系中所蕴含的“实心实学”思想,顺理成章地追溯到它是明清之际“实学”社会思潮的理论源头之一。
一、“本体工夫合一”的“实心”论
“实心”这一哲学范畴,从《王阳明全集》中共检索出16条。这16条资料中的“实心”,都是作为名词来使用的,如“实心体之”、“实心干事”、“实心修举”、“实心推求举行”、“实心为家”、“实心向化”、“实心归向”、“实心改过”、“实心无他”、“行以实心”、“爱民之实心”等。
这些条目虽未从正面系统地揭示出“实心”的内涵,但从对它的具体论述中可以看出王阳明所谓的“实心”如同“良知”、“天理”和“诚意”一样,都是对“心”的不同表述。在王阳明看来,“心”是“一”,而对它的表述则是“多。”他说:“心一而已,……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实理,天理)。”(《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以其良知“发见流行处”不可逾越“良知上自然的条理”,“此便谓之义;顺这个条理,便谓之礼;知此条理,便谓之智;终始是这个条理,便谓之信。”①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言,心即是天理;从“心,生而有者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五经臆说》》)、“心也者,吾所得于天之理也”(《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一《答徐成之》)而言,心即是“良知”;“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王阳明全集》卷三),“诚意只是循天理”,而不是趋利避害的“私心”。从其“诚”或“真诚恻怛”而言,心即是“诚意”;从其“虚者以实而虚,无者以有而无”而言,心亦即是“实心”。不管是“良知”、“天理”,还是“诚意”、“实心”,都是从本体论高度描述“心之本体”的,彼此之间也是相通的。
何以将本体之“心”称之“实心”呢?王阳明从“本体工夫合一”的哲学高度进行了系统的论证。
(一)“从自本体上说”。王门“四句教”第一句云:“无善无恶是心之体。”阳明释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传习录》上)谓“无善无恶心之体”,并非认为心是虚空,而是“不动于气”的“至善”。“至善者,心之本体也。”(《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王阳明说:“至善者,性也;性元无一毫之恶,故曰至善。“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传习录》上)这里所谓“至善”,不是与善恶之恶相对的善,而是与“良知”、“天理”和“诚意”同一本体层次的“至善”。这种“不动于气”的“至善”,是在“善恶末分之始”的本体之心,本体之心是“空空荡荡的”,是“不著相”、“不执着”的,即是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性,因而也是超感性的。从这一意义上,心之本体是无形体,无方所,无内外,无动静,是“无”、“虚”、“寂”、“常”、“未发”,一句话,“心(性)无定体”。但是,它又不同于佛教所谓的“枯井”、“槁木死灰”的虚无之心、寂灭之心②。在王阳明看来,它既是“未发之中”又是“发而中节之和”,既是“常”又是“照”,既是“寂天寞地”又是“惊天动地”,既是“无”又是“有”,既是“虚”又是“实”。
王阳明所谓“心”,即“著相”,又“不著相”。《王阳明全集》卷三载:“先生尝言:‘佛氏不著相,其实著了相。吾儒著相,其实不著相。’请问。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他以父子、君臣、夫妇为例,说明“心”是“著相”与“不著相”的合一,切不可因为“心”是“不著相”的,就否定它有“著相”的一面。《王阳明全集》卷三载:“先生(指王阳明)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这段对话,是从“本体工夫合一”高度,论证心是“无心”与“有心”的合一。“有心”与“无心”,是指著意与不著意。从本体上说工夫,本体虽明莹无滞,但仍须在事为上作为善去恶的工夫,所以,“有心俱是实”;如果不在事为上作功,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所以,“无心俱是幻”。从工夫上说本体,为善去恶工夫不曾对本体有所增减,本体仍是廓然不著一分意思,所以,“无心俱是实”;如果著了一分意思,善恶即失去中寂大公之体,所以,“有心俱是幻”。
王阳明所谓“心”,即是老子所谓“道”,“夫良知即是道”(《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道即是良知”(《王阳明全集》卷三)。《王阳明全集》卷一载:“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天。”“心”、“道”、“天”,都是本体论层面的哲学范畴。刘观时问“道”于王阳明:“道有可见乎?”答曰:“有,有而未尝有也。”又问:“然则无可见乎?”答曰:“无,无而未尝无也。”又问:“然则何以为见乎?”答曰:“见而未尝见也。”问者愈听愈糊涂,请他进一步解释。阳明说:“道不可言也,强为之言而益晦;道无可见也,妄为之见而益远。夫有而未尝有,是真有也;无而未尝无,是真无也;见而未尝见,是真见也。子未观乎天乎?谓天为无可见,则苍苍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时之错行,未尝无也;谓天为可见,则即之而无所,指之而无定,执之而无得,未尝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风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见也。”又问:“然则吾何用心乎?”答曰:“沦于无者,无所用其心者也,荡而无归;滞于有者,用其心于无用者也,劳而无功。夫有无之间,见与不见之妙,非可以言求也。”(《王阳明全集》卷七《见斋说》)在这里,王阳明以“道”和“天”为例,采取非有非无的双遣法,说明“心”是非有非无的宇宙本体,即是“有而未尝有”的“真有”与“无而未尝无”的“真无”的统一实体。如果不是按照这种辩证思维诠释“心”,势必会陷入“沦于无者”的“荡而无归”或者陷入“滞于有者”的“劳而无功”。王阳明是从“有无之间,见与不见之妙”中来说明“心”的。所谓“有无之间”,并非是“有”与“无”的之间,而是包含“有”与“无”两方面的肯定性思维。就“心之体”的“道无方体,不可执着”而言是“真无”,就其“无时无处不是此道”、“亘古亘今,无终无始”而言,又是“真有”。所谓“见与不见之妙”,不是人“各以其一隅之见认定,以为道止如此”,而是从自己心上体认,“向里寻求,见得自己心体,即无时无处不是此道。”这就是“真见”。这种“见而末尝见”之“妙”,即是一种典型的体验思维方式。
王阳明赞同禅宗“以手指显出”的点化人的方法,并以这种方法论证心性。《王阳明全集》卷三载:“一友举佛家以手指显出,问曰:‘众僧见否?’众曰:‘见之。’复以手指入袖。问曰:‘众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众人皆不明佛说之意。“先生曰:‘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鹜,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力。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久久成熟后,则不须着力,不侍防检,而真性自不息矣。岂以在外者之闻见为累哉!’”王阳明以手指出入之喻说明“心”或“良知”作为本体是“不睹不闻”的,是超感官的,看不着听不见,因此,不能从感官上的“有”或“无”来讨论“心”或“良知”。只有“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力”,“工夫方有个实落处”。
王门再传弟子徐樾的门生孙应鳌(1527-1584)深得王阳明思想的真谛,在其《淮海易谈》中,针对佛氏的“空寂之心”和聂豹的“归寂”之说,提出了“吾心原非空寂”的实心论。他说:本体之心“寂非沦于无,感非滞于有,则一是谓之中,万事万化之所由起也。”他进一步提出了“寂感体用”一贯之说,写道:“寂、感,人心也;寂感之间,圣人所谓一贯也。虽寂,天下之故未尝不感;虽感,而本然之真未尝不寂。故寂、感非二,是以两句话,明心之本也。”在“寂感体用”一贯之说基础上,尖锐地批评了佛氏的“寂、感”二分说,指出:“近来学问于人情物理之外,专讲出一段虚无寂静说话。夫虚无寂静,圣人未尝不以之教人,但虚者以实而虚,无者以有而无,寂者以感而寂,静者以动而静,所以为大中至正,不偏不倚也。外实以言虚,外有以言无,外感以言寂,外动以言静,畔道甚矣!”孙应鳌对“心之本”的分析,是对王阳明实心论的精采诠释。
(二)“有从发用上说”。王阳明所谓“心”虽有“虚无的本色”,但他不同于“仙家说虚”和“佛氏说无”,而“只是还他良知(心)的本色。”那么,什么是“良知(心)的本色”呢?他说:“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作得天的障。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王阳明又说:“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晨、风雨露雷,阴霾噎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所以,“人心与天地一体。”(《王阳明全集》卷三《传习录》下)
那么,“实心”的内涵又是什么呢?王阳明指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所同具者也。……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所以,我们必须从“体用合一”的哲学高度诠释它。
从本体上说:其一,“实心”是“纯乎天理之心”,“心之本体,即是天理”(《传习录》上),亦即“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弊,即是天理。”“以此纯乎天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上)其二,实心“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传习录·答聂文蔚二》),亦即是“天理之昭明灵觉,所谓良知也。”(《王阳明全集》卷五《答舒国用》)所以,“实心”只是人先天皆有的“是非之心”、“好恶之心。”它是人用以判断是非、好恶的唯一正确的主观标准。他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上)这里的“知”作为“心之本体”,先验地存在于“实心”之中。通过这一“虚灵明觉”之“实心”,人就会依它自然而行,产生出正确的道德行为,无须从外寻求人的道德行为的来源。
从发用上说:王阳明认为,浑然一体的实心或良知是“妙用无息,而常体不易”的“太极生生之理。”(《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天地间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传习录》下)“吾良知的流行不息”,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王阳明承认它流行发用既包括人的知与情的精神活动,也包括“声色货利”之物欲,内容十分广泛。
1.心与身。王阳明以心为体,以身为用,心与身是体用合一的关系。王阳明把“己(自身、自我)”分成“真己”(或“真吾”)与“躯壳的己(或“私吾”)”。“真己”即是“性”、“良知”、“天理”、“实心”。他说:“夫吾之所谓真吾者,良知之谓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笃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笃敬焉,斯恶之矣。”“从真吾之好,则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将家、国、天下,无所处而不当;富贵、贫贱、患难、夷狄,无入而不得;斯之谓能从吾之所好也矣。”(《王阳明全集》卷七《从吾道人记》)“躯壳的己”即是“耳目口鼻四肢”。“世之人从其名之好也,而竞以相高;从其利之好也,而贪以相取;从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诈以相欺;亦皆自以为从吾所好也。”“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而从私吾之好,“将心劳日拙而忧苦终身,是之谓物之役。”(《王阳明全集》卷七《从吾道人记》)王阳明引证老子的话评论曰:“‘美色令人目盲,美声令人耳聋,美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发狂’,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岂得是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时,便须思量耳如何听,目如何视,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动;必须非礼勿视听言动,方才成得个耳目口鼻四肢,这个才是为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躯壳外面的物事。汝若为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礼勿视听言动时,岂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视听言动,须由汝心。这视听言动皆是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所谓汝心,亦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团血肉还在,缘何不能视听言动?所谓汝心,却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唯恐亏损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礼萌动,便如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是为己之心,方能克己。”(《王阳明全集》卷一《传习录》上)
2.良知与见闻。王阳明从“体用合一”规定了良知与见闻、思虑的关系。他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
3.良知与七情。王阳明对良知与七情的关系论证说:“喜怒哀惧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别善恶,但不可有所著。七情有著,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传习录》下)又说:“盖良知虽不滞于喜、怒、忧、惧,而喜、怒、忧、惧亦不外于良知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夫喜怒哀乐,情也。既曰不可,谓未发矣。喜怒哀乐之未发,则是指其本体而言,性也。……喜怒哀乐之与思与知觉,皆心之所发。心统性情。性,心体也;情,心用也。”(《王阳明全集》卷四《答汪石潭内翰》)甚至认为快乐也是心之本体与工夫。他说:“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许多忧苦,自加迷弃。虽在忧苦迷弃之中,而此乐又未尝不存。”(《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所以,他主张“常快活便是功夫。”(《传习录》下)
4.天理(良知)与感官之欲。王阳明在《传习录》下中指出:“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发无蔽,则声、色、货、利之交,无非天则流行矣。”他肯定人的感官之欲,只要无毫发之私欲,则声、色、货、利,也是天理或良知的流行发用。
由上述可知,王阳明对“实心”或“良知”内涵的阐释,是立足于“体用合一”的心(性)一元论基石之上的。他说:“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传习录》上)又说:“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知,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不及,而蔽有浅深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在王阳明看来,不管是“仁义礼智”、“聪明睿知”,还是“喜怒哀乐”、“私欲客气”,都是人的统一心性在不同方面的表现,都是“实心”或“良知”的流行发用,都是“实心”或“良知”不可或缺的内涵。
二、“实地用功”的“实功”论
在“实心”论的基础上,王阳明进一步提出了“就学者本心日用事为间,体究践履,实地用功”(《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的“实功”论,它同佛教的“空虚顿悟之说”亦即“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机”是根本相反的,不可混为一谈。所谓“实功”,是指学者在“本心日用事为间”,由内向外的实际体认过程,即在身心上存天理、去人欲的修养过程。这是王阳明“实心实学”思想中最为精采的部分。
“实功”这一道德概念,从《王阳明全集》中共检索出5条。与“实功”概念相近的还有“实体”一词,共检索出7条。“实功”或“实体”都是讲道德修养工夫的。王阳明所谓“实体”,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名词,而是指在自己身心上“着实体察”、“以实体得”,“心灵体悟”,主要是教学者“实体诸心,以求自得”;使学者“躬修默悟”,“以实体得”;“着实体察,收拾为要”。他批评学者说:“因思日前讲学,只是口说,不曾实体于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末流之弊只成说话,至于人伦日用最切近处,亦都不得毫毛气力。此不可不深惩而痛警也!”(《传习录》下《与周叔谨》)又说:“良知即是天理。体认者,实有诸己之谓耳。非若世之想像讲说者之为也。近时同志,莫不知以良知为说,然亦未见有能实体认之者,是以尚未免于疑惑。”(《王阳明全集》卷六《与马子莘》)可见,“实功”即是“格致实功”,“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一句话,“皆吾修身中之实功。”
王阳明的“心即理”和“知行合一”,是他的“格致实功”论的两个理论支柱。“实地用功”包含有两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一是什么是用功的“实地”?二是如何在“实地”上用功?
什么是用功的“实地”?王阳明亲自通过“穷格竹子”和读书“穷理”,发现程、朱的“即物穷理”是“析心与理而为二”,“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明正德三年,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年谱》一)认为“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工”(《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传习录》中《答周道通书》)“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由此出发,王阳明对“世儒支离之惑”提出批评说:“后世不知作圣之本是纯乎天理,而专去知识才能上求圣人。以为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我须是将圣人许多知识才能逐一理会始得。故不务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察,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传习录》上)认为“在良知上用工”或“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既可避免“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之弊,又可杜绝“支离决裂”、“玩物丧志”之病,真可谓是一种“简易直截”的工夫。
如何“实地用功”即“在良知上用工”呢?王阳明认为通过“格致实功”即可达到“纯乎天理”的圣人境界。“格致实功”只是一种人在意念发动处作“为善去恶”工夫的修养方法。王阳明把“物”解为“事”字,把“格”解为“正”字。他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王阳明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知行合一”的“格致实功”论,分成“知行本体合一”与“知行工夫合一”两种模式。
“知行本体合一”,即是“就圣人心说”的一种“致知实功”。王阳明释曰:“《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见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又如知痛,必已知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知寒了;知饥,必已知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明儒学案》卷十一)这里,所谓“知行的本体”,是指知行的自然状态或本来面目。“知行本体,即是良知良能。”(《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王阳明发挥古本《大学》的“诚意”之教,以“诚意”阐释“真知行。”在他看来,“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传习录》下),“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意”即“意念”、“意欲”、“动机”,皆是“心之所发”,“意”即是“行”,“知行合一”亦即合于“意”。“意”有“私意”与“诚意”之分。趋利避害之意即是“私意”,循天理之良知即是“诚意”。若心之发动处未被“私欲隔断”,所发之意念不是“私意”而是良知之“诚意”,即是“真知行”,亦即是“知行本体合一”,“知”与“行”均蕴含在本体之中,圣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传习录》下《天道证道记》)圣人只在良知心体上用功。这是一种“即体以显用”的修养工夫和论证方法。
“知行工夫合一”即是“就常人心说”的一种“致知实功”。王阳明晚年提出的“四句教”,是从“体用合一”角度对“致良知”的经典诠释。他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认为“四句教”是“心之本体”由形上界向形下界翻转落实的过程。它与释氏之本心不同。《刘子全书》卷十《语录》指出:“吾儒自心而推之意与知,其功夫实地,却在格物,所以,心与天通。释氏言心便言觉,合下遗却意,无意则无知,其所谓觉,亦只是虚空圆寂之觉,与吾儒体物之知不同。其所谓心,亦只是虚空圆寂之心,与吾儒尽物之心不同。”释氏言心只有形上界而无形下界,“只是虚空圆寂之心。”这是一种“弃用而明体”的错误做法。
在王阳明看来,常人(亦称“下根人”)不同于圣人,只“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传习录》下《天道证道记》)所以,“下根人只在意上用工夫”即只“在意念上著实用为善去恶工夫,久之,心体自明。”(刘蕺山《阳明传信录》)王阳明说:“盖心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于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认为“诚意”工夫即是“致知”工夫。他又说:“但指其充塞处言之谓之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之心,指心之发动处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谓之知,指意之涉著处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悬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诚意的工夫。”(《传习录》下)这是一种“即用以明体”的修养工夫和论证方法。
由上可知,“致良知”是一种“格物之功”,亦即是由内而外的“实地用功”。王阳明针对佛氏明心见性、定慧顿悟之教,批评说:“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恍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所以,致良知“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而只是“在实事上格”的“实功”。
王阳明进一步把“格致实功”分为“静功”与“动功”两类。
所谓“静功”,即“学者悟入之功”。王阳明被贬的龙场驿,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极为恶劣,不仅要求自己能够从“得失荣辱”中超脱出来,而且还要求从贪生怕死的生死中超脱出来。于是,他在石棺里,“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可见,龙场悟道得力于“静功”是不言而喻的。王阳明三十九岁时,升为江西庐陵县知县,“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寺院,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王阳明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一)“静功”分为“静坐”和“省察克治”两层含义。“静坐”是离开一切事为、在心体上“收放心一段工夫。”王阳明在一封信中指出:“前在寺中所谓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也。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拏,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同上)所谓“收放心”,并非是教学者“坐禅入定”,而只是通过“静坐”工夫使心离开事物的纷扰,思虑的奔驰,把为物所役的心收回来,同佛教的禅定之说是有区别的。“省察克治”是在“静心”的前提下,进一步在心体上做“省察克治”工夫。他说:“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所虑,多是从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槁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人省察克治。”(《传习录》上)什么是“省察克治”?王阳明释曰:“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听着,才有一念萌动,即与克去。”即在静心时,通过“省察克治之功”,将心体中的私欲之根一一拔去,让心体如明镜,方可达到圣人境界。明正德五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与学者“论实践之功”。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蚀之镜,须痛磨刮一番,尽去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若驳蚀未去,其间固自有一点明处,尘埃之落,固已见得,才拂便去;至于堆积于驳蚀之上,终弗之能见也。此学利困勉之所由异,幸勿以为难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恶难,其间亦自有私意气习缠蔽,在识破后,自然不见其难矣。古之人至有出万死而乐为之者,亦见得耳。向时未见得里面意思,此工夫自无可讲处,今已见此一层,却恐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王阳明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一)在这里,磨镜之喻,就是“省察克治,扫除廓清”工夫的形象说明,教人实地用功、走向具体实际,与佛教的“禅定”之说是有区别的。
王阳明尽管将实学元素赋于“静功”之中,但是“静坐自悟性体”的教法仍有虚学的成分。王阳明曾在滁州倡“静坐”之法,以高明话语指点学者。他说:“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但是,“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稿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传习录》下)王阳明指出:“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洒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王阳明全书》卷三十三《年谱》一)他清醒地认识到离用讲体,离动讲静,必趋于空虚,流于清谈、厌事、枯稿之病。“静坐”离开事为、自悟心体,含有严重的虚学成分。所以,必须打破静与动、无事与有事、体与用的界限。“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传习录》上)钱德洪曾转述阳明之教说:“先生曰:‘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稿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无事有事,精察克冶,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良知原无间动静也。’”(《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刻文录叙说》)为了克服“徒知养静而不知克己工夫”之弊,王阳明提出了“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传习录》上)不管有事还是无事,是动养还是静养,都要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在事为上磨炼就是在心体上磨炼。这就由单一“静功”升华为“动功”与“静功”合一的“在事上磨炼”。这是一种即用以明体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实学,是王阳明最为成熟的体用兼备的工夫论。
在王阳明看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王阳明答陈九川“物在外,如何与身心意知是一件”时,指出:“指其充塞处言之谓身,指其主宰处言之谓心,指心之发动处言之谓之意,指意之灵明处言之谓之知,指意之涉养处言之谓之物,只是一件。意未为悬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诚意,则随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归于天理,则良知之在此事者无蔽,而得致矣。”(《传习录》下)他又指出:“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传习录》上)所以,致良知“亦不是悬空的致知”,而是“在实事上格”,也就是“在事上磨炼”或“在事为上用功”。“在事上磨炼”或“在事为上用功”,实际上,也就是“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
王阳明进一步具体地诠释了陆象山的“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传习录》上载曰:“(“陆”)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先生曰:‘除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即是“在事上磨炼”或“在事为上用功”。在这里,我们将它分为四类:一是在道德行为上做工夫。徐爱问孝道于阳明“不知亦须讲求否?”阳明答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个诚孝之心发出来的条件。”(《传习录》上)二是在喜怒哀乐人情上做工夫。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便是心之本体。喜怒哀乐是心体之发动,即是事物,或过或不及。随时随事将其调整适中,使其合乎心之本体,就是致中和的实功。三是在人的视听言动上做工夫。视听言动,是心之形体之运用。《大学问》云:“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心其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其形体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四是在人的不同境遇上做工夫。不管是处于富贵贫贱境地,还是处于患难死生境地,人必有不同心态反应。只有使之合乎心之本体,就是致中和的实功。综上所述,身与心本为一物,正心与修身原为一事,本体与工夫实不可分,其实都是“事上磨炼即心地工夫”的“格致实功”。
“格致实功”是王阳明“实心实学”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实学”这一哲学范畴,从《王阳明全集》中共检索出8条。这8条资料中的“实学”,都是从“格致实功”意义上来使用的。如他针对好友“希颜孝心纯笃,哀伤过节”,使“希颜茕然在疚”,失之中和之节。故阳明指出:“患难忧苦,莫非实学。”(《王阳明全集》卷四《寄希渊》)患难忧苦之时,正是“格致实功”之时。他针对王纯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说,而未尝实加克治之功”,“失之支离外驰而不觉”,“遇事辄有纷扰之患。”王阳明指出:“夫心主于身,性具于心,善原于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无形体可指,无方所可定,夫岂自为一物,可从何处得来者乎?故曰受病处亦在此。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从事事物物求个至善,而后谓之明善。……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王阳明全集》卷四《与王纯甫》二)王阳明针对“一切屏绝”之说,指出:“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粮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一切屏绝’之说,是犹泥于旧习,平日用功未有得力处,故云尔。”(《王阳明全集》卷四《与陆原静》)好友昆季虽用志不凡,敏而好学,但也存有世俗之见。认为“‘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王阳明指出:“谓举业与圣人之学相戾者,非也。程子曰:‘心苟不忘,则虽应接俗事,莫非实学,无非道也。’而况于举业乎?谓举业与圣人之学不相戾者,亦非也。”不管是“应接俗事”还是“勉习举业”,只要不忘圣贤之学,皆是实学;一旦忘记圣贤之学,皆是俗学。二者之分,只在“忘与不忘之间”。王阳明进一步分析说:“家贫亲老,岂可不求禄仕?求禄仕而不工举业,却是不尽人事而徒责天命,无是理矣。但能立志坚定,随事尽道,不以得失动念,则虽勉习举业,亦自无妨圣贤之学。若是原无求为圣贤之志,虽不举业,日谈道德,亦只成就得务外好高之病而已。”(《王阳明全集》卷四《寄闻人邦英邦正》)王阳明在友人信中,再次谈到“格致实功”。他说:“郡务虽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实学。以宾阳才资之美,行之以忠信,坚其必为圣人之志,勿为时议所摇,近名所动,吾见其德日近而业日广矣。”(《王阳明全集》卷五《答路宾阳》)甚至在诗歌中,王阳明也讲到实学。他说:“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须遣认教真。”(《王阳明全集》卷十九外集一《春日花间偶集示门人》)有一段王阳明与属官关于“簿书讼狱”的对话,最集中地表达了他的以“格致实功”诠释“实学”的思想:“有一属官,因久听讲先生之学。曰:‘此学甚好。只是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闻之曰:‘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讬,加以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传习录》上)综上所述,不管是在“患难忧苦”、“钱粮兵甲,搬柴运水”、“应接俗事”和“勉习举业”上,还是在“繁重郡务,民人社稷”、“坐起咏歌”、“簿书讼狱”上为学等,皆是在心上“去人欲,存天理”的“省察克治”之实学,若离开了这些“实地用功”,便是虚学。
钱德洪在《刻文录叙说》一文中,认为王阳明一生之教有三变:“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和’之说,直指本体,令学者眼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他在《西园闻见录》巻七中,详细地记载了王阳明的三种入悟之道:“阳明先生曰:‘君子之学贵于得悟,悟门不开,无以征学。入悟有三:有从言而得者,有从静而得者,有从人情事变练习而得者。得于言者谓之解悟,拟议触发,未离言诠,譬之门外宝,非己家珍。得于静坐者谓之澄悟,收摄保聚,犹有待于境,譬之浊水初澄,浊根尚在,才遇风波,易于淆动。得于练习者谓之彻悟,磨砻洗涤,到处逢源,愈震动,愈凝寂,不可得而澄清也。根有大小,故蔽有浅深,而功有难易,善学者之所至,以渐而入,及其成功一也。夫悟与迷相对,不迷所以悟也。百姓日用而不知,迷也;贤人日用而知,悟也;圣人亦日用而不知,忘也。学至于忘悟,其几矣!’”解悟、澄悟、彻悟(忘悟)三种悟法,与王阳明教法的三阶段是相当的。王阳明的教法,根据明代学术的变化,由言诠的解悟到静坐的澄悟,再由静坐的澄悟到“致良知”的彻悟(忘悟)的动态过程。与此相应的,在人格境界上,由日用而不知的百姓到日用而知的贤人,再由日用而知的贤人到忘悟的圣人的不断升华过程。他的“格致实功”论是最高境界的动静合一的工夫论,是最能体现实学精神、最具有现代价值的工夫论。
注释:
①王阳明指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习录》上)“仁义礼智也是表德。……主于身者,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己。”
②禅宗慧能指出:“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六祖坛经》)。
(责任编辑 梁一群)
B248.2
A
1008-4479(2010)02-0093-09
2010-01-18
葛荣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