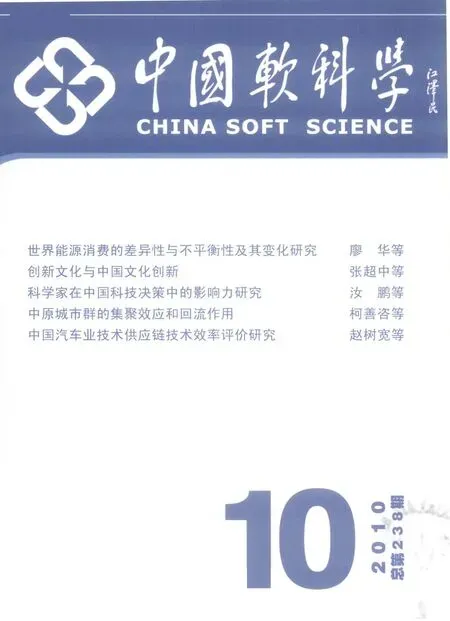创新文化与中国文化创新
张超中,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创新文化与中国文化创新
张超中,武夷山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38)
目前,我国创新文化建设明显滞后,不能适应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其基本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们没有意识到“自主创新”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范畴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范畴,另一方面,人们对自主创新差序格局的内在张力认识不够,旧的创新文化难以解决原创性资源稀缺问题。以原创性为中心开展创新文化建设首先需要创新文化自身的转型,并需要中国文化创新的支撑。在自主创新条件下,传统文化创新与新型创新文化建设能够相互为用,并促进和推动自主创新差序格局的生成。
自主创新;创新文化;差序格局;原创性;转型;中国文化创新
我们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提出实际上肇始于科学技术界,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决策思想主要来源于社会科学界之间存在重大不同。与这个现象相呼应的现象是,虽然自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开始,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原则,但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上述战略的理论研究和解释仍然显得薄弱,全社会至今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自主创新的共识。与此相应的是,一方面自主创新成为强势和主流话语,围绕自主创新的论著层出不穷,另一方面,学者们则又自感论证的分量不够,觉得媒体中突现的自主创新观似乎离自主创新的本来意蕴相差甚远。我们认为,上述不同、不足和矛盾的出现既折射出我国深化改革过程中旧规和新路的基本差异,同时又反映出创新文化建设需要文化创新支撑的基本诉求。可以说,应当在文化创新的意义上来深入认识和理解自主创新,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新文化建设。
一、自主创新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依赖
进入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年来,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反而促使一部分国家和个人对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更加重视,科技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一起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组成部分,科技创新和文化资源共同支撑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比之下,我国在提出自主创新的过程中,看到的主要是科技创新的基础性作用,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只是以创新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一般来说,创新文化对促进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及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事实上,我国在制定了许多扶持和促进自主创新的科技政策和措施的同时,创新文化建设则明显滞后,既缺乏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也很少推进对“非共识项目”的安排。因此从实际效果来看,促进自主创新的环境氛围的形成主要不是来自于创新文化,创新精神仍然受到各种因素的羁绊。例如,科研诚信应属于创新文化的内核,但我们观察到科研诚信问题日益突出,在对其治理效果未见好转的情况下,人们感受到的不是创新文化对科技创新的促进和生成,反而自主创新意识受到压抑和削弱。
如果说创新文化主要包括观念文化、制度文化甚至环境文化的话,那么在我们看来,当前创新文化建设存在的基本问题是仅仅从“创新”的角度而不是“自主创新”的角度去理解有关文化内涵,而在“自主”不在场或者隐而不现的情况下,自主创新意识的增强并发挥实际作用就会缺乏能动机制。这个问题的产生并不特别出奇,在我们社会的很多人都已经习惯于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的情况下,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从“创新”提出并受到推崇的基本动机上去理解和行动原不应受到多少指责。只是这样一来,“自主创新”则从国家的战略层面转瞬间变化为企业的利益诉求,其对全局发展的必要性和战略性就相对显得分量太弱。许多国外的政治家和学者一开始也不理解“创新”和我们提出的“自主创新”之间的区别,因为“创新”本来就是基于创新主体的创造性,天然具有“自主”性质,不需要突出强调“自主创新”。因此,当我国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一件具有特殊使命和意义的大事去做的时候,由于国情不同就造成了“自主创新”之翻译上的困难,“innovation”不是 ,“independent innovation”也不是 ,“indigenous innovation”勉强接近“自主创新”的意义,但其具有的缘于地域特色的保守性仍然表达不出“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导致“自主创新”言传性的困难。我们认为,“自主创新”本来就是一种文化范式,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这种范式所体现的价值既具有时代性,更具有永恒性。具体来说,自主创新是一种文化启蒙和思维的创造性转换,在对创新活动的迷失起到警醒作用的同时,也对创新的未来趋势作出基于永恒价值的规定和引领。创新文化建设应当围绕上述内涵开展,并直接体现出文化的本质功能。
从构建创新文化的实践效果来看,那种仅从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角度 (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去理解的“自主创新”并没有使创新文化建设形成一个热潮,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用语虽然变了,但是说话的人并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创新文化建设尚未达到改变“观念”的目标。显然,当人们意识不到的时候,所谓的“观念文化”建设不免于落实不到位,而在核心观念缺位的情况下,制度建设无由支撑,创新氛围无由形成。至于应当如何表述自主创新的核心观念,我们认为,对创新文化范式的研究固然有益于澄清工作,实际上仍然落在外围的层面上,没有直面“为什么要自主”这样的问题[1]。这种超越一般理性限制而略带感情色彩的问题的背后已经不是一个经济范式,而是具有历史记忆的文化范式。可以说,这种范式表达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感情,并用文化语言记录了文化的起点、历史演变及其未来的可能发展等方面。只有把握住中国文化关于“自主”的微妙宏旨,才能有助于把握自主创新的意蕴,并以此为基础开展创新文化建设。
文化本来是活的,创新也是活生生的,自主创新就应该让人们活活泼泼,有所触动而焕发精神。但是,在有人最初提倡自主创新精神的时候,人们感受到的却是一种久被压抑之后的呐喊。当然,这种呐喊一开始听起来有些刺耳,似乎不和谐,但是在战略决断层面,当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需要真正得到保障的时候,代表国家意志的最高决策者反而从中听到了和谐的声音。那么,到底是什么触动了决策者?其实,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非常普通的问题。在我们个人的成长过程、日常生活和交往中,会时不时遇到让人不自主的事情,因而感到不顺心。一般情况下,这些不顺心都是非常短暂的,并不值得深究,但是,当不自主一旦成为屈辱的象征的时候,那么,向往自主并做到自主,在性质上自然就是革命性的变化。一个人是如此,一个国家也是如此。回顾我国的近现代发展历史,不自主的事例比比皆是。即便是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当“核心技术是市场换不来或引进不来”成为新的共识的时候,加强自主创新就成为打破外力垄断的自然选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国家毕竟不是个人,满眼歌舞升平的人自然也难以体会到一个国家的艰辛。正是由于立场不同和角度不同,利益主体不同,所以自主创新战略从确立开始直到至今,争论和歧义不断,国家意志只不过是价值选择多样性中的一元,非国家性主体对自主创新的态度分化明显。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创新文化建设显然不能仅仅依靠强制性。在许多组织性行为并不利于促进认识深化的时候,如何减少干扰和阻力,使自主创新精神真正深入人心便成为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这样一来就形成如下态势:贯彻落实自主创新战略的精神和方针需要真正的活泼泼的创新文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组织性文化如何为创新文化建设不断创造条件成为一个难题。从天性来讲,人皆不乏创造性,是什么使创造性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创新文化建设应当直面这个问题。
借鉴我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有助于揭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分析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特点及其与西方社会的不同时,他认为这是“差序格局”与“团体格局”的不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2]。”翟学伟指出,在费孝通先生提出这个原创性的概念之前,他在 1936年就看到,美国式的社会学在中国是失败的,社会学在此前几十年对了解和改造中国社会未做出明显的贡献,而“差序格局”是他强调的社区调查、类型比较法与理论思考精彩而巧妙的融合的典范。这种典范也表现在费孝通先生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而不是严格定义的方式提出的,从而更增加了这个概念的解释能力,每个学者都可以从中读出新的内涵。例如,孙立平就认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稀缺资源分配是通过差序格局来实现的,血缘和地缘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而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关系将这种资源转成由国家来控制,从而也就引发了社会关系的变迁。翟学伟本人则认为,差序格局不仅是一个社会结构的概念,也是一个行动的概念,而后者将引发出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动态的研究理路,其中费孝通突出的这个“推”字让我们看到了其动态性以及动态性中所蕴藏的个人与家庭的抱负与理想[3]。
我们知道,自主创新从提出到推进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阻力,喻示着国家作为一个中心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费孝通先生的比喻非常符合传统社会特点的话,那么中国现代社会的特点实际上近乎一种“反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在经过了一百多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后,我们蓦然发现,我们所丢的“石头”基本上是外来的,是不自主丢在水面上的,因此“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的“样式”好像皱巴巴的,反映出一种心底里的痛。在这种意义上,“自主创新”确确实实应当是我们自己自主丢出的石头,但是由于“水”变了,也由于丢石头的时候心境不同,“波纹”的推展速度反映出的便不是一种自然节律,而是一种万象纷呈之后的“文化节律”,从而使创新文化建设面临着改变“反差序格局”的基本任务,成为了促进建立自主创新“差序格局”的基本措施。事实上,按照我国官方的正式解释,自主创新包括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层面或三种形式,从性质上来看,这种“差序格局”是以原始性创新为中心推扩开来的,但是由于我国不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的发源地,因此多年以来,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格局是一种“反差序格局”,我们可以探源,只是我们本身不是源头。这样一来,与之相应的科技活动和文化也是同样的格局,在注重科学技术的一般规范的同时,基本上不容忍与之不同的规范,从而没有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技术“差序格局”。如果说上述关于“差序格局”的理论也是行动理论的话,我们从中看到的恰恰是无助于为自主创新立基的行为,创新文化建设没有服务于中国科学技术多样化发展的目标。这种创新文化的格局难以适应并表述自主创新的精神实质,虽然不能说二者格格不入,但还是让人感到不能达到丝丝入扣的理想状态。比如,对中医药来说本不应该这样“推”,之所以多年来发生强制中医药“就”现代医学和科学之“范”的情况,说明我们的创新文化一定是出了问题。也就是说,当我们的创新文化倾向于否定我们自己的原创性成果的时候,也就“推”不出自主创新的“差序格局”。作为一种诊断创新文化问题症结的理论和方法,“格物致知”相当于“实事求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来看如何通过创新文化的转型从传统走向未来。
从大的格局来看,近百年来主导我国的创新文化是一种提倡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文化,这也是中国处于特定历史和社会发展阶段时的必然选择。受其影响,尽管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但这样一种创新文化的局限性就不可避免地日益暴露出来,其弱点之一是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弱点之二是受其长期影响而形成的创新思维和意识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达不到根本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使创新格局焕然一新的作用。由此我们看到,由于自主创新存在“差序格局”,创新文化也存在相应的“差序格局”,因此创新文化建设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在对之进行细分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设措施。根据我国自主创新的现状及其存在的瓶颈问题,我们认为,当前和未来创新文化建设的基本任务是解决原始性创新稀缺的问题,只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才能看到“自主创新”的文化本质及其“引领未来”的基础性路径,也才能说明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文化特性及其渊源所在。根据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目前的创新文化建设之所以措施乏力,是因为对自主创新“差序格局”的内在文化张力没有充分认识,这种张力事实上一直就存在,实际上就是“中西体用”之争的逻辑起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争论虽然仍将延续下去,但是与以前争论的不同在于,在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核心原则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的原创性能够以此为契机得到充分展现,中华民族的原始性创新能力能够得到充分释放,从而使一直以来原始性创新相对薄弱的格局得到充分改变,原始性创新将从稀缺变为富有。因此,创新文化建设的时代任务已经明确,就是从观念和认识上促进我国的原始性创新资源从稀缺到富有的根本性转变,真正建立自主创新的“差序格局”。我们认为,“再创新”的成效既取决于“原始性创新”的基础是否牢固,也取决于创新文化的转型,应当坚决改变长期以来约束创新的“技术决定论”观念,通过非技术道路通达创新的源泉。在此基础上,“集成创新”既是一种技术集成,更是一种文化集成,而如何集成仍然取决于我们对原始性创新的理解。
二、创新文化的原创性转型及其多元并存格局
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现实需求和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创新文化应当属于大文化的范畴,即创新文化的内涵、导向和建设已不再仅仅服务于科技创新的需要,而且要服务于中国文化创新的进程。这是“自主创新”带来的文化启示和作为核心战略原则应当坚持的文化属性。
在经过为期两年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战略研究之后,我国于 2006年确立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新时期科技工作方针。按照这一方针的自身逻辑,“引领未来”的起点就是“自主创新”,也就是说,如果“未来”是不确定的和可以想象的,那么“自主创新”不仅应当具有给予“未来”以“引领”的性质,而且应当通过自主的创新路径,能够使“未来”发展的内容具有确定的实实在在的把握。按照这样一种推定,我们必须对“自主创新”进行充分的研究,明晰其意义,理解其实质,把握其要领,做到对“自主创新”如掌上观花,真真切切,通过把握起点开创一个能够把握的未来。绝对不能如“雾里看花”,使“自主创新”的着力点流于虚泛不实,难负重托。但是,对这样一个关系未来的重大问题,近年来却鲜见其辩,特别是在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原则之后,有关工作虽然围绕着自主创新部署开展,但是全社会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自主创新”的热潮,可以说自主创新仍然是步履维艰。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与对“自主创新”的研究和解释力度不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自主创新差序格局存在的内在阻力有关,使得自主创新的短期目标不能服从于“未来”需求,造成对“引领未来”的钳制。因此,创新文化建设肩负着十分艰巨的历史重任,其逻辑起点就是“自主”。如果能够做到真正“自主”,其他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在文化意义上,“自主创新”与“创新文化”的差异并不太大,前者规定了创新的“自主”性质,把一般经济范畴上的创新转化为文化范畴上的创新,从而使“以我为主”不仅仅是一种自我期许,而且是一种通过对“我”的认识实现“我”的提升,并进而通过“我”之贡献承担“我”之责任,达到“我”的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责、权、利的结合。因此,“自主创新”与其说是竞争的需要,毋宁说是对“我”的鞭策和激励,是一种依靠自我贡献而不是借助外力的方式所实现的“创新”。在这种意义上,“创新文化”才具有一种本质上的归属感,使得这种“文化”不仅仅具有提倡和促进“创新”的功能,而且应当具有“文化”的约束和教化功能。很多年来,人们讨论和重视创新文化大多是缘于“创新”而非“文化”,从而使得文化的约束或助推功能渐渐淡化,流弊所至,则使现行的“创新文化”非但未能有效促进创新,而且丧失了文化的基本约束功能,于是,在创新活动中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屡屡发生。这种现象在当前的中国决不是个别的,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的这个“自主”没有经受文化传统的熏陶,所以在关键时期反而不能“自主”,不堪大用。至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们认为,若按照目前的通行看法,其实“创新”与“文化”之间也存在内在不一致的涵义,表现为新传统与老传统的文化冲突,使得“自主创新”的文化意义一直比较模糊,也因此使得“创新文化”建设不见起色,对自主创新的促进大多是缘于政策而非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从文化层面上澄清对“自主创新”和“创新文化”的认识就显得非常关键。既然是核心原则,我们就必须了解其“核心”何在。
在我们看来,党中央、国务院把“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原则,根本用意就在于强调中国一定要走自主发展道路。到底这条道路如何走,并且要创造出自己的特色来,关键就在于要“加强自主创新”。从字义讲,“加强”是“进一步强化”的意思,但是如何再迈这一步需要仔细掂量,其本义并不是要通过其他方式去“加强”,而必须按照“自主创新”自身的发展逻辑去“强化”。我们看到,自从“加强自主创新”以来,国家已经从财政、法律、行政、组织等方方面面制定和实施了许多政策措施,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但是我们也观察到,在具体落实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自主创新”的气势尚未随之明显加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原因是“创新文化”建设没有及时跟进,拖了后腿。正是由于“创新文化”的薄弱,其他政策措施的效力就打了折扣,使得“自主创新”根基建设的重要性问题暴露无遗。我们在这里并没有抱怨的意思,只是想指出这样一种事实,即相对于以往行之有效的手段来说,“加强自主创新”更需要一种特别手段,或者说一种核心方法,使得“核心原则”能够借之体现在方方面面,并表现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如果说其他手段皆是强制性的话,那么文化的方法则属于自愿自觉的性质,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主创新”。我们认为,“核心原则”的落实应当借助于文化的方法及其内源性力量。
从总体上看,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化早熟的国家,但是近现代的中国文化发展尚没有进入成熟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创新文化建设所面临的挑战要远远大于预期。我们想,无论从规模还是从内容来看,中国当代的思想文化争论并不逊于春秋战国时代,应当指出,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如何避免把“中西之争”单纯归结于利益之争,也是把握和处理有关挑战的核心原则之一。如果在大的文化格局的形成方面不能够宽容和包容的话,那么这种小肚鸡肠将会非常不利于创新文化建设,使得“创新”成为一种偏狭的创新。但是,能够做到兼容并蓄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中国来说,这不但是一个养气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养势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些漫长,所以我们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把“韬光养晦”作为与国际交往的方针。由于翻译的原因,国际上曾经对之产生了误解,以为中国要把真实实力掩藏起来,并因此以为中国将别有用心。在 2010年第 7期的《读书》上,有学者指出如此翻译和如此误解都缘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存在隔膜。他认为,其实从中国文化之理和作为了解中国经典的英国学者理雅格的翻译来看,“韬光养晦”的正解原意是:不主张用“光”,这种“光”之“明”本来就需要守护,否则就会越来越暗,因此需要“养晦”[4]。按照《老子》的看法,“养晦”有具体的理论和方法,就是要做到“知其雄,守其雌”,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其起点还是要能够做到“自主”,要知道是谁在“知”,是谁在“守”。现在看来,从“韬光养晦”到“自主创新”,中国文化精神在其中是以一贯之的,而之所以产生各式各样的误解,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文化讲究和推崇向内用力,至于这种修养在外接的时候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也只有达到和领会这种境界的有识之士才能知晓,否则,向内用力或被视之为软弱,或被视之为“阴谋”,结果都失之偏狭,结果人们做不到顺势而为,从容交往。作为与“自主创新”相应的“创新文化”,本质上应该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文化,而要满足这种要求,首先就要有“自知之明”,这正是费老所强调的。我们相信,在对创新文化有不同认识的情况下,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的一点应当是:创新文化发挥“潜移默化”功能的基础条件是首先有“自知之明”。但是,正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这一基础条件,导致“自主创新”议而难决,推而难行,做不到“真知真行”。这个挑战虽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但还是事出有因。
我们不愿意因为存在这个挑战而就去对其“因”抱怨不已,而宁愿把这种“因”的出现看作是一个积累经验并不断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作为一个探索性的课题,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是大气度和大力度的,其中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也是超越以往的,而为了把这种“异质”文化“中国化”,甚至有过“全盘西化”的提法和做法。全盘西化妥与不妥既是看法问题,同时也是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为了促进“中国化”的进程,中国在总体上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现在来看,“现代化”既是“中国化”的一个过程,但又不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化”,否则,“中国特色”的提法就没有多少必要性。至于如何实现“中国化”,很多人都愿意借鉴和吸收佛教中国化的经验,希望能够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抛开其它层面不说,我们看到,佛教的中国化并没有否定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反而让人看到了其自身蕴藏的创造性,借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可是在西方文化中国化的过程中,或明或暗都存在着否定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倾向,多年来造成的后果就是当我们要“加强自主创新”的时候,中国文化的空壳化现象竟然使得“自主创新”的主体非常模糊,严重一点说,就是利益主体很清晰,文化主体看不清。当然,笼统地说,官产学研都是自主创新的主体,分工各有不同,只是以上主体在具体担当的时候,其思维和做法的创造性尚需进一步的甄别。到目前为止,这个工作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其标志性的现象就是在自主创新的差序格局中,原始性创新可以说是依然处于悬空或缺位状态。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承认,我国的原始性创新是自主创新最薄弱的环节,亟待加强。我们认为,这样讲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说,如果不包括我国的传统资源基础,并且单纯指现代科学技术的话,上述说法基本上能够成立。但是,如果包括中国传统的原始性创新成果的话,上述说法就不仅值得推敲,而且值得进一步思考。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这样思考!在多数国民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情况下,猛然间让其认同传统文化实属挑战。我们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现代化导向的教育,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是学习、模仿、吸收和重现西方文化的原创性。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这种原创性在中国仍然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这说明我们没有学好,可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无论我们多么想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实际上其间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转变,由于在这方面缺少研究和经验,至今我们还在摸索如何才能实现西方文化原创性的中国化。这个任务本来应该是创新文化来完成的,可惜的是以往的“创新文化”存在一种偏向,不能在中西之间做到不偏不倚。我们提出这个问题,不是对先前的偏向进行批评,而是强调:为了加强和促进自主创新,创新文化应当转型。《大学》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经过审慎思考之后,我们认为,在很多人都把促进自主创新的重任寄望于创新文化的时候,忽略了在自主创新条件下,“创新文化”也需要自主创新。如果创新文化不能体现出时代精神,不能解决“中国化”的机制,那么应对挑战只是一种姿态,没有实力作为支撑。
在经过系统研究和比较之后,我国已经有学者提出了创新文化的转型问题。金吾伦教授认为:“把事物看作是一个生命体的观点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我们完全应该运用并且可能运用这种生命系统的观点来研究创新。学习型组织创始人彼得·圣吉过去更多地强调适应性学习 (adaptive learning),现在已开始强调生成性学习 (genegative learning)。创新与学习是不可分的。有人甚至认为创新就是学习。总之,我们的创新文化同样应该有一个转换:从适应性文化转向生成论文化。生成论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也应是中国创新文化的特色之所在[5]。”我们看到,创新文化的转型恰恰是指向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上述观点并不显得突兀,其对创新文化发展趋势的判断也具有前沿研究成果的基础支撑。在这里,我们认为,如果说基础科学的研究正在向主体和客体的交界处发展的话,那么要促进研究的深入发展,取得相关领域的原创性成果,就应当建设相应的创新文化,实现客体向主体的跃迁。但是,旧的创新文化已经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而新型创新文化的建设也不能仅仅在“氛围”上下功夫,而必须基于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实现科技创新与创新文化的深刻互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创新的潜力逐渐凸显出来。按照金吾伦教授的看法,机械论文化是今日流行于世的主导文化,它实际上是构成论文化,而中华传统文化是以生命一体的观点来了悟、体察、理解世界万物运行的法则,用生成论思想来体察宇宙万物的本源的[5]。我们看到,创新文化的这种转型来源于对自然原创性的另外一种理解和表达。在不否定其他文化传统也具有甚深智慧的前提下,中国人应当首先熟悉的是自己的传统。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因为即便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文化的转型无关,作为文化传承,我们也不应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学习,更何况传统文化在经过多年的边缘化之后又要承担起建设新型创新文化的重任。这样一来,我们对“自主创新”的信心更加坚定,避免了王国维所痛苦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心理上的冲突,创新文化的文化基础因此从贫瘠一变而为博大精深。
很多人在心理上对这种转变并不适应,甚至可能会产生新的精神焦虑。从现代生成论思想的起源来看,它源于构成论思想的发展却又与构成论完全不同。按照目前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及其产生的判断事物的标准进行衡量,若说生成论思想源于国外,则该思想多少显得具有前沿水平;若说它是中国内生的,好些人就平添几丝疑虑,以为这又是一种新的“格义”,牵强附会以自欺欺人。我们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心理抵抗倒不是十分担心,这本来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只是在此进一步指出,创新文化的生成论文化转型在本质上是一种对原创性认识的转型,由于发生了认识上的转变,就使得自主创新、创新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原来的隔膜几近消失,而在原创性的视野之下,自主创新呈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差序格局”,即集中国本土性资源和其它流行性资源等各种原创性资源于一体的多元格局。按照社会学的看法,“多元一体”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特色,事实上多年来作为争论焦点的“西元”早已进入中国社会并发挥巨大作用。通过观察和思考,我们认为,在新型创新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秉持积极开放的心态,对原创性资源的进入及其可能产生的矛盾应当本着“自主”的原则,在创造中化解。
三、以原创性为中心开展新型创新文化建设
新型创新文化是一种生成论性质的文化,也是一种整体论性质的文化。若论文化的基本性质,它本来就具有整体性,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次强调新型创新文化的生成论和整体论性质?这首先不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生成论性质的文化所以我们就去推崇它,而是因为这种文化不仅开启了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视野,而且能够对长期以来流行的还原论和构成论性质的文化起到补弊救偏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坚持整体论与还原论的辩证统一,是妥善处理新旧转型矛盾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而如何坚持尚需要在具体的创新实践中摸索经验。我们认为,新型创新文化的基本优点就是能够让历史告诉未来,让理论指导未来,让人文引领未来。国家战略本来就应当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而作为它的核心原则,“自主创新”不仅具有上述性质,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文化和创新方法。如果说通过其他方式难以解释“自主创新”的真切涵义的话,通过生成论性质的创新文化则能够与自主创新的文化精神对话。有位伟人说过,只有理解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地应用它。这里我们比较偏重于对自主创新的文化理解,这既是建设新型创新文化的关键,也是决定自主创新成效的基础。从这里出发,我们认为,新型创新文化建设应当以原创性为中心进行战略部署,只有解决了制约原始性创新的瓶颈性问题,才能确立自主创新的时代精神,带动自主创新的全局性发展,从而引领未来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
由于欧洲成为近现代科学技术兴起的中心,人们在研究这种历史现象时对起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正是人性的解放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为自然科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了条件。长期以来,人们都将神学视为负面因素,而事实上,科学与神学的冲突确实也是欧洲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事件。现在,我们把上述历史过程的过去与未来加进去,就会看到在此之前,出现了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和复兴,而科学精神正是对古代理性精神的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在此之后,科学的独立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科学精神越来越被新的“神话”所遮蔽和扭曲,出现了创新文化转型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由于科技与人文的日益分离,促进科学发展的创新文化越来越偏离原来解放人性的目标,表现为人们对科技的过分崇拜限制了科技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科技的自身发展也越来越表现出人文化的趋势,这就要求新的创新文化不仅要弥补旧的创新文化本身固有的缺陷,而且要在新的价值导向的引领下建设与之相应的创新文化。有鉴于此,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认为,中国文化的“自然合理”的理性传统比单纯的科学理性更能够促进未来社会的发展[6]。从文化属性来看,这种“自然合理”的传统是中国文化的原创性传统,一方面保持了原始宗教的合理性内核,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对其给予人文化的创造性解释,从而奠定了“生生不息”的文化精神。如今我们建设新型创新文化,不能僵化死守文艺复兴对希腊古典文化的学习经验,也不能单纯移植在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创新文化,而应当以新的视野重新看待“自主创新”所应当依赖的原创性传统路径。当前,人们都对中国的复兴给予无限的期望,似乎满怀信心,但是细推起来,很多人的乐观又不免是盲目的,因为就现实来说,我们对自己传统的了解并不比对西方传统的了解多多少。《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如果我们的立足点选择不好的话,那么就无法接续历史,从历史走向未来。我们认为,“自主创新”的西方经验可以借鉴,但其基础还是我们对自己传统的学习。事实证明,丢弃自己传统所导致的未来将是创造力萎缩的未来,做不到通过“自主创新”以“引领未来”。
我们提倡传统,不是因为对传统的盲目崇拜,而是因为对传统的深切认识,特别是基于传统之中所蕴藏的原创性资源。如果从近年来发生的文化现象来看,科学技术界对传统文化表现出越来越重视的趋势。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身体力行,并督促自己的学生认真学习和研究《老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校长朱清时院士基于科技自身向复杂性和整体性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东方科学文化复兴的观点。他们的做法和提法引起了很大反响,也引起了激烈争论,在我们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创新文化转型的诉求。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思想学术界的研究探索过程,在总体上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即希望能够在科技创新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新的结合点,其典型事例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共同推崇卡普拉在他的《物理学之道》中所阐明的物理学的发展与东方神秘主义相结合的观点。事实上,西方所称谓的“东方神秘主义”在中国的传统表现是“人文主义”,但由于食洋不化,更是由于对传统的隔膜,几十年过去之后,我们在这类问题上的研究并没有走得更远。那么为什么这个时代呼之欲出的创新迟迟不能付诸行动呢?我们看到,这里蕴藏着关键性的问题,即目前的创新文化仍然是一种“科学化”的创新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做法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种“科学化”看待“历史”和“文化”的做法已经引起了人文学者的批评,李德顺教授认为,“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实质上不是一个如何对待外部现成对象的问题,而是我们民族自身如何对待自己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命运的问题[7]。”破坏了传统的整体性就等于破坏了传统的自主性,导致“精华”成为没有依托、没有主宰、没有活力的传统。多少年来,人们大多把传统看成一个阻碍科学技术发展的因素,把二者看成是对立关系,今天我们从创新文化的角度来看,二者可能是促进关系。我们认为,自主创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看待传统文化的历史性视域,这种视域的基础性高度就是原创性,是集自然的原创性、文化的原创性和实践的原创性于一体,并与长期以来以“现代性”视角对原创性的解构完全不同的一种对原创性的理解。只有通过这种视域的转换,才能促进和完成创新文化的转型,从而为自主创新创造一个根本不同的文化环境和氛围。我们预测,在经过创新文化的这种生成性文化转型之后,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将是一种被解放而不是被肢解的原创性,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成原理所昭示的人的原创性潜力将被充分释放出来,其具体道路就是通过文化之路体察自然之道,并将原创性精神运用于创造性的实践。当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按照库恩的说法,改变一个人的看法是很难的,而改变社会上的看法则需要一个教育过程,依靠的是后来者。因此,对于自主创新,我们不能够太急功近利,即便在 2020年按照若干指标来看我们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也不能就此罢手。我们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只是加强自主创新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其未来发展的意义更大。
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加强自主创新是保障国家利益的核心战略原则,而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加强自主创新则是促进全球利益共享的创新发展方式转变所依赖的核心战略原则。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自主创新”才将真正成为“引领未来”的起点,并通过创造性的贡献奠定未来中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基础性地位,赢得世人的尊重和尊敬。目前,当代中国科学家为中国经济地位提升和综合国力增强做出了重要贡献,且正以自己的全部身心开创中国科学事业的创新时代。但是正如董光璧教授所提醒人们的那样,“我们也应当对自己的科学现状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目前还少有开拓新领域和与国际同行并驾齐驱的研究工作。中国人口约占世界的四分之一,而我们对于世界的科学贡献却只是万分之几。因为按科学家们发表的国际论文计,我们的份额只有百分之几,而且其中被引用的又只是这百分之几的百分之几。一位外国科学评论家将中国没能在科学上取得应有的进展引为忽视基础研究的反面教员,而一位洋人在背后讥讽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为‘模仿科学家’。中国人的科学创造力所受到的束缚、挫折和摧残是严重的,像幼儿的四肢由于约束得太紧而成为侏儒那样,他们纤弱的心灵由于被奴役的偏见和习惯所束缚而不能自行扩张。妨害创造力发挥的精神因素可以列举很多,而在我们看来,对待科学的过分实用主义的态度可能是中国人潜在科学创造力的主要杀手[8]。”我们认为,在新型创新文化精神的促进作用下,上述格局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很多人曾经担心的那种阿 Q式的对传统的自我认同,而是基于人文精神价值相对于科学价值的先在性及其选择性发展模式和道路。我们观察到,当代社会是一个通过立法促进科学发展和限制科学发展现象并存的复杂社会,促进抑或限制,各有各的理由,但其选择性发展的现象说明,尚存在超越于科学之上的价值领域。在这种现象成为趋势之前,人们总是抱怨中国传统文化限制了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或者说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现在我们说,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基于自然整体规律的选择性发展,并由此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在自主创新条件下,这种特色性的发展对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具有启示性的意义,即不仅中国科技的未来发展需要人文精神的引领,而且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未来发展同样需要人文价值的支撑。因此,新型创新文化建设应当因应这种发展趋势,促进价值选择观念的确立。我们看到,回归传统价值也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而中国文化传统所确立的价值准则对自主创新的价值定位同样具有原创性意义。可以说,自主创新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创新,是中国传统价值创造性转化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从根本性质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非常丰富的原创性资源,而中国传统价值的核心来自于原创性。如何挖掘和使用这些资源,这是加强自主创新、开展新型创新文化建设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与以往那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做法不同,我们在挖掘之前需要对其获得充分性的理解,而其中的关键是如何让现代人的精神与传统相接,特别是对于具体的个人,他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应用不是取决于对传统的误读,而是取决于对传统的认同。但是,即便在古代,对传统的理解也有所谓“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的不同,就是说作为同一个对象的原创性,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来具有不同的性质,并由此决定了相应的态度和行动。今天我们要释放传统的原创潜力,应当效法的是“君子”的做法。古人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非常注重其内外一致性的标准,不是仅从表面上做文章。这一看法在本质上与科学研究的原创性是相通的。我们知道,科学研究的原创性在于捕捉“灵感”并表达出来,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对原创性的一种体系性的表达,是对“灵感”的主客一体化特征的文化性阐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以理性和内化的方式做到了对原创性的理解和实践性的应用,后者则是以崇拜的方式来建立自己与原创性的联系。也就是说,“君子传统”的可贵之处是保持了原创性的整体性质,并通过自己体现出来,显现出生成论文化的传统人文典范。从加强自主创新的战略需求来说,新型创新文化的观念、制度和氛围建设离不开对承载其文化精神的人的素质提高与精神成长。可以这样说,原创性资源常有,而能承载原创精神的人不常有,因此,以原创性为中心开展新型创新文化建设,其重中之重还是人才建设,无其人则无其事,有其人则自主创新的大业可兴。这样的人就是“科学君子”,而“君子”做科学,“科学”则成为“君子科学”。
四、中国文化的自主创新与创新文化建设
随着近现代科学技术的普及,不仅中国人的生活深受科技的影响,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深受其影响,表现在社会和文化的方方面面。从来源和性质来看,科学技术既是西方社会的原创性成果,也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从大的趋势来看,近现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表现为思维的同化过程,而这种过程主要是一种学习和模仿,对原始性创新的要求在总体上不是太强烈。就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并基本上被作为“保守”和“落后”的象征。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则出现了一种新的格局,其基本特征就是在西学的输入和消化吸收过程中,面对西学的批判和质疑,各种中国固有学术仍获得了一定的创新发展。及至今日,我们很难说西学不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各种融合性创新无处不在,甚至源自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很多中国人的选择,但是我们又很难说西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不同于传统文化的异质文化。事实上,这种文化概念上的不清晰反映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社会中的存在。无论是以往还是现在,文化学者在坚持文化本位和吸收外来文化之间进行了多种可能性的探索,但是“中国化的西学”仍然没有人能够讲得清楚,达成共识。如今,加强和促进自主创新的现实需求使我们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在原创性的层面上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我们认为,这种发现与以往不同,即这是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推动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国家发展和创新意志的具体体现,不仅标志着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标志着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即将从学者个性化的探索进入一个组织化的应用阶段。如果说社会需求比个人才能更能够推动创新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自主创新将推动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创新,在此基础上才能加快新型创新文化建设,并反过来引领和促进自主创新。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注重创新文化与自主创新的关系,并没有深入思考中国文化也与自主创新具有内在性的关联。在前文中我们曾经谈到,“自主创新”不是简单的“创新”,仅从一般的创新意义上去做无法深入推进自主创新。事实上,如果从原始性创新的视野考察自主创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我们认为,我国当前开展的自主创新需要中国文化整体性创新的支撑,否则的话,新型创新文化建设也将陷入无源之水的困境。在这里我们不再做过多的理论性论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相接已有多年,除了那些过分极端的观点和做法,总体上来说,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融是人类文明史上大事,一定能够取得会通性的创造性成果,反过来促进和引领人类文明的发展。在这种理论性的论证和期待过程中,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学说,上述所谓对创造性成果的期待一方面是以传统文化的存在并发挥作用为基础的,另一方面则是以对西方文化的充分学习和吸收借鉴为条件。可以说,这是一个“知己知彼”的过程。但是,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我们还能够称得上“知己”吗?从一般的公共舆论来分析这个问题,可以说传统的缺失已是无可争议的社会事实,目前中国文化的主流不是传统,而是各种现代文化。因此,很多人认为传统的缺失是现代化带来的,但是,我们看到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发达国家仍然保持着比较完整的传统,说明现代化与传统之间的冲突可以有很好的解决之道。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能够成功解决这种冲突?而未来的解决之道又是什么?当然,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如果说我们对国外成功的经验没有透彻理解并创造性应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对本民族的成功经验也学习和继承得不够,或者也可以说中国社会尚未进入又一个创造力迸发的发展阶段,使得以往的经验或者教训都成为未来创新的温床。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如今提出自主创新的国家战略,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重新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其中的一个基础课题就是温故而知新,即应当在整个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深刻了解“自主”的历史、现状及其可能的未来,做好“知己”的工夫。假如没有这个工夫,“知彼”的过程就会成为自我同化而主体价值丧失的过程,难免“往而不返”,也就失去了“知彼”的初衷。对比一下,现在有人说实际上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传统,而很少有人说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懂得西方传统。我们说,即便目前是这样,未来则未必是,因为早有睿智之士对可学与不可学之处做过明辨,只是因为时代不同,这种真知灼见没有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已。如今则不同,在自主创新条件下,这种真知灼见不仅具有得到充分普及的可能性,而且能够给人们带来如下启示:即不同并不意味着冲突,所谓的“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理念,本质上更是一种实践方法,而如何实践则取决于人们的理解。因此,我们分析以往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根源皆在于不理解,而在理解之后,宰制在我,能动利用,随机运化,生生不息,其实这就是自主创新应当达到的境界。话虽如此,但也应看到,目前自主创新的基础确实很薄弱,所以要“加强”。
创新难,自主更难。如果能够做到自主,那么创新则能够生成,水到渠成。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设条件,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是缺少自主的原则,而是缺乏自主的心态。例如,为了加强自主创新,创新文化建设的核心精神就是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可是,如果说连我们自己本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都不能宽容的话,那么上述精神从何谈起?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的丰富而独特的原始性创新资源又何去何从?弗里曼·戴森指出,向各种可能性充分开放,打开“全方位的无限”是创新文化最宝贵的精神,基于这种精神,宽容“传统”和“失败”都是“开放性”的表现。面对全球危机和挑战,我们需要宽容,使可供利用的原创性资源越多越好。只有“各美其美”,才能“美美与共”。因此,新型创新文化建设的首要条件是回到传统,学习传统,体认传统,释放传统的原创潜力。从创新的应变方式来看,传统是以不变应万变型的创新,而所以如此,是因为万变不离其“宗”,不离其“主”,有其“主”才能打开“全方位的无限”,创造“各种可能性”。但是传统的上述原创性意蕴,很少讲,也很难讲。去年我们在研究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课题的时候曾经提出过就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补课”的问题,现在看来,新型创新文化建设仍然需要“补课”。如果说在以前的创新文化建设中由于导向不同而导致“缺课”的话,那么为了推进自主创新,“补课”工程应当纳入国家战略,进入每个人的精神世界。我们观察到,现在无论是民间社会还是党校培训,传统文化都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在经过多年来的现代知识强化学习之后,人们发现单纯的知识教育对解决精神世界的作用效果有限,因此迫切需要能够促进“自主”的文化教育。这种民间自发的“补课”趋势符合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社会意识支持,不过,在我国的科学技术领域尚未出现这样的趋势。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传统文化促进我国原始性创新的分析报告,这既说明了我国尚没有系统推进这项工作,也说明中国文化的创新进程尚没有与科学技术的前沿进展形成有效互动。在本章的开篇中我们就谈到,自主创新战略是我国科学技术界提出的,或者说表现为科学技术界的战略研究成果,而推动工作也主要由其承担。但是,我们观察到,“补课”工程需要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中国文化界的介入。近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我国学术界出现了追忆和缅怀20世纪学术大师的热潮,人们总结那些大师的成功经验,认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传统的作用,尽管有些大师是以反传统的风格和姿态出现,但是他们的学术成就仍然离不开深厚的传统基础。他们所烂熟应用的传统文化是传统社会带给他们的,但是我国现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对传统已经疏远太久,以至于我们仍然需要对传统的再启蒙。我们认为,这种现象不是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基于未来发展的战略需求对传统智慧的再发现,特别是对传统中蕴藏的原创性智慧的发现。因此,“补课”工程不是倒退,而是加强自主创新的内在要求,是对自主创新将要生成的新文化和新科学的启蒙,是促进未来全民族自觉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工程。
在这里,我们要再一次强调科技与人文的不可分离及其相互影响。在西方国家,科技与人文之间存在着非常微妙的关系,应当说其间的冲突已经得到深入认识,其解决之道具有西方的特征,即在整体上又重新走上了通过人文精神规范和重塑科技价值的道路。对我国来说,由于科学技术不是本土文化和社会的内生变量,所以存在一个科学技术“中国化”的过程,至今为止,这个过程非常曲折,而从整体上来看,可以通过科技与人文的关系来审视和把握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我们认为,在经过多年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之后,自主创新不仅有利于破除“科技至上”的观念,而且有利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的独特价值,创造新的文化,使中国文化的创新在服务和支撑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进入新的境界。事实上,如何保持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一直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基本主题。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费孝通先生通过“补课”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重大命题,目前这个具有总结性和启示性的判断已经成为共识。任何创新都源自继承与学习,中国文化创新则必然源自对自身传统的全面继承,所以需要补课。佛教中国化成功,是因为当时自身文化较强,可以吸取别人营养而为我所用。西学中国化不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异质性太强,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抛弃了传统,吸收别人营养的主体都缺位了。因此,“文化自觉”就是“主体自觉”,找回“自主”的感觉。为了推进“文化自觉”的进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我国学者已经将人文精神的缺失作为亟待解决重大问题提了出来,并希望能够在大学教育中恰当安排相关课程,而其教育指向就是“自主性”。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是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9]。”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自己的特色,并且与“自主性”紧密相关:“我们强调中国的变革有着自身的‘独特的道路’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基本认识:第一,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又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 30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大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那种简单照搬现成模式的方式不仅在历史中曾经导致灾难,而且也会在现实中将中国的变革引向歧途;第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10]。”我们认为,自主创新既是中国各种问题的集合点,同时也是化解发展问题的制高点,因为只有“自主”的“创新”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是中国文化的“自觉”传统给出的启示和答案。
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践方面,中国文化创新的任务尚未完成,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就是长期以来对“自主”的悬置,人们难以对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问题讲出系统而且实用的理论和方法。我们认为,在“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原则之后,新型创新文化建设为中国文化的创新不仅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而且提供了创新的动力。在经过长年累月的中西文化比较之后,人们总是在说西方文化的发展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但是这样的机遇和创新并不一定由中国抓住,相反的是,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推进自主创新,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可能成为其他文化创新发展的资源。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深刻体会到其实机遇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自主”创造的,因此我们说,自主创新在本质上不仅是一个文化命题,而且其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和方法,是以原创性为根基带动集成创新和引进吸收再创新的自由、自觉和自主的创新,是中国文化创新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可以说,没有中国文化的时代创新,自主创新的核心原则意义不明,而没有自主创新,中国文化的创新道路仍然需要摸索,可见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其创造性的结合是新型创新文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今年 6月举办的首届北京大学博雅论坛以“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的取向”为论题,一直提倡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林毓生教授在论坛上发表了“在中西对话的脉络中如何推动中国人文研究”的主旨演讲,他从人文的定义、推进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推动人文研究的内在条件三方面对中国人文研究发展问题进行探讨,其看法对创新文化建设很有借鉴意义。在他看来,人文学科是追寻人生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肯定人的价值,客体与主体创造性的整合,是人文研究的最大特征。他援引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和庞加莱的学术发现四阶段理论,论证推进学术研究的外在条件是在制度上和文化氛围中提供给研究者不受外界打扰的时间和空间。而在内在条件方面,强调树立问题意识,避免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如果犯了“错置具体感的谬误”,事物本身的特殊性就会被误解,或者它本身没有这个特性,但它被放错了地方,我们却觉得它有这个特性[11]。我们认为,在众多人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文化被放错了地方,而自主创新能够纠正那些“错置具体感的谬误”,并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价值和意义。
在历史上,改造传统与被传统改造一直并存,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现代科学尚不能完全包容传统,但我们并不为传统担心,因为这是新型创新文化建设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为了促进新型创新文化建设,我们认为如下原则将有利于化解已经出现或可能遇到的矛盾:如果科学不能包容,就让文化包容;如果文化不能包容,就让社会包容;如果社会不能包容,就让历史包容,而自主创新将创造新的历史。
[1]叶育登,方立明,奚从清.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9(3):87-93.
[2]费孝通.费孝通文集 (第五卷)[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334.
[3]翟学伟.再论“差序格局”的贡献、局限与理论遗产[J].中国社会科学,2009,(3):152-158.
[4]杨慧林.关于“韬光”的误读及其可能的译解[J].读书,2010,(7):88-91.
[5]金吾伦.创新文化:意义与中国特色 [J].学术研究,2006,(6):10.
[6]楼宇烈.唤醒“自然合理”的中国文化主体意识[A].张超中主编.中医哲学的时代使命[C].北京:中国中医出版社,2009.
[7]李德顺.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再思考[J].新华文摘,2006,(21):113.
[8]董光璧.百年中国科技回眸 [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1,20(2):98.
[9]甘 阳,陈 来,苏 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导言[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甘 阳,陈 来,苏 力主编.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总序[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林毓生.在中西对话的脉络中推动中国人文研究[N].科学时报,2010-06-22(B4).
(本文责编:王延芳)
The Innovation Culture and the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ZHANG Chao-zhong,WU Yi-shan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Info rm ation of China,Beijing100038,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culture is lagobviously in China and cannotmeet the need forpromoting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 at present.The reason is that people have not gained an insight into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thought it yet as an economical category instead of a cultural category,and thusmisguidespeople cannot understand fully the tension buried inside the differential mode of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cannot change the scarce condition of originative.So the previous pattern of innovation culture must be replaced by a new one that holds the originative as a core during the constructingwork,and the transfor mation of innovation culture pattern needs the support from a 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It is expected that both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nnovation culture will develop to a new stag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merging of the differentialmode of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digenous innovation;innovation culture;differential mode of the indigenous innovation;originative;transfor mation;new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G02
A
1002-9753(2010)10-0063-14
2010-08-11
2010-09-17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2009DP01-2)
张超中 (1965-),男,河南柘城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博士后。
——开阔的价值理论与经济实践的视野
——行走在历史和思想的深处——《王阳明统说》管窥
——《专注性与剧场性:狄德罗时代的绘画与观众》评介
- 中国软科学的其它文章
- 我国碳税设计中的政策目标协调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