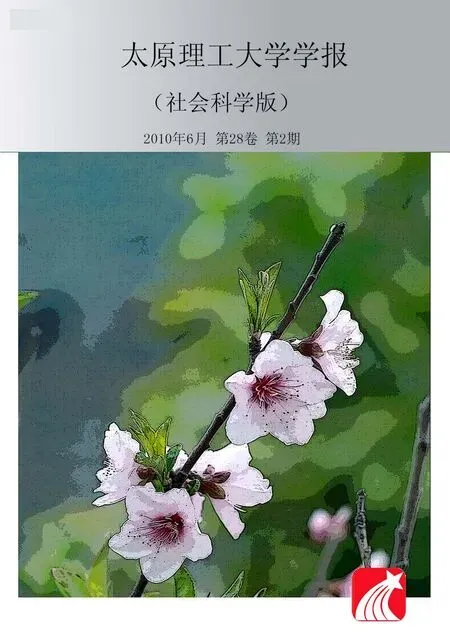译者的选择
——从解构主义视角看翻译
乔书静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一、解构主义的基本概念
解构(deconstruction)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代表一种方法(不仅仅用于哲学,也可以用于文学研究,甚至其他领域),旨在挖掘某一文本的深层意义。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否定了表面上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认为意义的根基其实是非常复杂且不稳定的,有的时候很难为大众所认可。德里达是解构主义的代表,他提出“解构”这一术语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的不满,他直接否定了意义的确定性,否认了结构的存在。
解构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智能或政治策略,对于我们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讲,它显然是一种阅读与思考的模式,因为我们最为感兴趣的是它的概念,将它看作我们理解意义的方法。如果我们想用这种方法去描述,并且将它运用于我们的文学学习中,解构——这一哲学策略将是个非常好的理由来开始我们的阅读之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说,作为一种策略,解构主义主要是用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因为它的实际目的是哲学内部严格的探索,并且能够代替一些神秘的哲学策略以及实践。[1]德里达本人是这样形容它的:在一个传统哲学的另一面,没有任何和谐的共存体,而是一片无条理的混乱。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既定的术语可以作为纲领,不仅是在价值观上,而且也在逻辑上。这一术语,总是可以用一种合适的方式去颠覆所有本系统内的混乱。
总体来说,解构主义的功能之一是生成篇章阅读,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很多不相容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意义。从表面上看,这个过程说明任何语篇都有至少一种阐释,语篇本身就会不可避免的将它的各种意义联系起来。在这些不同的阐释中,任何不相容的部分都会长久共存,所以,我们对这些意义的理解不可能超越某个确定的范围,德里达将这一点视为整个阅读的难点。希利斯·米勒对解构主义有如下描述:解构并不是某个文本结构的分解,而是一种展示,对它自身已经分解的展示,它表面上坚固的基础其实根本就是虚无缥缈的。
二、解构主义视角中的译者的“别无选择”
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他将原文(original text)看作源文(source text),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不可捉摸的,即使是“原文”,也只是对一种意象的阐释,因此“原文”同样属于“译文”的范畴,与我们所理解的“译文”是平等互补的,这一理论将翻译提升到与创作平等的位置。译者的地位也就随着原作者地位的提升而提升,与原作者一样,译者也是原本意义的阐释者,以主体地位参与到文本的重构中。[2]
解构主义认为,译者是创造的主体,翻译是创造的第二语言。译者不仅给予原文一个崭新的形象,使之能与另一世界的读者进行又一轮的交流,而且在另一种文化里延续了原作的价值。解构主义的意义“不在场”并不等同于“意义的否定性或意义的任意性”(no or anything)。文本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这并不代表译者有了随心所欲、随意阐释的权利。解构主义认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时时刻刻都要面临选择,这种选择被称为“Hobson’s choice”(无论哪种选择都不能令人百分之百满意)。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要么要求译者尽量忠实于作者,采取与作者所使用的语言相似或者相近的表达方式,来转述原文的内容;要么则要求译者尽量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3]译者作为“选择” 的主体,在“不可决定”中做出选择,需要发挥其创造性。[4]作为主体,最根本的能力是实践力和创造力,简言之,就是人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创造性体现在没有前在“模式”(formula or pre-specific program)可参考,要超越某一特定语境的“规范与规则”(norm and rule)才能创造出这种“选择”,却又不能完全超越或脱离这种“规范与语境”。因此,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几乎无选择余地的“选择”中显得尤为重要,译者所做的选择也更有创造性。
例如W.C.Williams的The Red Wheelbarrow一诗的译文。
原文: The Red Wheelbarrow
so much depends
upon
a red wheel
barrow
glazed with rain
water
beside the white
chickens
袁可嘉译: 那么多东西
依仗
一辆红色
手推车
雨水涂得它
晶亮
旁边是一群
白鸡
胡开宝译:那么多东西
依仗
一辆红色独轮
车
上面晶亮着雨
水
旁边有数只白
鸡
原文的移行现象非常突兀,也正是这种突兀,给了读者无限遐想的机会。我们对照两种译文后可以发现,袁可嘉的译文与原诗神貌非常相近,基本保留了原文的形态与韵律,唯独两处例外。一处是原文中wheelbarrow(在原文中是一个词)突然移行,将wheel与barrow分隔在两行,而译文保持了意向的连贯性,依旧将“手推车”译在一行;另一处是rainwater(在原文中也是一个词)用同样的手法突然移行,将rain与water分隔成两行,而译文也同样将“雨水”译在一行。之所以这么做,大概是考虑到汉语的表达习惯。
而胡开宝的译文处理大概是出于如下考虑。wheelbarrow和rainwater的突然分行是本诗的亮点所在,传神的表现了诗人的独特风格和个人意识;Wheelbarrow与rainwater分别被分割,效果是将意象分隔开来。Williams本人是意象派诗歌的代表人物,而意象派诗歌的落笔所在都是实物,本诗中总共有三个:车、水、鸡,将它们各自单独列成一行,更加突兀的跃入读者眼帘,加强了意象派的效果。
解构主义不仅揭示了翻译的创造性,也并未否认译者的主体性,但它却难以“规律性”。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尖锐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理论的魅力所在。面临一系列互相竞争的利益关系,译者不可能将所有因素都照顾到,这也是解构主义意义的“不在场”在翻译中得以体现的一个重要论据。
三、翻译:译者与作者的一场对话
一直以来,人们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下,把语言看做是反映客观世界、表达不同的人们的不同思想的工具,这就使得作者得到了塑造人们观念的绝对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一直致力于挖掘作者的原意,可以说,谁越多地发掘出原意,谁就越成功。所以,一部作品的原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就有了最为权威的解释权。只要某些读者误读了作者的原意,或者说,与原作者持不同的意见;只要作者予以否认,广大读者甚至评论家都将失去一切解释权。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规则,即作者的作品都是独白,而读者、译者以及评论家都是被动接受者。由于我们对语言的持续关注,我们发现语言的确定性与透明性是如此的不可获得,并且很多时候作者写出来的东西也未必就是他想要表达的东西。[5]正因为此,国际上很多评论家认为,追求作者原意这一行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他们开始关注作品本身,并把作品看作一个独立体,试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文本的结构、层次和语言的多义性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翻译研究来说极有意义。我们都知道,任何一种形式的文学活动都不能缺少三方面的要素:作者、文本,以及读者。可以说,没有读者的欣赏与参与,作品便不可能实现它的价值,所以,读者在文学活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读者的作用其实本不该如此过分强调,因为这样的话就无形中让读者拥有了文本意义的决定权,而文本意义是绝对不应该因人而异的。由此,文本的意义就从作者的独白变成了读者的独白,这种观点会直接导致翻译的胡译和乱译。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作品原本的意义?可以这样认为:读者通过文本的中介与作者形成对话,意义便由此产生。作者完成了作品的创作,然后便不在场了,留下千万读者去解读。这种解读,是读者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与原作者的对话中来,这个时候读者已经完全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作品意义的直接构建者。[1]
而翻译活动也绝对不是独白,而是一场对话。译者所面对的不是无感情无生命的文字符号,而是原作者内心的呼唤与呐喊、作者的立场与情感,无论作者在场与否,在对待文本内容这一层面上,译者与作者是一致的,他们的彼此呼应也就组成了一场生动的交流对话。无论两方的意见是否可以统一,或者双方的感情可否交融,作品里的意义总是在他们之间的对话中不断被磋商、被深化、被阐释。
以莎剧《哈姆雷特》中最著名的一句独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a question”为例,有各种译文,而每种译文都是不同的译者在与原作者的对话中生成的新阐释。
朱生豪译: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卞之琳译: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
黄北杰译:应活吗?应死吗?——问题还是:……
梁实秋译: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一个问题。
诚然,这四种译文都是四位大师对原文本进行阐释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却迥异,梁实秋先生认为to be or not to be是指哈姆雷特怀疑死后是否仍有精神或灵魂的存在及思考,而其余的三种均认为生命是一种当下的考虑;另外,that is a question的问题是指to be or not to be还是指下文的内容,黄北杰先生又与其余三位的看法不一;再者,“生存还是毁灭”与“应活吗?应死吗?”显然表达的语感是不同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意义阐释时的难以定论,因为真正的文学文本,特别是文学性很强的文本,从来都不会存在规范的解释,每种翻译都是一种译者与原作者的对话。
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对话的持续深入,文本的各种潜在意义才能够从作者的语言背后一一浮现出来,使得作品包含的种种可能的意义得到全方位的展示,这种全方位的展示往往是原作者本身也难以预料的。所以,不同的译者在翻译同一部作品时会创造出大相径庭的译文,正因为此,作品的意义与审美价值才能在不同的时代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中持续延伸和扩展。
四、结语
解构主义以一种多元化的视角展开对翻译的深层次研究,这种翻译研究范式打破了以科学主义精神为指导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研究的论断,打开了与翻译息息相关的一切可能的领域。这无疑扩大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步。但是更深层的问题是它体现了哲学的一个新的转向,即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带来了一种新的认知范式。
参考文献:
[1] Edwin,Gentzler.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 Baker,Mona.In Other Words:A Coursebook on Translation[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 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2.
[4] Wolfram Wilss.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Problems and Method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5]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