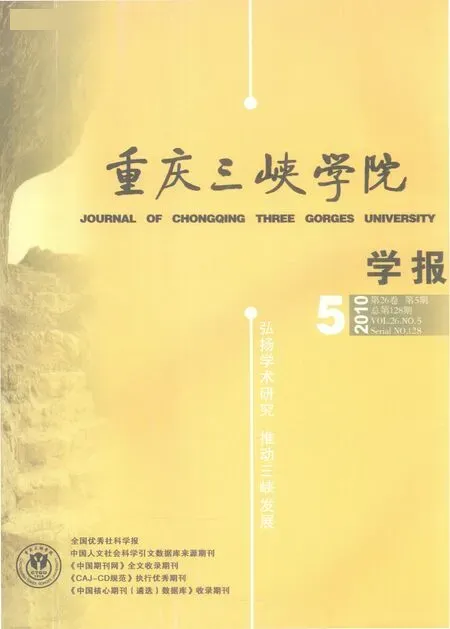族群历史溯源研究的语言学模型
曹 凯 张永斌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族群历史溯源研究的语言学模型
曹 凯 张永斌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081)
历史语言学在发展进程中建立起两种解释语言历史演变的模型——裂变模型和聚变模型。这两种模型同时也包含着语言学家对族群历史溯源研究的深刻思考。语言裂变从本质上来说是由族群裂变引发的,语言聚变则是长期而又复杂的族群经济文化互动造成的。
族群历史起源;裂变模型;聚变模型;族群史观
族群史研究不仅是民族学、历史学关注的课题,语言学界同样关注。历史语言学家常常会根据语言历时研究的结论讨论族群史问题,特别是族群历史起源问题。历史语言学家目前对东亚和东南亚各个族群的历史起源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他们迫切希望了解该区域内跨族群的语言文化特征相似性的导因:共同发源于某一个更古老的族群所致抑或是区域内密切的文化接触所致。
历史语言学在语言历时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阐释语言历时演变的两种模型:裂变模型和聚变模型。①这两种模型的先后建立不仅反映出历史语言学家对族群历史起源的深刻思考,同时也呈现出历史语言学族群史观的一次嬗变。本文将结合语言学研究,对族群史观的嬗变进行详细阐述,让其他学科的学者了解语言学家对族群史研究的探索。
一、裂变模型与族群分化
(一)裂变模型与进化论
基于欧洲明确的族群迁徙史,中世纪的学者就提出欧洲的某些语言发源于同一种“原始母语”的分化。随着欧洲人对印度、伊朗的古典文献的认识加深,他们更加坚信上述的同源分化论:从欧洲到印度的大多数语言都发源于所谓的“原始印欧语”。[1]1863年,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出版了《达尔文理论和语言学》一书,提出:“语言有机体”像生物物种一样生长、死亡,甚至演化成新的形式;一种原始母语会逐渐衍生出若干种子语;语言学家可以借鉴生物分类法对语言进行分类,将语言的发生学关系家族谱系化。他本人还在该书中绘制出印欧语系的家族谱系图。[2]这就是所谓的谱系树理论。这一理论关注语言在时间序列上的有序分化:一种原始母语经过长时间的分化,可以衍生出若干种存在着亲属关系的语言;这些语言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即语言特征的相似度)进行分类;分类层级一般包括语系、语族、语支、语言、方言等。我们现在也将谱系树理论称之为语言历时演变的“裂变模型”。
随着印欧语系假说的论证成功,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致力于探索操原始印欧语的人群的发源地。他们根据构拟出来的原始印欧语的词汇,考察词汇背后的社会、经济、生态情况,推测原始印欧语的故乡。荷兰历史学家李伯庚(Peter Rietbergen)指出,操原始印欧语的人群共同体可能是公元前7 000年至公元前5 000年之间居住在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和里海之间的一些游牧部落。[3]欧洲现代民族格局和语言格局的形成就是由这一古老族群迁徙和分化导致的。这些游牧部落从干旱的亚欧大陆中部不断向外迁徙,分化出欧洲大陆上不同族群,语言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发生裂变。
我们无法否认裂变模式与当时欧洲大陆狂飙突进的进化论有关,特别是民族学内部的古典进化论。当时的语言学家倾向于相信,人类进化的过程伴随着族群和语言的不断裂化:同一个语系或语族的多个族群起源于某一个古老的人群共同体。这一人群共同体具有客观上相同的体质特征和文化特征,当然最重要的是共享同一种语言,即所谓的原始母语。这个原本统一的人群共同体因为迁徙而散布到不同区域。因为时空差异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在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共享特征会逐渐产生变异,变异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展出新的语言和地域文化,有时候甚至连族群认同也会发生突变。
共同起源与连续裂变是当时历史语言学族群史观的核心内容。
(二)中国语言学家对裂变模型的实践
裂变模型在印欧语研究中取得成功,接着被移植到其他地区语言的历时研究中。东亚和东南亚语言的历时研究始于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和学者。进入20世纪,中国学者掌握了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方法之后也参与到探索中。学者们发现东亚、东南亚的不少语言具有一些跨语言的共同特征,逐步形成了“汉藏语系”的假设。1937年,中国语言学家李方桂在美国发表《中国的语言和方言》一文,明确提出汉藏语系语言的系属分类:汉藏语系应该包括汉语族、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4]这一谱系分类法大大促进了中国境内语言的研究。
洪洞大槐树、南雄珠玑巷、狄青征南等跟人口迁徙相关的传说在中国民间从来就很有市场。这构成学术界倚重迁徙分化说来解释现代汉语方言格局的社会氛围。不少语言学家相信两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两宋靖康之乱引发的移民潮促成了现代汉语方言的格局。人口迁徙的史料与口头传说、地方志、谱牒资料、古今政区建制都是学者用心钩稽的材料。分布在今四川、贵州、云南、重庆等省市的西南官话,语言学家认为它的形成跟元明清三代的移民有着密切关系。南宋至清代的三次朝代更替时期,今四川、重庆、贵州一带的战争都异常激烈。以南宋末年四川的反元战争为例,这次战争持续数十年,战况极其惨烈,据说“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5]战后,新的王朝都会鼓励周边省区的人民迁徙到西南一带,比如说“湖广填四川”。据刘晓南考证,宋代文人雅士提出的“蜀闽同风”可能反映当时蜀闽两地语言文化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但是,到了明清以后,外地移民大量增加。同时,以成都为中心,西南一带的方言日益接近北方官话,明清的文人雅士再也没有“蜀闽同风”的断语。[6]可见,移民对西南官话的形成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在讨论中国南方民族语言的发生学关系时,研究者同样会借助族群迁徙来辅证自己的学说。吴安其先生认为,操原始汉藏语的古老族群在黄河中游地区向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发展。往下游发展的族群形成汉族的主体,逐渐发展出原始汉语。在上游和中游的族群不断南迁,跟早期汉文献中的氐羌有密切关系。他们经横断山脉向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迁徙,衍生出不同族群,逐渐发展出藏缅语族的多种语言。[7]另外,学术界一般认为侗台语族的多种语言来源于长江中下游百越族群,也有人从百越上推到更早的东夷。[8]苗瑶语族的语言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武陵蛮”、“五溪蛮”,当然也有人把他们上推到更早中的三苗。[9]
不少中国学者相信操原始汉藏语的古老族群属于蒙古人种,语言比较统一,在某个遥远的时代分布在黄河流域。大规模的族群迁徙将他们的文化带到东亚大陆的广大地区。时空差异导致这一古老的人群共同体不断发生分化,衍生出不同族群,他们的语言也不断裂化。这种族群史观能够将早期汉语文献跟国内族群分布格局很好地联系起来,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二、裂变模型的瓶颈
裂变模型关注族群和语言的历史起源问题,对族群和语言发展从历时角度进行解释。在东亚和东南亚,遵循谱系树理论的经典操作模式的指导,语言学家将这一地区的众多语言分成六个语言集团:汉语族、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南亚语系、南岛语系。这个分类在学界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异议。语言学家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上述语言集团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就可以对东亚和东南亚族群之间的历史来源和历史关系给出进一步合理的解释。
围绕着上述语言集团之间的关系,语言学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基本上形成了两派意见。国内学者大体维持李方桂先生1937年提出的分类法,汉语族、藏缅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组成汉藏语系。邢公畹、郑张尚芳、潘悟云等学者甚至认为应该将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合并起来,组成一个超大语系。不同的声音主要来自国外。1970年代,美国学者白保罗(Paul Benedict)提出,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跟汉语没有发生学关系,只有接触关系;汉藏语系只包括藏缅语族和汉语,侗台语族跟南岛语系存在着发生学关系。他的观点很快在国际学术界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在国内也得到倪大白、陈保亚等人的响应。这两派争论的焦点就是某些共享的词汇是同源性的还是接触性的。[10]这一地区的语言历史关系探索于是成为国际语言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如果我们在族群史研究的视野下审视上述语言系属分类的论争,它其实也是关于侗台语族、苗瑶语族先民历史来源的学术观点分歧。这两个语族的先民到底跟南岛语系先民同属于一个早期人类共同体?还是跟汉语族、藏缅语族的先民同属于另一个人类共同体?抑或有其他可能性?
不过,论争带来了的巨大收获,最重要的是学界对裂变模型的反思。语言学界对裂变模型其实一直存在异议,只是一直比较微弱。施莱赫尔的学生施密特(J.Schmidt)提出“语言的波浪式扩散”对裂变模型进行补充。这让学者们首次发现语言裂变并不能完全解释跨语言的特征相似性。[11]方言地理学兴起之后,对语言有序裂变的质疑声逐渐增大,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语言裂变模型过分强调语言的有序分化,对语言的波浪式扩散和语言接触促发语言演变的潜在能量认识不足。
我们知道,通过对文化进化论的反思,播化学派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民族学内部兴起,其实跟语言学这一时期发展有异曲同声之妙。[12]随着语言学家对世界各地语言的认识加深,他们逐步认识到语言接触导致的语言特征变异很有可能会干扰人们对发生学的讨论。在巴尔干半岛、美洲印第安地区,语言学家发现双语或多语现象特别常见,语言接触异常复杂。人们通过对谱系树理论的反思明确了裂变模型的适用性。朱晓农总结出裂变模型适用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子语言的截然分化;另一个是分化以后互不影响,如果有影响,也看得出是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带来的一批文化词。[13]在族群接触和语言接触异常复杂的地区,裂变模型适用的两个前提很难保证。因此,传统的历史语言学研究方法似乎不适用于这些地区的语言研究。
三、语言聚变与族群接触
(一)语言接触与语言聚变模型
20世纪初,播化学派在民族学内部兴起,注重观察和研究人类文化的地理传播。语言学内部同时也在酝酿一次类似的革新。随着语言学家对语言接触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别是特鲁别茨科依(Troubetskoy)“语言联盟”说的兴起,一种新的语言历时演变模型逐渐建立起来。语言学家发现,在一些特定区域(如印第安地区、巴尔干半岛),操不同语言的族群密切接触促发语言特征的趋同性发展,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共享部分词汇。随着族群交流的进一步加深,语言差异可能会进一步缩小,逐渐融合或者说是“涵蕴”,有一种极端情况就是“混合语”的出现。我们将这种模型称为“聚变模型”。到过中国贵州、云南、广西等省区进行田野调查的语言学家、民族学家都会强调一个相同的田野经验,某些地区的族群兼用多种语言的现象特别突出。语言兼用在不少地区正是混合语出现的前兆。语言兼用和混合语与其说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不如说是族群之间的地缘接触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造成的。
中国南方的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的历史来源一直存在争议。早期的学者认为客家民系是汉族的一个重要民系,他们因为躲避历代的战争从中原迁徙出来,逐渐分布到江西、广东、湖南、广西、四川、重庆等省区。因此,他们的语言自然而然也是从中原汉语中逐渐分化出来的。早期语言学家给出的证据就是客家人的读书音系统跟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汉语特别接近。[14]但是现在的学者并不这么看,邓晓华借助人类学的理论批判早期研究者的解释是一种陈旧的“单线演进说”:他们过分倚重北方汉族的南迁说对客家来源进行解释,认为客家民系语言文化的形成是从“祖语文化一条直线贯穿下来”。[15]他认为早期研究者对客家文化的形成与其他族群文化的互动缺乏认识。客家民系中不仅有中原南下的汉人血统,还有相当的苗瑶语族、侗台语族人群血统。另外,虽然客家方言的音韵系统属于宋代北方中原音韵系统,但是客家方言的词汇系统则是北方汉语和南方土著民族语言混合而成。在南下汉人语言跟南方土著接触交流过程中,他们的语言日益发生聚变,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开始接近,逐渐产生了“惺惺相惜”的认同感。语言的聚变模型同样是族群的聚变模型,只是族群的聚变更加复杂而已。
语言接触研究的兴起与民族学内部的播化学派形成一种跨学科的呼应。有趣地是,德奥播化学派的代表人物施密特神父(Wilhelm Schmidt)同时也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自己是南岛语系和南亚语系语言研究的重要开创者之一。两个学科的学者几乎同时开始研究文化因素的跨族群、跨地域传播。文化的传播不仅带来族群文化特征相似性,甚至可能促发族群认同的突变。这种新的语言历时演变模型大大拓展了语言史、族群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实践视野。
(二)中国学者对聚变模型的实践
从当代考古发现和早期汉语文献来看,中国境内自古就有不同族群的活动。秦汉以后,大批汉族移民因为各种原因从中原地区向周边迁徙,他们的语言也扩张开来,跟周边的族群发生了更加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种长期接触对于中国境内的语言产生的影响,前代学者并没有太多关注。在汉语方言研究中,前代学者特别强调汉语随着汉族移民的迁徙在南方扩张,逐渐与中原汉族的语言分化。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似乎代表了某些语言学家对汉人南下之前早期中国南方的基本认知。这样的观念容易导致一种误区,南下的汉族和汉语在南方的分化滋生没有任何“杂质”。因此,南方汉族民系与南方汉语方言纯净性的神话一度在国内特别兴盛。
最近三十年,语言学家对中国境内语言接触的复杂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一些方言学家大胆地提出东南汉语方言具有混合语的性质。邓晓华认为“南方汉语非‘汉’”,而是一个“多元结构体”,是不断南下的汉族移民在南方跟土著族群长期地域接触和文化互动促成的。[16]潘悟云提出,东南方言形成的主体是南方土著,“他们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学习汉语,形成一种带有本族母语特征的混合语,以后通过双语的中间阶段,逐渐放弃了自己的母语,这种混合语性质的汉语就是东南汉语方言。”[17]以后,随着中央政府“编户齐民”政策的推进,这些南方土著也逐渐凝固了对汉族和汉语的认同。这种假说在汉语方言学界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闽方言、粤方言、客家话的混合语性质揭示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
更有甚者,陈其光、李葆嘉等学者提出,汉语本身就是一种混合语。这种观点几乎是颠覆性的。如果原始汉语真是一种混合语的话,那么汉族先民的起源就是多源性的。陈其光先生提出,上古汉族是由周边“羌、夷、蛮等族群的一部分人在黄河中下游经过长期联合斗争融合而成的”,而所谓的原始汉语(即为“雅言”)则是由“羌、夷、蛮等语言的不同成分聚合而成”。[18]随着汉族的迁徙和繁衍,这一混合语不断扩散,不断融合新的语言,不断裂变出不同地域方言,逐渐形成现代汉语方言的格局。
关于苗瑶语族诸语言的形成,李炳泽通过对族群史的重新认识,以及对“同源词”和“异源词”的分析,提出新的解释。[19]他虽然没有给出“异源词”的定义,但是这一概念的提出跟他的族群史观存在联系。他认为,操不同语言的族群“从不同地方迁移到一起,然后相互裹挟着来到武陵山区,最后又分开,向东成为畲族,向南成为瑶族,向西成为苗族”。在这一进程中,这些不同的语言“相互接触导致语言共同成分增加”,“共同受到其它语言的影响又增加一些共同成分”,不过继续迁徙使一体化进程没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原始苗瑶语”,苗瑶语族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是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倒是“异源词”值得特别注意,因为它们“各自继承了古代还没有与其它语言互相交流和未受其它语言影响之前的固有成分,其次是在不同地区分别受到其他语言的不同影响”。
上述几种推断是否可靠见仁见智。不过,聚变模型的建立拓展了语言研究的视野。它注重从不同族群和不同语言的互动中审视特定族群的文化特征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一模型下,学者不再满足于用历史考证来辅证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建立全新的族群史观和语言史观,对跨族群的文化特征相似性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与解释。语言学家相信,在某些情况下,跨族群的文化“播化”不仅能促成族群文化特征的相似性,甚至可能促发族群认同的质变。
四、结 语
裂变模型关注裂变与进化,聚变模型关注聚变与播化。它们是针对族群和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的不同方向的探索,看似相互矛盾。不过,这两个模型的先后建立不仅揭示出历史语言学族群史和语言史观一次嬗变,还揭示出左右语言演变的两种力量。任何现实中的族群或言语社团既无法维持内部的绝对统一性,也无法排除外来影响的干扰,因此常常处在裂变和聚变两种力量的博弈中。在世界上的许多地区,聚变与裂变的力量是可以区分的。不过,东亚和东南亚的族群互动与语言接触呈现出不一般的复杂性,这一区域的语言发生学关系的探索成为当代历史语言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有待时日。中国语言学家对于东亚、东南亚的族群历史关系和语言历时变异的探索会一直持续下去。
注 释:
①朱晓农在《方法:语言学的灵魂》一书中介绍了澳大利亚语言学家鲍伯 迪克森(Bob Dixon)提出的一种全新的语言演变模型—“间或打断的稳态聚合模型(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model)”时,将它译为“裂变-聚变模型”(见第223页)。本文中两种模型的术语来源于朱晓农教授的论述。
[1]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44-64.
[2]王远新.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5-32.
[3]李伯庚.欧洲文化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96.
[4]孙宏开.汉藏语言系属分类之争及其源流[J].当代语言学,1999(2).
[5]葛剑雄.中国人口史·辽宋金元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548.
[6]刘晓南.闽蜀同风与方言[C].《语言学论丛》第38辑,2008.
[7]吴安其.历史语言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9-138.
[8]李锦芳.百越族称源流新探[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
[9]李葆嘉.论华夏汉语混成发生的考古文化与历史传说背景[J].东南文化,1996(2).
[10]覃晓航.侗台语族谱系分类史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1).
[11]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42.
[12]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7-8.
[13]朱晓农.方法:语言学的灵魂[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3.
[14]黄志繁.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2007(4).
[15]邓晓华.论客家话的来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
[16]邓晓华.古南方汉语的特征[J].古汉语研究,2002(3).
[17]潘悟云.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C]//语言接触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 .
[18]陈其光.汉语源流设想[J].民族语文,1996(5).
[19]李炳泽.苗语跟周围语言的借词研究[C]//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郑宗荣)
Abstract:Two models are built to explain the language evolution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fission model and fusion model. The models are also used by linguists to think deeply in the research of tracing ethnic groups’ origin. Essentially, language fission is caused by ethnic groups’ fission and language fusion by long-term and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historical linguistics; fission model; fusion model; tracing of ethnic groups’ origin
Linguistics Models on the Tracing of Ethnic Groups’ Origin
CAO Kai ZHANG Yong-bi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81, China )
H0-05
A
1009-8135(2010)05-0105-05
2010-05-02
曹 凯(1981-),男,湖南澧县人,中央民族大学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张永斌(1976-),男,仡佬族,贵州大方人,毕节学院讲师,中央民族大学2008级在读博士研究生。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09GHQN02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