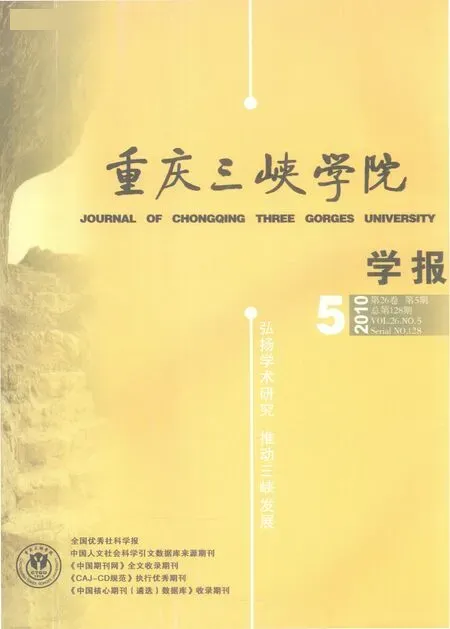《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文献价值寻绎
滕新才
(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重庆万州 404100)
《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文献价值寻绎
滕新才
(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重庆万州 404100)
《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是南宋夔州路安抚使徐宗武在抗元基地天赐城完工后撰写的碑文,如实记载了天赐城的创修经过和抵御蒙古入侵的作用,长期堙埋地下,清代方才出土,保留了宋蒙三峡战争的珍贵资料。
《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南宋;天赐城
公元13世纪,蒙古汗国在草原上崛起,横扫亚、欧两洲,成为南宋后期最主要的威慑力量。端平三年(1236)八月,蒙军大举入蜀,连拔54府州县,“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1]这是蒙古兵锋第一次深入三峡地区。嘉熙元年(1237)六月,蒙古大将梁秉钧由川西进攻“开、达、梁山、忠、万等州,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所征无敌,所向无前,如入无人之境”,[2]再次深入三峡腹心。两年后,蒙古都总帅汪世显统兵袭破开州,大败万州守军,占据长江上流优势,“鼓革舟而下,袭破之,追奔逐北,直抵夔、峡”[3](卷六《总帅汪义武王》)。很明显,蒙古迭年兴兵,偏师深入三峡地区,其战略意图是欲打通长江航线,“道施、黔,以透湖湘”[4](卷一百四十三《孟少保神道碑》),直取南宋江南半壁河山。这样,南宋在三峡一带的布防,就直接关系着大宋国运的安危,成为华夏江山永固、社稷长葆的玄机所在。
在四川战局“飘若风雨”、“亡形已具”的严峻形势下,淳祐二年(1242)六月,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兼夔州路转运使,赴四川主持防务。七月丙申(8月13日)余玠陛辞,宋理宗殷殷嘱咐他“当为西蜀经久之谋,勿为一时支吾之计”[5](卷三十三),寄予了莫大的希望。余玠采纳播州冉琎、冉璞兄弟俩的建议,在合州钓鱼山筑城,迁合州治于山上,屯田备战,且耕且守,全民皆兵;并推而广之,“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于是如臂使指,气势联络”[6](卷四百一十六《余 传》),建立起庞大的山城防御体系。
这个防御体系由20座城堡组成,三峡地区有万州天生城、梁山军赤牛城、夔州府白帝城和大宁监天赐城4处城防。所有城堡都建立在天然生成的悬崖峭壁之上,绝对高度不甚大,平均海拔只有500米左右,但山势险要,平地拔起,四周平岗错落,愈显其峥嵘嶙峋之伟岸;而山顶却纡缓宽平,逶迤连绵由百十亩至数十里不等,有田土可耕,有林木可用,有泉水可饮,足以容纳众多民户和驻军。且各城多背倚崇山峻岭,面临滔滔大江,水陆相连,握舟车之利,易守难攻,[7]兵民一体,耕战结合,从根本上扭转了四川被动挨打的局面。余玠之后,各地守将把他的战略构想付诸实践,并推而广之,建立了更多的抗元基地。大宁监天赐城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创筑的。
天赐城位于今重庆市巫山县龙溪镇天城村境内。这一带的行政区划在历史上屡有变动:秦汉置巫县,吴分设建平郡,治今巫山县;晋太康元年(280)分置泰昌县,治今巫山县大昌镇。北周时因避宇文泰之讳改名为大昌县,唐因之。宋开宝六年(973),因所辖宝源山盛产食盐,置大宁监,治今巫溪县,端拱元年(988)领大昌县,属夔州路。元至元二十年(1283)并入大宁州,明洪武四年(1371)复设大昌县,清康熙九年(1670)省入巫山县。要之,天赐城创筑时属大宁监,其遗址今地则属巫山县。
天赐城濒大宁河右岸,山势崎岖,四缘陡坡,高险可守;山顶却宽敞平坦,视野开阔,恰如上天所赐风水宝地,因名天赐山,城以山名。道光《夔州府志》载:“天赐山,在(巫山)县西北废大昌县东北四十里,有城连凤岭。”[8](卷六《山川志》)这里是川、渝、陕、鄂四省交界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号称“巴蜀咽喉,秦楚管辖”[8](卷三《疆域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远为全蜀咽喉,近为夔门锁钥”[9](卷三《疆域志》)。天赐城创筑的目的,就是为了抵抗蒙古军队由大巴山北麓向三峡腹心地带的进攻。
关于天赐城的创修者,很多资料记为宋将廉康,始作俑者乃《大清一统志》:“天赐城,在巫山县西北废大昌县西六十里,宋将廉康所筑,景定中守将徐宗武立石。”[10](卷三○三《夔州府》)因该书是曾经炙手可热的权臣和珅奉敕修撰、并以乾隆皇帝“钦定”的名义颁行的,所以影响很大。嘉庆《四川通志》原文抄录了这条资料,一字不替。道光《夔州府志》又依样画葫芦照引《四川通志》,光绪《大宁县志》更是奉《通志》和《府志》为圭臬,未加仔细甄别。
《大清一统志》并未交代所持何据,有妄言之嫌。作为全国地理总志,该书卷帙浩繁,内容庞杂,难免缺乏照应,留下顾此失彼的遗憾。由于《宋史》无廉康传,洋洋496卷中绝未提及廉康其名,使后人无从了解更多的信息。相反,现有文物、文献表明,天赐城的创筑者实在另有其人。
天赐城遗址东门松林中,赫然保存着一通摩崖石刻,碑额篆书《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9个大字,碑身高2米,宽1.23米,全文419字,字体较大,保存亦较完好,仅数字因风雨浸蚀而漫漶不清。道光《夔州府志》、光绪《大宁县志》均有著录,但文字互有出入,现据摩崖石刻校正,全文整理如下:
大宁虽支郡,实夔、峡后户,金、洋要冲。自迩年虏常突至,生聚日耗,为无城筑故也。壬戌仲秋,余来帅夔,奉总镇吕公命,俾就监择地,兴筑一城,为保聚计,即相视形势,去昔监四十里,得一山焉,名曰天赐,高险可守,具闻于朝,获命下可。乃计徒庸,虑材用,书 粮,卜吉起筑,调京湖戍夔总管白思恭部兵董役。知监事张宣乃宣使祥之子,挺有父风,晓畅军事,奉命惟谨,相与戮力,共济其事。自景定三年十一月上浣日兴工,抵明年四月朔告成,周围计九百六十余丈,粉雉矗空,楼橹连云,官有廨,粮有廪,兵有营,战守及备,靡不悉周。商贾往来,居民还定,耕屯日辟,跨两冬而虏不敢窥,此兴筑之效也。虽然,此城之筑,岂特为一郡计哉!藩篱谨固,可为金、房之障蔽;气脉联络,可为夔、峡之声援,殆天所以赐国家也,诚不偶得。继自今任郡守者,当思经始之难,而尽保守之力,一日必葺,克勤王事,体余创筑之本心也,其懋敬之!工费有籍,不书。
景定癸亥季冬吉日。右武大夫左屯卫大将军、知夔州主管夔路安抚司公事、节制本路屯戍军马、固始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徐□记。文林郎中差大宁监判赵孟柏篆额书丹。武功郎 门宣赞舍人、权发遣大宁监兼管劝农事、节制屯戍军马张□奉命立石。
由于年代久远,此碑长期堙埋地下,其重见天日纯系偶然。道光《夔州府志》透露说,“石刻久为土瘗,农夫掘土得之”,从而为后世提供了一篇非常珍贵的文献资料。关于它的作者,道光《夔州府志》作了一番简单的考证:“《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右武大夫左屯卫大将军、知夔州主管夔路安抚司公事、节制本路屯戍军马、固始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徐缺名记。……夔州峡口有铁柱,上刻‘守关大将军徐宗武’八字。以此观之,徐公乃徐宗武也。”[8](卷四《金石志》)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徐宗武于景定三年(1262)上任夔州知府,后兼管夔州路安抚司公事,对三峡军事防御体系多有建树:“铁锁关,即瞿唐关。旧志:铁锁关,在瞿唐峡口……景定五年,守将徐宗武于白帝城下岩穴设拦江锁七条,长二百七十七丈五尺,共五千一十股。又为铁柱二,各高六尺四寸,刻徐宗武字。后人因呼为铁锁关。”[8](卷十二《关梁志》)“铁锁,白帝城下崖穴中。宋景定五年,守将徐宗武置以拦江,计七条,二百七十七丈五尺。”“铁柱,瞿唐峡口石盘之上,竖铁柱二根,高六尺四寸。夏秋水没,冬春复见。上铸‘守关大将军徐宗武’等字。”[11](卷三十四《古迹志》)数百年后,该铁锁已荡然不存,但铁柱却完好无损,所铸“守关大将军徐宗武”等字仍历历可辨。在瞿塘峡北岸江壁上,还有一通徐宗武景定癸亥(1263)年末题撰的摩崖碑碣,右丞相贾似道书:“帅守淮右徐宗武,面奉开府两淮节度京湖制置大使、四川宣抚大使吕公文德指授,凿洞,打舡,铸铁柱,造铁缆,锁瞿唐关,永为万万年古迹。景定癸亥季冬吉日记石。当朝大丞相贾公似道。”[12]其时间与《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相当,是徐宗武同时苦心经营的两步战略,也是南宋三峡军事防御体系中遥相呼应的姊妹设施。该碑因夏季水急浪高无法靠近,冬季水枯悬高无法攀登,人迹罕至,至今保存完好,成为宋蒙战争史的重要物证。
《宋史》没有给徐宗武立传,从书中相关记载来看,他不仅加强了长江沿线的军事设施,还在夔州路辖区内到处实施余玠的山城防御战略:咸淳元年七月戊申(1265年8月24日),“夔路安抚徐宗武城开、达石城,乞推恩,从之”;咸淳三年二月丙子(1267年3月16日),枢密院奏报,“知夔州、夔路安抚徐宗武创立卧龙山堡囿”,宋度宗特“诏宗武带行遥郡团练使,以旌其劳”;咸淳五年五月壬申(1269年6月28日),京湖制置司禀告,“故夔路安抚徐宗武没于王事”,为他苦心经营的三峡抗蒙大业鞠躬尽瘁,请求优加赠恤,宋度宗诏令“官其一子承节郎”[6](卷四十六《度宗纪》)。道光《夔州府志·政绩志》为徐宗武留下一席之地,所披露的资料亦上述三条记载而已。
徐宗武于壬戌年(1262)仲秋任夔州知府。鉴于大宁是夔、峡二州上流门户,金州、洋州南下要道,近年来蒙古铁骑经常突如其来,生灵涂炭,缘于没有牢固的城池可供防守,故奉京湖制置使吕文德之命,下车伊始,就特别留意在大宁监范围内选择有利地势,兴筑城防,以为保境安民之计。功夫不负有心人,经多方考察,终于在距大宁监西40里的天赐山找到了理想的城址,奏告朝廷,获得许可后,又计算人工、考虑材用、上报粮草,并慎重其事地选择了黄道吉日,然后正式开工。所谓“上浣”,是指古代官吏的一种休沐制度:唐代规定官吏每十天休息洗沐一次,后人因将每月上、中、下旬分别称为上浣、中浣、下浣。景定三年十一月上旬,徐宗武调京湖制置司戍夔州路总管白思恭率所部兵丁正式开工,全面负责天赐城创筑工程。经过半年时间的艰苦努力,到第二年四月初一日(1263年5月9日)大功告成。
从碑文看来,天赐城当年颇具规模,周长3公里有余,女墙高耸,楼房连绵,官署、粮仓、兵营、民居,一切战守设施莫不应有尽有,基本上能抵挡蒙古军队绕道万州天生城、从大巴山北麓向三峡腹心地带的进攻。
大宁监知监张宣参与了创筑天赐城的全部工程,并且是其中的重要人物。然而其生平事迹后人知之甚少,光绪《大宁县志》仅有简略的“补遗”:“赵孟柏,景定三年任大宁监判,见《府志·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张宣,景定三年任大宁监兼管劝农事、节制屯戍军马,同上。”[13](卷六《秩官志》)《宋史》自然不会为这样的芝麻官立传,所提到的三位张宣,一是靖康中寿春军士,一是淳熙二年(1175)军帅,一是绍定四年(1231)御前中军统制,都不是这位大宁监“知监事”。其父张祥,徐宗武既称“宣使”,当是曾任四川宣抚使或宣谕使之职,但史无明载。《宋史》记张祥事迹数处:嘉熙四年四月壬寅(1240年5月11日),前潼川运判吴申与宋理宗讨论四川战事,说张祥有保全赵彦呐、杨恢两位制置使的军功,“敌人惮其果毅,宜见录用”[6](卷四十二《理宗纪》),后成为四川宣抚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孟珙部下得力大将,曾奉命屯戍涪州[6](卷四一二《孟珙传》)。假如张宣真是这位张祥之子,将门虎子,雏凤清声,那么徐宗武《记》中之“挺有父风,晓畅军事”也就所言不虚了。而且,根据余玠当初创立山城防御体系的战略意图,是必须将当地府州治所迁于山上,不妨还可以这样进一步推断:张宣在天赐城创筑完成后,曾长期率兵驻守,平时耕屯练兵,保境安民;一旦蒙古军队兵临城下,则全民皆兵,奋起抗战,保家卫国。
至于负责该碑书写镌刻的大宁监监判赵孟柏,也无从了解更多的信息。南宋末年,赵氏皇族以“孟”字排辈的人很多,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是其中翘楚之一。《宋史》一共著录了2 516位“孟”字辈,内有两位赵孟柏,均列《宗室世系表》,不知孰是大宁监判,抑或都与大宁无缘。按照宋朝建制,府州长官之外另设通判,共同处理府州政务,地位略低于长官,但拥有联署府州公事及监察官吏的实权,号称“监州”。《记》中赵孟柏的职衔是“文林郎中差大宁监判”,其来自朝中非常明显,属临时指派性质。虽然赵孟柏很可能是皇室子弟,但毕竟只是监判身份,比张宣品级略低,这就是《记》行文上对上司徐宗武不直呼其名,立碑者自己也回避名讳,而“篆额书丹”者却径署赵孟柏的原因所在。
天赐城创筑完成后,收到了很好的功效:商旅自由往来,市民安居乐业,开垦的耕田一年比一年多;截止徐宗武撰拟该《记》的景定癸亥(1263)年底,蒙古军队已有两年时间没有再兵临城下。而且天赐城的创筑,绝不仅仅是为大宁监一地着想,它既可作为金州、房州的屏障,又能成为夔、峡二州的有力声援,牢牢扼守着三峡腹心地带,遥相拱卫赵宋江南半壁河山,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难怪乎徐宗武感慨说:“殆天所以赐国家也,诚不偶得!”
宋蒙之间的战争,至忽必烈时代发生了性质的转变,特别是以1271年元朝的建立为标志,演变为封建政权改朝换代的战争。1267年冬,蒙古开辟襄樊战场,揭开了向南宋发起战略进攻的序幕。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取临安,南宋朝廷事实上已经灭亡。而四川重庆、合州、泸州、万州、夔州等沿江诸城,在王命“不达于四川”的情况下,仍坚守据点,奋起抵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元朝负责经略三峡地区战事的大将是阆州夔东路安抚使军民大元帅、骠骑卫上将军兼宣抚使杨文安,接连攻克梁山、万州、施州、咸淳、绍庆等地。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命荆湖都元帅塔海率兵由巫峡进攻夔州,杨文安派万州安抚使王师能领水军前往协同作战。在元军强大攻势下,夔州守将张起岩投降,夔府城壁遭到屠毁。大约在此期间,天赐城也结束了抗战的历史。
今天赐城遗址绝大部分墙垣已经颓废,仅少数地段仍依稀可见垒石为城的痕迹,周长3 200米,面积0.8平方公里。东、西城门相距约1.5公里,那通著名的《大宁监创筑天赐城记》就坐落在东门松林中一块岩石之上,当地居民通称为“小石碑”。西门处还有另外一通高大的石碑,当地居民通称为“大石碑”,位于一青色砂岩上,原高8米,因风化严重,现存部分高1.85米,宽1.65米,字迹多半模糊不清,仅勉强可以辨识“以人心为金汤,以人材为武库”,“有险为难,故以险守”,“与民共守,战胜攻取”,“遂而克宅于曲阜,魏武关山……”,“又有天下之壮忠,信甲胄礼书……”等字样,从中大致可知是行文典雅、涵义隽永的赋体作品,描绘了天赐城的战略地位,着重论述天赐城军事战守的策略,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落款是“大宁监教谕赵□谨撰,大宁监判赵孟柏篆额,屯戍军马张宣立石”,时间是“癸亥二月”,即宋理宗景定四年(1263)二月,比“小石碑”略早,成为宋元战争史的重要物证。但遗憾的是“大石碑”有很大一部分被销毁,是人为削平的痕迹,其原因则不得而知。
[1]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杨士奇,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一 [Z].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2]张藻.梁秉钧碑.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Z].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
[3]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6.
[4]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Z].四部丛刊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5]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
[6]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陈世松.余 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
[8]刘德铨.夔州府志[M].道光七年(1827)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1.
[9]李友梁.巫山县志[M].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1.
[10]和 .大清一统志[M].乾隆二十九年(1764)敕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1]杨德坤.奉节县志[M].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1.
[12]魏靖宇主编.白帝城历代碑刻选[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1996.
[13]魏远猷.大宁县志[M].光绪十一年(1885)刻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1.
(责任编辑:张新玲)
Abstract:The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ci Fortress in Daningjianis the tablet inscription written by Xu Zongwu, the Anfushi (a kind of military officer) of Kuizhou district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It recorded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ci fortress and its function of resisting the Mongolian. But it was buried underground until the Qing Dynasty. It helps to preserve precious document about the wars in the area of the Three Gorges betwee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Mongolian.
Key words:The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ci Fortress in Daningjian,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ianci Fortress
A Probe into the Documentary Value of The Recor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ianci Fortress in Daningjian
TENG Xin-cai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Wanzhou 404100, Chongqing)
K204
A
1009-8135(2010)05-0128-04
2010-04-30
滕新才(1965-),男,重庆荣昌人,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教授。
本文系重庆三峡学院教授博士科研资助计划项目《宋末三峡抗战体系研究》(09ZZ-044)阶段性成果-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