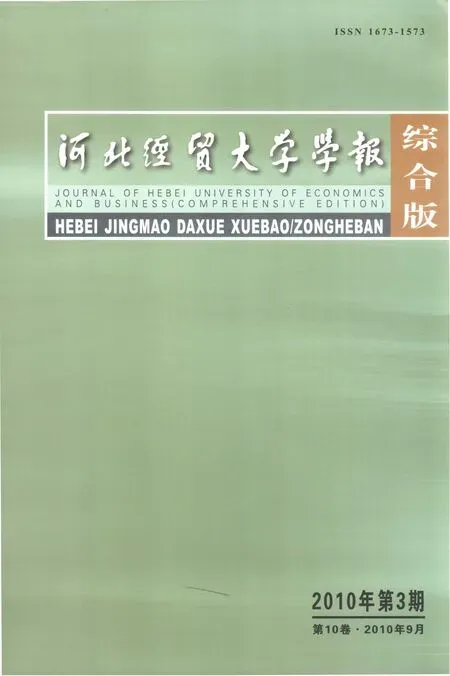从传播效应看巴金小说的心理建构
田悦芳
(1.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2.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文学研究
从传播效应看巴金小说的心理建构
田悦芳1,2
(1.河北经贸大学 人文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2.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巴金小说的叙述语、对话、独语等话语场景,以物象的生命化、情感的时空化、心态的动作化等方式,不但完成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而且实现了对读者心理的调控,在人物与读者相互间的心理建构中,以丰富的语义潜能实现了最大化的传播效应。
巴金;传播效应;心理建构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茅盾、沈从文等都是形成了自己文体特征的小说作家,然而在其身后都能找出酷肖的后学者,可是巴金的小说文体却难以模仿,其独特性很值得关注。对于这个问题,本文试从传播效应这个视角切入,探析巴金小说在心理建构上的独特性。
德里达说:“语言可称为在场与不在场这个游戏的中项。”[1](P10)也就是说,作家以文学语言建立起来的形象及整个世界是隐形的,需要读者依赖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想象出来,召唤读者建构,依赖读者的参与和领悟,将不在场的部分填充出来,从而实现文学作品的最终完成。巴金的小说,无论是流畅且富有真情的叙述语、向度复杂的对话,还是形态多样的独语,这些话语场景在完成传情达意这一基本的传播功能外,在小说的心理建构方面更是呈现出独特之处。也正是在这个向度上,巴金的小说获得了独特的传播效应。
曾有论者探讨过巴金小说的心理描写,认为它既不象中国传统的“情节小说”那样实,也不象西方“心理小说”那样虚,而是虚实结合,内外交叉。[2](P155)笔者认为,巴金小说写心理时,并不是单纯运用一种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而是以特定话语场景的设置来完成一种特定的心理建构,以实现独特的传播效应。这里的心理建构,既包括小说对人物的心灵探索,也包括小说对读者的心理调控,是二者在小说传播阶段实现的一种相互建构。“中国古代小说绝大部分以故事情节为结构中心,而几乎找不到以人物心理或背景氛围为结构中心的,这无疑大大妨碍作家审美理想的表现及小说抒情功能的发挥。”[3](P184)巴金的小说已经开始重视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并且非常重视对传播学意义上的受众——读者——进行心理调控,主要以物象的生命化、情感的时空化、心态的动作化等方式来完成小说的心理建构,从而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传播效应。
一、物象的生命化
将物象进行生命化书写,往往体现在叙述语中。无论叙事还是描写,以人写物和以物写人都是对物象进行的生命化书写,此时人物内心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互构性的,小说与读者也相互建构,形成了内在与外在并置呈现的艺术格局。
在巴金小说中,以人写物的叙述语非常多。如《家》中“夜死了。黑暗统治着这所大公馆”。作家将自然视同人的存在:给“夜”赋予了生命,给“黑暗”赋予了人的力量。这时,读者心理上获得的是“死”才有的阴森与孤寂,“统治”中令人恐怖的压制与幽禁。巴金小说改变编成电影后,已读过文本的读者总觉缺失了点什么,大约缺失的就是小说的这种心理建构带来的传播效应。
又如《月夜》:“圆月慢慢儿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指阿李随船的儿子阿林——引者注)的头发,孩子似乎不觉得。”“路伸直地躺在月光下,没有脚在那上面走。”“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里。那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像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小说以“翻过”、“横卧”、“颤动”、“梳”、“躺”、“洗”等人类才会有的动作来形容圆月、小河、月光、路等各种物象,展现这片静谧灵动的月色透出的生机,正与后面残酷的死亡悲剧形成对比,在反差中将人物心境渲染得淋漓尽致,读者心理获得的冲击力也就更大。
再如“月亮直往浩大的蓝空走去”(《家》),“茉莉花香洗着我们的脸”(《春天里的秋天》),“新香的空气梳着我的头”(《海的梦》),“歌声灿烂地开出了红花”(《火》),“月光轻轻地抱着树叶在我们周围的草地上跳舞”(《爱》),“春光渐老”(《丁香花下》)等等,这些小说把月亮、花香、空气、歌声、月光、春光等物象用“走去”“洗着”“梳着”“灿烂的开出”“抱着”“跳舞”“老”等词语进行了生命化书写后,不仅物象本身变得生动可感,更贴切地传达出小说叙事情境,也为读者阅读心理创设了共鸣的空间。
以物写人是一种很具中国传统风格的手法,很适于传达人物的婉曲心绪。在巴金的小说中,以物写人的话语场景也都是将物象进行了生命化书写。如《家》的第十章写觉新夜晚吹出的箫声。这段叙述语里,“不知从什么地方送来一丝一丝的哭泣”、“有时候几声比较高亢一点,似乎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来的婉转的哀诉”、“使得空气里也充满了悲哀”等语句,写的对象都是箫声,却以人的情感来形容,物象予以生命化了。箫声就是觉新的心语,就是他面对曾经的爱人梅的悲剧无以援手的深痛诉说。作家没有让人物直接诉说自己的悔恨和哀戚,叙述者也没有跳出来替人物说如何痛苦,而只是细腻描写箫声的哭泣、哀诉来映衬人物心理,但最为重要的是对读者心理进行了有效建构:箫声的哀诉——觉新心灵的凄苦——读者心理的共鸣,于是小说叙述获得良好的传播效应。
巴金小说对物象进行的生命化书写,在“陌生化”的语言形式中透出生命感受的逼迫和熟稔,以物象的生命质感,完成了对人物特定心理与读者阅读心理的双重建构这一别具特色的传播效应。
二、情感的时空化
对情感的书写,是巴金小说的显著特色。但他写情时很善于运用特定的话语场景将情感时空化,人物心灵呈现的深度与广度大大延展,读者的心理时空也随之延宕。
如《月夜》中的一段叙述语:“‘根生,根生!’那女人的尖锐的声音悲惨地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个,这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这是根生嫂找不到根生后,情绪立刻紧张起来的状态。小说以两句喊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加速度散播,来表现根生嫂恐惧情绪的一点一点加重,凸显人物绝望心理的渐进过程,读者的心理通过时间维度上的飞跑和空间维度上的旋转而延宕,而不是单纯的某一种刻板印象,取得的传播效果别具一格。
巴金小说中的对话和独语是最能体现情感时空化的话语场景。在错位型对话中,人物情感往往因心理向度的错位而被空间化。如《家》中觉民逃婚后,觉新对此事的情感态度是矛盾的,一面是觉得爷爷的话应服从,一面是觉得弟弟的行为应该支持,于是刚刚执行完爷爷的命令劝觉民回来,就马上开始为不能帮弟弟逃脱这门亲事而受到良心谴责,于是人物的心理空间被延展,灵魂的“深”被挖掘出来。《雾》中周如水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也是以空间化的方式予以展示的。在倾诉型对话和独语中,人物情感往往因心理长度的延展被时间化。例如《家》中觉新对觉慧就瑞珏搬出公馆生产的责问而进行的倾诉,剑云向觉民的大段告白,《憩园》中万昭华向黎先生的许多倾诉型对话,以及《新生》《激流三部曲》《春天里的秋天》《寒夜》等多部小说中以日记、书信等方式出现的独语,都是将人物情感在时间的延展中予以宣泄,将人物心理长度在自我的反复辩驳中大大拉长,于是读者的阅读心理在延宕中产生了共鸣。情感的空间化为情感带来重量和深度,人物与读者的心理得到相互建构,小说的传播效应增强。
三、心态的动作化
心态是巴金小说人物塑造的重要方面。以人物外在行为来展示心理,具有内在指向型的心态就被动作化了,但其旨归仍在小说的心理建构。
如《寒夜》中表现曾树生远赴兰州前矛盾痛苦的隐秘心态时,作家书写的却是她一系列的可视动作,如“朝床上一看”“急急走到床前去看他”“离开了床马上又回去看他”“痴痴地立了半晌”“用力咬着下嘴唇”“踌躇片刻”写留言信等,这一大段叙述语,就是对人物心态予以灵动可感的动作化,读者的共鸣心理得以强化,人物与读者的心理也完成了相互建构,小说传播中的感染力量也随之倍增。
又如《家》中觉新与梅在商场偶遇,梅的心理也是用觉新看到的她的一系列动作来呈现的:“……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我几乎要叫出声来。她抬起头来也看见了我。她似招呼非招呼地点了点头,又把脸向里头看,我跟着她的脸看去,才看见大姨妈在里头。我不敢走近她的身边,只好远远地站着看她。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把我看了好一会儿。我看见她的嘴唇微微在动,我想她也许要说什么话,谁知道她把头一掉,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进去了,也不再回头看我一眼。”这里通过觉新眼中梅的一系列动作,便将她犹疑(“似招呼非招呼地点了点头,又把脸向里头看”)、惊喜(“把我看了好一会儿”)、激动(“嘴唇微微在动”)和痛苦无奈(“她把头一掉,一句话也不说就走进去了,也不再回头看我一眼”)的复杂心态传达出来了,读者也就难免要为之动容。
人物独语也是完成小说心理建构的重要话语场景。但巴金小说对心态过程的展示,很少做静态描写,而是多以行动化的话语拓展心态空间。如汪文宣在妻子走后身不由己再次来到那个咖啡厅后,仍然要上两杯咖啡并与不在场的妻子交流的过程,便是以动作来展示人物当时无比痛苦与无限思念的心态的。另外,巴金小说中的梦境,很少美妙感,多是充满紧张与恐惧情绪的噩梦,在梦中经历一系列的挣扎行为,从而间接地把人物真实心态进行了动作化呈现,读者也身临其境般地与人物实现心理的相互建构,从而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
总而言之,始终注重“挖掘人心”的巴金小说,其话语场景有着精心的设置,在对人物心灵的探索中洋溢着对生命的满腔热情,故而小说能非常自然地把物象生命化、情感空间化、心态动作化,从而在完成对众多人物心理的开掘时能巧妙地调控读者的心理,实现小说与读者的相互建构,以丰富的语义潜能实现了最大化的传播效应,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复制的独特小说文体。
[1]【法】德里达.声音与现象——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符号问题导论[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袁振声.巴金小说艺术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Ba Jin'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mission Effect
Tian Yuefang
Ba Jin's novels employ narration,dialogue and monologue through the life of objects and phenomenon,the space and time of emotions,and motions of the psychology,to explore the inner world of the characters,and control the readers' mind.The greatest semantic potential is tapped to construct the psychological link between characters and readers so as to achieve the maximum transmission effect.
Ba Jin;transmission effect;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I206
A
1673-1573(2010)03-0066-03
2010-08-29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传媒视域中的巴金小说研究”(项目编号HB10QWX002)的阶段性成果
田悦芳(1975-),女,河北安新人,河北经贸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
关 华
责任校对:世 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