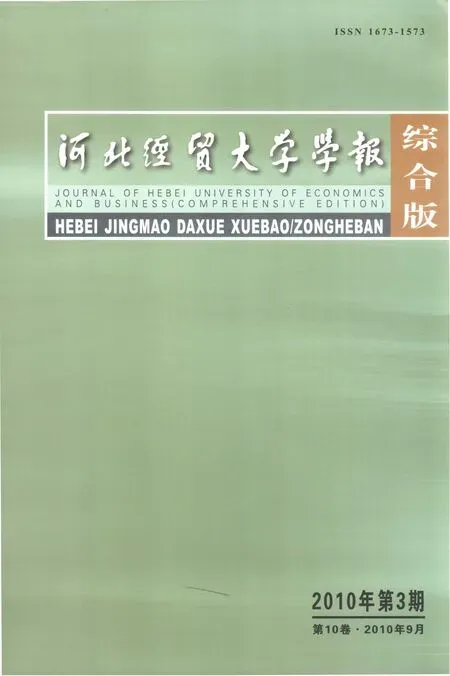《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形象的审美差距解析
游晓霞,刘伯康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河北 邯郸 056004)
●文学研究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形象的审美差距解析
游晓霞,刘伯康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外语系,河北 邯郸 056004)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小说家塞林格的代表作,这部小说自诞生之日就毁誉参半,对同一部作品的认识如此泾渭分明,主要是由于审美差距的存在。这里通过叙事学角度对主人公霍尔顿形象进行分析,发现不可靠叙述者的选取和双重叙事手法——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交替运用是审美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
审美差距;不可靠叙述者;叙述自我;经验自我
从1951年J·D·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至今,对于主人公霍尔顿这一形象褒贬不一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有人认为霍尔顿言语污秽、行为怪异,会对青少年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一度将这部作品列为禁书;但更多人认为霍尔顿身上忠实记录了美国20世纪50年代青少年的成长阵痛,通过对这一形象的审美体验,可以增进青少年对生活的认识,加强他们对丑恶现实的警觉。激烈的争论使这部作品历经半个多世纪而不衰,成为美国当代文学的一部扛鼎之作。
对一个文学形象产生如此大相径庭的审美感受,主要是由于审美差距的存在。所谓审美差距,是指由于历史、阶级、民族、文化、伦理道德、思想修养的不同,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审美趣味和审美理想,最终导致不同的审美评价。《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塞林格精确地运用多种叙事手法和叙事技巧,在文本内、在结构的各个层次中留下较多的不确定因素,这既是通往意义真相的迷障,又为读者搭建了一个驰骋想象的舞台。批评读者带着不同的审美态度,在破译创作意图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参与到人物形象的构建中,产生了不同的审美差距,更体验了强烈的审美快感,使得作品的召唤性也更强了。因此,研究霍尔顿形象的审美差距,找到其内在的原因,对于准确把握作者语义真相,重建审美期待视野有着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从叙事学角度分析,独特叙述者的选取和双重叙事手法的运用是霍尔顿形象审美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
一、真实的谎言:独特叙述者的选取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的同一年,韦恩·布斯出版了《小说修辞学》,提出“可靠叙述者和不可靠叙述者”的理论,布斯指出有这样一些叙述者——“这些叙述者装作他们似乎一直在遵循作品的思想规范来讲述,但他们实际上并非如此”①。里蒙·凯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不可靠的叙述者由于其道德价值规范与隐含作者的道德价值规范不相吻合,所以“对于他所讲述的故事和对故事的议论,读者有理由怀疑。”②霍尔顿正是这样一个值得怀疑的叙事者。
小说中,霍尔顿用回忆的口吻描述了自己三天流浪生活的所见所闻、随感所想。其间,他时而愤世嫉俗,时而随波逐流,时而言语高尚,时而举止龌龊,有时沉闷抑郁,有时夸夸其谈,粗看之下确实逻辑混乱、言不由衷,但细细品味又时常有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精辟言语。要分析这个问题,就必须认清其作为叙述者的独特性。显然,小说中的叙述者是可靠或者不可靠的,读者对他的言论是否该全相信,即对叙述者态度的差异,势必导致截然相反的认识。
首先,叙述者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例如,他像所有年轻人一样向往爱情,却不敢大胆追求只是耽于幻想。他自称琴是他的女友,对“琴理解得像一本书那么透”,把他们之间的爱情讲述得纯真无暇、浪漫温馨,甚至琴在下棋时的小癖好——“喜欢把国王摆在后排”这样的细节都了如指掌。但实际上这只是他的想象,琴根本不是他的女友,否则为何霍尔顿连和她打招呼都需要搪塞?甚至琴也不知晓霍尔顿就住在老斯特拉德莱塔的隔壁?读者通过这样的叙事者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客观真实必然有所偏差。
其次,叙述者的精神状态并不正常。作品一开始就明确指出霍尔顿住在一个精神病医院讲述故事,虽然不能藉此就认定霍尔顿的精神状况有问题,但显然作者塞林格是有意为之,故意造成霍尔顿讲的故事不够真实的假象。同时小说中一些细节描述同样暗示他在精神上存在问题。例如霍尔顿把比赛用的装备落在地铁上,导致队友们无法参加一次重要比赛,而他对此却没有丝毫内疚,“乘火车回来的时候,一路上谁也不理我,说起来倒也挺好玩哩!”这说明他在精神上确实异于常人,更加大了他作为不可靠叙事者的可能性。
第三,叙述者霍尔顿本身言行不一。他的思维纬度和肉身差距很大,实际生活中的他根本不像他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纯粹干净:他恣意放纵、装作成年人进出酒吧;他一边指责他人满口谎言假模假式,一边又编造同学的“感人事迹”,把谎言说得滴水不漏,堂而皇之的借口却是为了不让家长伤心;他最厌恶他人向自己说教,可又对室友阿克莱滔滔不绝地加以训斥,妄图以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去改变对方;他讨厌电影,可又不时在电影院里消磨时光;他明知“这违背我的原则”,却在劝诱之下招妓,如果不是良知的发现,他早已“一个劲儿地往下摔”了。霍尔顿说谎成性,张口即来,并乐此不疲,正如他自我评价那样:“你这辈子大概都没见过比我更会撒谎的人!”这种双重表现展示善与恶在他思想上的激烈交锋,同时也清醒地告诉读者:霍尔顿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霍尔顿绝不是通常情况下的可靠的叙事者。叙述者本身对于自身所经历事件的看法,并不是可信的,而是有多种解释方式。叙述者的判断能力是需要质疑的,霍尔顿不应该被简单地认定为一个精神病患者,也不完全是一个清醒的有觉悟的反抗者。他以不可靠的叙述者的身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空间。每位读者可以根据心中的“审美动机”做出自己的审美判断。如果读者认识到叙述者的不可靠,那么很容易从混乱的叙事迷宫中走出来,寻找到准确把握霍尔顿话语的方式,准确地填补叙述的空白。
二、此“我”和彼“我”:双重叙事手法的运用
乌里·马格林在对叙事文本的研究中,从时态的纵向角度将传统叙事分为三类——“回顾叙述、同步叙述、预示叙述”,将同步叙述的主体称为“叙述自我”,将回顾叙述的主体称为“经验自我”③。
仔细分析,我们发现《麦田里的守望者》既不是同步叙述,也不是简单的回顾叙述,而是通过叙述“焦点”在现在和过去间的不停闪动,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之间的相互转化,造成叙述者的面目不统一,塑造了一个既是言行颠倒的未成年人,又不时地透露出理性之光,像一个具有洞察力和反思精神的智者的经典形象。
霍尔顿说:“如果你想听,第一件事你可能想知道我在哪儿出生……可说真的,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我只想告诉你我去年圣诞节前所过的那段荒唐的生活。”这个开头看似语不惊人,实则有双重暗示意味:霍尔顿要表明他讲述的是“我”(本人)的故事;他讲述的不是现在的自己,而是一年前的自己。因此,小说中有两个“我”:一是追忆往事的霍尔顿,一是被追忆的霍尔顿。前者在叙述学中被称为叙述自我,后者被称为经验自我。作为叙述自我的霍尔顿和经验自我的霍尔顿在两个时空(一年前和一年后)有着两种不同的叙述视角,体现着他在不同时期对事件的不同认识。
作为经验自我的霍尔顿被充分还原了真实,言语粗鄙,行动猥亵,干着很多令人摸不着头脑的事儿。而作为叙述自我的他却是理性内省的,经常在不经意间对叙述自我表达感受:“我”戴帽子的时候,“把鸭舌转到脑后——这样戴十分粗俗,我承认,可我喜欢这样戴。我这么戴了看去挺美”,“把冷水龙头开了又关——这是我的爱好”。
经验自我与叙述自我的这种明显差异,也是很多读者认识的误区。如果将叙述自我看成一个经过理性反思拥有了客观判断能力的人,势必会认为霍尔顿在过去的一年中对曾经做过的事情有了清醒的认识,甚至轻信“荒唐的生活”是他对自己反省的肺腑之言。
然而未必如此,在游乐场中,霍尔顿担心菲苾从木马上掉下来,可他并没有如前面自己所说的那样,挺身而出担当“麦田里的守望者”,而是“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可别说什么去阻拦他们,那是不好的。”在这里,同样出现了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叙述转换。叙述自我冷眼旁观,代替经验自我讲述,他暗示道:尽管他曾经迫切地想做一个守望天真纯洁的卫士,让孩子们与假模假式的现实生活永远隔绝开来,但是他已经认识到这是一个乌托邦,有的孩子肯定会掉下木马——坠入肮脏罪恶的成人世界,正如他一样。“我”在现实人生中遭遇的困境是真实的,而“我”已经能够坦然面对。内心的危机似乎已经消逝,由于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叙述转换,使得叙事变得异常复杂,仿佛一层层的迷雾遮蔽了读者的视线,审美差距就此产生。
由于小说中此“我”和彼“我”,即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的不断纠结,使不同的批评读者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感受,有人认为,“在经历了生与死的洗礼后,霍尔顿逐步走上理性、成熟之路,以爱来宽容这个世界的不完美,最终回到社会的怀抱”④;有人从悲剧精神角度解读,认为遁世是弱者的行为,而霍尔顿最终疯了,这种癫狂是主动选择的“反抗”⑤,而且是更深层次的具有存在主义精神内核的反叛。而这种审美差距的存在恰恰是《麦田里的守望者》启发批评读者通过审美引发思考的意义所在。
正如RC霍拉勃所言:“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自身独立、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的观点和客体,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的反响,使文本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⑥。作者让一个不可靠叙述者清醒客观地做自我剖析,言之凿凿却很难令人信服;霍尔顿的讲述一边持续,一边又遭到质疑和颠覆——塞林格并没有为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的荒诞可笑开出一剂救世良方,而是在小说叙事中戏谑般地为读者审美设置障碍,用制造审美差距的方式使读者参与到文本创作之中,进而反思现实,探求出路,这一特点也使《麦田里的守望者》这一“当代的存在”获得了更为不朽的生命力。
注释:
①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等译,三联书店, 1989年版。
③戴维·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④傅燕晖:《生—死—回归之旅——解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⑤徐劲:《人生的悲剧,悲剧的人生——对霍尔顿·考尔菲德的心理分析》,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
⑥RC霍拉勃:《接受理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5年版。
[1]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M].施咸荣译.译林出版社,1999.
[2]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4]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5]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王峻岩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6]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 of Holden in The Catcher in the Rye
You Xiaoxia,Liu Bokang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s the masterpiece of American novelist Salinger.Since the first day when it came out, this novel has
both praise and criticism.The sharp contrast of th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is mainly due to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The analysis of the image of the hero,Holden,from the narration perspective,shows that the selection of unreliable narrator and dual narration-the alternative use of self-narration and self-experience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aesthetic difference.
aesthetic difference;unreliable narrator;self-narration;self-experience.
J973.1
A
1673-1573(2010)03-0083-03
2010-07-05
游晓霞(1980-),女,河北邯郸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英语教学;刘伯康(1975-),女,河北邯郸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语语言文学。
孙 飞
责任校对:马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