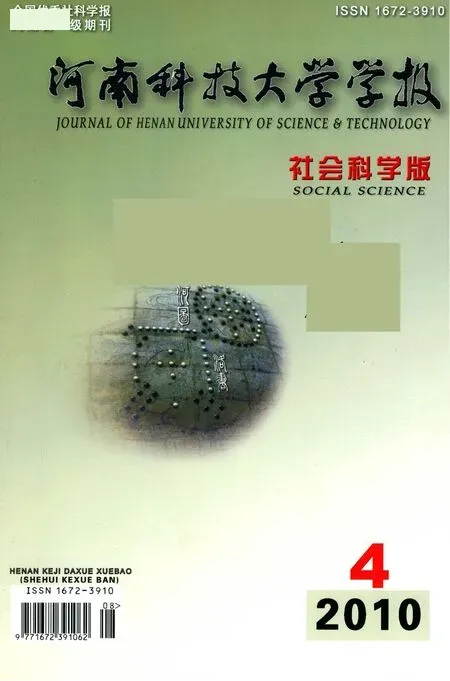物权行为客观存在论
——基于《物权法》第 15条之思考
杜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物权行为客观存在论
——基于《物权法》第 15条之思考
杜娟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物权法》的实施以立法的形式肯认了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但其文本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债权合意使当事人负担特定给付义务,物权合意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当推演构筑完整民法体系的时候,绕不开对物权行为的判断、肯定和运用;《物权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是立法者可为的选择,这并不妨碍物权行为是逻辑上的应然存在。
《物权法》;物权行为;物权变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第 15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从中可以读出三层意思:第一,以变动物权为目的的合同生效,并不必然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第二,物权不发生变动,不影响之前签订的以变动物权为目的的合同的效力;第三,以变动物权为目的的合同与物权的变动各有独立的生效要件,前者为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后者为登记 (动产为交付)。该条款仅规定了区分原则,并对之前学界热议的物权行为理论基本都采取了避而不谈的态度,以致后学之人多对物权行为不理解,认为我国法律否认物权行为理论和物权行为。本文试通过条分缕析的逻辑推演得出物权行为客观存在的徽证。后学不了解物权行为理论就不会真正的理解《物权法》第 15条乃至物权法整体,虽然物权法对物权行为理论是否承认不影响我们对物权行为客观存在的认识。
一、物权行为概念辨析
(一)以意思表示为中心的概念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的意思表示 (包括物权的合意)本身即是物权行为 (单独行为和契约行为),登记和交付是其生效要件。”[1]姚瑞光先生也认为:“物权行为,指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而成的要式行为。”[2]此观点代表了现今我国台湾地区的主流观点。[3]及至今日,学界关于物权行为概念的争议远未停息,从不同关注点入手对物权行为做的定义更是众说纷纭,但学者的见解大抵可以归为以上所举的两类,即物权的意思表示说和物权意思表示与形式的结合说。
笔者倾向于意思表示说,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两点。首先,登记是公法上的行为,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的私法上的行为,前者不能是后者的构成部分,登记不能作为法律行为成立要件。[4]尤其是在目前的中国,登记机关众多而未实现统一登记,按行政权限划分又增加了登记的公权力色彩,更不宜认定登记是物权行为的成立要件。其次,将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不妨碍登记和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表征。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不是同一的概念,物权行为解决的是当事人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或者说物权合意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此合意为内核、登记或交付为外部表征,物权行为生效物权发生变动。那种认为物权行为成立必然导致物权变动的观点,是给物权行为叠加了其不能承受之重。
由于作为生效要件的不动产登记和动产交付的行为,是一种客观存在无疑,所以,物权行为是否客观存在的问题,区别的焦点实际上集中在“物权的意思表示”或“物权合意”是客观存在还是根本不存在上。
(二)交付中的意思表示
1820年,萨维尼教授在大学讲义中谈到:“为履行买卖契约或其他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契约而践行的交付,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事实行为,而是包含一项以移转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至 1840年他在《现代罗马法体系》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物权契约的概念:“私法上的契约,以各种不同制度或形态出现,甚为繁杂。首先是基于债权关系而成立的债权契约,其次是物权契约,并有广泛的适用。交付 (Traditio)具有一切契约的特征,是一个真正的契约,一方面,包括占有的现实交付,另一方面也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表示。此项物权契约常被忽视,如在买卖契约,一般人只想到债权契约,但却忘记交付之中也包括一项与买卖契约完全分离,而以转移所有权为目的的物权契约。”
按照萨氏的主张,在基于买卖契约而发生的物权交易中,同时包含两种法律行为,即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物权契约)。我们或许可以说,德国学者善于思辨,但笔者看来萨氏此段的论述已丝毫不是试图创造一种抽象的甚至晦涩的理论体系,而是通过对交付的细致观察,精确点出交付伴有的合意或交付后的契约,这是对此合意或契约客观存在的善意的提醒。难怪江平先生和米健先生在《罗马法基础》一书中论到交付成立的条件时,除对主体、客体、正当原因和交付事实作出说明外,仍认为“让与人与受让人间须有转移所有权的意思合致”。因此,对这种合意或契约,质言之,物权合意、物权契约或物权合同的客观存在,论者已在有意无意间给出了有力的说明。
二、物权行为客观存在的逻辑推演
(一)对单方法律行为的剖析
单方法律行为是指依当事人一方的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的法律行为。最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是抛弃,抛弃也是处分标的物所有权的方式之一。当主体抛弃某物时,他心中必有抛弃的意思表示。单从形式上看,遗失和抛弃都表现为某物脱离主体占有,仅从形式上似不能认出二者之区别;只有从当事人内心意思表示观察,才区别出两种行为。为抛弃行为时,行为人主观上必有放弃某物所有权的内心意思,这种内心意思通过放弃某物占有的行为表现于外;当某物遗失时,当事人主观绝没有放弃所有权的意思。所以,同样是失其占有,遗失和抛弃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这正是当事人意思表示不同所致。
抛弃不是债权行为,因为“债是这样一种法律关系:一方面,一个或数个主体有权根据他要求一定的给付即要求实施一个或一系列对其有利的行为或者给与应有的财产清偿;另一方面,一个或数个主体有义务履行这种给付或者以自己的财产对不履行情况负责”。[5]抛弃,以直接变动物权的意思表示为内核,以放弃某物的占有为表征,证明了物权行为的存在。单方行为中存在物权行为一议,学界似无不同意见。[6]
(二)对双方法律行为的逻辑推演
双方法律行为是指双方当事人相对应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合同 (本文均指债权合同)是最典型的双方法律行为。签订以变动物权为目的的合同时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是:合同生效后的交付或登记是合同的履行行为还是一个独立的物权行为?笔者以此症结推演之。如果登记或交付为合同的履行行为,那么有当合同无效时和当合同有效时两种情况分别讨论。
其一,当合同无效时,已经办理的公示同样无效。合同无效,又称合同的绝对无效、当然无效,指合同因具有法定无效事由而当然地不发生效力。合同无效要溯及既往的消灭合同产生的影响,达到恢复原状的效果。在合同设立前的状态是:出卖人享有物权,买受人保有价款。合同被宣布无效以后法律上继续承认这一效果。但由于作为合同的履行,已经办理完毕公示,即动产转移占有、不动产完成登记。如此必有一个时间段权利人是这样的状态:物权公示为买受人,事实上为出卖人。出现了起码是这个时间段出现了公示公信原则的悖论。在登记错误致无权处分情况下,这种悖论也会有发生,因此对公示公信原则的违反不必大惊小怪,但必须意识到,公法行为的错误与私法制度设计之不周延,在合理私法体系构建上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在现今的交易社会,公示公信原则是解决物权归属的最重要的原则,法律行为变动物权是物权变动的最主要方式,当这两种制度冲突成为常态时,逻辑上的囹圄是需要正视的。
其二,当合同有效时,出卖人有履行的义务,很多问题在此亦无法解释。合同的履行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其合同义务,债权人的合同债权得以实现。[7]笔者发现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交付或登记虽“履行”但违背出卖人意愿,其效果如何?一般认为,在履行中出卖人的意愿是不那么重要的,重要的是给付行为,此处是转移占有或完成登记。继续推演,买卖合同签订以后,买受人在出卖人不知情时将标的物偷出而占有,或买受人与登记机关串通完成登记,也该视为合同履行完毕而构成标的物所有权的转移了。这个结论显然与常识相悖。认定登记或交付为履行行为时,悖论再次出现。
此推演也启发笔者意识到:签订以转移物权为目的的合同与物权的变动,是不可合二为一的两类规则。那么,下文转换思路认定登记或交付为物权行为,同样分合同有效和合同无效两种情形推演。法律行为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并依该表示的内容发生法律效果的行为。[8]当将合同行为和其后的登记交付分别看做独立的法律行为,知二者均是以意思表示为核心要素的行为。
其一,当合同无效时,物权行为仍然可以有效。物权行为为独立的法律行为,有其独立的成立生效要件,一旦满足,自可以有效。首先,公示公信原则在此运行不悖,上文分析的时间差问题被解决。只要买受人基于双方的合意取得了占有或获得了登记,买受人便取得所有权,至于合同之后被宣布无效不妨碍物权行为之独立。在此情况下,制度设计承认物权行为买受人得到所有权,公示获得的公信力也指向买受人,权利外观和权利实质相统一。如孙宪忠先生说:“该理论 (物权行为)最终解释了物权公示的公信力,物权为什么必须公示并能在公示后取得对抗任意第三人的效力的问题。”[9]145其次,在买受人向第三人转让同一标的物时,转让的是自己所有之物,是有权处分,转让第三人的合同当然有效 (如果是无权处分,即为无效合同了,参见合同法第 51条)。此时,第三人完全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这对维护社会上大量交易合同的交易安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现有的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体系下,或许可以引进德国民法现代化中认为无权处分债权合同亦有效的观点,在债权合同效力上达到同一效果,但无可否认无权处分亦有效是民法体系中的一种例外设计,当大量的转卖行为将这种例外变成常态时,有理由怀疑此体系设计移植的合理性。第三,同为典型的处分行为的债权让与,其无因性在学理上是不存在任何障碍的。同为处分行为,将物权行为与其原因绑定如此之牢固理由充分否?笔者从处分行为天然的法理基础中看到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无因存在。
其二,当合同有效时,因为同样要满足物权行为有效的条件,所以物权不必然变动。登记或交付为物权行为时为处分行为 (履行行为为负担行为不同于此)。那么,登记或交付内核的意思表示在物权行为生效上是至关重要的。在上文所举例子中,买受人在出卖人不知情下将标的物偷出而占有,显然无买受人意思表示要件在其中,标的物所有权固然不能转移。
三、否认物权行为客观存在的“手套交易说”及其质疑
认为物权行为纯为“技术的概念”是影响最大的对物权行为存在质疑的论说之一。对此,德国学者基尔克“手套交易”的比喻常被引用。基尔克说:“如果我们勉强地将单纯的动产分解为相互完全独立的三个现象时,的确会变为学说对实际生活的凌辱。到商店购买一付手套,当场付款取回标的物者,今后也应当考虑到会发生三件事情:其一,债权契约,凭此契约发生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二,与此债权契约完全分离的物权契约,纯为所有权的让与而缔结;其三,交付的行为完全是人为拟制,实际上只不过是对于单一的法律行为有两个相异的观察方式而已。今捏造两种互为独立的契约,不仅会混乱现实的法律过程,实定法也会因极端的形式思考而受到妨害。”[10]笔者谨认为,因噎废食万不可取。立法承认物权行为理论与否是价值判断,物权行为在体系上存在与否是事实判断。对于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上文已作论证,以价值的轻视否认事实的存在,是说不通的。尹田先生在《物权行为理论评析》中的描述非常可取:“德国学者对于物权合意或者物权行为的‘发现’,如同法学家对任何一种法律现象的‘发现’一样,都不是凭空臆想或者无端捏造的,都是以一定的生活事实作为根据的……虽然任何法律现象都是来源于客观发生的生活事实,但法律现象是经过对生活事实的抽象而形成的观念性表达,是生活事实的‘反映’,但绝非生活事实本身 (这就是极其熟悉社会实际生活的人非经专门训练也不能成为法官的原因)。”[11]
四、物权行为理论在我国的存在
(一)必然借鉴的国外物权变动立法例
1.意思主义。不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存在,认为依债权合同设定、让与物权时,物权变动只是债权变动的效果,不认为存在与债权行为分离的物权行为,把二者合二为一了。最典型的是《法国民法典》第 1138条第 2款之规定:“交付标的物的债务从标的物应交付之时起成立,即使尚未现实移交,也能使债权人成为标的物所有人,并负担标的物的危险,但在债务人迟延交付的情况下,危险由债务人负担。”第 1583条的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合同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
笔者禁不住对法国法上的意思主义产生一丝质疑:既然买卖合同成立并生效标的物所有权即从出卖人转移给买受人,那么随后的买受人要求占有标的物的权利就完全可以不是债权的履行行为,而是所有权返还请求权。因为,标的物已在合同生效时归买受人享有,买受人要求取回已为他人占有的物,正是所有权返还请求权要解决的问题。此时,只能得出买受人占有标的物的行为,既是所有权返还请求权的行使也是在主张合同履行利益,或者债权合同没有履行行为的结论,但此二者都是债法体系所不能容的。我们既然采用了德国法上的物债二分体例,用物债二分观点衡量制度便是应有之意。
2.物权形式主义。认为债权行为以外有独立的物权行为存在,物权因法律行为发生变动时,需要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并完成交付或登记的法定形式。《德国民法典》第 873条第 1款规定:“为转让一项土地的所有权,为在土地上设立一项权利以及转让该项权利,或者在该权利上设立其他权利,在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必须有权利人和因该权利变更而涉及的其他人的合意,以及该权利变更在不动产登记薄上的登记。”关于动产让与,其第929条规定:“为让与一项动产的所有权,必须由所有权人将物的占有交付与受让人,并就所有权的移转由双方达成合意。”
按照德国民法上“物权形式主义”理论,法律行为因其效果不同,分为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债权行为的效果是使特定债务人负担给付义务,物权变动是物权行为的效果。德国因为物权行为的发现,创造了逻辑上的完美。
3.债权形式主义。把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结合起来,各取一点。该立法例认为,物权变动的效力是债权行为、交付或者登记之形式共同作用的结果。既不认为物权变动效力由债权行为引起,也不承认是物权行为的结果,而是两者结合产生的效力。典型立法如《瑞士民法典》第 714条第 1款规定:“动产所有权的移转,应移转占有。”第 656条第 1项规定:“取得土地所有权,须在不动产登记簿登记。”第 963条规定:“不动产登记,须依不动产所有人的书面声明作成。该所有人对该不动产须有处分权。”第 963条第 2款规定:“但不动产的取得人有依据法规、生效的判决书或与判决书有同等作用的证书的权利时,无需所有人的书面声明,亦得进行不动产登记。”第 972条第 1款规定:“物权在不动产登记簿主簿登记后,始得成立,并依次排列顺序及日期。”第 974条还规定:“凡无法律原因或依无拘束力的法律行为而完成的登记,为不正当。”对于不正当的登记,受害人得诉请更正登记。一般认为,此规定表明该法典采有因说。
(二)我国物权法法条分析
以《物权法》第 15条为代表,知我国物权变动采用的既非物权形式主义又非意思主义,而是二者折中的债权形式主义。采物权变动合同的效力与物权变动效果区分原则,登记生效与登记对抗相结合。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动产物权变动不登记的,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但法律不要求必须登记的,当事人得自由选择 (登记的能够对抗第三人,不登记的不能对抗第三人)。总的来说,《物权法》对待物权行为采取模糊态度:承认区分原则,明确物权变动效力自公示起发生,而非因债权合同生效而发生;回避物权变动的合意究竟是来自物权合意还是原因行为的合同,或者与合意无关。
第一,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中,《物权法》承认物权行为制度的存在。第 127条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生效时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是发包人和承包人设立物权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同一旦生效,承包经营权人就得以对承包土地享有排他性的使用、受益权 (物权)。因此,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是物权行为似无疑问。
第二,采纳区分原则,承认物权变动自交付或登记之公示完成时发生。首先,第 6条的总括性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依登记,动产物权变动依交付,物权变动自登记或者交付时起生效;其次,在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 138、139条 )、抵押权 (第 185、187条)等他物权的具体规定中,也区分了物权设定效力与债权合同的效力,与总括性规定一致。第三,如前述,第 15条反向规定了区分原则。
第三,《物权法》回避了物权与债权合意是否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行为。因法律行为变动物权,须经当事人合意并经过公示,也就是公示是公开显示变动物权的合意。《物权法》仅规定了物权变动的效果经公示发生,但是公示的合意是债权合同还是物权合同,则不明确。但在法律适用中,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12]
五、结束语
可以认为我国物权法肯定了这样一种物权变动模式:物权变动效力自交付或者登记时生效,与当事人有无合意无关。笔者认为,忽略是否确定当事人物权合意和按什么主义来确定当事人的物权意思表示,是一个立法上的瑕疵,将给司法带来困境。一方面,既然采用德国的物债二分,在法律行为项下只承认债权行为而忽略物权行为,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当一个交易中既有债权行为又有物权行为时,我们决不能因为表层性的债权行为而否定较深层次的物权行为,应对二者加以科学的区分。”[13]另一方面,物权行为的存在也昭示了对当事人意志的尊重,物权行为理论“把物权的优先性与当事人物权意思表示相结合,然后又将他们与可以从客观上认定的法律事实相结合,从而实现意思自治的私法原则与物权特性的结合。”[9]167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 (五)[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7.
[2]姚瑞光.民法物权论 [M].台北:海天印刷厂,1988:14.
[3]梁慧星,陈华斌.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71.
[4]王泽鉴.民法物权 (一)[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79.
[5][意 ]彼得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 [M].黄风,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83.
[6]江平.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313.
[7]王利明.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17.
[8]张俊浩.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19.
[9]孙宪忠.论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0]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468.
[11]尹田.物权法理论评析与思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10.
[12]王卫国.民法学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14-215.
[13]蹇洁,胡阳帆.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及其意义之辨析 [J].经济师,2005(2):62-64.
The Ob jective Ex istence of Jur istic Act of Rea l R ight:Tak ing the Fifth Piece of the“Property Law”asan Exam p le
DU Juan
(Civil and Comm ercia l Econom ic Law School,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 l Science and Law,Beijing100088,China)
The imp lem entation of the p roperty law recognizes the discrim ination rule in real right alternation,while fails to adop t the theo ry of juristic act of real righ t. The agreem ent of debt pays parties specific ob ligations,and the agreem en t of real right m akes an effect of real right alternation.W hen constructing the entire system of civil law,peop le should rely on the judgm ent,affirm ation and use of the juristic act of real right.It is an op tion for lawm akers to adop t the theory system of juristic actof real rightor not,while thisdoes not p rec lude that juristic act of real right is logically existence.
“Property Law”;ju ristic act of real right;alteration of real right
D 923.2
A
1672-3910(2010)04-0108-05
2010-03-23
杜娟 (1985-),女,湖北恩施人,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