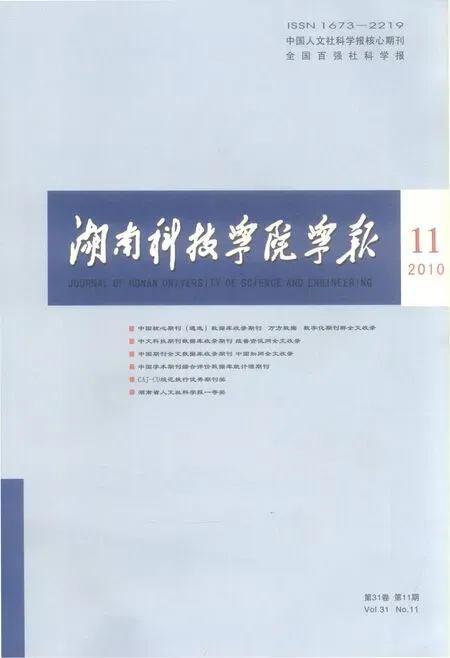《教长的黑面纱》中“也许类”词所暗合的解构两难
崔彦飞
(渭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陕西 渭南 714000)
《教长的黑面纱》中“也许类”词所暗合的解构两难
崔彦飞
(渭南师范学院 外语系,陕西 渭南 714000)
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是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名作,这部作品用词讲究,语义深刻,特别是似乎、仿佛、好像、没准儿等词的频繁运用,使得整个文本徘徊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语义矛盾,该文把这类词界定为 “也许类”词,通过对这类词的遣词分析认为,“也许类”词的使用所造成的意义矛盾,暗合了解构主义的两难状态,也就是否定“形而上”然而又预设了“形而上”存在的矛盾境界。
“也许类”词;意义矛盾;解构主义;两难状态
一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解构主义异军突起,对传统的西方哲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解构主义认为传统的西方哲学都建立在形而上基础之上,都好像在试图证明,在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一个终极的、超验的、以它为中心的东西。德里达在他的一篇代表性文章《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嬉戏》指出:“也许可以指出的是那种基础、原则或中心的所有名字指称,一直都是某种在场(例如:艾多斯、原力、终极目的、能量、本质、实存、实体、主体、揭蔽、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等)。”[1]P320通过对这种别名替代进行分析,他彻底地粉碎了结构主义的“以结构为中心”理论,从而也消解了形而上。虽然随后的几年通过他的力作《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声音与现象》,确立了他的解构主义理论,然而这种理论的哲学或者说对“中心”的消解,对于德里达本人而言也是一个痛苦挣扎的过程。他本人就曾经指出“我想试着一方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那种必要性,另一方面无需否定哲学,也无需去说哲学已经过时。这个困难就在于解构哲学而又不要瓦解它,我一直没有间断地处在这两极之间”,[2]P4不难看出德氏的痛苦的来源就在于在“消解哲学”与“无需否定哲学”之间, 如果消解, 也就是“试着一方面强调瓦解形而上学的必要性”,这正是解构主义理论所必须的;另一方面无需否定哲学,也就是说自己所讨论的不可避免属于哲学范畴,这正如 “消解一切形而上学的中心”也就预设了一个中心,使自己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霍桑已被公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作为一个道德家及讽喻作家,他沉迷于神秘的罪恶主题。[3]P1247神秘的主题使他的作品具有意义含糊的特点。他的名作《教长的黑面纱》通过频繁的“也许类”词的应用,使整个文本总是徘徊在肯定与否定之间,从而解构了文本确定的意义本源,同时也使得文本本身处于意义的矛盾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对解构主义德氏两难状态的一个绝好的注脚。
二
《教长的黑面纱》讲述的是一个教长突然间有一天带上黑面纱,并且戴上黑面纱辞世的故事。小说用词讲究,选词也别具匠心,在《教长的黑面纱》中,黑暗是通过使用black、dark、shade、shadow等词的多种形式直接表现出来的,又是通过conceal、hide、secret等词间接表现出来的;制造神秘的气氛,阴森可怕的效果,则用mysterious、strange cloud、ghost-like、horrible、frightened、tremor等词;而表达孤独痛苦的词则有gloom、sad、melancholy等[4]P85。事实上,通过对文本细读不难发现,“也许类”词的使用也可谓比比皆是,不胜枚举,本文中“也许类词”指的是“好象、仿佛、没准儿、也许、可能”等一些词,这些词否定中夹着肯定,肯定中又回归否定,在文本中作为高频词,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模糊的意义矛盾,而这也恰好暗合了解构主义的两难状态,本文正是以“也许类”词的使用为出发点,对《教长的黑面纱》这部小说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了遣词的赏析。
黑面纱的出场,霍桑就给予了似是而非的描写,这也是对黑面纱作为物质实体的首次着墨。“近些看面纱似乎(seem)有两层,除了嘴和下巴,一张脸给遮得严严实实。不过,也许(probably)并没挡住他的视线,只给看到的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蒙上了一层黑影”,①似乎、也许的运用,无疑正像黑面纱的“黑色”一样,给黑面纱蒙上了一层耐人寻味的神秘色彩。在他的笔下就连黑面纱到底有几层这个简单的问题,似乎都变得令人费解。“近些看黑面纱似乎有两层……”,为什么似乎有两层呢?在这种“似乎有”的推测和“近些看”的字眼中,意义的矛盾很简单的就显现出来了。“近些看”这个字眼暗含着一中肯定的描述,而“似乎有”两层,很显然只是一个猜测,不论它是肯定还是否定,它只是一种猜测,所以表达不可避免有了模糊的概念。事实上作为读者,谁想要一个模糊的答案呢?所以我们会不自觉的去问,作者为什么不写的肯定些呢?比如,我们可以和霍桑商定,把这句话改为“黑面纱有两层”,或者 “黑面纱并不是两层”,这岂不更为清晰明了。但在这部小说中霍桑似乎与明了无缘,而“意义含糊”更是其写作特点。
再往下读,紧接着在同一句子中出现了“也许并没有挡住视线”,“也许”这个不确定的推测字眼的接踵而来,那也就是说也可能挡住了,事实上当我们在做这样的结论的时候,好像小飞虫落入了蛛网,面临的只有被自己的结论吞噬的危险,既然是 “也许”,那还有一种没被挡住的可能;究竟挡住了没有呢, 我们只能处在不可终结的模糊边缘,或者霍桑想表达的是,也挡住了也没挡住两者兼而有之的意义,很显然这种说法造成的是更严重的后果,黑白不能调和的意义矛盾。而霍桑本人似乎是一个冷眼的旁观者,作为一个故事的叙述者,娓娓给我们道来的是他那种不确定的“也许类”陈述,在这样的陈述中,如果我们还想执着的去追求那种肯定,只能是劳而无功,我们感觉到的也只能是压抑和无力,事实上霍桑本人都说过“这该死的语言,到底是什么,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5]P308所以我们只能放弃这种肯定的或者说否定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确定的寻求,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否定这种文字的存在的必要性,正是由于这种文字的存在,它给予了我们好多信息,只不过我们排除的只能是,对意义“确定的”寻求罢了,所以最终导致的只能是“确定意义”的消解,当然很显然,我们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确定意义曾经”的存在,使人不难想到德里达的对哲学消解和预设的哲学存在的“两难境地”。既然 “似乎有”和“也许”导致了这种意义上的不确定,并且暗合了这种解构的两难,我们何不将其删除,变成确定的说法呢?比如我们可以把语句改为“近些看面纱有两层,除了嘴和下巴,一张脸给遮得严严实实。不过,并没挡住他的视线,只给看到的一切有生命无生命的东西蒙上了一层黑影”,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吗?当然不是,这样黑面纱的那种神秘,那种特别荡然无存,这也不符合整篇的语义气氛——黑暗,神秘,阴森可怕,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两个似是而非模糊的字眼,开启了整个文章的篇章,赋予了“黑面纱”以最显著的地位,引起了轰动,也为后文对黑面纱文本的意义的探索埋下了伏笔。
教长突然有一天戴上黑面纱的行为引起了轰动效应,“翌日,米尔福德全村除去胡珀教长的黑面纱绝少谈及其它,黑面纱及其背后隐藏的神秘,成了熟人在街头相遇必议的话题,也成了好心肠的妇女们在敞开的窗口说长道短的谈资……”所以对面纱主题的谈论可谓是众说纷纭,那么我们不自觉的会问,在当事人胡珀眼里,黑面纱又是怎样一种情形?有什么特殊的确定的含义呢?然而通过对下面一系列语句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放弃这种寻求, “也许类词” 的运用又一次把意义推向了矛盾,陷入了解构的两难。“小小一块黑纱,触目惊心,害得不止一位神经衰弱的女人被迫提前离开教堂。可是在牧师眼中,面无人色的教徒们没准儿(perhaps)就跟他的黑面纱一样令人胆寒呢。”“触目惊心”的用词不足为奇,事实上黑面纱产生的效应从一开始就显现了,“人们全都吃了一惊,即使来了一位陌生的教长,为胡珀先生的布道坛掸净坐垫,也没有比这更诧异的了”,然而令人驻足停留,引颈叹之的依然是那否定中夹着肯定的也许类词“没准儿”,“面无人色的教徒们没准儿就跟他的黑面纱一样令人胆寒呢”,通过没准儿,我们显然能感觉到教长无声的嘲笑,嘲笑着教众的虚伪,甚至人类的虚伪。这种感觉是强烈的,我们似乎能听见教长略带讽刺的反问——难道在世的人的罪恶不像我的黑面纱一样令人恐怖吗?然而“没准儿”这个非主观的客观字眼的运用,又似乎在悄悄的减弱这种力量,使得文本的意义在游移和偏离,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得不说这种感觉挥之不去,直到教长弥留的最后一刻。
“你们也互相颤抖吧!男人们回避着我,妇女们不表示怜悯,儿童们尖叫着抛开,只因为我带着黑色的面纱吗?在人们向他的朋友敞开心扉,向他的最爱恋的情人诉说衷曲,在人们徒劳地萎缩于他的造物主的面前,恶心地珍藏着他的罪恶的时侯,却把我视同魔鬼,只因为我在其下生活和死去的那个象征!我环顾四周,看啊!在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幅黑面纱”,“此时,听到这样的话的人互相畏惧着,退缩着,而胡珀神父便回到枕头上,成了带面纱的僵尸,嘴角上仍然存留着淡笑”。
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啊,控诉中带着悲凉,悲凉中透着从容。教长在通过黑面纱控诉着世界,缺乏同情、包容和温暖,让人感受到的只是孤独,无助和冷默,一切“只因为我带着黑面纱”,当然人们在“恶心的珍藏着罪恶,却把我视同魔鬼”的同时,我们可以断定教长的言外之意——假如教长戴的是有形的黑面纱,那么世人则隐藏着无形的黑面纱,正因为如此,“我环顾四周,看啊!在每一张脸上都有一幅黑面纱”。虽然他的控诉是悲凉的,但却是有力和从容的,“人们互相畏惧着退缩着”,即使成了“带黑面纱的僵尸,嘴角仍然留着淡笑”,他在从容地嘲笑着人们隐形的面纱及其它背后隐藏的虚伪的本性。分析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再一次确定“没准儿”词的使用,隐含了胡珀教长对整个人类虚伪的控诉和嘲笑,然而又为什么用“没准儿”呢,很显然这种“控诉和嘲笑”也只是 “没准儿”这个否定的推测词,所衍生出来的一种意义,它存在但不是唯一,正是这种存在而不唯一的状态,使我们又不得不回归到否定,从而在肯定与否定间徘徊,进入不确定的非此非彼的解构两难状态。事实上,难道这种“否定中夹着肯定,肯定中又回归否定性”的两难状态,不是这个也许类词“没准儿”的运用造成的吗?
教长为什么要戴上黑面纱这个问题,文本就根本没有停止过描述,包括三方面:人们流言飞语的猜测,教众代表团的正式询问和恋人的坦然追问。[6]P69-71下面的片段是在被教长拒绝摘下黑面纱后,对于伊丽莎白的一段描写,似乎伊丽莎白领悟到了黑面纱某种确定的含义。
“他就用这种柔中有刚的固执抵制了她的所有恳求。最后伊丽莎白只有默默地坐在一旁。一时之间陷入了沉思,大概(probably)是在考察用什么新办法能够把她的恋人从这种阴郁的怪念头中拉出来,这种行径如果没有其他含义,恐怕(perhaps)是一种精神病的症状。尽管她的性格要比他坚强,泪水还是滚下了她的面颊。但事实上,一种新的感情代替了伤心,她的眼睛木然地盯着黑面纱,这时突然仿佛(like)空中出现一道微光,黑纱的恐惧攫住了她,她蓦地起身,对着他直发抖。”
短短一段话,接连用了三个“也许类”词,这是文本意义含糊的又一次展现。“大概是在考察用什么新办法能够把她的恋人从这种阴郁的怪念头中拉出来,这种行径如果没有其他含义,恐怕是一种精神病的症状”,这是对伊丽莎白当时心里的一个细致描写,作为最深爱教长的人,一开始,伊丽莎白急切的想澄清一切谣言,弄清真正的事实,甚至低调陈述着教长的这一怪异行为,“这块面纱没什么可怕的,只不过它遮住了一张我总乐于看的脸”,但是当她遭到教长柔中带刚的拒绝后,按照正常的逻辑,她一定会竭力想办法,来补救这个事实。然而为什么文本没有这样做,作者就像一个反逻辑的人,偏偏要用“大概”是考察,“恐怕是”这样的推测性语言,他似乎也在暗示什么,似乎在暗示这亲密情人的无奈,在她的无奈中,隐隐约约我们能推测出,也许伊丽莎白在同教长的交流中感悟到了什么,所以就像弗莱所言的神启性文学的描写,“这时突然仿佛空中出现一道微光”,教长似乎也意识到了爱人亲密的共鸣,紧接着说道,“看来,你终于感觉到了”,感觉到什么了呢,“她没有回答……”文中再没有描写,而我们也无从所知,唯一我们敢肯定的是,他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然而某种东西也只是一种不确指的说法,我们又不得不陷入一种无言的两难。我们似乎能确定某种东西的存在,然而由于某种东西,本来就是一种不确指的说法,所以我们的确定又成了不确定,确定与不确定,不正像解构的“消解哲学又无需否定哲学存在的两难”状态吗?
三
对于解构的两难状态,除了德氏自己的苦痛挣扎外,事实在理论上,也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质疑。林秋云就明确质疑“作为一种抵制理论的理论,解构主义是否有自己的理论?”[7]P110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间是否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康德式的两难问题。丁尔苏也对这种矛盾有这样的分析:“解构主义声称的某个文本中的符号无休止的嬉戏,不允许文本呈现任何稳定的意义,这本身就表达了一个稳定的主张,很显然这是矛盾的。”[8]P41就《教长的黑面纱》这篇短篇小说来看,正是由于大概,恐怕,仿佛,也许等“也许类”的词的高频运用,从而使我们的解读,充满冒险性,把我们一次又一次从肯定摔到了否定,又从否定掷向肯定,同时这种“也许类”词造所成的意义矛盾,也有力地暗合着解构主义的两难状态。
注 释:
①文中译文皆选自胡允桓译,Selected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 Beijing:Foreign Language Press,2000年出版。
[1]Zhang Zhongzai, Wang Fengzhen, Zhao Guoxin, Selective Readings in the 20th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y[M]. Beijing: Langua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2.
[2]雅克.德里达,张宁.书写与差异[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Nana Baym.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2003.
[4]钱青.美国文学名著精选[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James Macintosh.Nathaniel Hawthorne’s Tales[M]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1987.
[6]崔彦飞.“黑面纱”在追问中延异[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10).
[7]林秋云.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外界的误解与自身的不足[J].外国文学评论,1998,(4).
[8]丁尔苏.解构理论之症结谈[J].外国文学评论,1994,(3).
(责任编校:王晚霞)
I106
A
1673-2219(2010)11-0153-03
2010-09-20
本文为渭南师范学院专项科研基金项目“解构文论在文学作品中的具体研究”(项目编号:07YKZ025)成果。
崔彦飞(1978-),男,山西长治人,讲师,英语语言文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西方文论。
——以山顶度假屋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