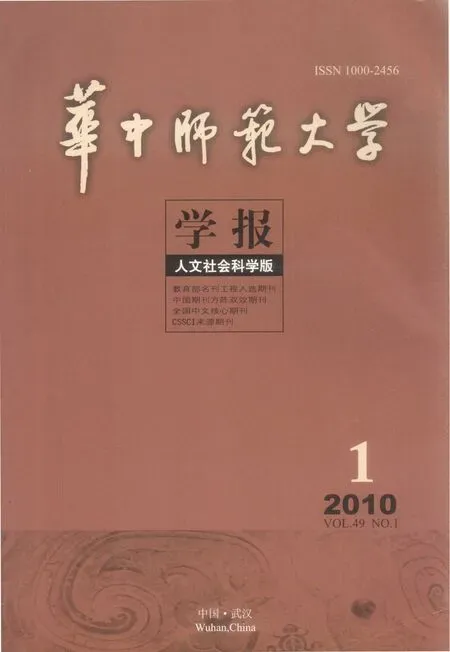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北京白云观与晚清社会
付海晏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晚清白云观在宗教、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宗教史的角度而言,晚清白云观在拓展、高涨全真龙门声势方面颇有功绩,白云观的历史与认同得到了强化,白云观的传戒步入正规与常态。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白云观尤其是高仁峒发挥了超越道教的作用,不折不扣是一个“政治中的神仙”。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而言,方丈高仁峒既是雅士,又是俗人,而白云观则是京城大众重要的宗教生活以及游乐场所。
晚清;北京;白云观;高仁峒
白云观的历史悠长,上可溯自唐代的天长观,金元之际因邱处机之故而成为全真龙门祖庭。清初有赖于王常月的努力,白云观以及全真龙门得以重振。迨至晚清,白云观的声势更为显赫。从既有资料来看,晚清白云观在宗教、政治、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是如此,长期以来,白云观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从不同方面拓展了近代白云观史的研究①。在学习、继承海内外学界已有重要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拟从宗教史、政治史、社会生活史等三个角度对晚清白云观略作进一步的梳理。
一、白云观与全真龙门声势之高涨
从宗教史的角度来看,白云观以其在宫观拓展、传戒活动的常态化、显赫信众的扶持以及宗教认同的强化等方面的显著成效昭示着晚清全真龙门高涨的声势。
庙宇或宫观在宗教史中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最近的一项近现代中国城市道士与庙宇研究计划中,主持者提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究竟道士与庙宇是近现代中国城市宗教中的两个独立的方面,还是他们有牢不可破的关联?在本文看来,道士与宫观都是宗教的重要内容,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牢不可破的关系,而且互相促进。晚清白云观的拓展以及住持道士颇有成效的劝募,全真龙门的声势才得以日渐高涨。
根据已有的观志以及碑刻资料可知,作为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藏蜕之所,白云观自建立以来就在全真道的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由于岁久倾圮,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燕王朱棣令中官董工重建前后两殿、廊庑库房及道侣藏修之室。宣德三年(1428)创建三清殿,正统五年(1440)建造玉皇阁、长春殿以及道舍钵堂,此后在正德年间屡有兴修。然而到清初,白云观的观基仍是“隘窄”,康熙中,有王善人者,创建三清阁,“规模宏丽”③。康熙四十五年(1706),白云观再次有兴修之举,扩东西南北四至,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长春殿、七真殿、灵宫殿、四圣殿、山门牌楼等④。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曾加修葺,“越三十年丙午,行春过此,顾念陊剥”,又发“内帑八千六百余,完饰如旧”⑤。
嘉庆十二年(1807)在张本瑞传戒后,“天建弟子”蔡永清与“彭蘧生太史,廖东生户部,各出赀,于院中西偏,立纯阳金殿,计金四千八百两”⑥。在郭教仁住持白云观时,蔡永清又“改立圜堂,修理戒堂,饭传戒诵经,安单息静,种种所需,莫不咸具”⑦。嘉庆年间,在蔡永清的努力下,常清观成为下院:“山左济宁州有常清观者,今为白云下院,余洎同人亦曾致力于彼,是以定议,彼中住持,永遵白云规约,亦同道相维之意也。”⑧
道光八年(1828),长白麟庆曾闻蔡子(尹志华指即为蔡永清)“近于防山间,得尹宗师太和宫址,拟筑白云下院”⑨。嘉庆二十四年(1819)已卯燕九节,长白麟庆访求十八宗庑不得,住持曰“庑相十八粟久失”。蔡氏云“尝足迹半天下,相惟此存,毁不复相,曷先绘素存真,奉粟补缺”。⑩十年后,即道光八年(1828),长白麟庆与蔡氏、马文、刘天成以及住持张合智重修宗庑,历三月而成[11]。道光二十四年(1844)善信王洪礼捐资创建真君殿[12]。
光绪十三年(1887),在高仁峒的主持下,白云观重修吕祖殿。“旧有正殿三楹,内有祖师法相……惟殿宇创自昔年,历时既久,不无残缺,尝思稍加修葺,苦于独力难成。幸地安门外帽儿护坛诰授二品命妇董母素霍拉氏,暨男舒明一门,好善乐于施舍。自光绪元年,接办祖师圣会,每岁四月十四日圣诞之辰……十有余年,虔诚未尝稍懈。去岁助善至观,见殿宇渗漏,慨然发愿,增修捐金四百两有奇。今春兴工数十日,修饰完整,焕然一新,此本观数十年有志未逮之事……”[13]在“董母素霍拉氏”家族的支持下,吕祖殿很快竣工,但是“一切彩画尚缺”。光绪十五年(1889),受父亲王海甫子江临危之遗命,京西罗庄“耆公英舫,全公颐斋”二人出金将殿内外添设彩画,“并及东西两廊殿前川堂八仙殿,榱题栋宇,焕然一新。复将相装严,并献殿中陈设”[14]。
晚清白云观最重要的宫观拓展,要属光绪十六年(1890)云集山房的修建。为何要修建云集山房?高仁峒曾云原因为:“峒自入观以来,猥司道纪,译经无所,申戒乏台,每逢檀越贲临,道侣集讲,客院未闳,用斯积歉,历有年矣。”[15]在内廷太监刘素云等人的捐资下,高仁峒“拓观后余地,中筑戒台,游廊环翼,北构开轩,以为众信善讽经祈厘、祝嘏筵寿之所。左右叠石为山,辍以亭沼,肃宾接众,规模宏焉。惟念善庆既资福缘,清规尤宜恪守,倘或因其区宇稍展,视同公宴之地,甚至作剧开尊、滋渎清净,则殊有负初心矣。”[16]是哪些人捐赠呢?刘素云助修园墙楼房银一万五千两,董大老爷助修山子银两千两,增景堂张宅山子作助修山子工料银两千两,孙七老爷助修山子银五百两,张大老爷助修山子银五百两[17]。云集山房的成功修建,不仅使得白云观有了必要的传戒场所,更为重要的是它成了白云观幽雅环境的象征,吸引了权贵、文人甚至是外国人来此游乐。清末日本人曾有观察:“因后苑假山,温室花卉宜游、宜观,故外国人好来此参观游览。”[18]
与白云观宫观拓展相伴随的是白云观香火、观产的增多。乾隆末,两淮盐政全德,“助产岁得息六百金,合志旧日所出,可千数百缗”[19]。九皇会是白云观最重要的香会之一,“自道光九年到十四年,合集黎金千五百有奇,前因修葺斋堂;糜钱五百千正,置地东安县郊河地一顷,价七百三十千正,每岁得租钱五十千正。”这些香火钱来自何方呢,碑刻表明是来自京城等地的62家商号,其中捐资最多的是源升号钱一百四十四千[20]。道光二十四年(1844)善信王洪礼创建真君殿后,“复捐钱五百二十二吊,置地八十七母[亩],岁收现租钱五十二吊二百文,作为真君殿永远香火之资”[21]。
嘉庆年间,白云观最大的施主乃是蔡永清,除前文所提到帮助拓展宫观外,蔡氏还屡次为白云观传戒捐助。嘉庆十三年(1808),蔡氏“捐白金六千为传戒费,以制钱千缗助庄田一区”。嘉庆十四年(1809),“入白金二千,又助梅厂庄园一区,计地四十五顷。又存质库白金八千,权子母为本观每岁传戒经费”[22]。正是在信众的支持下,晚清白云观逐渐积累了丰富的观产。据光绪十二年(1886)的碑刻可知,仅白云观的下院玉清观就有“田产四十四顷七十八亩三分”[23]。
除了普通百姓外,京城其他宫观的道士也多次捐资白云观。阜城门内南顺街吕祖宫住持叶合仁“俭省白金五百二十四两,典置香火地一顷二十三亩半……与法徒王教惠及徒孙杨永吉、陈永兴等面议,愿将此地施与常住,其历年所得租粮,永作皇经坛每日香烛小食之费。并历年正月九日玉皇诞辰;二月望日老君诞辰,两次香供道场之需”[24]。光绪七年(1881)三月叶氏将地契送至白云观。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在王教惠任吕祖宫住持后,又出积蓄钵金二百两,“仍作皇经坛及正二月两次香供道场之资,俾伊光师之善念,可以传绪久远,世世不替也”[25]。
同是吕祖宫住持叶合仁,在光绪九年(1883)率徒王教惠等人“将积蓄钵金二百两,并与常住,照料生息,以作每年七月十五日济孤施食法船纸码香供等项费用”。白云观恐其日久遗失废弛,故于光绪十年(1884)冬,“在京南固安县地方,自置田地一顷,从中按价,拨出地一顷七十八亩,按钱租,每亩得制钱四百二十四文,每年共得租钱七十五千六百八十文,以作永远功德之费。叶公前施地亩,永奉神明香灯。今又施银两,以济十类孤魂,真可谓普结善缘”[26]。
从已知资料来看,晚清白云观最大的捐资者,实乃刘素云也。《刘素云道行碑》云:
刘素云炼师法篆诚印,直隶东光人,自幼好善,儒道兼优,昄依在十九代方丈张耕云名下为徒,曾为本观护坛化主。计自同治辛末(同治十年,1871),募捐五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三百余人。期满张师南归,继之者为豁一孟师,调度有方,诸臻妥善。孟师复逝,于是众议举高云溪为住持。云溪为素云同戒至契,幸蒙素云竭力护法,于壬年岁(光绪八年,1882)复募七千余金,为衣钵口粮传戒费,受戒者四百余人。甲申岁(光绪十年,1884),又募捐九千余金,为传戒费,受戒者五百余人,以至修屋建舍,刊版印经,种种不可枚举。庙事当为家事,道侣视如手足,观中各事无不兴废修整,是素云之功德,已足昭垂永久。兹又虑及燕九、九皇祖师两圣诞、香供淡泊,敬约善士张诚明、张诚武以及内观信官助善者百余人,建立长春永久供会,起于光绪八年,每岁香供之费,约需三百余金。至丙戌岁(光绪十二年,1886),会中积蓄无多,素云恐失其传,又自捐三千二百六十金,购买昌平州地方上泽田十五顷有奇,每岁收租三百三十金,交本观为业,以为永远作为二会香供灯果之资,以垂永久。[27]
刘素云对白云观的贡献有多大?单纯捐资而言,光绪八年、光绪十年两次传戒捐资一万六千余两,燕九、九皇圣诞除发起长春永久供会外,另捐三千二百六十两。光绪十六年助修云集山房一万五千两。不加上其他的刊版印经、重勒碑刻等费用,仅上合计三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刘讯教授总结刘素云在1871年至1890年间一生捐资寺庙银四万四千二百六十两,其中白云观的捐资就占了绝大部分[28]。
对于白云观以及全真龙门而言,宫观拓展、庙产、香火、捐资的增多是繁盛的物质条件,它奠定了白云观晚清频繁传戒、扩充龙门声势的可能。
对于白云观的传戒活动,众多研究强调王常月改变全真秘密传戒为公开传戒,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白云观开坛传戒,受戒弟子多达千余人。对此有学者曾有研究表示怀疑[29]。事实上,白云观有记录的大规模的传戒始于嘉庆十二年(1807)。根据高万桑的最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在1807-1908年间,张合皓传戒1次,弟子108人;张教智传戒11次,受戒弟子925人;郑至祥传戒3次,戒子246人;吕永震传戒1次,戒子10人;张圆璿传戒4次,戒子633名;孟永才传戒3次,戒子 332名。在1881年继任白云观住持的高仁峒,在任内传戒4次,戒子高达1599名![30]刘厚祜根据所阅白云观所藏资料曾统计自嘉庆十二年(1807)起,至1927年陈明霦最后一次传戒,白云观先后传戒31次,受戒道士5702人[31]。高仁峒一人所戒徒众竟略近民国以前有记录数字的三分之一!即便是在全国全真丛林中,高仁峒以及白云观的传戒记录也是最高的。
众所周知,传戒是一项耗费巨大的活动,为何晚清白云观能实现传戒的常态化,尤其是高仁峒为何有如此惊人的传戒记录呢?正是有蔡永清、刘素云富有信众的捐赠,白云观能维系传戒活动。这些信众中,不仅仅有普通的善信,如设立九皇会的京城62家商户,吕祖宫住持叶合仁等,还有诸多官宦世家。通过碑文我们发现有完颜崇实家族,有重修吕祖殿的诰授二品命妇董母素霍拉氏家族[32]。
晚清全真龙门的繁盛还体现在霍山派的新创。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刘素云不仅仅是白云观的重要护法,他同时也是龙门霍山派的实际开创者。
刘素云,原名刘多生,法名刘诚印,道号素云,又号符合子,山东即墨人,明季迁至直隶东光县。其履历在《素云刘先师碑记》载:
师讳诚印,道号符合子,其先世山东即墨人,明季迁直隶东光县……庚戌年以故游京师,遂家焉。嗣以才识见知于怡亲王,因得名达天庭,诏入内侍,赐名增禄,又字德印……戊辰因奉差至白云观,适南阳张律师阐教观中,一见相洽,殷勤展拜,执弟子礼甚恭,此师皈依道教之始也……己丑年始授总管六宫事务之职嗣,即屡邀旷典,如园亭骑马乘舟回寓、疾时加赐黄金药品皆异数也。甲午恭遇万寿庆典,恩赏三品顶戴,三代以师贵,师益矢寅畏敬慎,将事终始不渝。[33]
据《素云真人道行碑铭》的记载,刘素云在同治七年(1868)入白云观,拜张圆璿为师,同治十年(1871),刘氏与高仁峒为同时受戒。由于对白云观的多次捐资,刘氏受到其师张耕云的赏识。光绪初年刘素云开创了“龙门岔支霍山派”,尊张圆璿为该派第一代宗师,刘素云本人则为第二代宗师,从此,太监有了自己的道派。霍山派的开创,扩大了龙门的声势,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刘素云、李莲英等太监与白云观的密切联系。王见川的精彩研究表明,由于刘素云的得宠,包括内务府等不少清廷官员乐意与其交往。在刘氏的带动下,诸多太监加入白云观成为信众,在光绪十二年(1886)的《长春永久圣会内廷会首》中,以刘素云、张诚五位引善总计62位内廷权监入会,其中就包括以道名“李乐元”入会的李莲英[34]。
在本文看来,晚清白云观以及全真龙门声势高涨的重要表现还体现于白云观历史认同的形塑方面,其中刘素云的重勒碑刻乃是重要的表现。
为何要重勒石碑呢?刘氏自言道:“白云常住,为长春祖师阐教之所。祖师生当于衰微之际,独开法统,力转鸿钧,伟烈丰功,实创玄门为未有。”可惜数百年来,“庙额数易,殿宇频增,碑志森如林立……特惜世远年湮,旧碑悉归旧碑磨灭”[35]。孟豁一住持白云观时慨然以重勒为自认,惜未遂愿即逝世。张圆璿继任住持后,嘱咐素云曰:“古人已往沧桑迭变,举功德事业,岁月所不能留者,悉以碑志载其真,而听其湮没可乎?汝性情春笃,乐善不倦,见义比为,他日能成孟公之志者,非汝而谁?”[36]正是在其师的勉励下,光绪十二年(1886)刘素云在同高仁峒以及其门下弟子的商议后,择最紧要之碑重勒。据小柳司气太著《白云观志》记载,刘素云捐资重勒了《白云观重修碑(正德元年原建)》、《长春邱真人道行碑(正德元年原建)》、《白云观重修碑(嘉靖年间原建)》、《重修白云观碑记(康熙四十五年原建)》,新立《罗真人道行碑》、《重勒诸碑记》、《昆阳王真人道行碑》、《七真道行碑》等。除了刘素云勒建的碑刻外,晚清高仁峒等人也勒了相当数量的石碑。这些碑刻从白云观的重修历史、重要善信义举、邱处机等神仙事迹等不同侧面强化了白云观的历史认同,从而在白云观以及全真龙门历史上扮演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白云观与晚清政治
早在雍正时期,白云观道士与政治即发生了联系,白云观道士贾士芳自称长于疗病,后承蒙雍正帝之召见,岂料因治疗中口诵经咒,并用以手按摩之术。“语言妄诞,竟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听我驱使等语”,贾氏遂被下狱[37]。此后,乾隆帝虽有发内帑重修白云观并曾有诗留念。但是,只是在晚清,白云观与政治的关系变得极为密切,甚至诡异。
晚清白云观与清廷政治发生联系,关键人物乃是刘素云。《素云真人道行碑铭》载:“南阳张真人传戒白云观中,公适因公至观,遂执弟子礼焉。”[38]刘氏去白云观所处理的公务实际上是料理慈禧太后之母“皇姥姥殡”事。据《太上律脉源流》记载:张圆璿“庚午(1870)再请传戒,时值皇亲照公府太夫人灵寄观中,师为虔诵《血盆经》。一藏百天之久,靡有怠容。蒙慈禧皇(太)后,恩赐紫袍玉冠,揖金助坛开大戒场,伯子公侯,接踵而来,请谒声名,播于远方”[39]。在高仁峒继承了白云观住持之后,由于与刘素云为同戒戚友的关系,高仁峒与慈禧以及李莲英等宫廷太监关系日益密切。野史、小说等各种史料对高仁峒勾结内廷、卖官鬻爵、同俄人勾结等恶行屡有生动的描述[40]。
高仁峒如何交通宫禁呢,各种史料均强调了高氏与内廷权监的密切关系。《清稗类钞》曾云高仁峒“与总管太监李莲英结异姓兄弟,进神仙之术于孝钦后。孝钦信之,命为总道教司”[41]。《北平旅行指南》也指出“阉宦如李连英小德张辈,皆其朋党”[42]。通过与刘诚印、李莲英、崔玉贵等内廷权监长久的密切联系,高仁峒甚至对慈禧均有较大的影响力。金梁曾记载高仁峒曾献慈禧金丹驻颜:“高老道,白云观主持也。与李莲英有连,能通声气,奔走者争集其门。高讲修炼,谓有点金术,问其秘,终不言。或曰:‘此能富贵人,不较点金胜耶?’高尝进金丹,时自诩曰:‘李总管献何首乌,其功不小,然亦金丹力,故太后老而不衰,能驻颜且健步也。’”[43]
由于高仁峒与李莲英等内廷太监结成朋党,且又受到慈禧信任,因此“卖官鬻爵之事,时介绍之。于是达官贵人之妻妾子女,皆寄名为义女”[44]。高仁峒喜交游,除太监外,高仁峒还同清廷权要关系要好。《小奢摩馆脞录》称由于高云溪为媒介,因此白云观为晚清卖官鬻爵之地:“当时如荣禄、奕劻、载恬者,皆与之有旧。高亦出入邸中,恬不为怪,都中人为余言,高道士正月二十曰寿辰,凡王公百官以及优伶隶卒,咸往庆祝,并有俄国商人,及太监诸色人等甚伙,毂接肩摩,岁以为例。则是当曰权势之煊赫,至今犹可想见矣。”[45]
《北平旅行指南》曾提到由于朝中权贵、宫中内侍,多寄名观中为弟子,兼以高氏与李莲英为朋党,“于是外省官吏,奔走其门。真[争]相结纳,视为终南捷径。高则暗操陟黜之权,颐指如意,一时声势煊赫,门庭如市”[46]。民初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在《清朝秘史》提到晚清拟改革内阁官制,不料忽被推翻,改从州县入手。为何有此反复,原来是那些唯恐大权旁落的要员走了高道士的门路,使得慈禧改了主意。
虞公编著的《民国奇闻》有《白云观道士》称高仁峒在晚清时期声势暄赫,炙手可热。“与朝贵通声气,督抚入京,且敬礼之,莫敢与抗”[47]。《都门识小录》记高道士一则史料生动地渲染了高仁峒的显赫权势:
白云观(西便门外迤西路北)高道士,今已羽化,供职上清矣。稽其生平功行录,实以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者也。观奉长春真人,正月十九日,真人诞辰,都中达官贵人、命妇闺媛,皆趋之。礼真人者,必拜高道士。言应酬者,遂以是日为高道士生辰,拜时或答或否。答者必其交疏,或名位未至者也;若直受之而不报,则顶礼者以为荣……比来都客为述高道士事,乃知黄冠中其有此不可思议之人物也。客曰:“往者吾就道士谈,旋有一人来,与道士最稔者。道士谓之曰:‘昨有某君属予为地道,欲得海关道。’余谢之曰:‘且慢,今朝廷方征捐于官,海关缺肥,监司秩贵,属望奢,恐所得不足以应上求,恁可犯不着也。’此人曰:‘仆有友某君,以知县分发山东,闻师父与中丞有旧,欲求一八行书栽培可乎?’道士欣然曰:‘此易耳,中丞新有书来,疏懒未及复,复时附数语足矣。’他日遇道士于南城酒肆。谈次,道士语一人曰:‘某侍郎之女公子明日出阁,予几忘之,适前日侍郎之夫人来谈及,匆匆不及备奁物,即以箧中所藏某总管贻我缎二端,乃大内物,总管所受上赐者,又以某总管赠我珍物二事,亦御赐品,备礼而已。’”此皆客述道士言。[48]
高仁峒的政治影响力不仅在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也发挥了不太光彩的作用。蔡鸿生教授多年前曾利用日人资料发现高仁峒曾允许华俄银行理事璞科第在观内居住[49]。《庚子国变记》也提到璞科第因高仁峒介绍因得以认识李莲英。叶恭绰曾回忆说:“前清与帝俄所订喀西尼密约,世皆传为李鸿章所为,其实李只系演出者,其编剧导演固由帝俄,而被动主体则为西太后;从中促进和穿插为李莲英与璞科第,则世人知者不多也。李与璞科第之联络,实由西郊白云观高道士为媒介。璞科第乃一国际侦探,其与高因何结合,不得而知。”[50]
最近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的研究证明了以上野史、笔记并非空穴来风,高仁峒确实是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日人高尾亨的1907年的机密报告强调通过高仁峒,“可了解李莲英以及宫中的诸种情况,以及二、三种政府各部门的内部消息”。尽管高尾声称高仁峒不通时事,“所谓政界里面的消息,不可期正中要害,且其所言既无系统,又欠缺要领,内容颇难判定。尽管如此,高仁峒的谈论,亦可作为参考”。谈话的内容要点“皇太后之近况”、“李莲英之势力”、“关于庆亲王等之消息”和“高方丈之势力”等各部分。在谈到跟李莲英的关系,高仁峒介绍李莲英、刘素云等均为道教信徒,还详细介绍了各大官员如何给李莲英行贿的细节。报告证实,高仁峒深得慈禧信任,各中央以及地方大员均寻找机会接近高氏:
白云观是中国道教之总本山。其方丈高仁峒,曾于团匪事变两宫蒙难之际,经李莲英斡旋,在太后身边伺候读经。太后由此皈依该方丈,年年赐该寺两百两之布施,又常有其他物品赏赐,可见白云观与宫中之关系尤为密切。高方丈具备既可接近太后之身份,同时又与李莲英关系密切。在北京的各中央大员,均在白云观寻找机会接近该人。那桐、徐世昌、荣庆等时时以该处庭园广阔清雅为名,在白云观举办宴会,并以布施为名,向高方丈赠送数百金,以求其欢心。[51]
白云观确与内廷关系密切,有学者强调高仁峒同慈禧的勾结一直延续到他们去世,证据是清宫《海晏堂等处陈设木器账》:光绪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906年11月15日),白云观进贡木根福寿三多盆景等摆设十件;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一(1907年11月6日),进贡海晏堂陈设,硬木福禄寿三星等九件[53]。
据高尾氏的观察,高仁峒与璞科第的关系“仍一如从前。该公使通过高方丈,探听宫中动向,然后又在暗中有所运动。”孔祥吉、村田雄二郎还提到日本对白云观所作的情报工作,如以日本驻华内田公使的名义,向白云观提供维修殿宇的经费一千两,并由此换取到了高道士以及大内太监的欢心。高道士传达李莲英的感谢话说:“日本和他国不同,共奉儒佛之教,从而理应对道教信仰甚笃。”对于日方介绍宫廷太监的请求,高道士同意将李莲英和崔玉贵介绍给日方,并说他与太监的关系“全属私交,与公事毫无所涉”。此外,日人还要求在白云观里购置公使“别墅”,如同璞科第的“大俄国璞寓”,不料被高氏婉言谢绝。
三、雅士 VS俗人:高仁峒社会生活略议
在宗教史与政治史中,高仁峒是神仙中人兼政治中人,那么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看,高仁峒既是雅士,又是俗人。
高仁峒是什么样的出身?高仁峒在《云水集》中曾自叙身世:
予姓高氏,实生于济宁,十五丧父,已厌尘情,又历四载,益叹浮生,行年十九,遂访赤松。辞我老母,别我弟兄,掉头东去。半夜揣行,如人接引,直上云梦,吴师座下,得接宗风,常加警觉,严定课程,返听收视,开觉通灵,省棉节食,化怒息争,藉得真趣。[53]
然而据《清稗类钞》云高氏则是因失金而遁入道观:
尽管入道缘由社会上略有非议,但是不可否认高仁峒在诗书画方面还是颇有志趣、成绩与文采的。高仁峒在光绪十一年(1885)左右刊印了《云水集》(上下册),辑录自己修道心得、偈语、诗歌等。从白云观历史来看,清代白云观道士中除王常月外,仅高仁峒留有文集,甚是难得。给《云水集》作序的“青渠散人李湍遇”曾赞高仁峒系“孝友中人”。高仁峒虽是道士,但亦推崇三教融通。其曾作诗赞孔子:“大成至圣启后承前,仰之弥高鐟之弥坚。心传一贯道有真诠,万世师表洵无间然。”[55]赞释佛曰:“弗我弗人佛自有真,去来现在视此根因。晨钟暮鼓警觉凡尘,清净世界广大精神。”[56]在文集后记中,高氏还推重“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修身为本十六字心法”[57]。这些偈语诗文的文采如何,高氏曾提到一位来观“先生”的感觉,后者称“此集文字虽佳,言空言悟见解却差”。高氏敬谢之特附文集后以备“同志者览”[58]。《北平旅行指南》提到他“机警善辨,且工绘事”[59]。在流传至今的高仁峒赠“莲舫弟台大人雅属”的对联中,高氏“太史公文五岳高,小将军书三山远”的书法颇有功力,且这一对联也颇为工整。高仁峒的徒弟陈明霦在《云溪道人吟》中赞其曰:“云成雨露满长天,溪上新花意快然。道有三端德智体,人人学此胜登仙。”[60]
在1900年义和团事变中,高仁峒劝募华俄银行总领事璞科第等人筹集巨款,购置米粟于白云观,在城区八处设粥厂施粥,“兼溥御寒冬衣之赐”[61]。光绪二十八年(1902),西便门内外二十一村勒碑赞誉其功德:
高云溪方丈,以东州之贤裔,广南华之真传,主教数十年,善行不可枚举。而庚子岁保卫村邻,筹募振济,尤有令人讴思难忘者。当联军甫至,京外震惊,方丈坐镇雍容,推诚联络,卒化嚣竞为礼让,民得安堵,又募劝华俄总领事、李大善士,桥梓设厂施粥,全活无算。近村老稚得免镝沟壑之虞,此皆出方丈之赐也。都人士睹承平,不忘危难,特追述方丈之义,举诸贞珉以垂永久。庶丰功盛德,益使闻风兴起焉尔。[62]
在晚清庙产兴学的倡导中,高仁峒也有相应之举。光绪三十二年(1906)闰四月二十九日高仁峒请办初级小学堂,特向学部禀请恳准立案。对此学部批到:“据禀已悉。该住持热心兴学,深堪嘉尚。惟堂中教习监学何人,应开具姓名籍贯,注明担任何项学科,并将所招学生名册呈部备查,再行核办。”[63]对于预定五月二十四开学的白云观道教学堂,《大公报》赞称筹画周备,所有办法“颇称完善,事当创始,该道士亦可谓煞费苦心矣”[64]。五月初八日,在白云观住持高仁峒呈明学堂教习、学生姓名籍贯清册请存案后,学部批称:“据禀及所呈清册名册均悉所列学科尚属完备,应准立案。再候本部派员查视可也。”[65]
在社会交往方面,高仁峒乐意与社会各色人物交往,对内交往的不仅有内宫太监,还有中央、地方大员。在对外方面,既有俄国人璞科第,还有日本使馆秘书高尾等人。此外,作为一个“世外高人”,高仁峒还极乐意与士人交游,并常在白云观内设宴。翁同龢日记曾记载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七(1892年3月5日)豫锡之在白云观请客,翁同龢应约的情形:“诣白云观豫锡之之约,荫轩未到,到者五客:荣仲华、李兰孙、谭文卿、祁子禾及余也。方丈高云溪,山东济宁人,治蔬菜尚佳,亦俗人耳。有姚道人者,能画,今往彰德。”[66]豫锡之乃晚清名士豫师。荫轩是徐桐,其他四人分别为荣禄、李鸿藻、谭钟麟、祁世长,皆是清廷大员。正是如此,高仁峒不仅同意在观内设宴,他本人以及能画的“姚道士”出面陪同。虽然高仁峒“治蔬菜尚佳”,但终究难脱翁同龢“俗人”的评价。高仁峒“俗”在哪里?翁同龢没有明言。黄钊在《帝京杂咏》中也有表达过道士的俗气:“但饶寡欲与清心,要语还征道行深,一事真人难免俗,白云观主说烧金。”[67]
本文猜测或是高仁峒的世俗言行举止导致被翁同龢这一帝师视为俗人。前述日人高尾氏在同高仁峒的交谈中,认为高仁峒“本人不通时事,所谓政界里面的消息,不可期正中要害,且其所言既无系统,又欠缺要领,内容颇难判定。”[68]本人以为高仁峒不通时事,见识不高,或可被视为俗人。但是,高仁峒被视为俗人重要的原因或是他的俗人的生活方式。
高仁峒曾作《戒酒》偈云:“酒沉迷性情乱,耗气耗神耗寿。”[69]但是多则史料记载称高仁峒喜到城内某酒家聚会:“南城酒肆,即杨梅竹斜街万福居。道士入城,每以是为居停。其肆东偏一院,境颇幽寂,凝神炼气,或无妨焉。故客欲以杯酒结道士欢,及道士饮人以酒,悉于是肆。肆善治鸡丁一品,其烹割术为道士秘授,肆人名之曰‘高鸡丁’云。”[70]
根据除了饮酒吃肉破戒外,高仁峒或耽于女色,并为人所诟病。《白云观道士之淫恶》一则野史,内云:“凡达官贵人妻妾子女有姿色者,皆寄名为义女,得为所幸则大荣耀。有杭州某侍郎妻绝美,亦拜峒元为假父,为言于慈禧,侍郎遂得广东学差,天下学差之最优者也。此不过举其一端耳。举国若狂,毫无顾忌。观中房闼数十间,衾枕奁具悉精美,皆以备朝贵妻女之来宿庙会神仙者,等闲且不得望见之也。”[71]民国时期,贾文岛在《白云观纪游》中提到白云观三清阁上有很多密室,晚清时期发生了诸多风流韵事,每到新正,“阁上满是北地胭脂,南朝金粉,髫影钗光,徘徊簪际”,达官贵人以及各王公的姬妾常有花样演出,而高仁峒就是此中的无冕王。在游至火德殿附近,作者发现一密室,提到:“听说此处便是仁峒道人的销魂窟,当年许多王公的姬妾,秘密进出,曾闹过几椿风流笑话,终因仁侗手腕灵活,没有发生惨剧,但街头巷尾,已都传为美谈。”[72]在《北平旅行指南》中,作者介绍了高氏晚年耽于女色的确证:“高晚年酖于女色,狎一孀妇,藏春于宣内某巷。热中者,乃又趋奉于孀妇之门下,以冀代为吹嘘,高病危时,犹奄卧于春帐粉被中,及舁之观内,逾日气绝。”[73]
2017年共有468门课程入选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本科教育课程)。其中涵盖《系统解剖学》《局部解剖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6门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而同样属于重要的医学基础课程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却榜上无名,基于此,建设高质量的《组织学与胚胎学》在线开放课程是组织学与胚胎学教学工作者的使命。
或是翁同龢了解高道士的如此行为,方有“俗人”的评论吧。
四、白云观与晚清社会生活
康豹教授在梳理西方学界中国社区宗教成果时,强调宗教在地方社会以及城市中的重要性[74]。在回答近代城市为什么需要宗教这样重大问题时,根据新发现的佚名日记,赵世瑜教授指出,除了扮演礼仪秩序的空间角色外,寺庙和宗教主要是满足人们日常的精神需求的工具。在民初的日常生活中,寺庙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不一定与信仰有关[75]。韩书瑞在 Peking Temples andCityLife(1940-1900)一书中精彩地展示了北京寺庙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如寺庙成为城市民众聚会或加强联系的重要场所,就整个城市而言,以寺庙为基地的一些活动如庙会、娱乐、慈善、政治活动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本文将以白云观为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示寺庙在社会文化中的重要角色[76]。
根据明清以来的竹枝词等丰富的地方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全真祖庭的白云观首先在宗教方面为道士以及城市民众提供了信仰的场所;对城市民众而言,除了宗教信仰的需要外,白云观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本身作为纪念邱处机的燕九节也从宗教节日扩大成为一个城市的大众节日,在这个空间中,娱乐、庙会、交游等活动频繁发生,城市中的各阶层,从官员、士人到普通民众,都曾在这个空间中积极地活跃着,正是如此白云观成为北京明清社会文化中的典型之一。
为何自元代以来白云观虽屡次顷坍,却又能受到眷顾、不断得以重建?最重要的因素或是白云观以及全真道教的重要宗教影响力。正月十九之白云观、元旦之厂甸、上元之观灯同称“上林盛举”[77]。“燕九节”之称始见元代熊梦祥著《析津志》:“正月一日至十九日,都城人谓之“燕九节”,倾城士女曳竹杖,俱往南城长春宫、白云观,宫观蒇扬法事烧香,纵情宴玩以为盛节”[78]。由于藏有邱处机的遗蜕,白云观成为全真道教的祖庭,也正是由于有关邱处机的神话,正月十九,由丘处机的生日而演变成为“燕九节”。
燕九节首先是宗教庆典,正是由于邱长春会化身来观的传说,使得道士以及信奉道教的民众纷纷聚集于白云观,在明清时期尤为兴盛。明清的文集以及竹枝词生动地描述了道士以及信徒们在燕九节会神仙的概况。明代刘若愚《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曾称正月十九日僧道辐辏,不论太监还是权臣,凡好黄白之术者,均赴白云观游览欲图能够得到成仙的丹诀。清代的方文在《正月十九日龚孝升都宪社集观灯》诗中写道:“京师胜日夸燕九,远近黄冠会白云。”民国初年李黄在《北平竹枝词》中形象地刻画了道士群集白云观的景象:“道德一经谁耐穷,白云观在白云中。缤纷满地黄冠影,若个青牛独自东。”[79]来会神仙的道士或本身居住在京城,也可能来自于全国各地,明代的一则史料曾称是日“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状貌诡异,衣冠瑰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中贵人多以是日散钱施斋。”[80]道士们在这一天会神仙,也期盼能有缘成仙。孙雄在《燕京岁时杂咏》写到“白云观里会神仙,万古长春额尚悬。三五黄冠廊下坐,私期鹤驭降乔住?”[81]
除了道士们会神仙,京城民众也趋之若鹜。会神仙不仅是纪念邱长春以及宗教信仰,更有祛病延年的妙处。于鸿在《燕九竹枝词》就曾写道:“才过灯节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夜内必有真仙降,缘遇却病竟延年”[82]。晚清丁立诚在《游燕九》的竹枝词中亦云:“岁岁燕九真仙临,有缘遇之凡骨换”[83]。为何能祛病延年呢?因为传说真人会授以神仙秘方,如还魂丹:“白云观里闹无端,走马何曾缚佛鞍。见说游仙来往熟,有谁拾得还魂丹。”[84]
正是出于祛病延年的实际考虑,民众期待能够会到神仙。一首竹枝词就表达了这种期待:“暂出西郊十里游,白云庵畔小勾留。年年燕九神仙会,知有真仙来降不?”[85]在未能遇到神仙的时候,感情则极为失落。孔尚任写道:“春宵过了春灯灭,利有燕京燕九节。才走星桥又步云,真仙不遇心如结。”[86]
是否有人遇到神仙呢?翻检史料,发现清人俞蛟的《春明丛说·白云观遇仙记》生动记载了康熙初年士子陈谷幸运地遇到了真的神仙,可惜由于自身白璧微瑕却错失良缘的故事。现实中,民众没有遇到真的神仙,倒是遇到不少假真人。孔尚任的竹枝词写道一个乞丐被误认为神仙的有趣案例:“金桥玉洞过凡尘,藏得乞儿疥癞身。绝粒三旬无处诉,被人指作邱长春。”由于根据传说真人下凡,化身千般,不少也藉此谋利:“才过元宵未数天,白云观里会神仙。沿途多少真人降,个个真人只要钱。”[87]
怎样在白云观里会神仙?有史料提到“男女至观焚香持斋彻夜达旦”[88]。有的为了等待神仙,则留宿观中。由于会神仙的时候男女混杂,谑浪无忌,有人视为不善之风俗。光绪十一年(1885),御史张廷燎奏请旨饬下地方官严查白云观倡为神仙之说及夜间容纳妇女:
查彰义门外迤西之白云观,每年正月十五至二十日等日,兴举大会,男女杂沓,举国若狂,首善之区,已不应有此恶俗。尤可异者,有会神仙之说。于十九日夜,妇女入观,于栏房屈曲中暗坐一室,即见神仙。光天化日之中,岂有此怪诞不经之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若不亟行禁止,诚恐恶习相沿,日久愈难挽回。相应请旨饬下该管地方官严行查禁。嗣后如再有倡为神仙之说及夜间容纳妇女入观者,从重惩办。至京城内外烧香赛会,有与此相类似,亦随时查禁。庶足以端风化而杜妖妄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89]
虽然清廷同意了张氏之奏请,令随时查禁以端风化而正人心[90]。但是妇女留观的现象并未有所改观。晚清时期,在高仁峒住持下,为方便朝廷权威的妻女之来宿会神仙,特在观中数十房间准备精美寝具。前文述及民初游记中记载高仁峒的风流笑话即是与会神仙密切相关。
尽管有关高仁峒的艳史并无确证。但是会神仙导致男女混杂有碍风化的事并非空穴来风。民国时期,有人归纳了迷信与不迷信的人两类人会神仙中举止。在正月十九日晚,迷信的和不迷信的男女,或富室妾姬、纨绔子弟,或下等地痞流氓,“率宿于观中,彻夜不眠,有的在床上辗转反侧,有的在各偏僻地点藏躲,期与神仙一晤。”有些老道甚至故意假冒神仙,“以钓众愚”。对于不迷信的男女,有观察者称他们抱着“醉翁不在酒”之意思,每每发生了风流趣闻,成就了男女的好事[91]。尽管如此,直到民国时期,留宿庙内会神仙,仍是民众趋奉之举。《首都杂咏》曾云:“白云观里会神仙,绿衣红男席地眠。我不求仙占吉利,窝风桥下掷铜钱。”[92]这首竹枝词不仅提到了男女正月十九晚上席地而眠会神仙,他们可能并非真的想成仙,更多的则是期盼吉祥。作为求吉的另一有趣方式则是打金钱眼。虽然有人认为这不过是白云观老道藉此敛财的手段,民初一首竹枝词感叹民众的愚昧:“堪笑愚民剧可怜,白云观里打金钱。世间尽是虚浮物,十八何曾有神仙。”[93]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百姓纷纷小试身手,因为根据白云观道士的说法,若能打中,可博得一年之吉利。汤陶厂在《京市旧历新年竹枝词》写到:“更有美人占幸运,争舒玉臂打金钱。”[94]此外,点星宿也是当时民众乐意参与的活动,尤其是对未婚女子而言,更有深意。有人观察到,女子在游观中“自按芳龄,就所司岁深,虔诚进香。名曰点星宿。樱口喃喃,殆皆祝早得如意郎君,拯登彼岸耳。或迳叩其意,则含情微诉,欲得星宿作月老,虽为谄词,亦殊动听”[95]。
会神仙、打金钱眼等活动使得燕九节具备了厚重的道教特色,但是民众积极地参与会神仙,使得燕九节成为北京最重要的娱乐节日之一,而白云观在燕九节中也成为大众逸乐的重要空间。
对于文人而言,寺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同时也是重要的雅集空间。元代以来,白云观作为京城重要的一处胜迹,不少文人雅士时常前往游乐、怀古,留下不少诗文[96]。一首竹枝词写到:“燕九嘉辰著典仪,崇楼杰阁有清规。栖霞羽士长春子,遗亭堪哦竹垞诗”[97]。在《燕九竹枝词》序文中,作者在概述燕九的盛况后,提到士人看重燕九的重要客观原因:由于京师初春严冷,只有燕九之游略有昔人晦日出行的遗意[98]。正是如此,陈健夫召集孔尚任、袁启旭、蒋景祁、陆又嘉、王位坤等人在燕九节游览白云观,九人“开筵茅屋”各为竹枝词十首。在孔尚任等人后,晚清民初文人在游览中,也留下了不少有关白云观的竹枝词。在文人的记载中,在燕九节中,不仅“远近道流皆于此日聚城西白云观”,“游人纷沓,上自王公贵戚,下至舆隶贩夫,无不毕集,庶几一遇真仙焉”[99]。
资料显示,白云观的逸乐充斥着观外观内,娱乐的方式则是多姿多彩,参与的民众更是形形色色。
清代,对于王孙公子、富商巨贾而言,走车走马乃是一样耗材显脸的荣事,对普通观者来看,也是好玩的乐事。晚清民国的不少史料、画报都提到白云观赛马的盛景。晚清《克复学报》曾记载1911年初(辛亥正月)王公亲贵在白云观驰马。民国时期的《闲话西郊》中就写道:“白云观西北角门外,有南北大道,昔为赛马处。”[100]晚清京城赛马均有一定处所,元旦自燕九,即“在白云观西北隅南北大道上”。所谓“赛马”乃是“走车走马”,而非普通的欧式赛马。所谓走马者,是豢养良驹,施以调教;走者,“非颠非跑,乃四蹄循序起落,一前左蹄,二后右蹄,三前前蹄,四后后蹄,周而复始,其疾如风,不颠不簸,细腻平稳,尤贵乎长距离始终不变步度也。走车则以骡驾轻车,御者斜跨车辕,扬鞭而驰,疾如电掣,虽曰赛车赛马,并非相对比赛也。不过各自驰骋。观众遇稳而快者,掠面而过,彩声雷动,啧啧称赞曰,此某府某邸也,车马主任,面现德色,以是为荣耳”。据介绍,“先期,由操茶棚业者,合资平治道路,洒以清水,不使灰尘飞扬。又于大道两侧,支搭席棚,售茶兼营酒食业,赛马日则万人空巷,观者如堵”[101]。
孔尚任等人的白云观游乐正是伴随着“走马春郊”这一活动,宜兴人蒋景祈就留有“金帆绿帻富平侯,击毬走马幽凉客”[102]。直到民国初年,走马竞赛在白云观旁仍是极为热闹:“寺邻更有白云观,老僧语我仅里半。相戒徒步车众屏,未抵寺门已喘汗。寺中游女多如鲫(时日观中有神仙会,游女如云)。寺旁竞马尤繁赜(庙外竞马会,观者如堵墙)。方外素号清净场,喧闹乃与五都敌。尘氛我已八斗耻,笑尔一石犹不止。免俗且未能,无怪营营满朝市。”[103]伴随着富人的走马,一些权贵富人以及白云观在燕九节还特意施斋,救济穷困。明燕九节时,“中贵人多以是日散钱施斋”[104]。清末汤陶厂的《京市旧历新年竹枝词》亦云:“王孙走马著先鞭,富室施斋结善缘。”[105]民国时期一位对白云观庙会颇有研究的学者提到“在昔有不少富人等在此日散钱布施,动辄数万”[106]。在庙会期间,白云观也有发放大馒头的慈善活动。正是有施斋以及游人众多,不少乞丐也蜂拥而至,期盼有所收获。陈健夫在竹枝词中就写道“鹄面鸠形大道边,丐儿争取列侯钱。拦街不避青骢马,都道今年胜往年”[107]。孔尚任的《燕九竹枝词》亦曰:“秧歌忽被金吾禁,袖手游春真可惜。留得凤阳旧乞婆,漫锣紧鼓拦游客。”[108]
除了观者如堵的赛马外,庙内外的赛会活动仍是花样百出。明代吴宽有竹枝词曰:“京师胜日称燕九,少年尽向城西走。白云观前作大会,射箭击毬人马吼。”《帝京景物记》也提到十九日的活动有“弹射走马”。在庙会中,吸引游人的另外重要娱乐还有唱戏。孔尚任的竹枝词写道:“七贵五侯势莫当,挨肩都是羽林郎。他家吹唱般般有,立马闲看扌州戏场。”[109]陈健夫也描绘了戏场的生动:“锣鼓喧阗满钵堂,莺弹花旦学边妆。三弦不数江南曲,惟有啰啰独擅场。”[110]在戏场中,有的唱秧歌,有的唱花鼓“秧歌初试内家装,小鼓花腔唱凤阳”[111]。
在庙会中,儿童也赶来看热闹。在初春,趁着会神仙,小贩来卖纸鸢。谢文翘的《都门新年词》就写道:“春秋巧制各争妍,娉态殊形卖纸鸢。更掷金钱郊外路,白云古观会神仙。”[112]儿童买后,有的在庙外放风筝,可惜因天公不作美而恼怒:“结伴儿童裤褶红,手提线索骂天公。人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113]有小乞儿藏身桥洞被人误认为真人下凡,也有儿童挤满了酒铺的案桌。
京城各大庙的庙会也与商品售卖密切相关。如东西庙,“东西两庙按日开,男女老幼去又来。所售都是日用物,更有鲜花厂田栽”[114]。据观察,民国时期在白云观庙会上,商贩在观内多设席棚,“卖食物与玩具者最多,以小漆佛为最有名,游者多乐购之,藉留游观纪念”[115]。白云观的庙会中,吃的喝的也都很丰富。官、商、小民各有选择:“官吃东涞商吃泉,烧刀只赚小民钱。连秋黍贵无乡贩,醉汉不如庚午年。”[116]还可喝茶吃元宵“紫云茶社斟甘露,八宝元宵效内做。今日携钱忍饿归,便门不及前门路”[117]。庙会中,还有不少游客斗酒“拇阵狂呼燕赵客,醉中还说看长春”[118]。酒市中,有人“当垆争买洞庭春”[119]。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生动地描写了燕九节声色俱备、动静兼有的娱乐感:“车马喧阗,游人络绎。或轻裘缓带簇雕鞍,较射锦城濠畔;或凤管莺箫敲玉版,高歌紫陌村头。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归许多烂醉之神仙矣。”[120]
正是白云观悠久的历史,尤其是会神仙的传说,使得吸引了道士以及城市民众蜂拥而至,形成了民众广泛参与的燕九节文化。在这过程中,白云观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场所,它也成为京城精英以及大众娱乐的重要空间。
在这篇小文中,笔者尝试从多维的角度探究白云观在晚清社会中的复杂面相。从宗教史的角度而言,晚清白云观在拓展、高涨全真龙门声势方面颇有功绩,白云观的传戒步入正规与常态,白云观的历史与宗教认同得到了强化。从政治史的角度而言,白云观尤其是高仁峒发挥了超越道教的作用,不折不扣是一个“政治中的神仙”。从社会生活的角度而言,方丈高仁峒既是雅士,又是俗人,而白云观则是京城大众重要的宗教生活以及游乐场所。但从进一步精进白云观乃至晚清社会史的角度而言,本文仍有诸多思考的空间,期待学界能有更多的成果出现。
注释
①笔者的《安世霖的悲剧:1946年北平白云观火烧住持案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62期,2008年12月)、《1930年代北平白云观的住持危机》(待刊稿)两文对有关研究成果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感谢高万桑、王见川、刘迅教授惠赠他们的大著。
②刘迅:《政治中的神仙:高仁峒方丈与清末全真道在北京的眷顾和权利网络及宫观扩展》,见熊铁基、麦子飞主编:《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③⑥⑦⑧[19][22]蔡永清:《白云观捐产碑记》,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707页。
④民国时期,白云观监院安世霖著有《白云观志稿》,强调是王常月重修之力,并概述经过。参见刘厚祜:《白云观与道教》,《道协会刊》第6期(1980年)。在王常月署名的《重修白云观碑记》中,落款时间为康熙四十五年八月,小柳司气太、李养正均指出此碑或有问题,因为根据完颜崇实等撰《昆阳王真人道行碑》,王氏卒于康熙十九年。
⑤《乾隆御制重修碑记》,李养正编著:《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06页。
⑨⑩[11]长白麟庆:《重修白云观宗师庑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09页。
[12][21]《真君殿香火偈》,《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0页。
[13]高仁峒:《重修吕祖殿碑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21页。
[14]高仁峒:《重修吕祖殿灵感碑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22页。
[15][16][17]高仁峒:《白云观拓修云集山房小引》,《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23页。
[18]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第31页。民国初年,一位女生在游览白云观时,赞云集山房各景点“出风入雅”、“得圣之清”、“均有佳趣”(闽侯林德育:《京师白云观游记》,《妇女杂志》第3卷第4号,1917年)。
[20]张合智:《九皇会碑》,《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0页。
[23]高仁峒:《玉清观田产碑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7页
[24][25]高仁峒:《四御殿皇坛香火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22页。
[26]高仁峒:《中元济孤勒石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3页。
[27]《刘素云道行碑》,《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4页。
[28]Xunliu.Visualized Perfection:Daoist Painting,Court Patronage,Female Piety and Monastic Expansion in LateQing(1862—1908),p87.为何刘素云如此多金?王见川教授指出系其向江宁织造索取交差回扣以及放高利贷等因。参见王见川:《清末的太监、白云观与义和团运动》,《汉人宗教、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台北:博扬文化,2008年,第219-220页。
[29]尹志华:《北京白云观藏〈龙门传戒谱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2期。
[30]Vincent Goossaert.The Taoists of Peking,1800—1949,ASocial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Cambridge(Massachusetts)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p145.
[31]刘厚祜:《白云观与道教》,《道协会刊》第6期(1980年)。
[32]刘迅教授曾注意到晚清官宦长期以来对白云观的眷顾,参见Xunliu.Visualized Perfection:Daoist Painting,CourtPatronage,Female Pietyand Monastic Expansionin LateQing(1862—1908),pp.75-89.
[3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清稗类钞》“孝钦后乐与硬刘谈”生动介绍了慈禧对刘素云的宠信,参见《清稗类钞》(第1册.阉寺类),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2页。
[34]王见川:《清末的太监、白云观与义和团运动》,《汉人宗教、民间信仰与预言书的探索》,第221-224页。另张雪松在《清代以来的太监庙探析》一文中对霍山派的传承略作了介绍(《清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5][36]刘诚印:《重勒诸碑记》,《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718页 ,第 718-719页。
[37]《雍正朝实录》(卷98,雍正八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09-310页。
[38]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87册),第128页。
[39]中国道教协会研究室编:《道教史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95页。
[40]徐柯曾提到“京华僧道多交接王公,出入宫掖,以故声价至高”(《清稗类钞》第10册,第4874页)。除了高仁峒外,徐氏还提到了道光年间京城灵官庙女道士广真“交通声气,贿结权要,朝士热中干进者,日奔走其门,冀系援致通显,或师事母事之,勿恤也”(《清稗类钞》第10册,第4875页)。
[41][44][54]徐珂编:《清稗类钞》(第10册),第4874页,第4874 页 ,第 4974页。
[42][46][59][73]马芷痒著:《北平旅行指南》,张恨水审定,北京:新华书局,1938年,第9页。
[43]金梁:《光宣小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45]《清代野史》(第7辑),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285页。另《雪桥诗话》曾云高道士“颇通声气,西园谐价,多以白云观为初桄焉”。瞿兑之据此有诗曰“车马纷纷燕九节,西园谐价觅黄冠。”参见瞿兑之:《燕都览古诗话》,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47]虞公编:《民国骇闻》,上海:襟霞图书馆,1919年,第19页。
[48][70]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101-102页,第102页。
[49]蔡鸿生:《璞科第与白云观高道士》,《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
[50]叶恭绰:《中俄密约与李莲英》,《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51][68]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京师白云观与晚清外交》,《社会科学研究》2009年第2期。
[53]转引自林克光:《白云观的后花园》,见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34页。
[53][57][58]高仁峒:《云水集》(下册),光绪十三年刻本,第1页,第43页,第43页。感谢学友李在全博士的努力与帮助,笔者方可窥得此书全貌。高万桑、刘迅两位教授较早留意到《云水集》的重要性。
[55][56][69]高仁峒:《云水集》(上册),第24页,第24页,第35页。
[60]陈明霦:《白云集》,见《藏外道书》卷24,第15页。
[61]《粥厂碑记》,《新编白云观志》,第724页。
[62]《云溪方丈功德记》,《新编白云观志》,第725页。
[63]《白云观住持高仁峒请办初级小学堂恳准立案禀批》,《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第42页。
[64]“时事”,《大公报》1906年6月22日,第4版。
[65]《白云观住持高仁峒呈明学堂教习学生姓名籍贯请存案禀批》,《学部官报》第2期,1906年9月18日,第44页。
[66]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505页。刘迅、王见川、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等先生注意到了翁同龢的重要评价。
[67][79][81][82][84][85][87][92][93][94][97][105][113][115]雷梦水等编:《中华竹枝词》(第1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9页 ,第 317 页 ,第 387 页 ,第 397 页 ,第 113-114 页 ,第 17 页 ,第 156 页 ,第 403 页 ,第 419 页 ,第 405 页 ,第 342 页 ,第 405页 ,第 223 页 ,第 397 页 。
[71]张祖翼:《清代野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8页。
[72]贾文岛:《白云观纪游》,《中外问题》1936年第14期。
[74]康豹:《西方学界研究中国社区宗教传统的主要动态》,《文史哲》2009年第1期。
[75]赵世瑜:《民国初年一个京城旗人家庭的礼仪生活——一本佚名日记的读后感》,《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76]张紫晨的《白云观传说的演变及北京有关的风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以及段天顺的《竹枝词与北京民俗》(《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初步探讨了白云观与民俗之间的关系。
[77][95]陈莲痕:《京华春梦录》,上海:广益书局,1925年,第29页,第30页。
[78]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第 213 页 。
[79][80][10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第 901 页 。
[83]丁立诚:《王风百首》,见胡寄尘编《清季野史》,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36页。
[86][98][99][102][107][108][109][110][111][116][117][118][119]李养正:《新编北京白云观志》,第671页 ,第 670页 ,第 670页 ,第 674页 ,第 672页 ,第 671 页 ,第 671 页 ,第 672 页 ,第 673 页 ,第 671 页 ,第671 页 ,第 671 页 ,第 672 页 ,第 676 页 。
[88]让廉:《(京都风俗志》,光绪二十五年,出版地点不详 ,第 3 页 。
[89]《御史张廷燎奏请旨饬下地方官严查白云观倡为神仙之说及夜间容纳妇女事》,国家清史工程录副奏片,档号3-5512-64。
[90]《德宗实录》卷202,光绪十一年正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74-875页。
[91][106][114]王言一:《白云观庙市记》,《宇宙风》1936年第24期。
[96]李养正在《新编白云观志》中就曾做了初步的梳理。
[100]白文贵:《闲话西郊》,出版地不详,1943年,第18页。
[101]白文贵:《闲话西郊》,出版地不详,1943年,第19页。晚清日人记载称赛马时并不赌钱,富家子弟有马者随意进马道比赛,纯粹是为博取观众赞赏,大露其脸。此外,也有妇女乘马车比赛者,名为跑车,马必肥,车必轻(参见《清末北京志资料》,第556页)。
[103]吟痴:《庚戍重九日客都门殊苦岑闑走邀同乡杨仲老彭达五游天宁寺白云观诸名胜归作长謌》,《娱闲录:四川公报增刊》1914年第6期。
[120]潘荣陛、富察敦崇:《帝京岁时纪胜·燕京岁时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2009-09-30
责任编辑 梅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