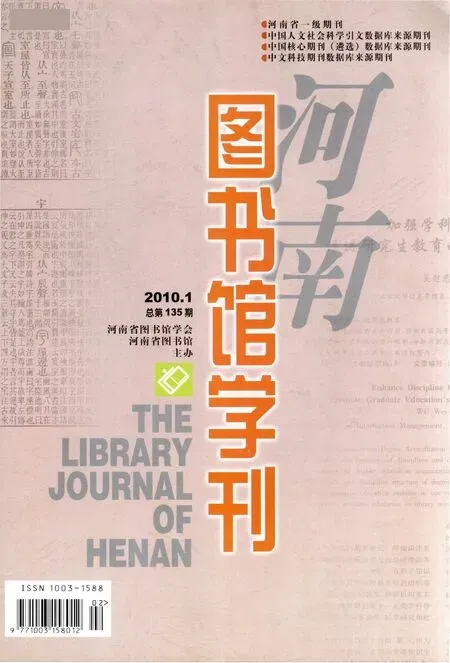论意识形态对图书事业的影响
陈雪梅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65)
引言
近代英国图书馆学家、曼切斯特图书馆第一任馆长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1812-1886)在其代表作《图书馆纪要》(Memoirs of Libraries,1859)中阐述过公共图书馆的两个原则:图书馆不应受政党的影响;图书馆是公共事业。
美国图书馆协会1948年通过、1996年再次确认的美国 《图书馆权利法案》(Library Bill of Rights)规定,图书馆资料不能根据作者的出身、经历或见解不同而受到排除;不能由于信仰和观点的不同对图书馆资料加以排斥或禁止;图书馆为完成提供信息、启迪思想的责任而抵制审查;图书馆与一切抵抗压制表现自由、思想自由的个人、团体合作;图书馆不能因为利用者的出身、年龄、经历、观点的不同而拒绝或限制其利用图书馆的个人权利。日本图书馆协会1979年5月30日修订和通过的日本《图书馆自由宣言》规定,图书馆拥有收集和提供资料的自由;图书馆严守使用者的秘密,反对一切审查。
图书既具备物质形态,又具有意识形态,是人们某种意识的反映。而人们的意识任何时候都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受时代的局限;受阶级、阶层及个人社会地位、社会经历的制约;受社会风尚、地域习俗的浸染。所有这些反映到人的头脑里,折射到典籍中,就使典籍具有了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图书是社会的产物,又直接影响社会。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书籍势必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结果,图书的出版、收藏、流通和使用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以维护政权的稳定。事实上,无论处于何种时代和文化,也不论是何种类型的图书馆,完全不受意识形态影响是不可能的。本文拟探讨意识形态对图书事业影响的具体方式。
1 鼓励收藏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书籍
图书是人类的思想文化产品,藏书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形式,因而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性。历代帝王或统治者对藏书的喜恶以及他们提出的政策,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当时藏书业的兴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记载秦代国史的《秦记》以及秦朝博士官掌管的《诗》、《书》、百家语等就不在烧毁之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把儒家学说奉为官学。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思想,视儒家学说的代表作为指导一切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和社会意识的经典,把重要儒学典籍称为“经书”,把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称作“经学”。经学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着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因此,历代经学书籍汗牛充栋,一直占据古籍四大部类之首,据《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达1773部、20427卷。
除官府藏书外,寺院收藏受统治者的影响也很大。唐代伟大的佛学家、佛经翻译家玄奘就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没有法事,又哪来佛籍呢?经书是寺观传教布道的基本工具,中国宗教对藏书的影响主体表现在藏经、刻经、抄经、传经、护经之中。寺观藏书不仅规模宏大,而且形式多样,既保留了大量的纸质宗教典籍,又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石刻经片。
宗教界一方面寻求统治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扶持宗教书籍的出版、收藏和流通。印刷技术的革新最先被应用到宗教上,显示出历史上人们对宗教的重视以及当时宗教书籍需求的旺盛,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宗教意识形态对图书事业的影响。公元868年4月15日刻印的《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雕版印本实物。雕版术刚问世时印得最多的是佛教的宣传品,包括佛像和佛卷。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印刷史上的重要变革时期,铅印成为印刷业的主流。1879年,英国人克拉科(J.D.Clack)在上海开始用煤气引擎轮转印刷机,使铅印效率极大地提高,成为书刊的主要印刷方法。最初铅印书籍多为宗教宣传品,如《圣经》、教义问答及各类劝善书,也有教会学校的书籍。
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动荡不安,官方藏书开始走向衰落,民间收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不同意识形态的主导作用直接影响着中国输入外国图书的类别和结构。在“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洋务派组织翻译了大量西方科技书籍。甲午中日战争后,有识之士意识到,光靠洋务运动是无法使国家强大和抵御外侮的,中国不仅需要学习国外的坚船利炮,更需要学习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开始输入大量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明清时期来华的传教士翻译部分欧洲科技书籍的同时,主要翻译了大量的基督教书籍,为在华传教服务。
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1918年,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把北大图书馆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国统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广大干部“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特别是边区的各种政策”,收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理论著作、革命军事著作、先进的经济理论和经营管理理论著作、富有科学文化知识的著作等,成为苏区图书馆藏书的核心和主体。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在图书内容方面特别注重选取思想进步的书报,以引导读者热爱国家和自己的民族,增强抗战的力量;而在沦陷区和伪满图书馆,日伪大肆出版报刊书籍,宣传“东亚圣战”等法西斯的和汉奸的卖国谬论。
不同的政权、政党和宗教总是鼓励和支持收藏符合自身意识形态的书籍,赞助的方式多种多样,如给予收藏和流通许可,提供经费、馆舍和人力等,为书籍题名或作序以扩大影响,重抄或翻印某些书籍以增加在社会上的流通量,指定某些书籍为官员或学生必读/考书目,对著录者实行奖励等等。
2 限制或禁止不同意识形态图书的流通
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统治者统一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在鼓励和扶持收藏符合其意识形态图书的同时,往往禁毁意识形态不同的图书。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因意识形态原因而遭焚毁的典籍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秦代的“焚书坑儒”导致大量儒家经书被烧,是毁灭中国文化的野蛮行径。其实,这种愚民政策是有渊源的,就秦国而言,直接来自商鞅的理论。“焚书”之举也非始自秦始皇,先秦就屡见不鲜了。那时,各诸侯国在打败敌国后,总要把敌国所藏不利于己的书烧掉,这在《孟子》、《商君书》等古籍上有很多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焚“削”典籍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仅仅是我国典籍发展的头两次政治劫难。“六朝灭纬”使畿纬之书遭到毁灭性破坏,在历经几百年的禁焚后基本灭绝。此外,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代武宗皇帝都曾发起过灭佛运动。“三武灭佛”使佛教典籍遭到重大破坏。
历代政府对典籍的损毁之烈莫过于清朝。清代皇帝是满族,他们对汉族的疑忌很深,并实行高压政策,促使民族矛盾尖锐化。汉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在清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斗争也十分激烈,这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有所反映。当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所著的书中就充满反满意识。为防止这些书流传,从顺治帝开始,清代统治者采取极端野蛮的禁书政策,并大兴文字狱,杀戮读书人。
清代禁书的主要方法有销毁、抽毁、篡改、杀戮。只要清廷认为某书“诋毁本朝”,就会被列为禁书,彻底加以销毁。对于只是个别地方“悖谬”、“违碍”的书籍,则抽毁或篡改涉及清朝禁忌的章节。被抽毁的除了少量属康熙、雍正年间的以外,大部分是明朝万历年以前的遗著;被篡改的主要是宋、元、明以前的书。此外,凡对历代君王(秦始皇、隋炀帝等暴君除外)不够尊重的言论,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见,均在需要改篡之列宋人攻击女真、明人涉及清朝先祖的书依照情况,或全部销毁或部分抽毁。清朝的禁书政策导致大量古书被毁。据后来统计,乾隆38至46年(公元1773年至1781年)的八年间,共收缴书板67000多块,全部焚毁。自顺治至乾隆代,销毁之书达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若加上抽毁、篡改以及一般性查禁的书籍,估计有十万部左右。
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勃兴,革命书籍的著述活动十分活跃,直接触及并威胁清政府的统治。为遏制革命思潮,清政府下令 “查禁悖逆各书”,对革命书刊大加查禁,仅1904年4月,谕令查禁的书目就达20多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禁书活动也十分猖獗,凡是抨击北洋军阀的腐败、宣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书刊都在查禁之列。据《北洋政府查禁书籍、报刊、传单目录》统计,民国元年至民国17年间,被查禁的出版物达460种之多。
查禁书刊是对书籍有形的毁灭,而统治阶级对某些价值观念的偏重则会对书籍产生无形的破坏。比如,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文人注重经史,看不起科技,称之为旁枝末道,因而古代科技书籍散失的现象严重。秦始皇焚书时,烧的主要是儒家经典、百家之书和各国史书,而兵书、农书、医书等生活、技术之书不在焚毁之列。但被列入焚书的儒家经典及诸子书,经过几十代人的发掘整理保存下来不少,后来又大量出现和流传,而那些没有烧的农书、医书等科技书籍反而几乎全部失传,成为佚书。
3 影响书目分类和对图书馆学性质的认识
早期对图书馆的研究主要是图书的整理和编目。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四部分类法”,起源于魏晋,是我国封建社会书目分类的主要方法,它用经、史、子、集类目名称概括各类书籍的性质和内容。“经部”收录儒家经典;“史部”著录历史书籍,“子部”以诸子著作为主,“集部”主要收录诗文和诗文评;其它三部不能归入的全部统归“子部”。
儒家虽是先秦最有影响的学派,但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本无主从关系。历代统治者以儒学为正统,儒家经典首先从“诸子百家”中单列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类别;而其他诸子的著作则全归属到子部,其地位大大低于经书。但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同为“经书”的作品其知识性质其实是非常不同的,有属哲学的《易》,有属政治的《周礼》,有属历史的《春秋》,有属文学的《诗》,有属科学技术的农、医、天文等。这种按作者的政治思想对知识进行分类的做法有着很大的缺陷,它注意到了儒家学者伦理思想的同,却回避了他们学术著作中的异,割裂了知识的内在联系,过于凸现学术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四部分类法符合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需要,但其科学性却很成问题,社会上对此分类颇有非议,且后来的目录上也有不用此法的。但清代乾隆修《四库全书》时以四部分类法分类,还说它“实为古今不移之法”。清代思想统治很严,皇帝说了话后,就不敢再有异议。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政治类书籍(尤其是革命书籍)大增,过去的分类法在类目设置、思想观点上不能适应新的需要。1950年,杜定友首倡新中国图书分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依据。我国五、六十年代的许多分类法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比如,《人图法》第一版地域重分表按国家性质和社会制度立类;《科图法》每个大类前都写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论XXX”等。与我国五、六十年代类似的是,前苏联的图书馆被要求“抑制与意识形态不一致的文献分类表,形成特殊的导读体系,以宣传思想意识较好的文献;借助巨大的馆藏体系,将与意识形态相抵触的文献隔离出来,为执政党的政策提供图书保障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1984)”。“……,书籍的分类,表明上只是学术性的东西,而实际上,一项学术的兴衰,也总是和政治关联在一起的。”
意识形态不仅可能干预馆藏和书目分类,特定时期还可能影响人们对图书馆学性质的认识,使图书馆研究带有浓厚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比如,20世纪5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从当时的意识形态需要出发,指出图书馆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甚至认为图书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性是图书馆学的本质属性。八十年代以后,随着学术理性的恢复,图书馆研究才开始逐步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回避阶级性。
[1]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Library Bill of Rights[EB/OL].http://www.ala.org/.
[2] 陈雪梅.从《三字经》看中国古代的知识分类[J].晋图学刊,2009,(6).
[3] 范并思等.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4] 贺显斌.论权力关系对翻译的操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
[5] 焦树安.中国藏书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 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7] 李致忠等.中国典籍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8] 王子舟.图书馆学基础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
[9] 文化部图书馆事业管理局.列宁论图书馆事业[C].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10] 奚椿年.中国书源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 肖东发、杨虎.插图本中国图书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2] 徐凌志.中国历代藏书史[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13] 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