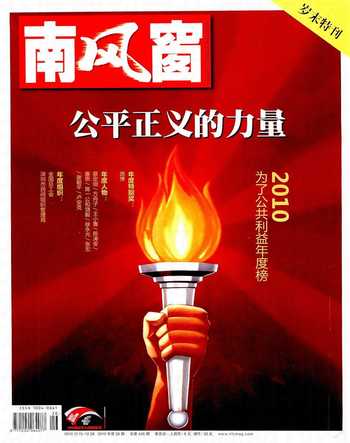书写“蚁族”的别样青春
张墨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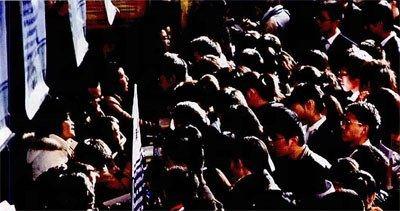
大学毕业、低收入、聚居在大城市外围的小村庄,和大多数为生计奔忙的劳动者—样,在困境中前行,如蚂蚁般微小,又如蚂蚁般执著,廉思将这样一个群体称之为“蚁族”。“蚁族”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图景里一部分人的困惑、焦灼、痛苦,迷茫和梦想,他们是时代的旁观者,虽也在剧场内,却毫无戏份。
与他关注和调研的对象一样,廉思生于80年代。但境遇却与他们截然不同,有着看起来繁花似锦的学业经历:本科学经济学、硕士修管理学、博士修法理学、博士后又转修政治学,且都是在名牌大学完成。博士毕业后,即成为对外经贸大学的教师。
2007年,通过媒体的一篇报道,廉思惊讶地发现:同在北京,机遇并不是垂青每一个年轻人。在海淀区最边上的村子唐家岭的实地探访中,他看到的是自己从未想象过的生活:“拿着1000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300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在这个村子里,有四五万年轻人正在经历残酷的青春。对同龄人生活场景的无法释怀,以及作为一个学者对社会问题的敏感,让廉思下定决心,开始深入研究这个群体。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廉思带领招募来的“志愿者”团队,深入到唐家岭、小月河等北京“聚居村”,开始对“蚁族”进行持续跟踪调查,倾听他们的声音,与他们共同生活,深入其内心世界。获得了有关这一群体的大量统计资料和第一手数据。“要想认识真正的中国,不能只坐在书斋里空谈,而要老老实实地去做调查研究,深入到基层,掌握第一手材料。”廉思说,他深受费孝通的影响,要用行走和记录的方式,勾畫出这个时代的社会图景。
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令大学的门槛降低、向更多人开放。逐年增加的大学生数量一方面使国民素质得以整体提高,一方面却催生了难以被有限的就业市场消化的毕业生,他们不得不面临毕业即失业的暗淡前景,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命运安排,来到大城市,却无法融入,成为处在城市和乡村夹缝中的“蚁族”。
21世纪第一个10年的中国,被更多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所包围:医改、房价、贫富差距……在诸多问题当中,大学生的就业显得“渺小”而不紧迫。2009年底面世的《蚁族》如同清醒剂,让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再次回归到大众的视线。它已经不只是一年又一年的扩招引起的就业问题,还有年轻一代对“北上广”的追逐所折射出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宁可在他乡过愁云惨雾的生活,也不愿意回到故乡谋求一份安稳的职业,显示了当下社会对于成功的单一定义。
“我想要呈现的,正是当代中国社会图景里一部分人的困惑、焦灼、痛苦,迷茫和梦想。”廉思说,尽管他所关注的这些人在传统的意义上,只不过是时代的旁观者。他们虽也在剧场内,却毫无戏份,甚至连跑龙套和坐在台下欣赏的资格都没有,或许只能站在舞台的侧面或幕后去窥视剧情的发展。但从他们的角度,却能折射出时代变迁。
当“蚁族”现象被广泛关注的时候,2010年4月,北京市宣布对“蚁族”聚居地唐家岭整体改造,拆除“蚁窝”建廉租房。此地的“蚁族”以始料未及的方式散去,有人开始批评廉思,他的调查和揭示反而打破了“蚁族”们平静的生活。廉思说,他不会因为曲解而改变初衷。
2010年,廉思继续对“蚁族”进行调查,与前两年有所不同,此次调查是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等7个“蚁族”大规模聚居的城市同时展开,共发放问卷5000余份,耗时半年有余,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蚁族”群体抽样调查。不仅涉及“蚁族”的生活、工作、需求、对社会现象的态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还对“蚁族”的身份认同、教育状况、社会公平、网络行为等进行深度分析。
《蚁族》给廉思带来了荣誉和褒奖,他开始过上不断被提问的生活。一些媒体甚至请他去谈房价、经济泡沫、文学和艺术,廉思都拒绝了。他说,自己只是做了一个知识分子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名青年学者,高扬起头或许也看不尽整个天空,但俯下身子却可看清脚下的方寸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