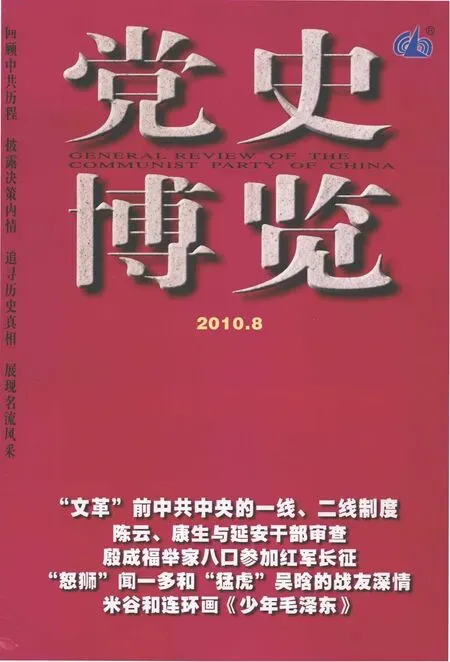陈云、康生与延安干部审查
○ 罗燕明
提到延安审干,非常不幸,人们首先想到的是1943年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然而从整个延安时期来看,审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制度,对于巩固、纯洁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起到了极大作用。它如同一架高效的过滤器,使延安能够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下大量吸收来自全国不同政治区域的新鲜血液,而把一切污垢渣滓拒之门外。这一历史功绩是与陈云分不开的。
在延安的党内斗争中,陈云和康生都支持毛泽东,反对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但是,他们的政治品质有天壤之别。陈云是一位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的伟人,而康生则是一个品质恶劣的政治投机者。延安审干本来由陈云负责,陈云在干部审查制度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由于种种原因,从1943年4月起,康生开始主导审干,破坏了已有的工作制度,使延安审干误入歧途,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陈云关于审干工作的四篇著名文章
从1937年12月到1944年3月,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共七年时间,审查干部是他负责的一项重要工作。在这期间,陈云根据中央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整套有关审查干部的原则和行之有效的政策,并随形势的发展使其不断调整和完善。《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收入了他在这一时期有关干部工作的一些重要文献,其中不少是关于审干或涉及审干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篇文章。
1938年9月的《论干部政策》
这是陈云在延安抗大的一篇演讲。当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不到一年,但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在这篇文章中,陈云把干部政策通俗地概括为 “用人之道”,提出了堪称经典的干部工作“十二字诀”:了解人、气量大、用得好、爱护人。
所谓“了解人”,指的是看人的思想方法。陈云指出,看人有两种毛病,一种是用一只眼睛看人,只看人家一面,不看全面;另一种是只看到这个人今天干了什么,没有看到他以前干些什么,只看到他本领的高低,没有看到他本质的好坏。陈云的结论是,看人不要只看一时,只看一面。对于一个人没有根本的估计,用人就会造成很大的错误。可以看出,“了解人”在当时主要指审查干部的长短处,包括能力大小、品质优劣,以便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关于“爱护人”,陈云说,当解决一个干部的问题,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的时候,要很郑重、很谨慎、很细心地去处理它。一个参加革命工作的同志,往往对于肉体生命并不重视,对于政治生命则非常重视,他宁愿牺牲一切,却不愿被党组织开除。陈云举了一个例子,有位青年党员上诉到中组部,说他被人供述为托派,失去了党籍,后来又恢复了,但过去七年党龄不算了。中组部内查外调,弄清了问题,承认了他的光荣历史。于是,这个人由过去的一个“死人”,只想“我还是到前线去牺牲掉算了”,变成“活人”了。陈云说,调查时间花了两个月,值得不值得呢?我看是很值得的。因为两个月绝对培养不出一个干部来,花两个月挽回一个干部再值得没有了。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陈云出席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前排右起:刘少奇、陈云、王明、凯丰、项英。后排右起: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康生。
“气量大”和“用得好”,讲的是用人方法。
1939年12月10日的《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
这是陈云在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对根据地加强了渗透。文章所谈的问题之一,是“纯洁干部队伍”。
陈云指出,边区的党员和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有没有坏的呢?当然也有。坏人有两种,一种是从外面混入边区的,一种是边区的和平环境中产生的。这两种坏人已查出一些,现在还有未查出的,正在继续审查。在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大发展时期,革命队伍里会混进坏人,少数本来革命的人会变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的任务是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纯洁党的组织,与各种坏人作斗争。要做好防微杜渐的工作。我们对于这样的问题,既不要麻木不仁,也不要惊慌失措。麻木不仁会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惊慌失措则会把事情搞乱。只要我们采取既坚决又稳妥的办法去做,纯洁干部队伍,巩固党的组织,是有保证的。
1940年8月14日的《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
1940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这一时期,延安和全国革命力量正处在顺利发展的状态中,边区的人员成分随外来知识青年的增多而日趋复杂。
中央指示包括九条,明确规定了审干由各级干部科负责。还规定了干部科的经常任务和工作范围、当前工作重点、各级干部科的不同权限,以及审干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如第五条规定除注意研究每个干部的长处外,特别要注意考查每个干部在政治上对党对革命忠实的程度。第八条规定在审查干部中,如发现某个干部政治上不可信赖,则须坚决撤销或调动工作;发现内奸叛徒则应坚决地清洗出去;但对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工作表现积极且忠实于党的路线即本质上好的干部则应加紧教育。要向党内解释:审干是巩固党的一种重要方法,防止因审查干部而造成干部在工作中不安的情绪,更须防止坏分子利用审干来挑拨党内的团结。
1940年8月14日,陈云为中共中央组织部起草的 《关于审查干部经验的初步总结》发出,共15条,既使中央指示具体化,也使审干经验成熟化和制度化。
陈云认为,审干有两个目的,不可偏废。一是为了发现干部的长处和缺点,以便适当地培养、使用、提拔和调动干部。二是为了发现党内的异己分子,以便清洗他们出党。这项工作必须细心耐烦,既不能疏忽大意,又不能冤屈好人。审干必须详细了解干部在入党前后的全部生活和历史,从历史的具体环境中识别出干部的长处和缺点,查出谁是干部,谁是内奸。对不同类型的干部注意审查不同的问题。党在鉴别某个党员是否忠实时,主要看党员本人,而不看他的家庭亲朋关系。审干材料,主要根据本人报告,同时又必须在每个重要关节上得到旁证。旁证越多越好,但须判断旁证是否可靠。如被审查者不同意证人意见时,在可能条件下,召集双方对质。
对某一干部的错误作结论时,应让本人出席,或将结论通知他;本人不同意结论而提出的理由,必须给予慎重考虑与确切答复。
1940年11月29日的《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
陈云在该文中指出,了解干部是制定干部政策的基点。审查干部必须区别好坏,了解优点和缺点。但在现状(延安招生,全国一时有很多人涌进来)下,首先要区别好坏,这种审查是必要的。审查干部必须实事求是,客观,严格。结论应该是不可反驳的。切忌以主观推测为根据,不能单看其言论和态度,主要看本质和表现。不仅看一时一事,主要看整个工作历史。不决定于家庭,决定于个人。不怕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允许隐瞒社会关系。审查干部必须对党对干部有高度的责任心。不能疏忽大意,不能冤屈好人。疏忽和冤屈都要承担责任。冤屈好人的责任并不小些。审查干部必须采取正当的方法,切忌耍手腕。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审查干部必须作出符合实际的书面结论,切忌含含糊糊和悬而不决,切忌空口无凭。

1937年12月,陈云在延安。
这四篇文章都是陈云在整风之前写的。但是读了之后,笔者有一个抹不去的印象,仿佛它们是陈云针对后来审干出现的严重偏差而写的。有些语言,如“绝对不准以特务手段对付党的干部”,简直就像在直接鞭挞冤假错案的制造者康生。
审干制度怎样防止冤案
从中共的历史经验看,审干最容易出现的偏差不是坏人、内奸、特务漏网,而是冤假错案泛滥。
审干的首要问题是由哪个机构审干。如果由组织部或干部部门审干,那么审干走的就是党内组织程序。搞错了,最多是开除党籍的问题。如果由保卫局、社会部、专案组等对敌斗争的机构来审,就要走反奸程序:发现嫌疑,先抓人,抓了再审,不怕你不交代。交代,有罪;不交代,对抗组织,也有罪。一旦搞错了,就要人头落地,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接下来的问题是靠制度审干,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审干。如果按前者,就要建立与完善制度,培养专职人员,排除主观主义。如果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审干,就要动员大家相互攻讦,相互揭发,相互审查,那就等于没有程序。今天你当特务,明天是他,后天轮到我,完全依运动形势而定,后果不堪设想。
在这些问题上,延安时期的陈云与康生之间存在严重分歧。陈云主张,审干必须由组织部负责。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前面提到的1940年8月中共中央和中组部的两个审干文件。前一文件的第二、三、四条,后一文件的第十三条,都明确规定了审查与管理干部统归各级干部科负责的原则。1941年4月11日,中央组织部发出由陈云主持制定的 《关于干部审查与填写党表自传的规定》再次强调,“对于干部的全部历史总的审查由中央组织部负责”。
陈云坚持这个主张,不仅因为审干理应成为干部部门的本职工作,更重要的,这是基于历史经验,其中还有血的教训。1931年,陈云进入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任中央特科主任。周恩来创立中央特科时借鉴了苏联 “契卡”的经验,其中一条原则是,不能把特科工作用在党内,不能对党内同志使用特工手段。
与白区相比,苏区的审干是惨烈的。那时,中共缺乏经验,没有专门的不同于政治保卫机构的审干机构,审干与肃反往往不分。在对敌斗争的残酷环境下,由于缺乏有效的审查甄别程序,党内斗争很容易引起相互猜疑。这是清党的由来。通常的,也是最容易实施的做法,是依靠政治保卫局实施肃反,其结果往往造成党内流血事件。
在苏维埃运动前期,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审干制度。审谁不审谁,由谁来审,怎样审,在什么场合下审,随意性很大。后来经过长征的考验,党内互信度提高,干部政策也逐步趋于完善。1937年5月,中组部部长博古在苏区党代会上首次把正确的干部政策概括为四条(陈云的“十二字诀”借鉴了这四条)。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军队政治机关的组织部 “专负党的工作和干部的审查与政治干部的配备之责”。
陈云接任中组部部长后最大的贡献,是为党建立了完整的干部审查制度。这些思想在前文四篇文章中已有所体现。笔者认为,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几点:
一、审查干部统一归组织部或政治部负责。组织部设干部科,由专职人员按规范实施审查,使审干成为党内的正常工作。
二、任何党员、干部都要接受组织审查。来延安的干部或青年学生,无论来自哪个地区、哪个部门、哪个级别,有无嫌疑,都必须持有正式介绍信向组织部报到,填写干部履历表,提供自传,回答组织的提问,接受组织的审查,待有了初步结论后再分配适当工作。
三、组织部有责任了解每名干部的全面情况,包括个人经历,家庭出身,社会背景,是否忠诚,政治表现如何,有哪些优缺点和功过,能力专长等。
四、设立长期保存的不断补充的人事档案制度。干部档案一般包括干部的履历表,自传,组织鉴定,有关问题的结论,经历证明,检举材料,谈话记录等。
五、工作人员有责任把需要专项审查的问题明确告诉审查对象,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互信,使受审者愿意向组织坦白情况。
干部审查制度的好处是明显的。
首先,它把审干作为党内问题来处理,用党内机构处理党内问题,实现了党内机关与对敌机关的职能隔离。审查中如果发现敌特问题,可以再移交对敌斗争机关。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专政机关对党内生活的干预。反观“文革”中的中央专案组,其最大的问题,是它拥有党内审查和对敌专政的双重权力。
其次,实现了审干由针对部分人和特殊问题的工作向经常性普遍性工作任务的转变。
再次,有利于实现材料集中。审干必须掌握真实可靠的材料,材料越多,越容易分别真伪和作出正确的结论。在这项制度下,中组部成为延安唯一有资格领导和承担审干重任的机构。它不仅集中了所有干部的档案,而且还从各地搜集了用于鉴定干部的其他材料。
最后,有助于消除审查者和被审查者之间的对立,有利于调动双方积极性,达到既清除坏人又保护干部的目的。
从整个延安时期的审干工作来看,1943年4月可作为一条分界线。之前,陈云负责审干工作,冤假错案是个别的、孤立的,且多来自康生领导的反奸部门,或由康生干预审干引起。之后,康生取代陈云,兼做反奸和审干工作,冤假错案大量出现。
康生是怎样破坏审干制度的
陈云和康生一起共事时间很长。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都做过特科、工运和白区的工作。1935年,他们供职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1937年底同机返回延安。他们还先后负责过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整风之前,在中央领导成员中,恐怕没有比他们两人的工作经历更为相近的。按理,康生应当支持陈云和中组部负责的审干工作,至少应当尊重审干制度才对。而实际上他一直冷言冷语地指责和质疑陈云的工作业绩,经常插手和干预陈云主持的审干工作,素怀取代之心。

当时,康生任中央社会部部长,负责反奸和安全工作。在陈云创立的干部审查制度下,反奸和审干有严格的区别。反奸通常围绕策反、通敌、告密、破坏、暗杀等敌特的现行活动进行,这是情报部门和保卫部门的正常职责所在。党内的干部审查主要是审查干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并非针对现行的敌特活动。任何党员干部都要经过和接受党的组织审查,这是党内的正常工作。在审查中如果发现了现行的敌特问题,再移交社会部等保卫部门查证和处理。一般来说,干部的档案资料都由组织部门掌握,社会部等保卫机构只有敌特材料。因此,康生无法像在苏区时期那样越过党组织,依靠保卫部门直接审查干部。在陈云主持中组部工作期间,由于存在干部审查制度的屏障,康生只能在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和敌特案件范围内个别地制造冤假错案,很难在全党范围推行他的那一套。
后来康生是怎样破坏审干制度,取代陈云插手审干的呢?根据现有史料和相关回忆录表明,他是从1942年制造王实味冤案入手的。在王实味案之前,康生同年处理了两起特务案。一起是张克勤案。张是西北公学的人。由于该校隶属社会部,康生可以直接下令抓人。张被屈打成招,康反让他披红挂彩,利用这起假案为自己贴金。另一起是吴南山案。吴是农村青年,参加了特务训练班。他是主动向延安保安处自首的,也被康生利用来炫耀其反奸成就。
王实味案有所不同,王是中央研究院(前身为马列研究院)的人,属于党内问题,由院党委审查。康生无权直接下令抓人。他必须等候党内审查的结果。只有当王的问题在党内定性并涉嫌敌特后,他才能接手处理。在康生看来,把王案定为敌特性质具有特殊意义,既可证明延安党内已混入了大量特务(王是党的高级知识分子,同中央领导人一样,每月有五元津贴,吃小灶),又可证明现行干部审查制度无效,必须改变。
王实味问题本来是党内问题,对他的批斗中引出了托派历史问题。又因历史问题,有人指责他的小团体属于托派活动。王来延安时经过审查,讲清了托派问题,中组部存有材料。他很坦然,著文说:“一个党员政治上的骨头,要由中央组织部来鉴定。”院党委对王案的定性花了很长时间,反复考虑是定为反党行为,抑或只是政治立场的错误。
其间,康生躲在幕后做了不少手脚。他从1942年4月开始搜集王的现行活动材料,调阅了中组部的档案,企图用王的自述材料指控他是托派特务,但均无所获。于是康生要求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当面汇报。汇报中,康生指责中央研究院有温情主义,说“王实味是双料的,不仅是托派分子,还是国民党蓝衣社的特务”,暗示社会部掌握了不便公开的证据。
中央研究院党委书记十分惊讶,但认为康生作为社会部部长总不能凭空乱说。受康误导,中央研究院党委又用了几个月时间,最后下决心把王等人定为“托派组织活动”和“五人反党集团”,于10月23日开除了王的党籍,将其移交社会部。
王被社会部收审后,进入反奸程序,被进一步指控为敌特。1942年11月,康生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要求帮助搜集王实味等人的特务材料。周恩来的复电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定不了案,王一关就是几年,一直拖到解放战争爆发,最后还是被康生下令以“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这一不伦不类的罪名枪决了。
康生花了很多时间,用尽心思才搞定王实味。由于反奸和审干两权分立,康生只有反奸权,没有审干权。利用反奸权干预审干,成本高,时效差,无法在全党推广。康生的用心是把反奸的声势造大,进而夺取审干权,再利用审干权把反奸运动推向全党。
1943年3月20日,康生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反奸工作。他大肆渲染敌特渗入,形势严峻,声称抗战以来,国民党普遍实行奸细政策,最近从审查干部中才发现这一政策的阴谋。他要求把审干当做1943年工作的重要一项,同反奸结合起来。在这次会议上,中央采信了康生关于“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的说法,不再认为现行的干部审查制度是有效的,怀疑组织部门专责审干是否有利。这时的陈云,在关键时刻,不幸患上心脏病,住进医院,离开了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岗位。
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把“审查干部与肃清内奸”作为纠正错误思想三阶段之后的整风任务,并规定了完成时间。
陈云休息了,《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下达了。社会部部长康生出掌组织部门的审干工作还需要一个名义,这个名义就是“党与非党干部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
关于审委,我们知道的很少。它发没发过传世的重要文件,开展过哪些活动,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史学界有不同说法,可能是1941年夏秋,也可能是1943年4月;它是由谁提议成立的,由哪些人员组成,我们也不清楚,只知道康生被任命为审委主任,而且知道他篡夺审干权时已有了这个身份。
根据现有材料并结合当时的背景,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审委是根据当时任务成立的临时机构。作为委员会,它具有协调相关常设机构的职能,其成员一般来自这些常设机构。审委有审干权,没有机关,它必须依托常设机构才能发挥作用。它依靠哪个机构办事,通常取决于主要负责人来自哪个机构。康生担任审委主任,耐人寻味。审委一方面给了他指挥审干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使他可以动用社会部的强制手段进行审干。这就是说,康生取代陈云主持审干,名义来自审委,执行程序和手段却出自社会部。
1943年4月1日,当《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还在酝酿时,审干大权在握的康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布置抓人了,当月就抓了400多人。陈云创立的很好的干部审查制度,就这样遭到了无情的践踏,整风由此走上反奸和审干并举的歧途。康生先动用社会部的力量,以肃反方式审干,继之又搞群众性的“抢救运动”,一发不可收拾。结果,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面收拾残局,替他向受害者赔礼道歉。
- 党史博览的其它文章
- 殷成福举家八口参加红军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