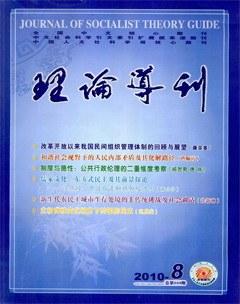现代哲学的危机与出路
——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思想述论
寇爱林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510006)
现代哲学的危机与出路
——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思想述论
寇爱林
(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州510006)
现代哲学的危机主要表现为科学的大一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对自身的曲解。身处危机的现当代哲学家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提出了各自的拯救方案。维特根斯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通过前期对哲学与科学的划界和后期哲学不必成为科学的分析,既没有得出哲学必然是科学的结论,也不主张逃避到非理性的领域,更不满永远徘徊于哲学的混乱。他虽没有完成拯救哲学的任务,却为我们走出危机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哲学可以像科学那样关注现实但不必成为科学,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但不应成为常识。
哲学;科学;危机;出路;维特根斯坦
一、现代哲学的危机与拯救方案
危机意识是西方哲学发展的内驱力,它逼迫着哲学家们不断地思考哲学的性质和未来,不断地对以往的哲学观念进行追本溯源的反思和批判。这种危机和批判意识不仅支配着像笛卡尔、休谟、康德和黑格尔这样的传统哲学家,也更为明显地体现在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等现当代西方哲学家身上。
从哲学史角度看,西方哲学面临了两次大而严重的危机。第一次是在中世纪,神学一统天下,哲学为神学所吞没。如何将哲学从神学的危机中拯救出来?这是近代哲学家们所面临的最为重大和艰辛的任务。怀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近代哲学家们借助理性与科学两大武器,力图将哲学从神学危机中拯救出来,使哲学从烦琐而无聊的空谈走向对人自身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关照。笛卡尔无疑是发起这一运动的最为耀眼的一位,休谟则把笛卡尔采集的火种打出了一颗火星,康德进而把它燃成了熊熊大火。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在与神学的斗争中终于大获全胜,并在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在黑格尔百科全书式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那里达到了巅峰。
然而当人们陶醉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将自然科学的模式作为人的其它一切认识活动或认知方式的基础与典范之时,近代哲学所依赖的理性与科学却摇身一变成了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随着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崩溃,现代哲学又陷入了新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主要表现为:科学的大一统以及由此而来的思想对自身的曲解。这是一个“全面性”的危机,它既表现在对“世界”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对待“人”的问题上。[1]188哲学能成为科学吗?换个问法,哲学能避免成为科学吗?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存在及其价值问题就成了现当代每个搞哲学的人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对此,身处危机中的现当代哲学家们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提出了各种拯救哲学的方案。通常有这么三种:
第一种反应是欣然接受哲学是门科学的结论。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对理性与科学依然充满信心,认为危机的出现并不在于科学与理性方法本身,而在于哲学恰恰缺乏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严密性和精确性,因而力图通过使哲学获得更多的科学性与普遍性而摆脱危机。譬如实证主义者,胡塞尔、罗素、波普尔等就是这样,其中胡塞尔的思想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人根本的生活危机表现为科学危机,能否走出危机取决于一场真正哲学与虚假哲学的斗争,即取决于把理性认识的普遍存在作为自己任务的哲学和放弃这一任务的哲学之间的斗争。“哲学的历史目的是成为所有科学中最高的、最严格的科学。”[2]2以往的哲学虽没有抛弃这一目的,但始终没有实现这一目的的能力和途径,换言之,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并不存在。胡塞尔毅然担负起了建构严格科学的哲学这一历史重任。然而,无论是现象学的本质还原还是先验还原,都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困难,并不能保证作为严格科学的先验现象学的自明和绝对可靠。
第二种反应是非理性主义的态度,这类哲学家坚决反对第一种做法,因为在他们看来,正是理性主义的肆虐和唯科学倾向的思维方式造成了危机。因此,他们以非理性制约理性,以非科学反对科学,以个性对抗共性,以相对否定绝对,以个体的经验代替普泛的逻辑等等,力图把理性因素和科学的思维方式驱逐出哲学的领域。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思潮大多如此,而以海德格尔为典型。海德格尔强调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着魔的时代”,人们着魔于技术及其技术制造的无限统治,而且由于人们对其本质——座架的毫无察觉,加剧了时代的急难和危险。“说到底,座架占统治之处,便有最高意义上的危险”。[3]946因而,危机的产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不仅产生于对人(人性,人生的意义)的忽视和对存在的遗忘,而且产生于科学技术及其思想方式的“无限统治”。为此,海格德尔反对从抽象的、一般的、理性的人出发,而主张以处在烦、畏、筹划中的此在为开端;反对以永恒性为基础,要求在时间性中考察事物;放弃传统哲学“是什么”的本质主义提问方式,坚持直接面向事物本身的现象学方式;排斥逻辑的理性的思维态度,认为只有诗一般的顿悟才能领悟存在本身。但他似乎对这种拯救及其整个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不抱有什么希望。宣称“只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我们只是“在思想和诗歌中为上帝之出现准备或者在没落中为上帝之不出现做准备”,而最大的可能是“我们瞻望着不出现的上帝而没落。”[3]1306
第三种反应可用“永远陷在混乱状态中”来形容。做出这种反应的哲学家不情愿哲学成为科学,却苦于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又不愿采用非理性的态度,所以就一直为困扰他们的问题所纠缠,使思想在不断遮蔽中误解着自身,也可以说在不断误解中遮蔽着自身。他们中有些思想家试图通过将哲学与科学的界线搞模糊以应对危机,如实用主义,但最终要么是科学,如杜威;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如詹姆士。另有一些思想家试图使哲学成为某一领域系统的独立研究而获得独立地位,但这实在不过是对科学的妥协,在步步退却中仍免不了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逻辑哲学、心理哲学等。
显然,这三种回答,都不足以使哲学真正从危机中走出。第一种将哲学降格为科学的女仆,第二种极有可能使哲学走入另一个极端,第三种更无获救的希望,哲学将永远在混乱和黑暗中徘徊。那么还有没有其它路可走呢?这是维特根斯坦所思考的。如何拯救哲学?这是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主旋律,也是他毕生的事业。他人的努力及其失败促使维特根斯坦对传统的科学的哲学观念进行了严厉无情的批判,开始尝试与别人决然不同的拯救危机之路。
二、哲学与科学的划界
哲学能避免成为科学吗?换言之,哲学能走出科学的危机吗?维特根斯坦的答案是肯定的。他终其一生都在反对那种科学的哲学观念,要求破除传统哲学对科学的过分依赖和盲目崇拜,为哲学和科学划出明确的界限,以拯救哲学。
事实上,维氏在一开始从事哲学问题的思考时,就明确地要求将哲学与科学区分开来。早在1913年的《逻辑笔记》中,维氏就指出:“在哲学上没有演绎;它是纯粹描述性的。哲学并不提供实在的图像,它既不能确证也不能驳倒科学的研究。哲学是由逻辑和形而上学构成的,逻辑是其基础。……哲学是关于科学命题(不仅是初始命题)的逻辑形式的学说。‘哲学’这个词永远应该指某种超乎自然科学或低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与自然科学并列的东西。”[4]23-24显然,维氏已经把哲学与科学相区分:哲学因不能提供关于实在的图像,也就不能证实和反驳自然科学命题;科学从假设出发,通过演绎得出结论,而在哲学中,既没有假设,也没有演绎,只有纯粹的描述——一种对于逻辑形式的描述。这个逻辑形式把哲学与科学相联系:哲学是关于科学命题的逻辑形式(即弗雷格和罗素所倡导的现代数理逻辑)的学说;哲学要么是科学的女王要么沦为女仆。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氏通过可说与不可说的区分完成了对哲学与科学的严格划界工作。该书的中心任务是为思想和语言划定界限,亦即说明哪些东西是可说的和可思考的,哪些东西是不可说的和不可思考的。根据图像论,“命题是实在的图像”,[5]4.01(注:凡出自《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的引文按惯例只标明节号。如4.12指该书第4.12节,而非页码。下同)因而语言可以描画世界中的事实,换言之,事实是可以言说的。凡是可以言说的东西都能够清楚地加以思考,而凡是不可说的也就不能思考。虽然“我们不能思考我们所不能思考的东西”,[5]5.61但可以通过“为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从而也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5]4.114可说的东西有世界中的事实,以及数学和逻辑;而不可说的东西主要有命题和实在的逻辑形式、语言和世界的逻辑性质、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以及有关美学、伦理学、人生和宗教的命题。关于事实命题的总和构成了自然科学的命题,因而自然科学命题就是可说的和可思考的;而哲学是不可说的,只可显示,因为它处理的是不可说、不可思考的世界之外的事项。因此,科学的任务是研究和说明世界之内的事物,而哲学则是对语言和思想的澄清,并“限制自然科学争论的范围”;[5]4.113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是构建理论体系,而哲学不是理论,只能是一种澄清思想和命题的活动,并在这种活动中显示自身。传统哲学的错误就在于试图超出语言的界限,去说那不可言说的东西,去构造庞大的、科学的形而上学体系。要避免这种错误的正确办法就是:“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也就是与哲学无关的某种东西之外,就不再说什么。”[5]6.53
维氏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在他的意义理论中得到了强化。根据图像论,一个命题要具有意义,必须符合两个条件:首先,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必须符合逻辑语法规则;其次,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必然要对事实有所陈述,从而具有能为经验验证的可能性。据此他把命题划分成三类:⑴自然科学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们的逻辑结构合格,描画了经验事实,并且最终可以由经验事实验证其真假,因而属于有意义的命题。⑵逻辑和数学的命题,是缺乏意义的。因为它们虽对事实无所陈述,也不能为经验事实所验证,但作为重言式或矛盾式命题,在符号系统里具有自身的意义,就像“0”是算术的记号系统之一部分一样,离开它,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陈述任何自然科学命题,因而这类命题可称之为缺乏意义的命题。⑶形而上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既不能作为事实的逻辑图像,也不是重言式和矛盾式,因而它们是完全无意义的胡说。就此而言,自然科学的问题都是有意义的,都是真正的问题,也都是可以回答的;而哲学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根本上就不是个问题,因其答案是不可言说的。
维也纳学派继承了维氏的意义理论,并将他发展到极端,以此来“拒斥形而上学。”但这却是对维氏的误解,因为他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并不是像维也纳派那样要拒斥或清除形而上学,而是要拯救哲学。因为在维氏心中,哲学尽管不可说、无意义,但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它和我们的生命紧密相关。卡尔纳普后来也意识到了这点,他说:“当我们圈内读维特根斯坦的书时,我错误地以为他对形而上学的态度与我们相似。我对他书中关于神秘的言论不够注意,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和感情跟我的差得太远了。”[6]234确实,维氏通过把形而上学划到不可说的领域,从而使形而上学得到了很好的保留。在《逻辑哲学论》中,他通过对语言(命题),世界(事实),尤其是逻辑的大量言说最终在事实上构造起了一个精致的逻辑哲学体系。显然,这与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5]4.112的主张相左。这表明,在前期维氏虽然坚持“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之一,”[5]4.111但还没有把哲学与科学完全区分开来。他还没有彻底摆脱传统哲学观念的影响,因而最终也没能使哲学避免成为科学。那么,在后期他是否完成了这一任务呢?
三、哲学不必成为科学
在前期,哲学不是科学的重要论证就是基于图像论而做出的可说与不可说的划界和命题意义的区分。在后期,维氏基本上放弃了可说与不可说以及命题意义的区分,这是否意味着他也放弃了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呢?没有。恰恰相反,维氏在后期的《哲学研究》中以语言游戏说为基础更为精练和彻底地表明:哲学与科学毫不相关,哲学完全可以避免成为科学,科学充其量可能会产生需要由哲学处理的新的概念问题。
在后期的维氏看来,科学的研究或者是关于经验事实的研究(经验科学),或者是关于抽象的演绎关系、数量关系和空间关系的研究(逻辑、数学等纯粹科学)。而哲学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或称“概念研究”,是通过消除对语词用法的误解而澄清思想的描述活动。显然,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之间有着较大的区别。但是以往的哲学家在提出哲学问题或企图为它们寻找答案时常常混淆了哲学命题与科学命题,将本来有关语词用法或符号系统的选择之语法问题等同于有关真假的科学问题,企图用科学的方式取代语法问题,从而导致人们缺乏对语言的“全貌概观”,用某种僵化的、刻板的思路或模式对待丰富多彩的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这正是“哲学病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偏食。”[7]I.593正是诸如此类的混淆与误解,给哲学家们带来了困惑与不安,造成了哲学的危机。
因此,哲学研究应与科学研究截然分开,科学方法不仅不能帮助人们治愈理智疾病,反而加深了人们思想的混乱。因为科学力图通过说明或解释的方法推演出事物普遍的共同本质,但本质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哲学只能用不同于科学的方法对事实或事态进行描述。具体说,第一,科学构建理论,而哲学没有也不可能构建这种理论体系。科学通过提出某种假设,经过论证和实验,推演建立理论和体系。哲学研究则不能有任何假设,也不提出理论,因为哲学命题是语法命题。因而哲学家的工作不是效仿科学家们去建构理论体系,而只是为特定的目标汇集提示,[7]1.127在语言迷宫的“所有交叉路口上竖起路标,以便帮助人们通过危险地段。”[8]35第二,科学追求一种精确性和完备性,而哲学“不追求精确性,而追求一种概貌全观。”在维氏看来,哲学无法在精确与不精确,完备与不完备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哲学也不应企图划出这条界限。第三,科学研究的方法是说明和解释,而哲学的方法只能是描述。说明总是试图将特殊的事例、众多的现象还原为尽可能少的若干基本原理、原则和规律,或者用普泛的假设和一般的原则推演、解释个别的现象。描述则不进行人为的概括和推演,不是远距离而是尽可能地接近事物,完全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展示事物。哲学的问题不能用科学的研究或者新的发现来解决,而只能通过语言的观察描述来消除。具体到语言上,描述旨在向我们表明:对语词使用的正确与否(是否合乎规则);语词用法之间的诸多关联和过渡;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和不相似性,等等。显然描述更有助于我们澄清语言的迷雾,正确的使用语言和发挥其作用。
就此而言,哲学研究是一种语法研究,它不能仿照科学的语言模式来构造自己的语言模式,更不能以科学的话语方式来取代自己的话语方式。因为科学的语言模式仅仅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之一种,只是科学家在某一层次、某一角度、某一领域用来分析说明事物的本质,因而不能将其抽象化、绝对化以代替其它的语言游戏。否则就会使语言丧失其原有的功能,导致理智的迷雾。因而在哲学研究中,不能有对哲学命题的解释说明,只能有对哲学命题错误性的描述;不应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应去寻找消除问题的方法;不应有对哲学命题的逻辑证明,只应有对日常语言用法的总体观察。一言以蔽之,哲学只能是种活动,一种对日常语言用法的观察描述活动,只“陈述每个人都承认的东西。”[7]I.599
但哲学研究只是对日常语言的描述而不提出任何理论,这是否意味着把哲学变成了常识呢?维特根斯坦坚持,这决不意味着哲学只需停留于日常生活的信念之中,也决不意味着哲学沦为了常识。日常语言是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但我们不能拘执于语词的个别使用,而应在我们的生活形式和日常生活中达到对日常语言的概貌全观,即整体把握。正如我们生活在某个城市中,这个城市里的学校、医院、街道、邮局等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但哲学的研究并不停留在这些熟悉的东西上,而是要努力获得对这个城市的全貌再现。因此我们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使哲学回归了生活,但并没有使哲学成为常识。他并不试图做出迄今为止最为深刻的新发现,而是要获得对于语言的明确理解,即获得我们人人都充分了解其用法的总体观(清晰表象),以消除哲学的混乱,澄清思想。因而在他看来,哲学虽始于常识,但却并不停留在常识的范围内。哲学并不是要为常识命题进行辩护,而是要阐明他们的地位和意义。
维氏通过严格区分哲学与科学,把哲学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堂拉回到了粗糙的地面,但却又使之避免成为科学与常识。“科学的”哲学应当而且必须终结,这是确定无疑的。维氏的结论在分析哲学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卡尔纳普针锋相对地宣称:“哲学就是科学的逻辑。”[9]57石里克虽然同意“哲学不是一个命题体系,它不是一门科学”,[10]9但仍有资格被尊为“科学的女王”,因为哲学的授意活动就是确定和发现科学命题的意义。罗素自不待言,在他看来,哲学与科学都是关于世界的理论,都以追求世界的真理为目标,因而哲学应该也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由是我们不难理解罗素何以把《逻辑哲学论》视为杰作,而对《哲学研究》不屑一顾;将前期的维氏称为“天才”,而认为后期的维氏“丢弃了他的天才,在常识面前贬低自己。”[11]33
四、余论
虽然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命运以及当今西方哲学仍旧混乱的图景表明,维特根斯坦并未能完成拯救哲学危机的任务,但是他对于危机的思考和拯救方案无疑是与众不同而有启发性的。他没有得出哲学必然是科学的结论,也不主张逃避到非理性的领域,更不满于永远徘徊于哲学的混乱。他虽没有完成拯救哲学的任务,却为我们走出危机指出了一个新方向:哲学可以像科学那样关注现实但不必成为科学,哲学必须回归生活但不应成为常识。在这个科学主义至上的年代,如果我们顺着维氏的致思之路,回到我们语言的大地基,回到原初的本真生存境域,哲学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如果我们能对自己所处的中国传统进行一番维特根斯坦似的反思和批判,关切我们当下的历史处境和生活方式,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和合共生,中国哲学的发展又将怎样的不可限量。
[1]叶秀山.思·史·诗[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C]//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
[4]维特根斯坦.逻辑笔记[C]//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全集(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5]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陈启伟.《逻辑哲学论》中的形而上学[C]//陈启伟.西方哲学论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
[7]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8]维特根斯坦.文化与价值[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
[9]周湘滨.世界当代哲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
[10]石里克.哲学的转变[C]//洪谦.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11]贝克尔,海克尔.今日维特根斯坦[J].哲学译丛,1994,(5).
[责任编辑:黎峰]
B 521
A
1002-7408(2010)08-0095-03
寇爱林(1973-),男,陕西耀县人,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方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