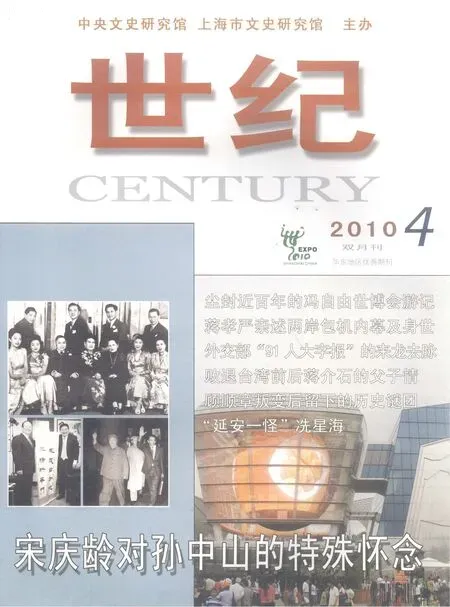出版局长劫难记
史 鉴
上海出版界的头号人物是上海出版局局长,党副书记是二把手,兼任副局长,所以“文革”期间上海出版界的劫难记,要从局长说起。
这里说的上海出版局长,指的是罗竹风。“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虽然已经不做局长了,但是因为新局长到任未久,所以出版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账仍都算在他的头上。
罗竹风是上海党内中上层领导干部中有学识和事业心、愿有所作为的人,自1957年起任上海出版局代理局长。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性格爽朗,善识人才,因此对出版社编辑所处地位,深表同情。编辑待遇很低,没有正式的学术职称,不为社会重视,罗竹风经常为他们说话。出版社一些编辑对他也有知遇之感。
短文一篇 写丢局长乌纱帽
1961年至1962年期间,由于“大跃进”失败,思想控制有所放松,重又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报刊上于是允许有些不同意见文章发表。罗竹风便用“骆漠”的笔名,写了一篇杂文《杂家》,登在1962年5月6日《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为编辑鸣不平。杂家指编辑,文章说这也是一家,编辑为作家辛勤审阅文稿,修改加工,但书出版,作家名利双收,编辑“年年为他人作嫁衣裳”,默默无闻。这本来说的是事实,而且文章宛转陈词,不过表达了编辑们的一点心里话而已。并且又是一篇小文章,读者看过并不在意。
但是不幸的是,这样一篇小小的杂文,没有逃过姚文元的注意。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其时还未称为“文痞”,但背地里人们已经把他叫做“金棍子”,意即这根棍子是经过“御封”的。此人叫他“棍子”、“文痞”,还是抬举了他。实是豢养、训练有素的一匹恶犬,熟习主人的癖好脾性,凭着他的灵敏嗅觉,到处为主人嗅寻猎物,谁要被他嗅中,吠上一声,咬上一口,谁就倒霉了。1957年“反右”以后,他的文章与“御笔”已相去无几,投给任何报刊,不敢不登。他的一篇批评《杂家》的文章,很快就出来了,也登在《文汇报》上,指责《杂家》的作者有鼓动群众不满现状之嫌。1957年“右派”的“反党罪行”之一就是“为民请命”,罗竹风知道此人碰不得,连答辩文章也不敢写。
当然事情并未到此结束,《杂家》这笔账已经记好了。1962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从中央到地方,又逐步收紧思想控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是一个以善体上意著称因而受到垂青、飞黄腾达的人物,所以上海跟得最快,1963年初春马上召开了思想工作会议。会议的重点是批判了两个人:一个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另一个就是罗竹风,“罪名”就是写了《杂家》。柯庆施说,这篇文章等于就是你这个出版局长,带了一群编辑,到市委来喊冤请愿。于是撤了罗竹风的出版局长之职,贬到辞海编辑所去编《辞海》。上海人说,姚文元一篇文章威力真不小,一个局长的乌纱帽就丢了。陈其五则被贬去扬州农学院任一闲职。
“文革”后的1980年下半年,上海作家协会成立国际笔会上海中心,选举罗竹风做理事,要他填写自己作品的代表作。他说笑话道:“我的代表作就是《杂家》!”这句笑话含有多少辛酸滋味,知情人是体会得到的。
老账新算 十年屈辱缘此起
照说,罗竹风已经受到贬黜,他离开出版局后的事就不该由他负责了。但是不然,按照历次运动“痛打落水狗”的规矩,一个人无事便罢,只要一旦被挂上了什么事,罪名就会越来越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罗竹风就被作为出版局“头号走资派”,揪回出版局进行批斗(“揪”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专用词语之一),从此开始了他的长达十多年之久的屈辱悲惨生活。
对罗竹风的批斗,跟批斗其他“走资派”或“牛鬼蛇神”一样,不外是大字报和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揭发、批判他的“罪行”。反正他做过的每件事、说过的每句话,无不成罪,而且歪曲捏造,不许分辩。其中《杂家》这篇文章,更是他的“大罪”之一,柯庆施还只说是他带着编辑请愿,这时就说是他带着编辑“向党进攻”,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有一次有一个出版社开批斗罗竹风大会,就把曾经在公开场合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过的一些编辑,拉去陪斗,仅这个出版社就有十余人之多,当然,事实上在内心赞赏这篇文章的人要多得多。
对罗竹风的抄家也是很残酷的,任何造反派都有权去抄他的家。先是出版局的造反派,再是他两个女儿在上海中学读书,学校的红卫兵也去抄,都抄了不止一次,什么东西都抄光了。他的夫人、女儿稍提出一点轻微的抗议,就被暴徒侮辱殴打。后来传说全市将有一次毁灭性的大抄家,即砸烂所有家具,并将施用各种酷刑。那时造反派打人,不许还手,一还手就是“现行反革命”,妻儿也成为“反革命家属”。所以被打的人只能忍痛至死。有名的《西风》杂志主编黄嘉音,是从上海文化出版社远贬到青海去的,就是在被打得忍无可忍时反抗了一下,立即成为“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瘐死的。罗竹风夫人听到这个毁灭性大抄家的风声,不敢不信,连夜带了三个女儿逃往青岛避难。罗竹风是有罪之身,不能逃,一逃就罪名更重了。
囚徒生涯 朝夕请罪促投降
事实上,他也逃不了。从开始揪回出版局,他就被监禁起来,失去了自由。这在当时也有一个名称,叫“隔离审查”,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创造之一。造反派都有这个权力。审查什么呢?审查过去的历史,把一个人过去做过的事,用现在“革命”的尺度加以衡量,定出罪名。一个人,凡是在“旧社会”活过来的,他所做过的事,现在看来当然都是不革命或反革命的,都是有罪。所以人人诚惶诚恐。被“隔离审查”的人,日夜有人看守。除了批斗时,由人押解出外,其余时间整天关在一个小屋子内写“交代”。每个被审查的“牛鬼蛇神”,大概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写过几十万字的交代。尽管你交代的都是事实,也总归说你“不老实”,随时提审,施用各种手段,有时威吓,有时胁诈,甚至拳打脚踢,要你“低头认罪”。有一次原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老作家梅林,就是在提审时被一个造反派小头目打翻在地,不能动弹,还要骂他装死。
受到“隔离审查”待遇的囚徒,除了挨批斗、写交代,每天仍得学习《毛泽东选集》,早中晚三次站在毛泽东像下“请罪”。当时“牛鬼蛇神”请罪时都要背诵《毛选》中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据说这篇文章原是出于已被撤职的陈其五(淮海战役时任宣传工作)之手。陈是桐城派古文三大家(方苞、姚鼐、刘大櫆)之一的刘家后人,这例子很多,参加革命后改换姓名,有的子女也随之改姓。当时传闻这篇投降书作者不止一人,陈为其一,即使所传不一定准确,作者另有其人,陈也“与有荣焉”了。
在罗竹风“隔离”期间,发生过一次“同伙犯”诬陷事件。事情是这样的:一个与他每天一同学习的“同犯”,有天忽然向造反派报告,揭发罗竹风毁坏“宝像”(即毛泽东照片),证据是罗的一本《毛选》里封的照片被打上了十字交叉。这是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罪,按这罪行,罗竹风就可被判刑,甚至枪毙。但是经过一再审问,罗竹风矢口否认。他说他的这本《毛选》曾被这个告发者借去过,归还后并未翻阅过,直等他被告发,方才发现。于是又转而审问这个告发者。经过几次调查核实,这个告发者在查获的打叉用的圆珠笔证据前,不得不招认,是他想借此诿过罗竹风,为自己立功赎罪。真相大白,罗竹风幸而逃过一难。
关禁罗竹风的囚室,常有迁移,最后一次是关在上海出版文献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一间本来不能住人的管道室内,用几块砖头垫着打个地铺。这是一所小洋房,原主听说在香港成了大轮船公司的老板,他大概想不到,当初造这所房子,后来做了牢监之用。同囚室还关着一个中华书局的老编辑。这位老编辑的“罪名”是曾应过国民党文官考试,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因此怀疑是国民党特务,也被隔离审查。一个局长,一个小编辑,原是不会结识的,这次却做了铁窗难友。
阴森凄厉 被迫承揽一切罪名
一个人处在当时那种失去自由的恐怖气氛中,日日夜夜听到的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拒不交代,死路一条”的阴森凄厉的口号声,加上对家人的怀念,对前途命运的绝望,神经脆弱的真要被逼得发疯。只有处在这种境遇,一个人才会了解为什么应该提出“免于恐惧的自由”作为民主社会奋斗目标之一的意义了。罗竹风还是坚强的人,他没有发疯,但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他也只得把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全部承揽下来。其实他也曾是“箇中人”,深知“罪名”是早在斗你之前已定好了的,用“态度好坏”、“从宽从严”一套做法来诱你招供,使你不得不听从摆布。
对罗竹风的定案处理,是在一九六八年八九月份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出版系统之后的事。工、军宣队掌权之后,逐步酝酿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分期分批定出“罪名”,予以结案。其间一度宣传推广过一种叫作“群众定案”的方式,就是把某人的“罪行”,交由群众讨论,定出“罪名”,由同级组织或上级组织批准。这原是历来群众运动的一贯做法,叫做“走群众路线”。但群众在根本没有法制制约的狂热情绪的冲动下,只会发表不负责任的极端意见,采取极端的行动,以此表示“革命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检察和法院判刑,也把罪犯的所谓“案例”发给群众讨论,而群众讨论时就只会听到一片“枪毙,枪毙”之声)。罗竹风也经过这样一次的“群众定案”。那次大会的名称就叫“对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罗竹风群众定案大会”。罗竹风对要他承认的什么“罪名”都接受了,悔过了,但是不行,还是说他“死不改悔”。“群众定案”这个方式,后来中止了,改为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共同定案。
从严处理 感恩戴德
罗竹风的正式定案大会,是在上海衡山路上的风雨操场(今上海国际网球中心)举行的,带有全市示范性质,形式极为隆重。那时出版界已和新闻界合为一个新闻出版系统,因此这个大会把《解放日报》总编辑魏克明也和罗竹风一起定案,作为“走资派”认罪好坏、从宽从严处理的样板(有人常把这种定案会称作“宽严大会”)。
那天一早,就把出版界和新闻界的“牛鬼蛇神”一齐押解到风雨操场,分别圈坐在草地上,由造反派监督,勒令交代“罪行”。出版局的一个圈圈里,集中批斗那个兼党委副书记的副局长。只因加入共产党前,他做过国民党保长的文书,所以也算一大“罪名”。但他是做党务工作的,属于政工干部,所以在出版局“走资派”里仅是次要脚色。这天早上,被押解来的大批“牛鬼蛇神”,大家事先不知道这个批斗大会又要玩什么花样,但也预感到将有重大的宣布。当他们被押解进大会会场,看见台上横幅大标语,就知道罗竹风要被判处理了,由于联想到自己的命运,心里都有些紧张。
这个大会,可算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新闻出版界批斗“走资派”的一大高潮。首先是人数多,其次是整个会场气氛的低沉恐怖,最后就是对罗竹风处理之重,出人意外。这次会上宣布了两个不同的定案决定:魏克明从宽定案,因他老实交代“罪行”,认罪态度好,不戴帽子,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罗竹风从严定案,因他不老实交代“罪行”,态度恶劣,不知悔改,作敌我矛盾处理,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会场上尖厉的口号声响彻云霄:“打倒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罗竹风!”打倒反革命分子罗竹风!”“罗竹风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戴着红袖章的工宣队、军宣队和造反派,显得兴高釆烈。低头站在会场后排的“牛鬼蛇神”虽然也要跟着不断举手呼叫口号,心情却大不一样,他们只感到背上一阵阵阴风袭来,毛骨悚然。
就在宣布罗竹风为“反革命分子”的这次大会上,罗竹风站到麦克风前,表示感恩戴德,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对他的宽大处理。大会之后,罗竹风又被造反派押解到各个出版社,向各出版社被关在“牛棚”的“牛鬼蛇神”现身说法,要这些人以他为榜样,赶快老实交代“罪行”,不要自寻绝路。罗的这顶“反革命分子”帽子,一直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倒台为止。戴了“反革命”帽子,倒把他放回家了。每月发给三十元生活费.但是家中家具全部抄光,连一张床也不剩下,在空荡荡的房间里,他孤单一人睡在地板上。妻子、女儿躲去青岛避难,不敢回来。
监督劳动 认真研读《二十四史》
1969年到1972年这段期间,新闻出版系统人员全被赶到“五七干校”去劳动,“牛鬼蛇神”也都带去监督劳动,罗竹风当然也在其内。他虽然年过花甲,但劳动却很认真。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的五七干校,地点在上海郊县奉贤县的东海之滨。这里是一片长满芦苇的盐碱地,让这些知识分子披荆斩棘,建房立屋,种菜插秧,自力更生。
五七干校号称“一面劳动,一面学习”,所谓学习,就是批判斗争,你批我,我批你,或自己批自己。“牛鬼蛇神”无权批别人,只能低头挨批,但可以批别的“牛鬼蛇神”。那时三日一小会,五日一大会,不是揪斗这个,就是揪斗那个。罗竹风已经成了一只“死老虎”,造反派对他兴趣不大了,平时把他放在一边,但是每逢有什么批斗大会,一定要把他押上台去陪斗示众。徐铸成是他的老搭档,常常并排肃立在讲台边上,因为他们二人算是新闻出版系统最大的两个“牛鬼蛇神”。
1972年后,批斗的热潮有所降低,各个机构逐步成立,恢复工作。上海几个出版社虽然都在“砸烂”之列,但书还是要出的,于是合并成立一个大型的综合出版社,人数有一千七八百人之多,不仅是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出版社。工、军宣队和造反派,忙于争权夺利,分配位置,对“牛鬼蛇神”的监督管理也就有所放松,凡年老体弱的,都允许请病假,或者放在资料部门做点清闲工作。罗竹风也就以病为名,从五七干校放回上海。有次对朋友说,他趁这个机会,倒真读了点书,主要通读了《二十四史》。他发现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句名言,原来出自《明史·朱升传》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方才懂得历史确实不可不读。
“文化大革命”于1976年终告结束,罗竹风同其他“走资派”一样,恢复工作,精神焕发,老当益壮。先后担任上海市社联副主任、主任,主编《汉语大词典》,并在他的领导主持下成立编纂处和出版社,推荐青年人出任实职工作。上海出版系统的人都很尊敬他,见到他还是称他老局长。但是“文革”这段经历,在他一生中,无疑是刻骨铭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