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性足病的中医诊治
阙华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外科 上海 200032
糖尿病性足病的中医诊治
阙华发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中医外科 上海 200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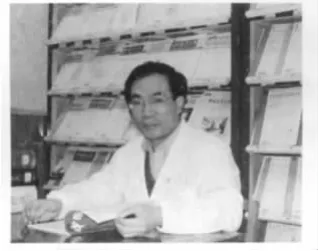
阙华发,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医外科学术带头人,附属龙华医院主任医师,中医外科科主任。担任中国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常务委员及疮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负责国家科技部“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行业科研专项、上海市科委科技攻关项目等15项课题,获国家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及三等奖、“颜德馨中医药人才奖励基金”中医一等奖等。发表学术论文52篇,出版专著20部。
糖尿病 糖尿病性足病 并发症 中医药疗法
糖尿病性足病是糖尿病主要、常见而严重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临床以下肢麻木、刺痛、发凉、间歇性跛行,继而出现溃疡、坏疽为特征,发病率高,危害大,治疗难度大,是糖尿病患者致残、致死和造成沉重医疗花费的主要原因之一。如何促进糖尿病性足溃疡愈合、降低截肢率、致残率和死亡率,并降低随之带来经济负担,是国际研究的热点,也是当今医学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糖尿病性足病的治疗是多方面、综合性的,包括多学科结合(内分泌科、肾科、神经科、骨科、眼科、外科),中西医结合治疗。目前西医治疗集中在药物治疗(控制血糖、积极控制感染、改善微循环、改善神经功能、纠正水、电解质、酸碱平衡紊乱、积极支持疗法等)、局部治疗(外用生长因子、新型敷料等)、外科手术(清创术、植皮术、血管重建、微创介入及截肢等)等措施,总体疗效不理想,截肢率及致残率较高;并且有治疗时未全面考虑不同阶段局部创面达到愈合的实际需求和条件的微环境,对不同局部创面缺乏适宜、积极的干预措施等治疗瓶颈。中医采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整体与局部辨证相结合,内治与外治相结合的分期辨证治疗方案,取得良好疗效,能加速溃疡创面愈合,降低高位截肢率和致残率,改善局部和全身症状,提高生命质量。
1 病因病机
糖尿病性足病属中医“脱疽”、“消渴”等范畴。我们观察了463例糖尿病性足病患者,平均发病年龄在70岁以上,糖尿病的平均病程>12年。提示高龄人脏腑功能失调,正气不足,肝肾之气渐衰;素体消渴,阴虚之体,水亏火炽,火毒炽盛,热灼营血,瘀血阻滞;又消渴之人,多喜膏粱厚味,而致湿浊内生,湿性滞下,湿热互结,复因感受外邪及外伤等诱因,以致气血运行失常,络脉瘀阻,四肢失养,瘀久化火蕴毒,热毒灼烁脉肉、筋骨而发为坏疽、溃疡。可见糖尿病性足病发病与湿、热、火毒、气血凝滞及阴虚或气虚关系最为密切。其病机特点是以虚实夹杂,本虚标实,正虚血瘀,络脉瘀阻为其本,湿热火毒为其标[1]。
我们在传承全国中医外科大家顾伯华先生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经过多年的临床实践,认为糖尿病性足病病机的特点是“因虚感邪(湿、热、毒),邪气致瘀,瘀阻伤正,化腐致损”,形成虚、邪、瘀、腐四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变化,从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病证。急性发作期,患者消渴日久,气阴亏虚,气虚则运血乏力,阴虚则血行艰涩,以致气血运行不畅,脉络阻滞,瘀阻更伤人体正气,正气虚则皮毛不固,易于感受邪毒,邪毒郁于局部,由瘀化热,由热成毒,促使邪毒愈来愈盛,正气愈来愈衰,病情趋向恶化;好转缓解期,邪毒衰退,十去七八,正气渐复,然正虚则无力推动血行或托毒外出而使毒滞难化,病情缠绵;恢复期,邪毒已退,正气来复,络脉瘀阻,病情渐渐向愈。可见本病发生、发展、变化,均存在“虚”、“瘀”之象。其中“虚”是受邪条件及血瘀伤正的结果,为发病的根本原因及决定因素;“邪”既可以是在“虚”的基础上的外因,又可以是血瘀后的病理产物,造成和加重“瘀”,为发病的重要条件;“瘀”为虚、邪的病理产物及生腐之源,为发病的关键;“腐”、“损”为疾病发展的必然结果及转归,从而出现各种不同的病证。因而“虚”、“瘀”、“邪”是糖尿病性足病溃疡创面难以愈合的关键环节。
2 治疗方法
2.1 基础治疗 ①控制血糖。应用胰岛素迅速控制血糖在6~8mmol/L之间,血糖控制良好者,逐步以口服降糖药取代胰岛素。②控制感染。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选择高度敏感的抗生素短期应用。③改善肢体血液循环。凯时10ug加入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1天1次。④支持疗法和对症处理。纠正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纠正贫血及低蛋白血症等。
2.2 中医内治
2.2.1 湿热毒盛证 多见于急性感染期及局部分期的黑期、黄期。趾(指)多呈湿性坏疽,局部破溃湿烂,肉色不鲜,脓液大量稀薄棕褐色,气味腥秽恶臭,或混有气泡,局部红肿灼热,疼痛剧烈,发展迅速,坏疽溃疡常蔓延至足部或小腿,或见多个穿通性窦道,伴发热,口干,食欲减退,小便短赤,大便秘结。血糖、血白细胞显著升高,舌质暗红或红绛,舌苔黄腻或光薄少苔,脉弦数或滑数。治宜凉血清热解毒,和营利湿消肿。方用四妙勇安汤合四妙丸加减。常用生地、赤芍、丹皮、当归、玄参、银花、黄连、蒲公英、地丁草、黄柏、土茯苓、苍术、生米仁、牛膝、生黄芪、皂角刺等。
2.2.2 热毒伤阴证 多见于急性感染期及局部分期的黑期。趾(指)多呈干性坏疽,局部干枯焦黑,溃破腐烂,疼痛。舌苔黄或黄腻,舌质红,脉细数或弦细数。治宜和营活血,养阴清热解毒。方用顾步汤或四妙勇安汤和增液汤加减。常用药物如生地黄、赤芍药、丹参、玄参、麦冬、石斛、黄柏、薏苡仁、蛇舌草、蒲公英、生黄芪、皂角刺、牛膝、生甘草。
2.2.3 湿热瘀阻证 多见于好转缓解期及局部分期的黄期。局部红肿消退,坏疽溃疡蔓延趋势已控制,脓液减少,臭秽之气渐消,坏死组织与正常组织分界渐趋清楚,疼痛缓解,发热已退,血糖已控制,血白细胞恢复正常,舌苔薄白或腻,脉细数或弦。治宜清热利湿,和营托毒。方用三妙丸、萆薢渗湿汤加减。常用药物如苍术、黄柏、薏苡仁、土茯苓、当归、生地、赤芍、丹参、桃仁、葛根、忍冬藤、牛膝、虎杖、生黄芪、皂角刺、生甘草。
2.2.4 气虚血瘀证 多见于修复愈合期及局部分期的红期、粉期。局部破溃,腐肉已尽,脓液清稀,疮面经久不敛,肉芽暗红,色淡不鲜,上皮生长缓慢,疼痛较轻,伴面色无华,神疲乏力,胃纳减退,心悸气短,畏寒自汗,舌质淡胖或暗红,舌苔薄腻,脉虚细。治宜益气活血,托里生肌。方用补阳还五汤、四君子汤合六味地黄丸加减。常用药物如生黄芪、党参、白术、茯苓、当归、丹参、赤芍、仙灵脾、熟地、山萸肉、牛膝、生甘草等。
2.3 中医外治 根据局部创面基底的颜色将创面分黑期、黄期、红期、粉期四期进行辨证治疗。
2.3.1 黑期(坏死组织期) 创面牢固覆盖较多黑色、干性坏死组织或焦痂。治以煨脓祛腐,选用金黄膏、红油膏等油膏厚敷,或外用清凉油乳剂等油性制剂外敷,使局部疮面脓液分泌增多,干性坏死组织或焦痂软化,出现溶解、脱落,促使疮面基底部暴露,后行蚕食疗法。
2.3.2 黄期(炎性反应期) 创面基底坏死组织较少,炎性渗出为主,创面基底组织明显水肿,呈黄色“腐肉”状,或有少量的陈旧性肉芽组织。①贴敷疗法:若局部疮周红肿灼热明显者,外用金黄膏;若局部疮周红肿灼热不甚或疮口周围发湿疹者,外用青黛膏;若局部皮肤发凉、瘀暗,外用冲和膏。②提脓祛腐:适用于腐肉未脱者。在脓腐多而难去之际,先短期选用八二丹掺布疮面,外用油膏提脓祛腐;在腐肉将脱尽,脓水已少时,或局部溃疡色泽较暗滞,可外掺九一丹。③祛瘀化腐:适用于腐肉难脱者。活血祛瘀药物如脉血康胶囊、蝎蜈胶囊等外用。④浸渍、湿敷疗法:适用于创面分泌物多,或味秽臭者。用黄连、马齿苋、土茯苓、土槿皮、明矾、红花等清热利湿解毒中药煎液浸泡患处,后湿敷患处。⑤切开引流及药捻引流:适用于脓肿形成或引流不畅者。宜切开排脓,或予药捻蘸九一丹引流;若合并气性坏疽或坏死性筋膜炎,必须根据原则进行有效处理。⑥拖线技术:适用于穿通性溃疡或窦道者。在常规消毒、麻醉下,可采取低位辅助切口,以银丝球头探针探查后,将4号丝线4~6股贯通管腔,每天搽九一丹于丝线上,将丝线来回拖拉数次,使九一丹拖入管道内,10~14d后拆除拖线,加垫棉绷缚法7~10d,管腔即可愈合。⑦灌注疗法:对脓腔较深或筋膜下、肌间隙感染灶相通,或创口小而基底脓腐未尽,药捻引流无法到位者,清热利湿解毒中药煎液灌注。⑧箍围疗法:对局部红肿,或患趾胖肿,经久难消者,用如意金黄散与清凉油乳剂油箍围。⑨蚕食疗法:适用于腐肉组织多者。在感染控制,血液循环改善,坏疽转成干性、坏死界线清楚的基础上,应分期分批逐步修剪清除腐肉,以不出血或稍有出血,无明显疼痛为度。一般对坏死组织及一些有碍肉芽、上皮生长的组织逐步修除即可,并尽量保护筋膜及肌腱组织。
2.3.3 红期(肉芽增生期) 创面基底新鲜红润,肉芽组织增生填充创面缺损,创缘上皮开始增殖爬行或形成“皮岛”。①生肌收口:适用于腐肉已脱,脓水将近者。外掺生肌散,外用白玉膏、红油膏。②煨脓长肉:适用于创面干性者。外用复黄生肌愈创油或清凉油乳剂。③活血生肌:适用于溃疡色泽苍白、暗红而不鲜润红活,新生肉芽及上皮生长缓慢者。外用活血祛瘀药物如脉血康胶囊、蝎蜈胶囊等。④湿敷疗法:适用于新生肉芽及上皮生长缓慢者。用黄芪、乳香、没药等益气化瘀生肌中药煎剂湿敷。⑤熏洗疗法:适用于新生肉芽及上皮生长缓慢者。用黄芪、乳香、没药等益气化瘀生肌中药煎剂熏洗。⑥垫棉绷缚疗法:适用于疮面腐肉已尽,新肉生长,周围组织有窦腔者。在使用提脓祛腐药后,创面脓液减少,分泌物转纯清,无脓腐污秽,脓液涂片培养提示无细菌生长,可用棉垫垫压空腔处,再予绷带加压缠缚,使患处压紧,每天换药1次,促进腔壁粘连、闭合。7~10d管腔收口后,继续垫棉加压绷缚10~14d,以巩固疗效。
2.3.4 粉期(上皮化期) 肉芽组织基本填满创面基底,上皮增殖、爬行,或皮岛间融合,呈粉红色。治疗同“红期”。
3 临床运用
由于糖尿病性溃疡受许多因素(病因、病程、既往治疗方式或方法、部位分布等)的影响,它们合并症多,病情复杂,治疗难度极大,很难找到与治疗创面相同的对照。故目前疗效评判多以患者自身治疗前后创面情况的变化进行对照。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治疗463例糖尿病性溃疡患者,治愈305例,显效82例,有效37例,无效39例(其中截肢26例,死亡8例),截趾48例。总有效率91.6%,痊愈率65.9%,痊愈显效率83.6%,截肢率5.6%,致残率10.4%,死亡率1.7%。305例痊愈病例,创面愈合时间为14~272d,平均(71.1±52.2)d;治疗后患者溃疡数量、深浅、范围、溃疡表面色泽、新生肉芽组织、新生上皮组织、局部肤色肤温、患肢麻木疼痛、运动障碍等局部症状均有明显改善(P<0.05),而且神疲乏力、纳呆、气短、面色不华、头晕目眩、口干咽燥、腰酸腿软、便秘、自汗等全身症状也显著改善。此外,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下降是2型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的危险因素,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将有助于预防和延缓2型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采用国内公认的“糖尿病患者生命质量特异性量表”,对患者进行治疗前后生活质量变化的调查。患者生活质量总分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改善(P<0.01),尤其在糖尿病对生理、心理影响以及治疗对患者影响这三个维度改善明显(P<0.05)。
进一步通过前瞻性、中心、队列研究,在控制血糖、控制感染等治疗的基础上,中医治疗组采用益气化瘀为主的综合治疗方案,西医治疗组采用手术治疗(动脉旁路术、球囊导管扩张术及支架植入手术、静脉动脉化手术、坏疽清创切除术、截肢术、截趾术等)。结果发现,中医治疗组80例中,痊愈24例,显效21例,有效21例,无效14例,其中截肢7例,截趾5例,痊愈率为30.0%,痊愈显效率56.3%,总有效率82.5%,截肢率8.8%,截趾率6.3%,创面愈合时间10~100d,平均(33.2±4.0)d;西医治疗组41例中,痊愈7例,显效14例,有效12例,无效8例,其中截肢2例,截趾10例,痊愈率为17.1%,痊愈显效率51.2%,总有效率80.5%,截肢率4.9%,截趾率24.4%,创面愈合时间12~46天,平均(28.7±4.3)d。两组比较,痊愈率、痊愈显效率、总有效率、愈合率、创面愈合时间、截肢率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中医治疗组的截趾率明显低于西医治疗组(P<0.01)。
中医治疗组治疗后积分合计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其中中医证侯量化单项积分,如溃疡数量、溃疡深浅、溃疡范围、溃疡表面色泽、新生肉芽组织、新生上皮组织、肤色、皮温、疼痛、运动障碍、发热(体温)、口干咽燥、神疲乏力、纳呆、气短、面色不华、自汗、头晕目眩、腰酸腿软、尿黄赤、便秘(P<0.01),以及脉率(P<0.05),中医治疗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而间歇性跛行距离、肌肉萎缩、麻木、动脉搏动、大便溏薄等症状,中医治疗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别(P>0.05)。西医治疗组治疗后积分合计较治疗前明显下降(P<0.01);其中中医证侯量化单项积分,如溃疡深浅、溃疡表面色泽、新生肉芽组织、新生上皮组织、间歇性跛行距离、肤色、皮温、疼痛、运动障碍、动脉搏动、口干咽燥、神疲乏力(P<0.01),以及溃疡数量、溃疡范围、纳呆、气短、头晕目眩、尿黄赤(P<0.05),西医治疗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明显下降;而肌肉萎缩、麻木、发热(体温)、面色不华、自汗、腰酸腿软、便秘、大便溏薄、脉率等症状,西医治疗组治疗前后无明显差别(P>0.05)。
中医治疗组与西医治疗组治疗后中医证侯量化积分比较,综合积分中医治疗组明显低于西医治疗组(P<0.05)。中医治疗组在改善局部证候(溃疡表面色泽、新生肉芽组织、新生上皮组织)以及正虚证候(神疲乏力、纳呆、头晕目眩、腰酸腿软、口干咽燥(P< 0.01),气短、面色不华、自汗(P<0.05))等方面优于西医治疗组;而西医治疗组在改善血瘀证候(间歇性跛行距离、动脉搏动(P<0.01),疼痛、运动障碍(P<0.05))方面优于中医治疗组;从卫生经济学指标而言,中医治疗组患者住院费用(13524.8±8474.3)元,明显低于西医治疗组(22256.10±10621.05)元(P<0.05)。
4 结 语
4.1 分期辨证,益气化瘀法贯穿治疗始终 “虚”、“瘀”、“邪”是糖尿病性足病创面难以愈合的关键环节,治疗当以补虚、化瘀、解毒为大法,通过去除“虚”、“瘀”、“邪(毒)”关键因素,促进创面修复愈合。结合《医林改错》:“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虚无力,必停留而瘀”,《医学衷中参西录》“因气血虚者,其经络多瘀滞”等理论,确立益气化瘀治疗法则,建立“益气化瘀法”贯穿疾病治疗始终的观点,形成益气化瘀法为主治疗糖尿病性足病内外结合的综合治疗方案。然临证当分清虚、瘀、邪(毒)的性质、轻重和主次等,在疾病不同阶段应有所侧重。并根据《理瀹骈文》所说:“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即内治之药,所异者法耳”。在同一治疗原则指导下,适时应用内治、外治法。通过内治,以调节整体而达改善局部的目的;通过外治,药力直接作用于局部而达改善局部的目的。
急性感染期,湿热火毒炽盛呈蔓延之势,治疗宜解毒祛邪为先,以清热解毒利湿化瘀的中药内服外敷。内治宜用大剂清热利湿解毒之品祛邪外出,制邪保津养阴,迅速截断扭转病势,常用药物如萆薢、黄柏、薏苡仁、土茯苓、金银花等,并兼顾益气化瘀,益气重用生黄芪以扶正托毒,使毒邪移深就浅,易于化脓,毒随脓泄,活血化瘀之品选用赤芍药、牡丹皮、虎杖、大黄等活血清热药物;好转缓解期,湿热之邪十去七八,正气亏耗,正虚难以鼓邪外出和推动血行,治当清热利湿解毒之品递减并渐停,益气化瘀和营托毒之品渐增。修复愈合期,邪热已去,正气不足,脉络瘀阻,治当益气扶正,化瘀生肌为主,佐以解毒祛邪等法内服外用,使气血充盈,托毒外达,正胜邪退而收功。常用药物如生黄芪、太子参、白术、茯苓、当归、赤芍药、川芎、丹参、桃仁、红花、地龙、水蛭、仙灵脾、山萸肉、黄精、熟地黄、补骨脂、鸡血藤、葛根等,并常用大剂量的黄芪与化瘀通络之品相伍,寓化瘀于补气之中,使经络通达,瘀浊易化。
4.2 全身整体治疗与局部外治相结合 糖尿病性足病是一种慢性、进行性、全身性疾病,患者多数病情重,多有心、脑、肾、眼病变,肺部感染、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紊乱等合并症,并发症多,治疗难度大。因此,急性发作期,病势骤急,病情重危,发展迅速,宜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全身整体治疗为主,控制血糖和感染是治疗的关键。中医内治宜祛邪为先,用大剂凉血清热利湿解毒之品祛邪外出,制邪保津养阴,迅速截断扭转病势,对溃疡创面不宜过早采取彻底清创、坏趾截除等手术疗法,否则,常使病情加重,溃疡蔓延扩大。但若合并深部感染、坏死性筋膜炎等局部病灶影响全身病情稳定,则应先治其局部后稳定全身。好转缓解期,血糖及感染得到有效控制,湿热邪毒已十去七八,正气亏耗,应根据溃疡性质,以局部外治法为主,并内服扶正和营托毒,清热利湿中药。如此,整体与局部兼顾,内治与外治结合,通过多个途径主动创造在不同阶段局部创面达到愈合的实际需求和条件的微环境,促进创面愈合。
4.3 注重局部辨证,分期选用综合外治法 糖尿病性足溃疡创面愈合是一个序贯、连续、综合的复杂过程。近年来国外基于对慢性创面的病理性愈合过程而提出的“创面床准备(wound bed preparation,WBP)”概念,即在系统、全面、综合评估(包括全身性评估、创面局部评估及创面愈合的不同阶段评估)的基础上,根据创面基底的颜色将创面分为黑期、黄期、红期、粉期,分别代表创面处于愈合过程中的组织坏死期、炎性渗出期、肉芽组织期、上皮化期;同时提出应根据创面的不同时期动态综合选择适宜的针对性局部干预措施,主动创造一个相对适于创面愈合的微环境(湿性环境),加速创面的愈合或为进一步进行手术达到创面的修复创造条件[2-3]。创面床准备是一个多步骤的系统的创面处理方案,尤其注重应用TIME原则,即T(tissue nonviable)坏死组织,I(infection or inflmmation)感染和炎症,M(moisture balance)湿性平衡,E(epithelialization)上皮化。它着重去除影响创面的细菌性、坏死性、细胞性负荷(即T、I),保持创面的湿性平衡,运用敷料、生物因子等创造一个相对适宜的创面微环境,加速创面愈合或为手术创造条件(即M、E)[4]。运用WBP理论治疗糖尿病性足溃疡等慢性难愈性创面,对临床有较好的指导作用,已取得良好的疗效[5]。
“外科之法,最重外治”,合理、适当、及时的外治是治疗糖尿病性足病、降低高位截肢率和致残率的关键。我们在全身辨证论治调节整体以改善局部的同时,尤其注重并细化创面的局部辨证,辨证动态选用外治法。黑期,外治可用煨脓祛腐法及蚕食疗法;黄期,根据腐肉组织多少及脱落难易,疮面脓液的形
质、色泽、气味以及量的多少,疮周组织红肿热痛等特点,选用提脓祛腐之升丹制剂外用及清热利湿解毒中药煎剂湿敷,以及贴敷疗法、蚕食疗法、浸渍疗法、拖线技术、灌注疗法、祛瘀化腐等;红期、粉期,根据创面肉芽生长及创周上皮爬生的情况,予生肌长皮的生肌散等外用及益气养荣、祛瘀生肌法中药煎剂湿敷或熏洗、垫棉绷缚、煨脓长肉、活血生肌等疗法。
4.4 活血祛瘀法在祛腐生肌中的应用 我们认为,慢性难愈性创面,由浅入深一般可分为脓腐层、瘀滞层、正常层。其中瘀滞层局部组织的发展变化是治疗关键,若腐肉持久不除,脓液淋漓不尽,则耗损正气,邪毒不尽,瘀滞层可腐坏,促使溃疡加深;若脓腐脱尽,邪毒清除,则正气复,气血通,瘀滞区肌平皮长,疮面愈合。糖尿病性足病病机特点是“因虚感邪(湿、热、毒),邪气致瘀,瘀阻伤正,化腐致损”,其中“瘀”为虚、邪的病理产物及生腐之源,为疮面难愈合关键。气血瘀阻经络,则可妨碍气血运行,阻碍气血生化之机,以致新血不生,正气无由恢复,使疮面难以得到精气津血濡养滋润,新肌不能生长;瘀久化火,致使热盛肉腐,血肉腐败,则液化成脓。如此,脓腐不尽,新肌不生,疮面久不愈合。因此,只有局部溃疡疮面气血运行正常,经络疏通,才能恢复正气,托毒外出,化腐排脓,生肌敛疮收口。我们提出“祛瘀化腐”、“活血生肌”观点,将脉血康胶囊、蝎蜈胶囊等活血祛瘀药物直接外用于局部疮面。在脓腐未尽时,能祛除局部气血凝滞,疏通经络,恢复正气正常运行,促使局部化腐排脓,毒随脓泄,邪去而正复,从而清除阻碍创面修复的腐,并为生肌创造条件;在脓腐已尽,新肌不生或难生之际,能使络脉畅通,血能载气,血流则气行,气血运行通畅,精气津液随气血运行至患部,滋润濡养皮肉筋骨,化生新肌,修复组织缺损,促使创面愈合。如此,调整局部功能状态,恢复局部气血正常运行整体环境,促使则腐肉组织逐渐化脱,新肌渐长,疮面愈合。
4.5 注重煨脓湿润法(煨脓祛腐法、煨脓长肉法)、拖线技术的运用 外治法中尤其要注重煨脓湿润法的适时运用。溃疡疮面修复需要一个有津液的湿性环境,津液有滋润和濡养皮肤肌肉等作用,津液不足,则皮毛、肌肉、骨胳、脏腑等失其濡润之功,一切药物难以到达靶组织,疮面修复难以进行。煨脓湿润法可以保持创面湿润,创造一个适宜在不同阶段局部创面达到愈合的实际需求和条件的环境,以利于坏死组织的脱落,并促进肉芽组织和上皮组织的新生,加速创面愈合[6]。祛腐阶段,疮面呈干性坏死或结痂,宜选用油膏厚敷或油性制剂外用以煨脓祛腐,加速干性坏死组织溶解或结痂软化,促使疮面基底部暴露;生肌阶段,疮面较干,可用油性制剂如清凉油乳剂、复黄生肌愈创油盖贴以煨脓长肉,促进肉芽组织及上皮组织新生。
此外,对穿通性溃疡或窦道,传统治疗采用切开疗法,损伤组织多,瘢痕大,修复时间延长,我们基于中医学“腐脱肌生”创面修复理论,在药捻疗法与挂线疗法基础上,借助“微创”治疗理念,运用拖线技术于治疗中,有组织损伤小、愈合快、瘢痕小、痛苦少等优势,从而缩短疗程,提高疗效。
4.6 重视骨与肌腱创面暴露的处理 糖尿病性足病病的特点之一是多伴骨病及病变沿肌腱的走行而发展,因此,骨或肌腱裸露创面的处理是临床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明显坏死的肌腱和骨骼,可在失活的组织处外用九一丹等提脓祛腐中药,应用“蚕食疗法”逐步清除坏死组织,并注意保留肌腱和骨骼周围尚未失活的组织;对没有明显坏死的肌腱和骨骼,可在裸露处外用生肌散、脉血康胶囊、红油膏纱布、复黄生肌愈创油、黄芪注射液等补虚化瘀生肌的中药;如此,促进新生肉芽组织和上皮组织生长,将裸露的骨质或肌腱覆盖,促使创面完全愈合。
[1]阙华发,唐汉钧,向寰宇,等.益气化瘀为主综合方案治疗糖尿病性足溃疡临床观察[J].上海中医药杂志,2010,44(1):14-17.
[2]FalangaV.Classifications for wound bed preparation and stimulation of chronic wounds[J].Wound Repair Regen,2000,8: 347-352.
[3]Krasner D.Wound care:how to use the red-yellow-black system[J].Am J Nurs,1995,5:44-47.
[4]Schultz GS,Barillo DJ,Mozingo DW,et a1.Wound bed preparation and a brief history of TIME[J].Int Wound J,2004,1:19 -32.
[5] 李新强,朱家源,陈东,等.应用“创面床准备方案”局部处理糖尿病足溃疡的效果分析[J].中国临床康复,2006,10(24):48-51.
[6] 阙华发,陆德铭,唐汉钧.外科煨脓长肉湿润法研究[J].中华中医药学刊,1999,18(2):3-5
2010-12-01
·论 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