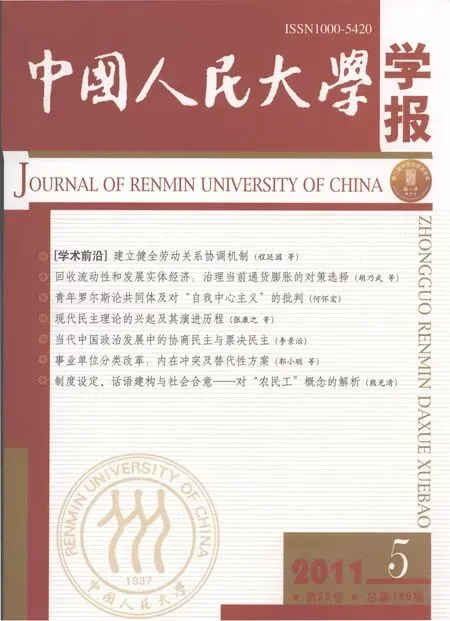从北魏龙门石窟艺术透视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
黎 臻 袁济喜
在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的研究中,关于南北美学与文艺精神的交融是一个难题。最典型的问题是:北朝石窟艺术的秀骨清像、风神潇洒,何以与南方的玄学与佛学精神之美如此契合?李泽厚先生最早在《美的历程》第六章“佛陀世容”中提出:“今天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尽管都在北方石窟,但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当时作为整体的中国一代的精神风貌。”[1](P115)而南朝的美学精神是当时的主流。但此书并没有对这个结论做出具体的论证,此后的相关论著也大都付之阙如。如果不能从学理上证明南北审美文化交融与北朝石窟艺术精神的关系,则魏晋南北朝美学与艺术的研究始终无法前行,可能陷入独断论的泥淖之中。本文以北魏龙门石窟为中心,依据现存的相关文献与文物遗迹,对此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冀推进此方面的研究。
一、龙门石窟的文化溯源
龙门石窟的文化源头,与洛阳的特殊形态直接相关。北魏龙门石窟,是北魏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石窟寺开凿的重点。其佛像造像、供养菩萨和供养人的形象都已经由云冈石窟中雄浑粗犷的键陀罗式和凉州模式等北方少数民族风格一变而为崇尚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审美情趣。洛阳作为中原文化的集聚地,有深厚的积淀和内涵,在北魏时期又受到南方文化的泽溉,风雨沧桑,历经陶染,为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此,我们以洛阳为中心来探讨南北文化在这一时期的交汇、升华。
洛阳地处中原腹心地带,自西周初年开始,就被认定为“天下之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它在历朝历代中都处于都城或经济、军事重镇的地位。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定都洛阳,洛阳的文化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曹魏时期,曹丕称帝亦建都洛阳。魏正始年代,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与清谈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的显学。他们所开创的“正始之音”融合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文化,建构了魏晋风流的精神渊薮。西晋统一后,许多南方名士入洛,使洛阳文化注入了南方文化因素,陆机、陆云兄弟以及顾荣等江南世族名流的迁入,更使南北文化交流呈现出新格局。
西晋南渡,士族名流南移,洛下之风泽被江南。魏晋时期著名的玄学清谈,便是以洛语为“正音”,金声玉振,琴瑟相和,给人以音乐美的享受。东晋迁于江左,时人每提及洛阳,便有“寄人国土,心常怀惭”之感。《南史·谢恂传》中谈到:“(王彧)尝与(谢)孺子宴桐台,孺子吹笙,彧自起舞,既而叹曰:‘今日真使人飘摇有伊、洛间意。’”[2](P529)伊洛玄风在东晋乃至南朝遗韵犹在。而洛阳在经过五胡乱华时期的萧条之后,到北魏时重新振兴。魏孝文帝积极学习汉民族文化,将洛阳深厚的历史底蕴重新恢复。东晋南朝的士族们秉承着优秀的汉文化继续发展。对于谁代表了汉文化的正宗,南北方各持有自己的观点。北魏杨炫之所著的《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景宁寺”条记载了这样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
洛阳青阳门外孝义里北是车骑将军张景仁宅。张景仁是会稽山阴人。北魏正光初年(公元520年)随同萧宝夤归入北魏。永安二年(公元529年),萧衍派主书陈庆之送北海王元颢入洛阳僭称帝位。张景仁在南时与陈庆之有旧交,便邀其至家。当时的司农卿萧彪、尚书右丞张嵩、中大夫杨元慎、给事中大夫王眴都在座。陈庆之醉酒之中嘲笑:“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相承,当在江左。秦朝玉玺,今在梁朝。”[3](P105)杨元慎正色反驳:“江左假息,僻居一隅……礼乐所不沾,宪章弗能革……我魏膺箓受图,定鼎嵩洛,五山为镇,四海为家。移风易俗之典,与五帝而并迹,礼乐宪章之盛,凌百王而独高。”[4](P105-107)杨元慎将江左地区的地理位置、环境、语言风俗、历史等细数了一遍,认为洛阳原为中原文化正统,而南方则是蛮野之地,对于江南文化不屑一顾甚至鄙夷。杨元慎的义正词严,让陈庆之无言以对。后来陈庆之回朝之后,“钦重北人,特异于常”。他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5](P108-109)他在北地看到的是礼仪富盛,人物殷阜,因此对北方的看法发生转变,“羽仪服式悉如魏法,江表士庶竞相模楷,褒衣博带,被及秣陵”[6](P109)。
杨元慎是中原士族,属弘农杨氏。“元慎清尚卓逸,少有高操,任心自放,不为时羁。乐水爱山,好游林泽。博识文渊,清言入神,造次应对,莫有称者。读老庄,善言玄理。性嗜酒,饮至一石,神不乱常。慷慨叹不得与阮籍同时生。”[7](P109)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便是魏晋时期中原地区的名士风流。《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景明寺”条记载了“文宗学府”的邢子才,“衣冠之士,辐辏其门,怀道之宾,去来满室。升其堂者,若登孔氏之门;沾其赏者,尤听东吴之句”[8](P116)。正是这些文化名流,使得北魏后期洛阳的文化繁荣,像陈庆之这样的人物也发出“北人安可不重”的感叹。其实,杨元慎是将北魏胡人政权赋予中原汉族文化的正统,显然已经置换了其中的政权文化内涵,说明中原文化传统已经成为北魏政权的正宗。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文化交融经由北魏政权的主观努力,大大向前推进,呈现出互相纠结、难分主客的情势。
洛阳深厚的中原汉文化底蕴,使得龙门石窟在此时期的开凿也带有强烈的汉化色彩和南方文化的审美内涵。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造像与传神
古阳洞是龙门石窟开创最早、内容也最丰富的北魏皇室洞窟,在石窟中可“览先皇之明踪,睹盛圣之丽迹”(《邑主仇池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记》)。古阳洞下层列龛的佛教造像以及本尊右侧菩萨像等都是面相清秀,眉目如画。北壁靠下的礼佛图浮雕,前有身披袈裟的比丘尼引导,其后的供养人是两位长裙曳地的贵族妇女,随后依次是侍女和拱手侍从。画中人物修长瘦削,长裙飘逸,清貌秀容。宾阳中洞亦富丽堂皇,“它上承云冈昙曜五窟造像那种大体大面,概括洗练,强调外轮廓线,从而造成雕塑整体感极强的显著特点;又下启隋、唐造像圆润、丰满,更加写实,从而渐次世俗化的趋势”[9](P95)。圆雕大像雄健朴实,礼佛图浮雕精致入微。本尊释迦牟尼佛面相清秀,嘴角上翘而微笑;西侧主佛像带有清癯秀美的气质,瘦肩细脖,袈裟似褒衣博带。随着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早期的平城式样开始逐渐衰落,在与汉族逐步融合的过程中,这种“秀骨清像”成为南北的审美标准,清秀的佛像逐渐流行起来。
其实,早在西晋时代的洛阳就已经风行此种褒衣宽袖、潇洒不羁的形象。洛阳出土的几件墓碑就表现出清丽纤巧的艺术风格。“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刘氏墓碑……碑右侧连体石面上刻一高冠袍服即褒衣博带者外向,双手擎羽葆。”[10](P71)另张纂墓碑石刻上亦有高冠袍服侍者。北魏龙门石窟“秀骨清像”式的供养人物的形象可以说是这些人物形象的直接继承。洛阳的魏晋审美气质经过五胡乱华时期直至北魏,一直延续下来。
同样,北魏龙门石窟造像艺术的清秀气质,在南京栖霞山石窟中可以大量见到。南京栖霞山建有栖霞古寺,隐士明僧绍在南齐永明元年(公元483年)时舍宅为寺,名曰“栖霞精舍”,明僧绍之子为了纪念其父,与玉智度禅师合作开凿了三圣像。据记载,三圣像佛龛上出现佛光,引来齐梁贵族凿石造像,栖霞山千佛岩便形成。其中的摄山大像是栖霞寺石窟中的主佛,佛身连座高四丈,是由齐梁著名僧人僧祐主持修建的。这些佛教造像多面容清瘦秀劲,嘴角上弯露出微笑,衣着褒衣博带、衣褶层叠,优雅端庄,充满了沉静超然的气度。由此可见,南北造像中的审美精神追求互相渗透,异曲同工,浑然一体,说明南北审美文化的融合已趋于高度成熟。
(二)维摩诘像与审美解读
南北审美文化的交融,我们还可以从维摩诘人物造像的美学情趣中探真。维摩诘是早期佛教中的俗中求真、教化尘劳的大乘居士。维摩诘出入于帝王人臣、君子庶人中,一面随时行乐、自我修行,一面教化别人认知“四大皆空”、“一切皆空”从而普遍得度。作为亦僧亦俗的审美人格典范,这种审美人格与当时玄学家们于名教情欲中追求自然的生活情趣大相契合。维摩诘位极人臣、富甲天下,但又是一位超尘拔俗的“菩萨”,这种双重身份和潇洒的审美生活方式正是魏晋名士们十分羡慕的。鲁迅先生曾说,魏晋士大夫爱不释手的三种小玩意之一便是《维摩诘经》。①鲁迅先生在《吃教》一文中说:“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见《鲁迅全集》,第五卷,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在龙门石窟宾阳中洞前壁雕像最上层就是维摩诘变的内容。据《维摩诘所说经·方便品》所记,维摩诘以佛法教化众人,伪装患病便于宣传,当世人前来问疾时,维摩诘便广说四谛。《文殊师利问疾品》中便是文殊师利前往问疾时,维摩诘在病室中阐述教理,与文殊师利问答。因此,在很多石窟中常常有维摩诘与文殊师利相对而坐的形象。宾阳中洞这一幅便是。维摩诘斜倚在案几上,张口奋髯,从容论道,表现出了南朝士人的清谈气质和艺术风格,大有南方士大夫“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11](P148)的情状。在云冈石窟第七窟也有身着居士装、手执麈尾的维摩诘像。麈尾是魏晋名士清谈时的重要道具,维摩诘手执麈尾论道,已与清谈名士无异。维摩诘的题材在佛寺壁画中十分兴盛。顾恺之首创维摩诘“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12](P110),使得维摩诘居士带有了中国士大夫的姿态与气质,此后形成一种画维摩诘的风尚。陆探微、张僧繇等都模仿这种风格,至宋代《维摩天女》,维摩诘也是作病容。
这种魏晋士人的审美趣味反映在南朝绘画艺术的领域中,便是由顾恺之开始描绘的维摩诘清瘦遒劲的气质与风度。东晋绘画自顾恺之以来,强调“以形写神”,“神”不仅是指精神生命,更是一种审美意义,是魏晋所追求的超脱自由人生境界的感情表现。它强调的是人作为感性存在的独特的“风姿神貌”。维摩诘恰好是这种典型人物。对此,唐黄元之在《润州江宁县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中评顾恺之画的维摩诘,曰:“目若将视,眉如忽嚬,口无言而似言,鬓不动而疑动。”[13](P1606)这正是作品传“神”的表现。顾恺之《洛神赋图》线条简洁流畅,人物飘逸,带有士大夫超然的理想人格,表现出来的也正是此种风神。
南方著名的佛教雕塑家戴逵,绘画情韵绵密,风趣巧拔。他认为古来制造佛像形质朴拙,不足以让供奉者“动心”,于是悄悄听众人论佛,将其褒贬言语详加钻研,积思三年,刻为佛像,使之如有神明,令众人膜拜。《世说新语·巧艺》中载:“戴安道中年画行像①《大唐西域记·屈支国》:“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语戴云:‘神明太俗,由卿世情未尽。’戴云:‘唯务光当免卿此语耳。’”[14](P387)佛像融入了亲切自然的人间情感,佛像即人像,其审美风格也属于当时社会的流行风尚。
另有南朝宋时画家陆探微,所作之画秀骨清像,似觉生动。这种“秀骨清像”的审美风格,就是包含了容止之美和人格之美的双重内涵。绘画对象在外形上的体貌瘦隽、骨像清朗、衣冠清举飘扬,强调骨体表现。作画之人需风神超迈、笔迹劲力,才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同时画作中需要表现出一种清通、超拔的精神人格之美。这是谢赫六法中所要求的“骨法用笔”,也与魏晋以后追求人格的超脱和风清骨俊、潇洒飘逸的审美内容相一致。黑格尔指出:“希腊诸神所表现的理想却是一些个别体,在普遍典型的范围之内仍各有特性。理想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所要表现的那种心灵性的基本意蕴是通过外在现象的一切个别方面而完全体现出来的,例如仪表,姿势,运动,面貌,四肢形状等等,无一不渗透这种意蕴,不剩下丝毫空洞的无意义的东西。”[15](P221)魏晋南朝时期的绘画及雕塑艺术开始摆脱两汉时雄伟朴拙又带有浪漫神秘色彩的特点,开始变得重视气韵风度和超然飘逸的精神美,而且精细臻丽、绵密巧致。这种精神美融进佛教造像艺术中,自然会影响到北魏的造像艺术。
二、南北文化因素如何与龙门石窟造像艺术汇合
龙门石窟中蕴藏着南方的审美精神。然而,南北文化元素是如何汇集于此的?这是关键之所在。为此,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南人北奔
士人是南北文化交流的主体。在晋宋之际,由于战争及政治斗争的原因,大量南人流亡北魏,其中包括东晋宗室人物和南方大族。他们给北方文化带入南方文化的元素。刘裕灭后秦,司马休之父子率百人入魏,其中有渤海刁雍“性宽柔,好尚文典……又泛施爱士,怡静寡欲。笃信佛道”[16](P871);王慧龙出自太原王氏,北朝贵族崔浩以女妻之,并因为其鼻子大,而称“真贵种也”。这些与东晋宗室人物一起入魏的大族士人都在北魏受到礼待,对北魏皇室及贵族阶层的审美心态与风尚有一定的影响。南朝士人将江左谈论义理的风尚带入北地,使得魏晋时期的庄老玄学、经史之义,以及魏晋风度的举止风仪、雍容雅量都在北魏审美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影响到帝王的文化修养与审美风尚。北魏孝文帝读经史庄老,好诗赋铭颂,亦擅长佛学。宣武帝元恪有大度,喜怒不形于色,善于讲论,尤长释氏之道,又端严若神,诚然一位南朝士大夫的形象。当时,一些北方汉人和鲜卑汉化的王公贵族对于玄学清谈都习之不辍,蔚为风尚。很多北魏贵族或士人,在与北奔的南朝士人交往的时候,受到南士的影响,而审美风尚变得偏向于南方,更加有南士风度。
《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条“尚书令王肃”中记载:王肃属琅琊王氏,曾经仕于萧赜。后来由于他的父亲王奂及兄弟为萧赜所杀,于是他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奔入北魏。当时,魏孝文帝正在筹建洛阳,因为王肃博识旧事,所以多参与造制之事。可以推测,当时北来的南人,不仅在日常的学术文化及生活习俗方面影响北人,而且还多参与洛阳的造制活动,也使得其审美风格向宫殿、佛寺等建筑方面渗透。
(二)互相遣使
北魏时期,南北朝廷的正式往来主要通过互相遣使聘问来完成,而使者的聘问也是南北文化互相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途径。南齐永明年间,南北几乎每年都有互相聘问往来,永明九年(公元491年)更是春夏秋冬各一次。使者的往来,对南方文化的北渐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南齐使者有辅国将军刘缵,通直郎裴昭明,平南参军颜幼明,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司徒参军刘斅,车骑参军沈宏等,其中裴昭明是裴松之之孙、南齐太学博士,范云为萧子良幕中“竟陵八友”之一。他们在使魏期间,对北魏的文化有了重要的影响。延至梁时,南北遣使更是出现盛大场面。《北史·李谐传》记载:“既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矜,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梁使每入,邺下为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礼赠优渥,馆门成市。宴日,齐文襄使左右觇之,宾司一言制胜,文襄为之拊掌。魏使至梁,亦如梁使至魏,梁武亲与谈说,甚相爱重。”[17](P1604)南使入北,邺下倾动,子弟聚观;北使遣南,梁武亲与谈说,甚为爱重。这正是南北文化在使者交流上凸显出来的活力。陈时又有姚察,兼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北周,北周刘臻亲自将《汉书》有疑问的地方拿去请教。可以见出,使者的交流有益于北方学术文化的发展。
(三)艺术交流
北魏时期,艺术家的交流进一步加强。我们以北魏画家蒋少游为例。蒋少游,“敏慧机巧,工书画,善画人物及雕刻。虽有才学,常在剞劂绳墨之间,园湖城殿之侧,识者叹息,少游坦然以为己任,不告疲劳。官至将作大匠、太常少卿、前将军、都水,兼此四官。赠龙骧将军青州刺史,谥曰质”[18](P382)。蒋少游不仅是善画者,也可以说是北魏文明的设计者。他一生跟随孝文帝,参与了北魏的冠服、宫殿、陵寝、石窟等的设计和规划,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合流与交融,对南北审美文化的糅合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的功绩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服饰。《魏书·蒋少游传》提到:“及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冠服之成,少游有效焉。”[19](P1971)在冠服的设计中,蒋少游的功绩不可磨灭。他推崇新式样,六年之后设计完成,盛兴于世。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20](P322)这符合魏晋时期日趋宽博的服饰特点。云冈石窟后期佛像及北魏龙门石窟佛像,都是这种褒衣博带似的形象,可见这种影响是有史可稽的。
第二,摹写宫掖。北魏孝文帝时开始修建太庙、太极殿等,并开始准备迁都洛阳。他派遣蒋少游去洛阳“量准魏晋基趾”,并于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派遣他为李彪副使出使南齐,暗中观察南齐都城建康的城市布局与规划等。在《南齐书·魏虏传》中有一段详细记载:
(永明)九年,遣使李道固、蒋少游报使。少游有机巧,密令观京师宫殿楷式。清河崔元祖启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输之思。宋世陷虏,处以大匠之官。今为副使,必欲模范宫阙。岂可令毡乡之鄙,取象天宫?臣谓且留少游,令使主反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许。少游,安乐人。虏宫室制度,皆从其出。[21](P990)
蒋少游出使南齐,“图画而归”,将建康城的制式与北方城郭结合起来,为洛阳城的建造提供了楷式。洛阳新城是魏晋文化、平城塞北文化、江南文化以及佛教文化碰撞与交融的结果。蒋少游在洛阳新城的建立上起了重要的作用。
蒋少游也是北魏一位名画家,《历代名画记》中将蒋少游列于后魏能画者第一人。《水经注》中有记载:“(皇信堂)堂之四周,图古圣、忠臣、烈士之容,刊题其侧。是辨章郎彭城张僧达、乐安蒋少游笔。”[22](P313)可以想见,善画人物与雕刻的蒋少游,作为匠作大将,在孝文帝大力开凿龙门石窟、兴建佛寺的时期,定会参与到其中。他出使江南的经历让他的设计风格及图画风格都带有南北审美的交叉融合。在北魏还有诸多能工巧匠,为宫殿的制作、佛寺的建造等作出了贡献。“初,高宗时,郭善明甚机巧,北京宫殿,多其制作。高祖时,青州刺史侯文和亦以巧闻,为要舟,水中立射……世宗、肃宗时,豫州人柳俭、殿中将军关文备、郭安兴并机巧。洛中制永宁寺九层佛图,安兴为匠也。”[23](P1971-1972)这些能工巧匠在匠作大将麾下,为洛阳城的建造和佛寺石窟等的创作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蒋少游在对龙门石窟的创制与审美风尚的引导中,也将南朝文化融入其中,使得北魏中晚期的佛寺石窟风格呈现出汉民族的中原及江南文化特色。
(四)南北僧人交往
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宗教却往往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在这种情形之下,艺术确是在为和它不同的一个部门服务。但是只要艺术达到了最高度的完善,它所创造的形象对于真理内容就是适合的,见出本质的。”[24](P130)龙门石窟体现出来的佛教美学意蕴是直接从佛教生成出来的,佛教的传播是通过南北僧人的交往而得以实现的。
佛教初入中国,分南北两条路径。北方僧人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原始风貌,而南方佛教与儒道合流,僧人也显现出江南士人的风尚。高僧道安师从佛图澄,早年与其徒众一直辗转活动于河北、山西一带,后到达襄阳、江陵。不仅受到了桓豁、朱序、郗超之流的达官贵人以及习凿齿这些名士们的礼敬,而且还受到了东晋皇室的礼遇。道安在长达15年(公元365—379年)的襄阳时期,不仅每年要讲两遍二十卷的《放光般若经》,而且还从事于注述等其他各种宗教学术活动,后又回到长安继续讲学与译经。
东晋高僧慧远最早在北方追随道安,后居庐山,成为南方佛教的首领。他与北方佛教中心人物鸠摩罗什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促进了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姚秦弘始三年(公元401年)冬,鸠摩罗什到达长安,慧远主动致书通侯,向其请教。其时,与慧远亲近的僧人慧观听闻鸠摩罗什入关,便自南徂北,访覈异同,风神秀雅,思入玄微。亦有僧人竺道生初入庐山,幽栖七年,后与慧叡、慧严同游长安,从鸠摩罗什受业。这些僧人都是在慧远与鸠摩罗什所处之间游历,对南北佛教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鸠摩罗什回龟兹,慧远作书挽留,还将晚年著作《性法论》送给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也把最初译出的《大品般若经》回送。二人对《大智度论》还作了往返酬答和切磋,后人辑成了《大乘大义章》。慧远与鸠摩罗什的联系使得南北佛教学术频繁交流。
魏晋时期的玄学传统,在佛教介入之时对其包容。僧人们在与南方士大夫阶层的交往中也出释入道,带有浓郁的士大夫气质。高僧支道林与江南名士殷浩、郗超、孙绰、袁宏、王羲之等都交往密切,他注的《庄子·逍遥游》让诸名士多加赞赏、叹为观止。这种僧人的名士化对佛教造像中的秀骨清像、隐机妄言等的士大夫形象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其时有很多僧人四处游学,见识了诸多不同区域的审美文化,对于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僧人昙度游学建康,造访徐州,后受北魏孝文帝邀请到平城讲法,学徒自远而至千余人。而沙门释僧诠,为北土学者之宗,后铺筵大讲,化洽江南,姑苏之士并慕德归心。这些由南入北或由北入南的僧人们促进了南北佛教交流,可以推测,他们的交往对南朝佛教艺术的推广亦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审美趣向携带着浓厚的南朝士人的气质,与佛经义理等一同被僧人们介绍到北方,同时也与北方的自我特征相结合,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见的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特点,其中以北魏迁都洛阳之后开凿的石窟和营建的佛寺为主要代表。《洛阳伽蓝记》卷四“城西永明寺”条记载僧人菩提拔陁:
今始有(歌营国)沙门菩提拔陁至焉。自云:“北行一月,至句稚国。北行十一,至典孙国,从典孙国北行三十日,至扶南国……从扶南国北行一月,至林邑国。出林邑,入萧衍国。”拔陁至扬州岁余,随扬州比丘法融来至京师。京师沙门问其南方风俗,拔陁云:“……凡南方诸国,皆因城郭而居,多饶珍丽,民俗淳善,质直好义,亦与西域、大秦、安息、身毒诸国交通往来。或三方四方,浮浪乘风,百日便至。率奉佛教,好生恶杀。”[25](P173-175)
菩提拔陁是一位外国僧人,从南方历经诸国进入北魏洛阳,并与洛阳沙门交谈南方风俗等事。这样一位历经多国的僧人,又在江南地区停留过不短的时间,且以江南文化为主题与洛阳僧人交谈、问答,也形成了南方文化北渐的一种重要途径。
北魏时期,佛教的西域传入线逐渐为南方海路传入线所替代,而佛教造像风格,也随海路传入线进入南朝,这种南方文化北渐的过程也成为一种必然。5世纪初时嚈哒人进犯笈多王朝,在键陀罗地区统治了60年(公元460—520年),终结了键陀罗艺术。其时,盘踞在高昌的沮渠政权和柔然与北魏亦互有敌意,因此,北方的佛教东传之路在北魏文成帝以后便停滞了。自北魏孝文帝改制以后,造像风格便主要从南线传入。刘宋时期,游历狮子国、阇婆国的罽宾高僧求那跋摩于广州上岸,在灵鹫寺宝月殿北壁画罗云像。罽宾僧人昙摩密多也“斩石刊木,营建上寺……于是息心之众,万里来集,讽诵肃邕,望风成化”[26](P122)。很多天竺僧人同他们一样,都是由海路东来,在建康和沿海地区建造佛寺。北方佛教东传的传统之路的寂灭和南方海路佛教造像的频繁东来,使得北方佛教的主要造像风格更加依赖于南方,这也是魏都洛阳石窟造像风格南化的一个原因。
同时,僧人与佛教造像的关系也是其审美风尚寄寓于造像艺术风格中的一个方面。佛教造像,在魏晋之后逐渐兴盛,至东晋南朝时期达到高峰,北朝造像之风也兴盛一时。当时的许多高僧,都利用佛像来宣传佛理,创作的佛教造像理论蕴含了深刻的美学精神。东晋名僧慧远怀着对佛法的虔诚之心,与门人集重资造了东晋著名的丈六金像。佛法无边,可以通过佛像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以满足人们的膜拜。慧远指出,佛教造像既可以怀远存近、道福兼弘,而且还可以“四辈悦情,道俗奇趣”(《晋襄阳丈六金像颂》),正是通过这样的造像活动以及赞颂佛像,从而达到宣扬佛法、向人们传递佛教信仰的目的。慧远在《万佛影铭》中谈到:“法身之运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图终而会其成。理玄于万化之表,数绝乎无形无名者也。若乃语其筌寄,则道无不在。是故如来,或晦先迹以崇基,或显生涂而定体;或独发于莫寻之境,或相待于既有之场。独发类乎形,相待类乎影,推夫冥寄为有待耶?为无待耶?自我而观,则有间于无间矣。求之法身,原无二统,形影之分,孰际之哉?而今之闻道者,咸摹圣体于旷代之外,不悟灵应之在兹。徒知圆化之非形,而动止方其迹,岂不诬哉?……神道无方,触象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万佛影铭》,《广弘明集》卷一五)法身(佛的性相)是超乎物外、无形无名、无所不在的,因此如来佛显迹于莫寻之境、既有之场。慧远让人绘画图影,刻铭赞颂,正是大力宣扬“法身本无二统”,佛身灵迹无处不在、神妙广大的观点。慧远在绘制佛影时,曾派学生去请谢灵运作铭,谢欣然应允。谢灵运在铭文序中说道:“摹拟遗量,寄托青彩,岂唯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佛影铭》)阐发了造影的重要性,阐明绘画图影是为了传写佛的神明。在铭中,谢灵运还描绘了慧远所建佛影台之美:“周流步栏,窈窕房栊。激波映墀,引月入窗。云往拂山,风来过松。地势既美,像形亦笃。彩淡浮色,群视沈觉。若灭若无,在摹在学。由其洁精,能感灵独。”(《佛影铭》)由此可见,慧远的造像美学精神集中在形神之辨上,他集中宣扬的是形尽神不灭论,他的佛学精神更多地投注在佛像造像美学理想与旨趣上面。东晋名僧支遁也推动了弥勒信仰和弥勒造像。支遁作《弥勒像赞》对弥勒从少时升迁到成佛的过程进行了歌颂,并描绘了弥勒所在的美誉境界。其时弥勒信仰日益广泛,弥勒佛造像在各地供奉,后来在剡山石城寺的弥勒佛石像正是在支遁的像赞及弥勒信仰中发展而来的。
三、结语
南朝绘画艺术的中心是佛画,佛画与雕塑艺术的审美风尚受创作者的审美倾向及社会主流审美倾向的影响。南方士人影响下的佛学及名僧,是佛画艺术的对象和典范。这种带有浓烈士人气息和玄学气质的佛教造像因此而产生。这是创作主体与欣赏主体双方都共同具有的审美倾向,这些审美趣尚在北魏龙门石窟造像中也可以窥见一斑。在南北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南方绘画对北方审美精神和艺术形式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北魏佛教造像“令如帝身”,它的造像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情感。虽然我们今天无从考见许多艺术家的事迹,但毫无疑问,北魏龙门石窟风格迥异的清秀气质,突出地反映了当时的艺术特色和人们的审美情感。在南方绘画中,从顾恺之到陆探微的画风,都在魏晋风流的意蕴之中。由于南朝流亡士人的北奔、互相遣使来往等,南北文化逐渐交流融合。同时,西域佛教东传在北方的线路被中断,也使得南方海路被频繁使用,北魏时期的造像风格主要由海路传入南方再北传,这就在一个方面促成其佛教造像风格南式化。而在画家、雕塑家等巧艺之人的南北交流以及佛教僧侣的游方带来的南北两地佛教审美特点的传播,亦使得龙门石窟造像风格具有浓厚的南方士族文化的气质。这促成了佛教初入中国即与南方名士风流巧妙结合,从而得以在汉民族文化的土地上立足。正是这样,从佛教造像的艺术风格也渐趋人间化、士人化,充满了形神之美,开启了唐代佛教艺术的风韵。透视南北朝审美文化的交流,可以见出中华文明是在历史的交流融合中走向成熟,臻于内在和谐的。
[1]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
[2]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
[3][4][5][6][7][8][25]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洛阳伽蓝记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
[9]宫大中:《龙门石窟艺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0]宫万琳:《北魏龙门“秀骨清像”与西晋墓志画像》,载《美术观察》,2002(1)。
[11][20]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
[12][18]张彦远撰,冈村繁译注:《历代名画记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3]董诰等编,孙映逵等点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4]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15][24]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6][19][23]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
[17]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1]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2。
[22]郦道元著,陈桥驿校正:《水经注校正》,北京,中华书局,2007。
[26]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