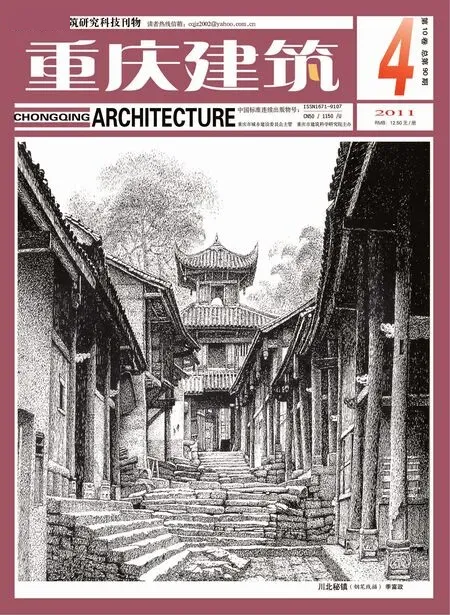走向“公民建筑”再思考——兼与周榕商榷
朱涛

争鸣
何为“公民建筑”?
很多人追问:到底什么是“公民建筑”? “‘公民建筑’是指那些关心民生,如居住、社区、环境、公共空间等问题,在设计中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并积极为现时代状况探索高质量文化表现的建筑作品。”在我看来,该定义含四要素——关心民生、体现公共利益、倾注人文关怀、高质量文化表现,用来启动传媒奖的系列活动,已经足够清晰、有力。同时它也足够宽泛、开放。既然说 “走向”,显然指该活动是一个动态的探索过程,旨在弘扬一种意识、一种追求,开始往前走。既然“公民建筑”是一个建设中的文化概念,就很难,也没必要一下子把它的内涵填实,外延封闭起来,塑造成一个结论性的术语。它更应像柯布的“开放的手”——给予和接纳的手,在今后的历程中,不断给予中国建筑以鼓励和提出要求,不断接纳各方人士共同参与发展出来的理念、经验和实例。
不管目前“公民建筑”的定义有多宽泛,南都对“公民建筑”的倡导意图是非常明确的:在中国社会各界积极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建筑能否在空间维度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南都作为一家以推动中国公民社会建设为己任的大众传媒,能否利用传媒奖系列活动,对中国建筑在这方面的发展,有所推动?“走向公民建筑”可以成为,也应该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过程中无数环节中与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个环节——我相信这是整个“中国建筑传媒奖”的信念基础。
“公民社会”与“公民建筑”,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但是有人不理解或不认同这信念基础,不断提出质疑:“没有公民社会,哪来公民建筑?”就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在当下中国非公民社会的状况下评选“公民建筑”,实为“缘木求鱼”。
周榕在文中援引了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其论证依据。周这样诠释该理论:“人类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生产的结果,空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反映,空间结构必须与社会结构相匹配。”由此,他得出结论:“‘公民建筑’必然是‘公民社会’的产物而非导引。中国建筑传媒奖的尴尬在于:在没有‘公民社会’基因的大环境下试图评选出‘公民建筑’,其结果,除了让中国建筑‘被公民’之外别无它途。”周榕还进一步批评设置传媒奖的理想过于虚妄:“希冀借助‘公民建筑’这一团虚假的烛火,寻找到通向公民社会的秘径,中国知识精英‘很傻很天真’的本来面目于此可窥一斑。”
首先感谢周榕提到列斐伏尔!让我本人一下子意识到列斐伏尔的理论对我们今天探讨公民建筑实在有重大意义。列斐伏尔的空间写作一贯坚持对单一空间-权力机构的批判,呼吁决策者和规划师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尊重,与艺术家、建筑师、规划师们保持密切交流,曾激发众多空间领域的知识分子和职业工作者参与1968年的社会运动,并深刻影响了八十年代法国、德国的城市规划政策。这样一位空间思想家,我会毫不犹豫地称他为一位“公民建筑理论家”!对这样一系列思想家学说的研讨,相信会为我们在中国逐渐充实“公民建筑”理念有很大帮助。
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列斐伏尔对公民空间实践产生如此
重大积极影响的理论,怎么会在周榕文中推导出一个如此消极,令人沮丧的“不作为”的结论!设想列斐伏尔本人仍在世,在深圳参加传媒奖活动后,会劝告大家识时务,放聪明点,回家洗洗睡了,等将来某天中国的公民社会“自己”实现了,会自然“生产”出个公民建筑吗?
“空间生产”,是公民的,还是 P民的?
在我看来,周榕论证的一个主要症结在于他把列斐伏尔的 “空间生产”理论理解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于是城市空间是社会中主导经济力量的意识形态的反映。但就我的理解,列斐伏尔的理论贡献恰恰在于突破了这观点。列斐伏尔明确提出空间和建筑不单单是对主导政治经济机构的消极反映,它们也可被看作是积极塑造人们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参与性力量。关注“日常生活”,而不是消极臣服于主导权力和秩序,是任何有意义的空间实践的出发点——这可说是列斐伏尔理论的核心概念。在列斐伏尔看来,恰恰因为空间和建筑是我们社会的权力关系构筑过程中的重要因素,人们——那些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主体,才有必要和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到对空间的感知、使用和生产中。
列斐伏尔喜欢举“城市节日”的例子来说明公民们如何积极进行他们的空间实践。一个只关心控制意识形态或商业消费的官僚机构,极容易生产出单调、乏味的城市空间——但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在“城市节日”中,市民们(也就是公民们)欢聚在一起,以巨大的热情和创造力,以生机勃勃的空间活动和形式,可以戏剧性地转化城市的僵死空间格局,从中人们感受到生命解放。也许在现实中“节日”效果过于短暂,也许在理论论述中“节日”概念听起来更像个浅显的比方,但列斐伏尔的确认为“城市节日”作为一种另类的、积极的、自下而上的空间实践,其策略和效果是有启发性的,值得深入探讨和推广。
写到这,我想起自己的一次类似体验。2010年12月18日,第二届传媒奖颁奖晚会的前一晚,我到深圳音乐厅听“时代的晚上——崔健2010深圳音乐会”。之前很多崔粉丝表示不解,我本人也有所怀疑:崔健洋溢反叛激情的摇滚,咋会安排到一个“体制化”的古典音乐厅中演出?更让我觉得不妙的是,观众入场时音乐厅专门出通知:为安全起见,请观众在演出过程中,不要站立,不要走动——看来整晚上就会是“崔健古典音乐会”了。但是,崔健几首歌下来,大大出乎我所料,让我终生难忘的事情发生了:在“体制化”的坐席上正襟危坐了十几分钟的观众们再也忍耐不住了。不管男女老少,大家纷纷站起来,挣脱“空间束缚”,有的跑到走道上,有的围到舞台前,一起跟着乐队狂舞。我看到一对老两口,刚开始站起来还有些扭捏,但很快便随大家进入“忘我”的摇摆状态。连分布在各层平台上负责维持秩序的保安们,居然都摇身一变,成了带头“捣乱”的啦啦队员。我目睹这一正统、高雅的古典音乐厅,刹那间被转化为一个超级大迪厅,而且比通常夜总会的迪厅音响更好,空间也更动态!这类似列斐伏尔的“节日”:人们的热情参与,戏剧性地转化了“压迫性”的空间定义和格局,大家从中获得了生命解放。我相信,不管一个社会结构多僵硬,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和热情参与,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多层次和尺度上的空间里,都蕴含着某种程度的“公民性”,或说人性绽放的潜能。发掘它们,弘扬它们,我想正是“走向公民建筑”的追求。
而周榕文中这样断言:“在基本人权都遭到蔑视和践踏的P民社会中,一切披上‘公民’外衣的建筑都必定是‘伪公民建筑’,那些所谓的‘民生关怀’和‘人文关注’,要么是嗟来的恩赐,要么是P民相互取暖的温热和小心翼翼的求取,决非堂堂正正的权利享受。”
我感觉这席话有双面含义:一方面有对不公正社会的讨伐,读起来有愤青式的激进;但另一方面也透出对价值、希望和积极变化的可能性表示不屑的虚无。我读着心里产生一连串的问题:再悲惨的社会,其内部总有人性存活的空间吧?总有人与人互相关心,表达温情的可能吧? “公民建筑师”的工作,是不是可以在这些层面上展开?难道仅靠鸟巢和水煮蛋两个被“阉割”了公民性,沦为“P民建筑”的例子,就能推导出在全中国就根本做不出任何有公民性建筑的结论?难道不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社会资源和媒体关注过于集中到那些缺乏公民性的建筑上,传媒奖才大声呼吁:“形象工程的时代该结束了,漠视公众建筑质量和空间利益的时代该结束了,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开创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难道建筑师细心为用户设计一座小桥,一个街角,几步台阶,或一个居住小区,难道那些志愿者、建筑师到灾区帮助重建,难道谢英俊、刘家琨和无止桥团队的工作,到头来都是生产了一堆“披着‘公民’外衣的‘伪公民建筑’”,都只是“嗟来的恩赐”,或“P民相互取暖的温热和小心翼翼的求取”?
我几乎要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前公民社会”中,最可怕的还不是很多“基本人权都遭到蔑视和践踏”的外在状况,而是一种内在信念的放弃:随时方便的将外在社会状况拎出来作为推脱一切的借口,全然放弃自己对公民权利的争取和公民积极改造社会的职责的担当,拒斥任何进步的可能和行动的意义。这实际上是在主动配合压迫性的体制,将自己贬为消极的P民。 “被P民”已经够可悲,主动把自己“P民化”才是真正无可救药。
谁“走向公民建筑”?
再回到口号“走向公民建筑”。这里,主语省略掉了:究竟谁在走向?哪些人在参与?
正如公民社会本来就不是天上掉馅饼,自动掉下来的,而是靠无数个有公民意识的社会成员一起努力建设出来的,“走向公民建筑”也是靠无数个认同该目标的人一起走出来的。我这里仅谈两方面力量:建筑界和大众传媒。
既然是建筑奖,其中一个主体当然是建筑界。大陆、台湾和香港的建筑专业人士借传媒奖这个平台得以相互交流。传媒奖的系列颁奖是对各获奖者的莫大鼓励,每个获奖者也都对奖项彰显的价值极为珍视,包括我本人。而本次最佳建筑奖的空缺,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周榕所断言的“意味着中国建筑集体失败”,而是评委们判定在众多认可“公民建筑”价值的候选作品中,没有一件突出的作品,能全面地达到他们确定的“公民建筑”的一系列标准。各作品之所以能被提名或入围,已经意味它们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也得到了传媒奖委员会的认可。奖项的空缺,与其看作是 “集体失败”的宣判,倒不如看作是评委会对中国建筑创作的更高期待。
同时建筑界实在不该以对峙的态度看待大众传媒。在当今中国,推动公民社会建设的主导力量之一无疑是进步的大众传媒。南都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刻理解,提出“走向公民建筑”的理念。与此同时它也很清楚自己作为一家大众传媒,不足以做太多的建筑专业判断。在现代建筑文化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仍十分脆弱的状况下,南都如将建筑评奖的任务独自包揽下来,或全然推给任一组大众传媒人士,都无法保证建筑传媒奖的品质,甚至无法保证该活动能有序的延续下去。南都的策略是发挥自己的强大组织力和感召力,打造出传媒奖这个平台,热心邀请一批认同“公民建筑”理念的建筑传媒编辑和专家上台来主持该项目,同时也邀请一些社会、文化人士成为组委会成员(如艺术评论家栗宪庭、文化评论家梁文道等),再稳步探索向社会开放的渠道。当然在连续几年的执行过程中,有很多环节有待改善,但从整体上看,至少我本人想象不出来一个比这更慷慨的姿态和更周全的操作策略了。
南都与专业媒体和专家们的分工合作,对“公民建筑”的推动力是其它任何单一媒体和组织无可比拟的。这对中国建筑文化发展是大好事。我怎么也看不出这种互动双赢的合作,何以被周榕读解成“建筑输了,传媒赢了”的你死我活的下场。在周榕看来,由于今年最佳建筑奖空缺,“建筑输了”——这点我不同意,前面已经谈过;而不管发不发最佳建筑奖,周榕认为“传媒铁定成为赢家”。逻辑是:若发这个奖,南都可以捧出个明星来;若让该奖空缺,南都则可以“转化为生动的社会事件”,“爆炒成抓紧眼球的戏剧”。相形之下,周榕甚至还分析道,后种结果更有“传播价值”。传媒奖评委和南都在实际操作时有没有这么深谋远虑、精于策划?我无从得知。但我这么看:归根结底,任何传媒,不管是大众还是专业传媒,其定义就是“传播信息的媒体”,它们当然要在乎传播力度和效果。只要认可“公民建筑”是个进步理念,只要确认传媒奖活动意义深远,南都和众多专业媒体倾全力宣传、推广相关活动,“爆炒”相关事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了解,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传媒与建筑:这个杀死那个,还是这个支持那个?
我在2008年与南都的对谈中曾提过大众传媒对建筑文化的影响可以是把双刃剑。负面的结果可能是“媒体杀死建筑”——商业化媒体的发达,容易导致读者对建筑的理解仅停留在文字和图片上,而远离对建筑物本身的综合判断,忽略建筑物背后的社会政治、伦理、公正性等重大问题,不再关心与建筑直接相连的社会现实和日常生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建筑界就该把洗澡水与婴儿一起倒掉,断然排斥和大众传媒合作。在保持足够警醒的同时,我们是完全可以积极的发掘和拥抱“媒体支持建筑”的潜能的。现代建筑史上成功例子比比皆是。在20世纪上半叶,如果没有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力推动,先锋建筑师们怎么可能发起“现代建筑运动”? 马里内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909年横空出世的《未来主义宣言》,没有局限在艺术家和建筑师圈里流传,而是首发在巴黎《费加罗》报的头版(《费加罗》当时已是法国乃至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大众传媒,或许今天中国的南都与之相当)。卢斯(Adolf Loos)在1903年办的杂志《他者》,其副标题是“一个将西方文明引入奥地利的杂志”,其中不光展开他犀利的建筑文化批判,还大谈现代男性如何穿着,美国式的抽水马桶对现代文明的贡献,等等。柯布西耶不光在1920年代和朋友办过探讨现代艺术和科技的《新精神》,还在1930年代参与编辑《计划》(Plans)杂志,推广“工团主义(Syndicalism)”思想(一种以劳工运动为主导的社会主义思潮),并研究该思潮在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上的体现。同样,20世纪下半叶的很多重大城市建筑思想发展,也是专业和大众传媒互动促成的。如1961年写出《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促成西方城市规划观念产生根本转变的雅克布斯(Jane Jacobs),本人并不是一位受过专业训练的城市建筑作家,而是个大众传媒作家。再如今天影响力巨大的库哈斯,不光他的建筑思想善于从大众文化中吸取养分,他本人极重视通过大众传媒传播自己的主张,连他自己的建筑写作风格和思考方式都深受他早期从事记者写作的影响,等等。
总之,在今天,在传媒、建筑和公民社会建设三者之间,与其不停地自我暗示“我们做不了这个,做不了那个”,最后大家都患上激愤、暴戾、无望加冷嘲热讽的犬儒病,不如更积极地探讨“哪些成功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能通过各种努力来促成一些变化”。南都在2008和2010年主办两届“中国建筑传媒奖”,已经创造出一个很多人不敢相信的奇迹——成功启动了“走向公民建筑”这个开拓性旅程。在新年之际,我为它祝福:惟愿它千万不要因为什么原因半途而废,而是能吸收越来越多同道的积极思考和建设性参与,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帮助中国建筑真正开创出一个“公民建筑”的时代!
(选自:朱涛建筑师的BLOG)
小帖士
建筑理论家周榕简介
周榕,男,1968年生。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硕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副教授。
近年来,在中国超速城市化浪潮与癫狂的建筑大跃进进程中,周榕始终保持着一个评论家应有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和批判勇气。在这一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空间巨变现象面前,他以冷静的头脑、敏锐的观察力和犀利的观点,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重视角,梳理、解析其背后隐藏的思想资源、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批判性地揭示出中国高速、盲目而无根的城市化建筑狂潮所带来的巨大危害与隐含危险。
在城市思想领域,他坚持不懈地反对宏大、超验、纯粹、理性、完美、非时间性的乌托邦城市思想模型,并对自上而下配置资源、集权式指令性安排空间秩序、严密而僵化地进行空间控制的现行城市规划和管理体制进行了系统化的学术批判,并以“微规划”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替代性的解决方案,提倡自下而上、复杂拼贴、差异多样的包容性和生长性城市组织模式。
在城市社会学领域,周榕始终关注被城市发展的物质表象所遮蔽的社会正义的缺失与社会公平的失衡。早在2004年,他就在“租界城市”的写作和演讲中指出,必须警惕利益集团通过合法的城市空间掠夺、空间固化和空间割据令城市弱势群体遭受永久化的结构性损害。此后在各种公众场合,周榕不遗余力地对这种现象进行持续的抨击,并在“2006年中国前卫建筑论坛”上就此与开发商潘石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经过全国数百家媒体报道,引发了全社会关于“开发商是否与人民为敌”的大讨论,开中国房地产批判的先河。
在建筑评论领域,周榕长期以来一直将建筑创作置于综合性的“社会空间生产”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将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思想方法引入建筑批评的体系框架之中,从而令“从形式论形式”的建筑评论拓展了自身的维度与深度。在积极推动真正的现代建筑精神在中国得到理解和普及的同时,他更加重视本土思想资源对于当代中国空间营造的积极作用,并试图将二者融贯为一个新现代中国建筑价值体系。在周榕看来,建筑应该成为人类享受自由的界面、感知世界的媒介、发掘本心的入口、重续文化根性的途径;而不应是奴役我们的强大外部秩序的帮凶、浮华时尚的模特、湮没自性的傀儡、乌托邦戏剧的演员。因此,对于时下中国流行的浅表化、时尚化、消费化的建筑热潮,周榕一直保持着足够的警惕并进行了充分的抨击。
(来源:中国建筑传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