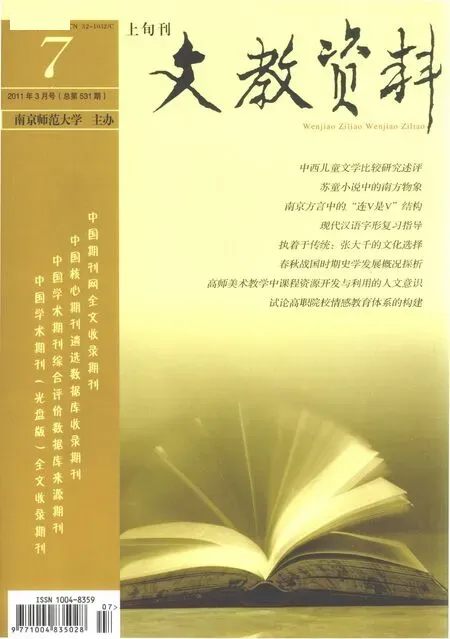王冕梅花诗创作的心理成因探究
王琦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元末诗人兼画家王冕,现存诗集《竹斋集》中共存诗719首,其中咏物诗133首,而咏物诗中的涉梅诗则有110首。可见梅花诗是其咏物诗歌的创作主流。
20世纪学界对王冕的梅花诗就特别关注,研究多以传统理论解读,大致不出三个方面:(1)从梅花诗或梅花题画诗发展的历史角度来探讨王冕的梅花诗。(2)从绘画艺术的角度来探讨王冕的梅花题画诗及其梅花诗与绘画的关系。(3)从文本解读的角度探讨王冕梅花诗的寓意及风格问题。若以文学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关照王冕梅花诗的创作,探讨王冕为何选择“梅”作为咏物诗的主要表现对象并进行大量创作,则颇能对王冕梅花诗创作的心理成因进行深层的解读。
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与作家的心理活动密切相关,文学心理学认为,人们创造文学作品,从酝酿、触发、构思到执笔写作和修改、完稿,期间有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①王冕创作了大量以梅为题材的诗歌,而驱使诗人进行这些诗歌创作的动因则来自于其强烈而且复杂的创作动机。当今文学理论界普遍认为:“在文学创作中,创作动机的实现(即产品完成)固然要依赖材料的储备和艺术发现的获得,但实际上创作动机却常常是暗中支配和决定作家搜集材料的范围及其艺术发现方向的潜在操作力量。有什么样的创作动机,实际上也就暗示了作家某一具体作品——或其一生的文学活动——在选材和艺术沉思上的走向。”②所以,探究王冕梅花诗创作的心理成因必须考虑其创作动机的心理发生。在笔者看来,王冕梅花诗歌创作动机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是创作主体心理定势的选择;二是诗人内在心理驱力的触发。
一、王冕梅花诗创作心理定势析解
创作动机的产生,离不开主体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在所有的主体心理因素中,经常起作用的是心理定势效应。人的所有活动,都是在某种定势作用的基础上发生的。作家对生活的感知,一般是在定势作用下的选择。一个作家常常会对别人认为很值得一写的事情无动于衷,而在旁人看来不足挂齿的小事,却可能激发出他强烈的创作动机来。③在王冕的诗集中,涉梅诗多达110首,而其他题材的咏物诗则比较少,像咏竹诗有16首,咏兰诗有3首,咏松诗歌有3首,咏菊诗仅有1首。可见,王冕在咏物诗表现对象的选择上很明显是受到心理定势作用影响的,而这种心理定势的作用主要是通过诗人的文化结构与其思想认识限定两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王冕的文化结构是表现其梅花诗创作心理定势的重要方面
作家的心理定势往往通过他的文化结构表现出来,这种文化结构是作家经过教育和文化陶冶而形成的。作家的文化结构对其在创作上的影响是巨大的,一般来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反映都只能从他的文化结构中诱导出来,只有纳入作家文化结构中的事实才会激发出作家的创作动机。④在特定的社会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总是带着特定文化的特质,作家的文化结构,不完全由其个人决定,从更高层次来看是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所以,在同一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们的文化结构或多或少都打上了这一文化系统的烙印,他们各自文化结构中的事实也会因此呈现出许多相似性。试想,如果梅未曾被纳入到我国的传统文化系统中,没有成为在这一文化体系陶冶下文人文化结构中的普遍事实,那么,梅也就难以激发出历代文人们的创作动机,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就不会出现大量的咏梅文学作品。
梅迎寒映雪,先春而开,高格逸韵,报春而不争春,历来为人所欣赏。梅作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表现对象,在历代文人的不断认识与发掘过程中,逐渐超越其本身的自然属性,而成为一种文化象征,被纳入到我国的文化系统之中,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梅文化。而这种梅文化广泛影响着在这一文化系统中文人的创作,并且在文人创作的过程中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梅由普通植物到文化象征,历经了漫长的过程。杨万里《洮湖和梅诗序》记载,先秦时期“梅之名肇于炎帝之经,著于《说命》之书,《召南》之诗,然以滋不以象,以实不以华也。……至楚之骚人,饮芳而食菲,……尽掇天下之香草嘉禾,……盖远取江篱而近舍梅,岂偶遗之欤,抑或梅之未遭欤”。《诗经》中《召南·摽梅》、《秦风·终南有梅》等篇,虽涉及梅,但多只言片语,且梅并非主体,此时人们更重视梅树果实的实用功能。随着社会发展与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对梅独特的花色、花味、花姿美有所认识,至魏晋时期“南北诸子……诗人之风流至此极矣,梅于是时,始一日一花闻天下”。到唐宋时期,“及唐之李杜,本朝之苏黄,崛起千载之下,而躏籍千载之上,遂主风月花草之夏盟,而梅于其间始出桃李兰蕙而居客之右,盖梅之有遭,未有盛于时者也”。⑤在唐宋文人的推崇之下,梅虽出桃李兰蕙之后,却被尊于万芳之上。而“梅花之最终上升为重要的文化象征,主要是由文学领域造成的”。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离骚》遍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矜重,‘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第一公案。”(《梅花字字香》提要)道出了咏梅文学发端于魏晋,经隋唐五代发展,至宋代激发,形成高潮的过程。宋代咏梅文学全面繁荣,梅的文人趣尚、精神气质大体浮现,相关诗集、梅谱等专集涌现。咏梅自其时成为中国文人士大夫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之一。⑦梅的精神象征价值与寓意寄托等基本审美观也于宋代被文人广泛接受,成为文坛一种普遍的共识。此时的梅已经不再仅仅作为一种物象而存在,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被纳入到我国的文化系统之中,成为文人内在文化结构中的事实。也就是说自宋代起,文人爱梅、种梅、画梅、写梅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在特定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个人文化结构的诱导,表现出一种心理定势。
进入元代,这种传统文化依旧影响着广大文人,在其影响之下,梅也依旧是广大文人内在文化结构中的重要事实。所以元代文人仍然爱梅写梅,元人爱梅,选编有大量的梅花诗集,如郭豫亨的《梅花字字香》,冯子振的《梅花唱和集》和释明本的《梅花百咏》,等等。其中元人最著名的梅花诗集当属方回辑《瀛奎律髓》第2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二梅苑》载:“方回撰《瀛奎律髓》于著题之外别出梅花一类,不使溷于群芳。”足见其对梅的重视。元人写梅诗,其梅花诗创作非常繁荣。仅《元诗选》中收入的梅花诗就有两千多首,约占宋代梅花诗的一半。元代梅花诗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时代特色。“从形式的角度而言,元代梅花诗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大型连章体组诗”。⑧作为传统文人的王冕,受传统文化的陶冶与时代风气的影响,爱梅、种梅、画梅、写梅。王冕“平生爱梅颇成癖”(《题月下梅花》),并自号为梅花屋主、梅叟、梅翁。王冕种梅,“隐九里山,树梅千株”,⑨“爱梅亦与梅与邻”。⑩(《题墨梅送宋太守之山东运使》)王冕善于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顷”。王冕写梅,进行大量的梅诗创作“写梅种梅千万树”(《梅花四首》其一)。在写梅的过程中,又强化了对梅的情感,而“赋梅赋得梅花情”(《题墨梅送宋太守之山东运使》),并且将梅视为兄弟,“青松是兄梅是弟”(《有感》)。可以看出,在传统文化的陶冶中,梅已经成为王冕自身文化结构中的重要事物,因而在王冕的实际创作活动中,梅较于其他事物更能唤起他的创作动机,表现出一种心理定势。王冕曾在诗中写道:“近来消息真堪笑,却说梅花不要诗。”(《白梅五十八首》其二七)认为需要为梅写诗。除此以外,王冕的咏梅诗在形式上也体现着元代多咏梅组诗的特色,在王冕的110首咏梅诗中,以组诗形式出现的就有6组共103首,像《素梅》58首等则是元代梅花组诗中的代表性作品。
(二)王冕的思想认识限定是表现其梅花诗创作心理定势的又一方面
心理定势“表现在思想认识对知觉范围的限定上。人对各种事物的知觉,都是在他的认识范围内发生的,超出这个范围,他往往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些伟大作家之所以能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生活现象中,看到它的深层底蕴,从而激发出强烈的创作动机来,正是由于他们对生活有着深刻认识的结果”。同理,一个对梅没有足够深刻认识的人,即使经常见到梅,也难以由梅激发出强烈的创作动机。
王冕善于画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竹斋集》中载:“冕工于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可见梅是王冕绘画作品中的重要表现对象,与王冕的艺术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画家的王冕以艺术家的敏锐对梅进行着细致的观察,因而自然会对梅有着深刻的认识。王冕对于梅的认识,在其所作《梅谱》中就有体现,《梅谱》中载:
论花花卉之中,惟梅最终清。受天地之气,禀霜雪之操,生于溪谷,秀于隆冬,淡然而有春色,此岂非造化私耶?然今贤士大夫咏之不足,而又画之幽绝,故可知矣。……
墨梅指论古今爱梅君子,与写真为花,传神自出一家,非入画科,名曰戏墨。发墨成形,动之于兴,得之于心,应之于手,方成梅格。……但要观之,不足咏之,不足精神,潇洒出世尘俗,此梅之得意入神,非贤士大夫,孰能至此哉?……梅干不老,便同桃李,老干带浓,多枯节眼,就节分梢,嫩枝带淡,无十分妆点。……
在王冕看来,梅花是百花之中最清雅高洁的,画梅必须把握住梅的外在特性方能得梅之传神。对于画梅与作梅诗的关系问题,王冕也有独到的认识。《梅谱》中云:“写梅、作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古人以画为无声诗,诗乃有声画。是以画之得意,犹诗之得句,……”所以王冕“每画竟则自题其上,皆假图以见意”(徐显,《稗史集传》),而王冕诗歌中的“梅之品题常多传入画”。王冕不仅对梅的外在形态与内在精神意蕴有深刻的认识,对梅的历史发展也有深刻的认识,在其所作《梅先生传》中就反映出了梅史。《梅先生传》云:
先生名华,字魁,不知何许人?或谓出炎帝,其先有以滋味干商高宗,乃召与语,大悦曰:“若作和羹,尔为盐海。”因命食采于梅,赐以为氏。梅之有姓,自此始。……迨周有摽有始出仕,其实行著于诗,垂三十余世。汉成帝时,梅福以文学补南昌尉,上书言朝廷事,不纳,亦隐去。……先生雅与高人韵士游,徂徕十八公山阴此君辈皆岁寒友。……天宝大历间,杜甫客秦山,邂逅风雪中,巡檐索笑,遂为知心,每语人:“仆在远道,无可与人与语,得梅先生,少慰焉。”甫为一代诗宗,心所赏好,众口翕然。于是先生之名闻天下,……人为先生叹非其所,先生曰:“苟不盘根错节,安能以别利器?”知先生者,敬爱愈重。钱塘林逋,眉山苏轼,咸以诗歌美之。盖欲以片言行者,必托先生藉口;苟非先生之为容,则语言无味。百世之下,闻其风而高之。……
这里纵贯古今,将不同历史时期与梅相关的事件穿插到一起通过高度拟人化的手法将先秦至元这一时期的梅史反映了出来。通过《梅先生传》大致可以勾勒出梅因滋得名于先秦,咏梅始于汉魏,梅因杜甫闻名于唐,因林逋、苏轼的推崇而“闻其风而高之”这一条历史发展脉络。可见王冕对梅的历史文化发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所以,对梅有着深刻思想认识的王冕,极易由梅激发出强烈的创作动机,表现出一种心理定势。
二、王冕梅花诗创作心理驱力触发寻绎
文学心理学认为:“创作动机是推动作家真正进入艺术创作过程的内在需要或心理驱力。”推动作家创作的动机是复杂的,如情感需要得到表现的压力,对文学的向往与理想、荣誉和物质利益考虑,对社会的某种责任或使命感的驱使,等等。每一个作品的创作动力,都是一系列动机所形成的合力,具体表现在作家身上,就是一种十分强烈的想写、想创作的心理冲动(即心理驱力)。对于创作动机的发生心理基础,心理学中有“缺乏性动机”和“丰富性动机”两种概念。王冕梅花诗创作动机的心理发生基础固然复杂,但大致是基于缺乏性动机和丰富性动机两个方面。
(一)王冕的缺乏性动机是触发其梅花诗创作心理驱力的基本原因
所谓缺乏性动机,就是基于人在生存中的某种缺乏或痛苦而产生的动机。这种动机的发生多基于精神上的失衡和追求,并且以一种要求重新取得平衡的内驱力而起作用。如对压迫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让许多作家如鲠在喉,不得不用笔一吐为快,宣泄心中的块垒,以求心理的平衡。像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国外的“愤怒出诗人”的说法都基于此。对于王冕而言,他的缺乏性动机的发生则基于自己入世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心理失衡。王冕幼年聪颖,闻名闾里,“宾客皆回头,指为汗血驹”(《自感》)。他勤学刻苦,又接受过系统的儒学教育,“会稽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称通儒”(《明史》卷二八五)。传统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知识分子多以参与政治、匡时济世为人生目标,王冕自然也不例外,他在《自感》中述志道:“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施勒金石,以显父母誉。”希望秉承忠义之心,使国君尊崇唐尧与虞舜,欲洗净天下的嚣薄虚伪实现民风朴实,立碑刻字留下为世人所传扬的名声,为父母彰显荣耀。因而,王冕怀着积极的入世之心,渴望有所作为,可是“屡应举不中”(《明史》卷二八五),最终“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自感》)。自己的入世理想无法在现实中得以实现,便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失衡,并在此心理基础上形成了缺乏性创作动机。为求得心理上的平衡,王冕便将自己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的理想付诸于诗歌创作中,借诗歌以浇心中之块垒,寻求一种替代的满足。宋濂撰《王冕传》中说:“冕屡应进士举,不中,叹曰:‘此童子羞为者,吾可溺是哉?’竟弃去……”王冕最终放弃了仕进,转而追求“事业留诗卷”(《漫兴十九首》其十六),用诗歌抒写自己的用世之心与怀才不遇的感慨。
在特定的时世下,诗人的入世理想无法得到实现,而有着和羹之用的梅也有类似的遭遇。“绣衣骢马金陵道,谁把梅花仔细看?”(《偶书》)诗人的心理失衡与寒梅的不遇相契合,而基于这种心理状态形成的缺乏性创作动机触发了王冕梅花诗创作的心理驱力。在这种强烈的创作心理冲动的推动下,王冕创作大量的梅花诗寄托了他怀才不遇的感慨,传达出他的入世精神。《书·说命下》载:“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是殷高宗命傅乐为相的话,以烹调喻治理国家,说明梅的果实具有和羹的实际用途,指出梅有治国之才。以后多以“调羹”喻治理国家政事,“调和”则为做宰相之喻。在王冕的梅诗中时常会套用或化用这类典故,借以表露自己的治国之才用世之心,以及怀才不遇的感叹。寒梅有“鼎鼐既不辱,风味良自珍”(《孤梅咏》)的治国之才,自然会有“他年鼎鼐调和,不改山林节操”(《梅花三首》其一)的品行,而且“岁寒寄语高人,可问调羹消息?”(《梅花三首》其三)渴望有所作为。只是在当时的时世下鲜有人识其治国之才:“和羹风致谁能解?个个花开耐岁寒。”(《红梅十九首》其五)因而无法真正有所作为,因此诗人在咏梅诗中发出“岁寒风致少能解,野草安能识此情?”(《白梅五十八首》其四)“玉雪玲珑瘦影重,不同桃李媚春风。十分清致无人解。……”(《白梅五十八首》其十)“可笑燕山人事别,春风只看杏花红。”(《红梅十九首》其三)的感叹。既为寒梅的不遇而叹息,又传达出了自己的入世精神与怀才不遇的感慨。
(二)王冕的丰富性动机是触发其梅花诗创作心理驱力的重要因素
丰富性动机则与缺乏性动机相反,它不是为了解除缺乏或痛苦,而是一种寻求刺激和满足的动机。丰富性动机超出了直接的生存需要,表现为对探索、理解、创造、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渴望。创作上的丰富动机,还表现在作家为了自我的实现而进行艰巨的创造。他们有一种要把自己的胸怀、抱负、情感、理想扩大到周围世界的强烈欲望,正是这种欲望迫使他们走上了创作之路。王冕是高洁之士,在兼济天下的入世理想无法实现的情形下便寻求独善其身,“慷慨不同时俗辈,清高多读古人书”(《水竹居》)。追求高洁清雅的情操,坚持自己不媚世俗、独立不拔的人格操守。而寒梅在“春风处处竞繁华,桃李无言亦好花”(《素梅》其十八)的世风下依旧“平生固守冰霜操,不与繁花一样情”(《素梅》其十九)的自身特质恰与王冕追求高洁的自我实现理想相契合,因而在诗人看来,“我与梅花颇同调”(《梅花四首》其三),“梅花见我殊有情”(《题画兰卷兼梅花》)。所以,在王冕追求高洁品行、独立人格等自我实现的心理基础上便形成丰富性动机,直接触发了王冕梅花诗创作的心理驱力,使诗人产生将自己的胸怀、抱负、情感、理想借助梅花诗扩大到周围世界的心理冲动。
在此心理驱力的作用下,王冕创作了大量的梅花诗。诗人将寒梅“清苦良自持,忘言养高洁”(《梅花十五首》其二),“潇洒托身溪谷,清高不染红尘”(《梅花三首》其二),“平生清苦能自守,焉肯改色趋樽罍?”(《梅花四首》其三)“平生固守冰霜操,不与繁花一样情”(《素梅五十八首》其十九)的自我操守充分表现出来,借以寄托自己淡薄名利、孤傲高洁、超逸脱俗的人格操守。《梅花十五首》其十五写道:“明洁众所忌,难与群芳时。怀贞岁华晚,只有天地知。”更是道明了梅因其高洁而遭众花所嫉妒,不能与凡花同时开放。而梅的那种不怕冰霜严寒的坚贞品质,也只有天地才能知晓。写出了坚守明洁、为众所嫉的境遇和怀贞岁晚、天地可知的那种坦荡。虽是写梅,却暗示了诗人坚守节操的决心和不畏世俗所忌的坦然。
综上所述,王冕的梅花诗创作有其深刻的心理成因,而创作心理的定势作用与心理驱力触发则是其梅花诗创作动机形成的主要原因,两者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与其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一起推动了王冕梅花诗创作动机的生成。强烈的创作动机促使王冕进行了大量且独具特色的梅花诗创作,从而让诗人在咏梅文学史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注释:
①参见王先霈著.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
②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130-131.
③参见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设,2003:149-152.
④参见钱谷融,鲁枢元主编.文学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设,2003:153.
⑤[宋]杨万里.诚斋集(卷79四部)丛刊本.
⑥程杰.梅花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的发生.南京师大学报,1998,(4).
⑦参见王峥.中国古代题画诗中的题梅诗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⑧王辉斌.宋金元梅花诗探论.荆楚理工学院学报,2010.1,Vol25,(1).
⑨[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74.
⑩引自[元]王冕著.寿勤泽点校.王冕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本文所引王冕的诗句皆出自此处.
[1][元]王冕著.寿勤泽点校.王冕集[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钱谷融,鲁枢元.文学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
[4]王先霈.文学心理学概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