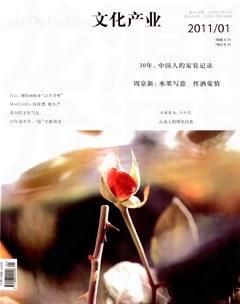古酿酱油,今时荒
慧莉
毕师傅拿来一把木勺。从竹篦子里舀出酱油来,灌满了一木桶。泛天光的酱油翻腾出酱香,在隆冬中既浓郁又清冽,“这就是生抽,顶顶好的极品,味道最浓了。”
竹篦子是两千年来中国传统酱油酿造中抽油的专用器具。在乌镇叙昌酱园的大晒场,齐齐整整的两百多只大缸,每一只缸里都有一只竹篦子,就像一口深井,并外的豆瓣酱是大地,而井水,就是酱油,留守着夏日开酿以来的沉积。每只青灰大缸都戴有半米多高的斗笠,倒扣在缸上,犹如座座城堡,气势磅礴。
毕师傅取好了酱油,给缸口拉上尼龙网纱,再罩上斗笠。过去。网纱用蚕丝做,框在竹匾子上做纱罩,现在尼龙代替了蚕丝,斗笠还是一样,每一个都写有“叙昌酱园、咸丰九年”的字样。160年前,一位名叫陶叙昌的乌镇人以自己名字为号创立了叙昌酱园,是乌镇有史记载以来最早的酱园,也是现在乌镇仅剩的一个传统酱园。在这里,毕师傅和另外几位老酱人还沿袭着中国人两千年来的古法酿造,依照农历时节,做豆瓣酱、抽秋酱油,酿酱菜和酱肉。
说起来,中国酱油的发明和自古以来中国人的爱酱密不可分。早在周朝时,酱的生产就很发达。《周礼天宫篇》中就有“膳夫掌王馈,食酱百有二十甏”的记载。那时,盐很紧缺,即使贵族也惜盐如金,倒是更愿意用盐来制酱。无论肉酱、鱼酱,盐在其发酵过程中,不仅帮助其防腐,也增加了咸味和鲜昧。当时用酱丰富,食不同的肉,用不同的酱,最后延伸出一种美食的礼制和游戏,食者往往通过酱来判断之后要上的菜,无怪,致力恢复周礼的孔夫子有所谓“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之言。
酱油在古代,则称为“清酱”,大约是要从口感上与肉酱、鱼酱的厚腻作区分,由豆瓣酱而来。没有人知道,是谁最先将豆瓣酱的酱油过滤出来,成为一种调味料,即使不吃厚实的豆瓣酱,亦可尝其鲜味。当古往今来的百姓们适逢高温的三伏便热衷于酿造一坛豆酱时,家酿酱油,成为不得不收获的副产品。
酱园,即是在家酿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古时候,“酱园”又称“酱坊”,旧称“水”当铺,亦有“荒年熟酱园”之说。这“荒年”和“熟酱”二字,即透露出酿造的苦熬,与成酱的稀微难以成正比。故此才有了集中酿造,并且通常以“前店后坊”,一家酿制,分销邻里。这就是“酱园”了。
酱园里的制酱设备主要有缸、灶,甑、竹篇、架、发酵间、园场,原料却极其简单,就是黄豆、面粉、盐。最早的酱园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史记》所载汉代就有“通都大邑,酤一岁千酿,醯酱干现……蘖曲盐豉千苔”的情景。之后的中华大地,各地的酱园不计其数,凡数百家聚落的小邑镇,必有酱园的存在,以供百姓居家之需,通都大邑内的分布则以道、里、街、区计。元代流行的民间俗语“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见必是以酱、酱油当做了经济商品,是为一种副粮,每日可以钱换得。
清朝规定,开办酱园,业主得具监生以上学衔,并由官署核发“酱帧”,也就是营业执照,是一块烙有“官盐”两字的木牌,意为“官准经营,不用私盐”。有了盐帧,就可在酱园两字前面冠以“官”字,官酱园的头衔由此而来。
叙昌酱园便是一家官酱园。
快六十岁的毕师傅已有三十年制酱经验,算得上是老师傅了。他说,如今超市里卖的配制酱油,到室内用蒸汽酿造,每天都可以酿,速度是快了,可味道上也就“过得去”而已,哪有传统酱园里的日晒雨露来的好。十二道工艺全凭学徒时的“眼看、心记、手研、鼻嗅、口试”,从搬料、汰豆、浸豆、蒸豆、拌料、制曲、制醅、舞酱、榨油、晒油、酿成出缸,作头师傅一道道把关,出缸要凭鼻嗅晒油香味,手研酱汁厚度,口试酱油鲜度来定夺。这其中的过程之考究,两千多年来,师傅带徒弟,徒弟成师傅,代代皆如此。
首先要保证用具。立夏一开始,要赶在三伏之前,洗净大缸。这是成败第一步,“忌缸罐泡洗未净”,还要确保无漏,《齐民要术》中说,“用不津瓮,瓮津则坏酱”。用水亦然,古时的办法是取大清早的井水,也就是“井花水”、“五更水”,这样一天的取水还未开始,井中水经历了一晚的沉静,也最清净。还可以用冷开水,清朝李化楠《醒园录》就记录:“做酱用水,须腊月内择极凉日,煮滚水放天井空处,冷透收荐,待又泡酱及油用,此水量益人,夏不生蛆虫,且经久不坏”。
器具完备后,制曲便开始了。毕师傅说,之所以要将制曲放在立夏以后,是因为这时日夜的温差已经缩小,利于发酵制曲。大豆洗完后,高温蒸煮过,须煮8小时,才能吸饱了水。蒸煮时豆料须逐层加入,熟时方能上下一致。蒸料不均,则酱必败。之后在制曲的小屋子里铺上竹帘子,将豆子连汁带汤裹上面粉,撒在竹帘子上。加入适量种曲,称之为拌料。豆面充分拌合后,均匀装入竹匾中发酵,这过程就是制曲了,需要三十几天时间,其间须严格控制温度,并经过两次翻曲,方能成熟。
这时的豆子就叫酱粞,看着极像鱼皮花生。之后,便只等那股难忘的潮热来临,下入缸中。不是每个三伏天都能下酱粞。据说在沿海地区,老一辈人们坚持说,断不能在涨潮的时分下酱粞,不然就要坏事,以后每日潮来,酱缸里也会不断吐泡翻沫,对于晒酱和日常生活,都是忌讳的。
一切安置停当,把长满绿衣的豆瓣捏碎,取来“井花水”,倒入盐,搅匀澄清,取清汁泡黄蒸,用手搓揉,将黄色浓汁倒进缸里。这一步,用盐是关键,汉代《风俗通义》有“酱成于盐而咸于盐”之说,毕师傅介绍,一斤酱粞,两斤盐水最为宜。之后,便是整整一个夏日三伏的“念念不忘”。酱牺在向阳通风处接受“日晒雨露”,潜心发酵,这“日晒雨露”并非虚讲,伏天里艳阳高照,需在缸口上盖一块薄纱布,挡蝇尘,且不影响日照。晚间天降夜露,需事先揭去纱布,让夜露降到缸里,按传统的说法,酱是要受得夜露精华,味道才可上佳。还须恐淋雨。夏日雨多急,一有风起云涌,得赶在落雨前给缸盖上盖子,即使上盖,也不能密封,需留出气缝,否则酱面便闷黄了。《齐民要术·作酱法第七十》中写道“雨,即盖瓮,无令水入,水入则虫生”。所以,在白天,酱园总有老师傅的看护,晚上老师傅们回家之前,也会因为夜来阴晴、是否需要加盖而踌躇,想必,如果有人值夜班,也必然睡得警醒些。
初晒十天须每日搅动几遍,十天后每天搅一遍,到满三十天时不再搅动了。这满满的缸,每一天都在烈日下发生改变,现代人说的微生物,就是酿酱的法宝,除了盐的咸味之外,鲜味、甜味、酸味、酒香、醋香的形成,全都靠它们。入缸后一百天,出三伏、酱、熟透了。这便是酱油的底子。
立秋一过,夜露显降,可以抽酱油了。立秋这天要抽的油,《齐民要术》中称为“秋油”。豆瓣酱此时可部分收缸,经过研磨成细酱,剩余的就用来抽油、腌菜。
竹篦子的样子其实和竹篓子差不多。古人们把它说成篦子,取自古代女性梳头用的那种梳子,那时的女性洗头不频繁,用梳齿细密的篦子可以梳掉头发上的尘屑。竹篾编成的竹篦子也同样纹理极细,方便拦截酱醅,又能让酱油自由通过。不消片刻,竹篦子就满是酱油了,这便是两千年古法酿造的中国酱油中,生抽、老抽之“抽”字的生动由来。
除了抽取之外,酱园里还有木头做的压榨机,把酱醅装进布包内,放在压榨机内,用杠杆原理压榨,一头是大而沉的石块,另一头,就有酱油缓缓流出了,省时也省力。毕师傅介绍,木榨机实则是抽油的末端,已经过几抽的酱醅,不能再用做豆瓣酱,再泡上盐水,灌入白布带,用榨汁机炸出最后的白原油,自然质量不如抽油。
回过头来,“抽”字当然也有“提取”之意,不需任何抽取外力。抽出的酱汁舀出注进洁净的缸,捞出豆渣,加水加盐熬煮,在太阳下再晒半月,生抽酱油经过沉淀后,取底部的深稠部分,即为老抽,口感更为浓郁、鲜美,自不是如今的配制酱油中,加了焦糖的可比得了。还可以二抽、三抽,不过,自然是头抽质量最佳,倒入白碗中,再倒出来,头抽的碗壁上还挂有一层油光,就像瓷器上的“挂釉子”一般,光灿灿的。把腌过的蹄髓、鸡、鸭、鱼置于酱油中,再过一星期后风干,酱鸡、酱鸭也是酱浓至极。
这才是古之所谓“八珍之首”的酱油——没有酱油,任由美味皆不成昧。
只可惜,像毕师傅这样幸运的老制酱人,如今已所剩无几。上世纪下半叶,近代工业科技的引用和工厂化生产,使依照传统古法酿造的官酱园渐渐落伍,生产跟不上,纷纷倒闭。即便是如此日晒雨露,不含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古法酿造酱油,除了在乌镇的旅游景区被当做民俗项目保护下来的叙昌酱园,其他的酱园公司,似乎只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里,还能寻得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