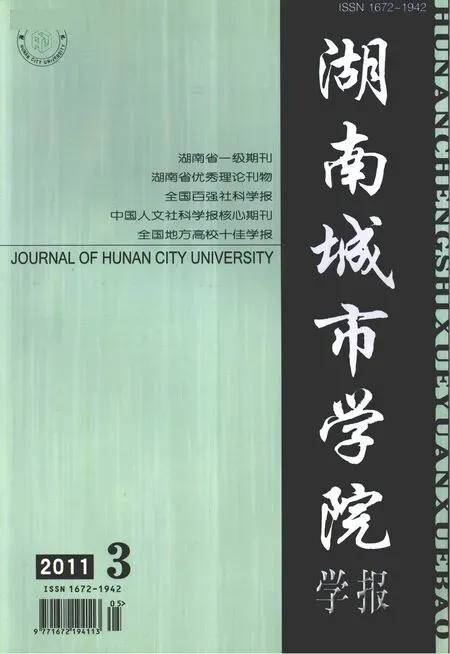论壮族作家谢树强的农村题材小说
刘纪新
谢树强,壮族,广西宜山人,因其小说多取材于农村,反映农民生活,素有“农民作家”之称。谢树强的农村题材小说大多创作于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收入《村丑》《犁头村风情画》两部小说集,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广西农村的历史性变革。
一、反映改革开放初期广西乡村的社会现实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整个广西文坛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一统天下,谢树强的小说也汇入了这股现实主义洪流,积极反映经济改革时期广西乡村的社会现实。
70年代末,党和国家调整政策,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积极调动各方面力量开展经济建设。谢树强的小说《娃他妈》《夕照青山》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在《娃他妈》中,“我”是一位生产队长,已经被文革中的政治运动整怕了,对任何新政策都持观望态度,所谓“过水看前人”。为此,他阻止“娃他妈”做队里的记分员,怕她又要搞在文革中批判过的“工分挂帅”。然而,时代已经不同了,“娃他妈”的“工分挂帅”搞起来了,人们的积极性明显提高了。小说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也明显带有配合政策的创作意图,消除人们对以往政治斗争的恐惧,放弃观望态度,积极加入到改革事业中来。在《夕照青山》中,青山大队的支书是一位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物。他想方设法劝导文革中被赶走的老中医回来工作,并把这件事情当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完成新时期总任务的一件大事”来做。
农村政策调整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领域,也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生活,影响到农民的心理。谢树强的小说《腰杆直起来了》描写了一位富农韦喜双,多年来始终在提心吊胆中度日,而今不同了,大家都平等了,他终于挺起了腰杆。正如小说中的队长所说:“这样才能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呀。”《在春光融融的日子里》描写了队长的儿媳春秀,在丈夫去世后,为了摆脱队长的控制,想独立出去,始终不能如愿。实行包产到户后,她终于如愿以偿,而且与长生开始了新的生活。《禾黄米熟》描写一个鳏夫与寡妇的恋情。早年,他们向队里提出申请,遭到斥责和谩骂。实行包产到户后,他在儿子的支持下,终于与相爱多年的寡妇走到一起。
文革后,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精神回归,作家直面现实,揭示问题,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积极介入现实。“20世纪80年代前期的壮族小说处于一个现实主义回归和深化的阶段,作家积极发挥文学干预生活、批判现实的作用,揭露批判阻碍历史进步的种种丑恶现象。”[1]231谢树强的小说同样表现了这种精神。
包产到户,积极开展多种经营,是文革后中国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它使得农村经济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根据生产力的水平调整生产关系,踏上了农村经济现代化的正途。谢树强的小说不仅反映这种历史进程,而且勇于揭露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恭喜发财》中,五叔承包队里的猪,赚了很多钱,引起其他人妒忌,队长竟然更改了承包合同,打击了五叔的积极性,第二年的承包合同没有人愿意签了。队长及时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向五叔道歉,恢复原来的合同,把五叔应得的部分归还了五叔。在《人少好过年》中,唐不穷承包鱼塘赚了两万多元,惹得人们眼红。第二年,一些领导家属也加入进来,他的收入远不如第一年了。转过年来,又有许多人要加入,唐不穷再也不想承包了,队里却不允许他退出。他告到县委,最后,县委书记出面清理了那些只想沾便宜的人,唐不穷才继续承包下去。《卖粮》描写包产到户给柳老喜带来了丰收,可是交公购粮时遇到了麻烦,粮所要求以队为单位统一交,他必须把黄豆换成谷子。正在柳老喜六神无主的时候,粮所领导经过研究,改变了陈旧的政策,允许单家独户交公购粮,柳老喜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上述问题可以说都是前进中的问题,都是在新的经济政策实施初期出现的,有的是因为政策不配套,有的是因为一些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还没有抛开“大锅饭”的思想。
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都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包产到户也触及到那些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成为改革的反对者。小说《趁着现在还早》塑造了一位生产队长“我”。文革期间,“我”很少下地做农活,常常根据个人关系安排社员的工作,还曾经对韩家媳妇动手动脚。“我”对田里的农活早已生疏了,所以一再阻止实行包产到户。但是人们趁“我”出外办事的机会把地分了,“我”不得不接受已成的事实。此后,“我”的日子再也不好过了,村民们再也不怕“我”了,人们开始挖苦“我”:不会做农活,过去却得最高的工分。韩家媳妇也斥责“我”过去总想沾她的便宜。妻子与“我”吵架,一气之下跑回了娘家。《大山的日子·牛祭》中的二幺是队里出了名的懒人,他坚决反对包产到户,想赖在队里。最后,他虽然选了最好的田、最好的牛,不但田没种好,连牛也被虐待死了。
二、塑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性的农民形象
谢树强在小说中塑造了一批具有典型性的农民形象,他们中有走在经济改革前列的农民:“娃他妈”(《娃他妈》)、五叔(《恭喜发财》)、唐不穷(《人少好过年》);有积极贯彻党的政策的农村基层干部:青山大队支书(《夕照青山》)、生产队长(《腰杆直起来了》)、黄所长(《卖粮》);也有反对改革的人:斤斤(《在春光融融的日子里》)、“我”(《趁着现在还早》)、二幺(《大山的日子·牛祭》);还塑造了一些自私落后的农民:多富(《少嫂》)、老耿(《隔壁邻居》)、二叔公和来算(《远亲近邻》)。
其中,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是极左思想的受害者,阻碍改革的农村基层干部。前者的代表是《党债》中党小组长黄裕华。土改时他是农会小组长,为站稳立场,他拒绝了与地主远房侄女的亲事,导致他直到三十多岁才娶了一个满脸雀斑的女人。“四清”期间,他为了表现积极,平白赔了集体两百斤谷子。“割尾巴”那年,本来“割”不到他,他却为表现自己坚决的态度,主动献出一头猪。这样一来,他家日子越过越穷,年年吃救济。实行包产到户,他又要了最差的田,并且不以为然地说:“共产党员就是吃苦在前。”为此,他被评为模范党员,还上县里开会。可是,一年下来,他还是要向上面去要救济。黄裕华正是一个极左思想的受害者,只注重政治表现,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继。这位年年吃救济的党小组长,显然已经不是新时期农民学习的楷模,不仅没有走在普通农民的前面,而且成了时代的尾巴。
党支书老石(《犁头村风情画》)是落后的农村基层干部的代表,他仍然用文革中形成的眼光看待农村经济改革,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仇世清在文革中曾被定为“漏划富农”,现在他通过烧砖窑富了起来,要聘请苦瓜叔做顾问。老石认为这是雇工剥削,是让贫农重新沦为长工。于是,他极力阻挠,在苦瓜叔断炊的时候,他宁愿把自己家的米送给他。听说仇世清要扩大生产,要用好田换秋凤的“水尾田”,他主动找上门去,跟秋凤换田。可是,这一切已经是大势所趋,老石只能是螳臂当车,最后,连老石的儿子也被仇世清雇去做帮工了。
谢树强小说中的农民形象不仅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农民的共同特征,而且带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地方特色,真正做到了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其中,黄裕华、老石这类人物刻画得尤为成功,应该说,他们都不是坏人,但是却成为阻挠历史进步的阻力。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可笑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个人在历史面前的无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壮族小说中,谢树强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很成功的,虽然站在今天的角度反观这些人物,会看到很多不足,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作家都能够超越历史的局限。
三、对小说艺术的探索
谢树强尤为注重发掘具有浓郁乡土特色的民间语言,这种追求从他的第一部小说《少嫂》中就表现得很明显。他在小说中这样描写玉英:“俗话说:家有千金,旁人有称。玉英人品如何,大家还不知道?”关于玉英的公公多福,小说是这样介绍的:“多福是粉球滚芝麻——凡事总想多沾点的人。”谢树强小说语言的乡土特色不仅表现在叙述语言,更表现在人物语言方面。在《娃他妈》中,生产队长“我”的语言就很有特色。当“娃他妈”指责“我”对新政策持观望态度时,“我”申辩说:“赞成我也赞成。不过我还是过水看前人,等别人……”当听“娃他妈”说明天就恢复定额管理时,“我”没好气地说:“又不是等米下锅,急什么?”“蛤蟆都出四两力,现在你见哪个不积极?”关于谢树强的小说语言,前人也曾给予好评,他们认为:“谢树强作品的语言是桂西北壮族山区语言基础上加工形成的,所以俗语、俚语随时可见,读来清新爽神。”[2]“他的语言,流畅自然,通俗生动,充满情趣。”[3]
谢树强对于小说叙事手法也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小说《趁着现在还早》、《娃他妈》、《腰杆直起来了》、《远亲近邻》都采取了第一人称限制叙事。其中,《趁着现在还早》、《娃他妈》中的“我”都是生产队长,前者一再阻止包产到户,后者对新的经济政策持观望态度,他们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以他们的视角切入小说,取得了反讽的艺术效果。
谢树强擅长短篇小说创作,这个时期的中篇小说尚且不够成熟,如《犁头村风情画》更像是一篇经过扩充的短篇小说。小说只是通过一段段的追述来扩充篇幅,情节主线的发展不足以贯穿起一部中篇小说,人物的设置、矛盾冲突的安排更像是一篇短篇小说。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壮族文坛上活跃着一批现实主义小说家,其中陆地、韦一凡、黄钲、潘荣才、黎国璞、韦编联、韦维组等人的小说题材相对广泛,而孙步康、梁芳昌、谢树强则各自经营着自己独特的题材领域。孙步康以描写小镇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而著称,梁芳昌以表现铁路职工的工作和生活而著称,谢树强则以创作农村题材小说著称。当然,由于广西地处西部,壮族作家多生长于农村,很多作家都会涉足农村题材,但是,如此专注于农村题材的只有谢树强,正是为此,他也被称作“农民作家”。
[1] 雷锐.壮族文学现代化的历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8.
[2] 维学.广西乡土文学的一朵奇葩——简评谢树强的小说创作[J].河池师专学报, 1991(2):
[3] 丘振声.一本为农民写的书——读谢树强同志的小说集《村丑》[J].南方文坛, 19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