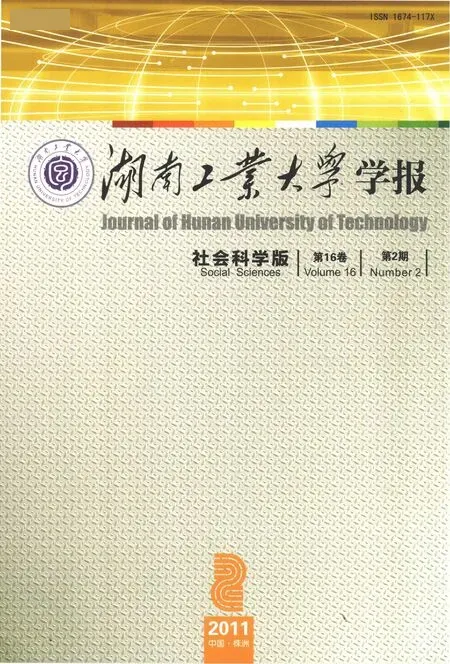犀利哥“被走红”社会与心理源解析*
罗秋明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株洲412008)
犀利哥“被走红”社会与心理源解析*
罗秋明
(湖南工业大学商学院,湖南 株洲412008)
犀利哥从一个有精神疾患的流浪汉突变为大红大紫的网络红人,其中不乏大众对犀利哥不幸遭遇的同情与关注,但事件更多的是反映出大众猎奇、从众、投射等心理动机;网络及其各种便利的链接、共享工具为人们的聚集提供了犀利哥事件的技术基础,而网络身份的匿名性则成为犀利哥事件各种不同声音寻求表达及其网络群体无责行为的安全阀门。
犀利哥;大众心理;网络传播;匿名身份
Abstract:Brother Sharp,who suddenly transformed from a mentally ill tramp to a well- known internet celebrity,has drawn great public attention and sympathy to his misfortune.But this incident reflects more of the general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s of people in the society,such as novelty,conformity,projection.What’s more,kinds of convenience of internet links and sharing tools can provide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event prorogation.In addition,the anonymity of internet identification plays the role of“safety valve”for those who try to express their own opinions and at the same time avoid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ibilities.
Key words:Brother Sharp;common mentality;anonymous identity
城市小巷,流浪汉、乞丐,杂乱的头发,脏而破的衣服——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形象是我们不难见到的,这与“走红”、“出名”看似没有什么关联。然而犀利哥,这样的人群中的一个却恰恰“被走红”了。一幅偶然在街头拍摄的照片,与大众注意力之间是怎样建立联系的?积聚起大众足以建立和摧毁一切的力量源自何处?深入分析犀利哥被走红事件,不难发现犀利哥的被走红正是其自身的身份与形象特征,经由便利、快捷的网络途径,与大众关注与猎奇、同情与投射、自主与从众等多重心理动机相契合的结果。如果说“犀利哥”纯属偶然,“犀利哥现象”则是必然。
一 心理图式的颠覆:犀利哥与大众注意力的对接点
大众心理图式的颠覆是犀利哥吸引大众注意力的引爆点。每天都有大量的信息、图片通过各种工具传上网络,但走红的却是犀利哥。这正印证了网络时代名人诞生的新游戏规则:有价值的不是信息,而是注意力。犀利哥之所以能够吸引大众注意力,是因为他“酷的外表、乞丐身份、‘时尚’造型”的统一。就其外型看,犀利哥虽然酷,但生活中这样外型的人多得很,并不见得都受人关注而被“走红”;就其身份看,流浪汉、乞丐也很多,人们在街头巷尾每每遇到他们,并不愿多瞧他们几眼,甚至想快速逃离,更不会有多少人对他们表示真诚的关注;就他的装扮而言,不知从何处捡来的破衣物,混搭出某种具有“时尚”意蕴的效果(这本身就是对时尚的一种讽刺),但生活中时尚人士到处都是,他并不显得更出众。单独就其中任何一项原因,都不可能导致犀利哥的被走红,但几种因素整合在一起就使犀利哥具有了某种独特性。“犀利哥”之“犀利”,与其说是来自他的外貌、眼神与服装,不如说来自我们这些看去正常的人因其贫穷、身份与帅之间畸形的味道与反差对他的“犀利化”。他既是乞丐,却酷,却时尚,这样由乱发、香烟、烂衣、眼神构成的另类形象的新奇和独特性,正好颠覆了人们固有的心理图式,也就具有引发人们好奇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条件,具备了某种传播的价值。也正因为这样,当犀利哥剃了胡须不再“犀利”时,很多人觉得很失望。
二 投射与宣泄的出口:犀利哥被走红的心理源
犀利哥与很多网络红人不同的是,他是被走红的,犀利哥在被犀利的过程中,其实不过是充当了一个符号而已。有人借之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有人借之娱乐和消遣一通,有人借之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他只能被动地接受甚至无所谓接受,他不能也无法应对或反抗。与其说大众关注犀利哥是因为同情其遭遇,不如说是自身多层心理动机的另类表达,犀利哥的出现只不过是为众人筑建了一个宣泄与投射的出口。
1.投射心理动机。心理投射是将自己的思想、态度、愿望等个性特征,不自觉地反映于外界事物或者他人身上的一种心理作用。在犀利哥被走红的过程中,大众评论、跟帖赋予了很多他不可能自知的标签。诸如“极品乞丐”、“乞丐王子”、“最潮名星”、“超酷帅哥”等等,然而这些都是网友调侃的解读,并不是犀利哥本人真正拥有的社会地位和素质潜力,本质上这是一种网民们自娱自乐的方式,通过这样的娱乐把自身深层的心理动机投射出来。[1]在这个意义上,“犀利哥”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人们把自己想拥有的、所缺乏的、羡慕或痛恨的东西都投射在犀利哥身上。有网友自编了《潮人乞丐歌》:“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哥行走江湖太久,也就有了传说。哥不是有型,只是为了生活,哥从不寂寞,只因寂寞总是陪伴哥。哥红遍网络,可网络不属于哥,哥行走在人群,却像是走在沙漠,哥不求名利,只求下一顿午餐是什么。有人问,有手有脚,为何要这样的存活,因为过去太多,哥不想再去选择,没有选择的选择,这就是结果。哥回忆太多,只剩下饥饿,哥不是不懂感情,因为感情伤害太多。人生原本赤裸裸,这就是传说中的哥:一支烟,往事随风去,烦恼尽解脱”。歌词借犀利哥折射了小人物的艰难与无奈。生活中许多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面前无能为力,只能做一个无聊的看客,而孤苦无助的“犀利哥”就正像是他们要找的形象代言人。同情犀利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同情着生活中的千千万万个自己,正如网友所言,“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乞丐,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无助地穿越冷漠如戈壁的繁华都市!”,“不知到哪一天,我们也会成为犀利哥!无论我们再帅再酷,我们也无法抵挡来自人性深处的阴冷寒流!”网友对犀利哥的关注可以看成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社会不公平现象和生活保障、社会支持不足的一种表达。他们通过努力帮助犀利哥,并最终帮助他找到家人,平安回家,也是在给自己的内心圆一个暂时并不能实现的梦。
2.释放生活压力。现代人身处社会转型的时代,文化认同感越来越弱,而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与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婚姻、家庭、工作、房子、车子、票子等压得人们喘不过气,迫切需要找到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犀利哥”的出现正好契合了人们解压这一心理需要。一方面,人们借“犀利哥”来表达自己因人生际遇、职场竞争而产生的各种情绪感受,如相对剥夺感、无助感、寂寞空虚感等;另一方面则又通过对犀利哥的同情显露出自身的优越感,终而获得内心的平衡。“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认为自己有地位,我们就需要有人不如我们。”[2]在犀利哥事件中,绝大多数积极参与者都是普通民众,他们相对于那些有着较高或稳定的社会地位的人来说,通常会有更强烈的优越感需要,所以很多人对犀利哥表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不断地跟踪事情的进展,了解“犀利哥”的各种信息,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帮助他,并通过各种各样的帮助增强自己的自信,找到心理上的平衡和慰籍,缓解自己内心的压力。
3.反叛话语霸权 。在社会转型时期,大众通常容易形成较强的相对剥夺感和反叛精神,人们需要对权威的颠覆、对新兴事物的好奇和追求。瑞士社会心理学家维雷娜·卡特斯对此现象有着深刻的分析:“转折阶段有它自己的规律:不久前还有效的、可靠的东西突然受到了质疑,开始时不满的情绪滋长,然后蔓延开来,生活越来越焦躁不安,新的目标出现在我们面前,开始还是模糊不清的,与其说表现为新的思想和计划,还不如说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3]在网络大规模影响人类生活前,只有合乎意识形态要求的新闻事件才有机会进入传统媒介话语生产者视野,大众无处发声,基本处于失语状态。而在网络时代,各种快捷、方便的利于人们进行相互交流与沟通的社会性工具“清除了公众表达的障碍,从而消除了大众传媒的特征性瓶颈,专属媒体从业人员的种种工作被广泛的业余化”,[4]36在这个“人人皆记时代”,新闻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进入公众意识。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可以成为媒介出口,可以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公然谈论各种社会事件,公开袒露个人的情感或精神空间,以此来实现自己的言说欲望;甚至对话精英,挑战权威,在现实生活中难以获得的关注与尊重在这虚拟情境中得到补偿。在犀利哥哄红的过程中,动力正是来自于具有草根性的普通网民们。“网络里汇聚的力量越大,说明现实生活中精神的压抑越严重。‘犀利哥’等现象可以说是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空乏与网络世界里‘无意义表达’的一次集中凸显”。[5]与其说网民们是要哄红犀利哥,不如说是借犀利哥事件,用怪诞、荒谬来反抗,并带着厌恶、攻击、热捧等方式来炒作,寻求颠覆现实生活的快感;并以此对自身空寂的心灵进行抚慰,对小人物的卑微无助寻求心理补偿,对生活、职场的压力借机释放。
三 无组织的组织力量的聚集:犀利哥被走红的社会源
跨越地域、国籍的不同年龄、身份、职业的人们为何会因为犀利哥而聚集在一起?网络及其各种便利的链接、共享工具为人们的聚集提供了技术基础,同时网络身份的匿名性则成为各种不同声音寻求表达及其网络群体无责行为的安全阀门。
1.社会性软件建构了群体互动的平台。“互联网正使得集体行动的各种形式成为可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大也更分散的协作性群体也因之诞生。”[4]31如果不是在网络时代,如果没有网民们的热议和追捧,一个社会底层小人物扬名中外几乎无法想象。犀利哥事件的发生是一个社会互动的过程。所谓社会互动是指社会上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通过信息的传播而发生的相互依赖性的社会交往活动。在网络变得无所不在之前,犀利哥即使被个别人关注,他的影响也可能只是很小范围的,因为人们的集群行为大体上只能局限于自己所属的正式群体之中。群体越大,成员之间彼此的互动越来越困难,也就是说因为传播工具的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们之间的互动影响。然而现在不同了,网络的功能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个角落,信息的传递会在瞬时发生,“任何人在任意时间发布任何事情,并且自从发布的那一瞬,它就支持检索并可以从全球访问到了”。[4]45虽然这里建构的是“一种基于话语的、临时的、短期的、当下的组合,而不是一种长期契约”,但这种传播因其主体的多元化和匿名性、传播关系的交互性、传播内容的广泛性、信息传播的即时性、信息检索的便捷性,使得网民在群体讨论中很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当犀利哥出现后,正好契合了网民情绪和动机,各种信息就交织汇聚到一起,舆论声浪排山倒海而来,最终达到了一呼百应的心理共振效果。
2.个体匿名催生网络群体的失范行为。以网络为平台的虚拟社会较之现实社会情境更容易出现个体或群体的匿名性或去个性化现象。因为参与者都无须展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个体处于匿名状态,人们暂时不再相互疏远,职业、身份在这里被取消,在这里显露出的只有一个身份——网民,因而更像奥地利心理学家洛伦兹所说的“无名群众”。无名群众的自我意识、责任感明显较弱,而被压抑的本我寻求释放的欲望得以增强,他们只接受简单而极端的感情与观念,情绪冲动、易变、急躁,易接受暗示。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对于群体心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在群体心理状态下,有意识的人格消失殆尽,无意识的人格得势。“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匿名状态下不明确的个体标志,不必承担破坏规则的后果,会导致责任分散心理的产生,理性思考和自我控制能力减弱甚至消失。而现实生活中日益沉重的生存压力使人们需要一个情绪宣泄的合法出口,犀利哥正好成为这个泄洪口,人们既可以借此自由倾泻情绪,又不必担忧责任、道义等。再加之群体行为的相互模仿、群体情绪的相互感染,个人会受从众效应的影响,跟随大流而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构成类似犀利哥事件的网络集群行动。
犀利哥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是因为它遇到了极其适应自己的当代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基础。在犀利哥事件上,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有太多太多,社会的救助体制、媒介的道德和伦理,人的价值与尊严,大众哄抬犀利哥背后种种复杂的动机与心态……不可否认的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代大众空虚浮躁、哗众取宠甚或冷眼猎奇的心理倾向,以及媒体功能的失调等问题。但从事件的背后也传递着超越事件本身的价值:首先,它张扬了人的自由个性,代表了个性自由诉求和个体力量释放的积极意义,反映出当代大众一种强烈自主意识,也表现了国人的关心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和批判意识;其次,它使人们达到了自我解压、情绪宣泄的目的;第三,它在某个侧面昭示着一种变革未来的力量正以超出人们想象的速度和方式在崛起,群体行动的各种新形式成为可能。正如克莱·舍基所描述的:“具备新能力的群体在形成,它们的工作无须遵循规律规则,克服了限制其有效性的传统桎梏。”[4]45这些在网络背景下以匿名的个体聚集而凝聚起来的群体力量,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足以建设一切,也足以摧毁一切。因此,要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让网络不再是匿名者狂欢的天堂,而成为呈现人性中善良一面的主要场所,就必须加强文化、价值引导,构建网络行为规范,重建人们荒芜的精神家园。
[1]安晓东.“犀利哥”现象下的网民心理[EB/OL].[2010- 03 - 23].http://hongfan.nwu.edu.cn/cms2008/article/2010/0323/article_18984.html.
[2]戴维·迈尔斯.社会心理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260.
[3]维雷娜·卡斯特.克服焦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09.
[4]克莱·舍基.未来是湿的[M].胡泳,沈满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5]武 菲.网络文化狂欢背后的心态解读[EB/OL].[2010-04 -05].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 -04/05/content_3167431.htm.
责任编辑:黄声波
Analysis of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Source of Brother Sharp Becoming Popular
LUO Qiuming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Zhuzhou,Hunan 412007,China)
G206.3
A
1674-117X(2011)02-0062-04
2011-01-15
罗秋明(1962-),女,湖南华容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消费心理学与高校教学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