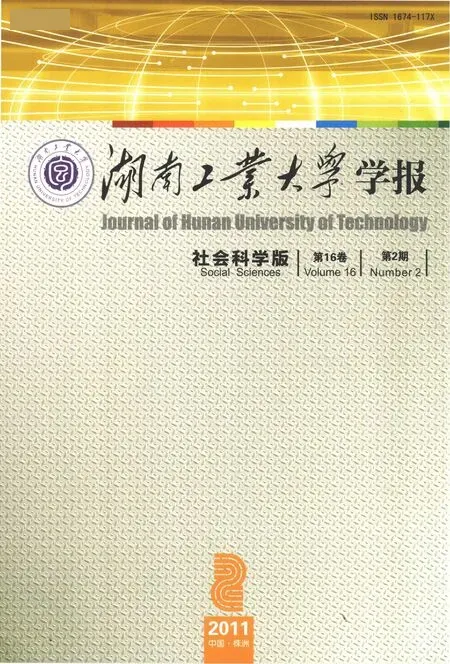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主导倾向*
邓 楠
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主导倾向*
邓 楠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永州425100)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劳伦斯一生最受诟议的著作。其作品的主导倾向究竟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社会的批判,或是对现代性爱彻底解放的极力首肯,还是二者兼而有之?众说纷纭的主题使《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成为文坛最复杂的作品之一。不论评论家对其作品作何种评判,但该小说的主导倾向只有一个,那就是倡导男女性爱的和谐统一。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性爱主题
Abstract:Lady Chatterley’s Lover is the most controversial works by Lawrence.Whether its dominant tendency is to criticize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or to approve modern sexual liberation,or both has been the focus of argument in the literary circle.No matter what the critic is,the dominant tendency of this novel is only one-advocating sex harmony between men and women.
Key words:Lady Chatterley’s Lover;Laurence;theme of sexual love
在20世纪初,即1928-1929年间,欧美文坛上最令人震惊和广受争议的一部书出版了,这就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此书的出版,首先遭到英国出版署和英国上层统治阶级的强烈反对,因小说过多的赤裸裸的性爱描写而导致他们向法院起诉,欲治作者伤风败俗的罪行。而下层民众却认为该小说痛斥了英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的生命力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是一部健康的文学作品。英国上下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这场官司旷日持久,直到1960年,法院才做最后的判决,允许该书正式出版。[1]耗时32年,虽然说不上漫长,但是以法院判决而胜诉,这在文坛上可谓史无前例。一言以蔽之,《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遭人褒贬的关键就是它的主题,或者说它的主导倾向。反对它的人,坚持该书通过男女主人公的性爱关系描写,丑化了人类,表现了低俗的淫秽的情调;肯定它的人,认为该书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是一部将社会批判性内容与性心理相结合的作品,突出强调小说的社会批判性价值。[2]笔者以为这样界定它的主题或主导倾向还有其缺陷,因而再次重申它的主题或主导倾向仍很有必要。通过有理有据的争辩,可以进一步引导该小说研究的深入开展。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它的出现为何引起轩然大波?它究竟要宣扬什么?现在让我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一看它引人褒贬的真实面目。
一 小说的主题:批判扼杀性爱与享受性爱的双重交织
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分别叫作克列福特·查太莱和康司丹斯(妮称康妮)。查太莱出身贵族,是一位矿主的儿子。康妮是一位乡绅的女儿。查太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从前线回来休假时,结识了康妮,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然后闪电般地举行了婚礼。查太莱假期结束,恋恋不舍地告别妻子上了前线。三个月后,他被炮弹击伤,返回故里。但自腰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此后,两人的夫妻生活便失掉了欢愉,查太莱变得暴躁粗鲁,康妮真正成了守活寡的贵族少妇。不久,查太莱雇请了一位森林狩猎人梅乐斯。康妮一见梅乐斯就被他瘦长精悍的身体所吸引,很快与梅乐斯成了知己,互通款曲,过上了原始的彻底的性生活。梅乐斯以前结过婚,他的妻子与人私奔。就在梅乐斯与康妮如胶似漆的时候,梅的妻子又找回来,要求和梅乐斯重续前缘,但被梅乐斯拒绝。梅妻一气之下,公布了他与康妮的不正当关系。梅乐斯只得向查太莱辞了职,前往伦敦谋生。从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归来的康妮闻此信息,便私下约了梅乐斯,要与他伦敦相会,并去信告之查太莱,他们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不如离婚作一个了结。这便是小说的基本情节和主要人物。
应该说,小说的主题并不复杂,归纳总结一下,其实就在两个字上:一是“批”,二是“立”。正如蒋家国先生所言:“死亡与再生主题在《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中是结合在一起的,两者相反相成。”[3]“死亡”就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批判,“再生”就是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肯定。他不赞成把这两方面内容加以割裂。但自小说出版后,“批”和“立”之间形成了两派,也就有了两个主题之争。所谓“批”,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扼杀人性和摧残生机,压抑和扭曲人的自然本性,特别是性与性爱的本能。劳伦斯在他的作品中力图表现:以性欲为爱情基本力量的自然本性,如何受到机械文明的摧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自然关系如何遭到破坏。而小说的这种社会批判意义又集中体现在查太莱身上。劳伦斯本人称他是“人性孤立”和“世界人类死灭”的代表。作为一个煤矿主,他把成千上万的人作为工具,加以操纵、驱使,任其摆布,而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渐渐失掉其旺盛的精力和强劲的体魄,有的人变得四肢不全,染上各种各样的疾病。他与康妮已经没有性爱关系,甚至也没有了爱情,但是他却为了贵族的家庭利益和虚假的名份需要,硬要康妮与之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可以这样说,查太莱既是现代社会罪恶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现代文明的牺牲品。一方面,他在金钱欲和权力欲的驱使下,让无数劳动者失去生机,甚至萎靡不振;另一方面,现代战争将他这个生理健全的人变成了废物。因此,现代文明,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彻底地解放人,反而将人置于没有生机的绝境,使人异化。所以,这一点足以表明英国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巨增,并未给现代人带来福祉,更多的是无穷的灾难和难以书写的罪恶。作品的这种社会批评性价值为不少评论家所认同,成为评论家替其辩护的重要的理由之一。
所谓“立”,就是指作者在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邪恶的基础上,确立的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和建立理想蓝图、实现完美人生的途径。在小说里,作者把他的理想和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集中投射到康妮的身上,而这一点使许多评论家、上层人物和贵族难以接受。他们普遍认为这是小说的败笔,因为“泛性”的描写,难以启齿的通奸已变得光明正大,人是否像作者所描写的那样已降为不受任何约束的低等动物呢?显然,作者是有意对抗既存形成的传统道德观念,这种思想的倡导,对英国社会的法制、伦理道德与秩序都是一个冲击。这是扰乱社会秩序的危险的信号。反对派的声音很是强硬。对《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误读”成为20世纪初期的一道“风景”。在“立”的问题上,笔者有着自己的看法,而这一看法恰恰不是小说的败笔,反而是小说的亮点,也是作者所要倡导的主导倾向。作者正是通过康妮对社会和家庭的反叛以及她与梅乐斯细腻的性爱生活描写来宣扬他的主张: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的欲望得以充分发挥,让性欲与情爱充分地结合起来,不再割裂它们,保持其两者的有机统一,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机械统治下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放出光彩,才能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关系。要让被工作化摧残了生机的英国重新获得活力,就必须使自然的力量重新活跃起来,而性与爱便是生命和自然力量的最高代表。因此,劳伦斯强调,拯救死气沉沉的英国的“唯一的灵药是恢复男女两性关系的自然性”。劳伦斯所主张的“通过性使英国获得新生”的观点,在我们看来,有其特殊的、阶级的和历史阶段性的含义。
首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原始时代人的性与爱是有机统一的,人所表达爱意的欲望通过性得到实现,而性不受禁忌的充分实现与满足又能使爱进一步深化与稳固。到了阶级社会后,男子掌握了社会的权力,以大男子主义为中心的男性文化开始对性与爱的问题加以控制与割裂。一方面藉口所制定的道德伦理反对宣传性欲,赞颂人的精神恋爱、精神愉悦,反对肉体的满足;一方面男性文化又以个体的强烈占有欲将女性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一夫一妻制本来是稳固两性关系、稳固家庭关系、稳固性与爱和谐统一的制度,但实际上只是限制了女性,而许多男性却没有受到制约,上层达官贵人可以纳妾,皇帝王爷可以立妃储备女嬖任自己享用。同时,统治阶级又考虑男性的利益,专门设立妓院,让具有一定经济势力的男子进妓院满足肉体的需要,解决生理的性饥渴。为堵女性之口,封建统治阶级又专门设贞节坊,树贞节牌,厚女性懿德,使女性忍气吞声,不敢有所造次。性与爱在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完全被割裂开来。男子和自己的妻子规规矩矩,真正的性满足却是妃子、小妾、妓女等女性。长期的性与爱的割裂,女性不敢谈性,望性却步,男子也不敢公开议论它,仿佛谈论它有一种卑鄙下流之感。这势必造成这样一种社会状况:男子与自己的妻子做爱都正儿八经,而真正彻底的性享受却在妻子之外的女性;女子要么得不到性欲的满足,要么得不到爱,婚姻很难谈得上什么质量。在过去,已婚女性因不能得到性满足,或不能得到爱者而提出离婚是不可想象的。男子休妻却大有人在,而休妻的理由大都是因女性姿色而起,可男性往往又找其它的藉口作为遁词来加以搪塞,谁也不愿承认是因性不能满足而致。人类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而性与爱的关系却始终没有摆正,爱情婚姻成了用金钱等级衡量的砝码,普通老百姓更加为生存而奋斗,性与爱的问题被放置一边。当人们为衣食住行而焦虑,为温饱问题而发愁,哪还有余暇和精力去考虑性与爱的满足与实现呢?所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一步加剧了性与爱的分裂。性与爱的对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家庭与社会问题。[4]此问题由来已久,只不过是劳伦斯要加以重新开掘而已。由此观之,劳伦斯“通过性来使英国获得新生”的主张是非常有意义的话题。
其次,从具体的时代背景来看,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一切唯机器而行,人成了机器的奴隶,成了战争和炮弹的牺牲品。人的关系被异化,人创造了机器等先进的生产工具,但工具反过来制约了人,人的生命力逐渐萎缩。劳伦斯显然对此大为不满,他希望恢复男女两性的和谐关系。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我们文明的巨大灾难就在于对性爱存在着病态的仇恨的情绪”;[5]3“性爱从来能够使彼此间关于温暖和激情的意识相互沟通”,“性爱是根,直觉是叶,美是花朵”;“20岁的女人非常可爱,因为这样年纪的女性性爱就会在她脸上温柔地呈现,就像在一株矮矮的蔷薇树上,到了这样的时候,蔷薇花儿就要绽开似的。所谓魅力其实就是美的魅力。然而性爱的魅力其实不外就是美的魅力而已。”[5]9他还强调说:“美既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也不是面貌上的某种安排。美是感受到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可以相互沟通的关于美好的概念。”[5]11劳伦斯还认为:“性与美是同一的,就如同火焰和火一样。如果你恨性,你就是恨美。如果你爱活生生的美,那么你会对性报以尊重。”[6]因此,“惟有以自然、清新的坦率来对待性才是上策。”[7]在这里,劳伦斯反复重申了性爱的重要性。性爱是一种美,而美无固定的模式,美是一种体验。应该说这些观点富有深刻的哲理性,令人耳目一新,给我们许多启示。总之,性爱就意味着美,代表着魅力。离开了男女之间的性爱,人类丰富多彩的生活似乎就缺少了生机与活力。劳伦斯的这篇文章写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同年,毫无疑问,他的这种观点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展示。查太莱与康妮的性爱没能实现,所以没有精神与生理的愉悦,没有欢乐,也没有令人回味的美感。而康妮与梅乐斯的性爱得到了实现,两者和谐统一,所以既有生理与精神的享受,又有生命的诞生,焕发了勃勃的生机与活力。这就是劳伦斯终生追求的目标,也是他在小说中要“立”的观点,他要宣扬与肯定的东西。小说的主导倾向清晰而明显。争辩是它,不辩也是它。这其实应验了中国的一句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再次,劳伦斯在写作《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性爱小说的时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大行其道。弗氏特别强调人的潜意识或无意识,潜意识更多地表现为人的原始欲望、原始本能。在原始本能中以“力比多”最为活跃,而“力比多”就是人的性欲、性本能。人的性欲过度压抑就会抑制人的生命活力,甚至导致精神障碍或“情结”。人的性欲必须寻找正常发泄的途径。劳伦斯深受这种精神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小说中大量描写人的性欲,以此说明工业化社会对人的性欲泯灭。所以,在性与爱的问题上,劳伦斯反对对性爱本能的任何束缚,鼓吹彻底的性解放,主张回归到充分自然的状态中去。他的人物也都是力图回避一切社会责任的“自然人”。他试图用性关系摆脱对金钱和私利的依赖,或者摆脱资产阶级虚伪的道德和所谓现代“文明”的束缚,这是进步的、合理的。但是,如果反对任何形式的限制,摈弃一切社会伦理道德的约束,这根本就是对“泛性论”的推崇。同时,在男女爱情上,究竟如何处理和认识生理的“性”与精神上的“爱”的关系?这两者究竟谁更重要?恐怕劳伦斯还是侧重于“性”。这样,劳伦斯就让人的自然生理本能取代了人的崇高的精神之爱。
二 小说的主导倾向:性与爱完美和谐的统一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这部作品“批”与“立”的双重主题,究竟哪一个是中心话题?蒋家国提出应该是两者的融合。笔者以为这多少有些折衷嫌疑。真正要确定其主题,我们认为还得依据文本的描写与作者创作的意图。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作者有他的偏爱,读者也有他的选择。可事实是:小说把“批”的内容只是作为基础,而把“立”的内容作为了主干。应该说,劳伦斯更偏重于“立”,更看重“立”。作家把主要笔墨集中于“立”上,突出强调了性与爱之间的和谐,并断言任何社会缺乏了这个“主干”,一定会缺少美,缺少魅力,缺乏生机。这是作者寻找的解决英国工业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甚至,小说家描写男女性爱关系时,又往往将大自然的美景与之结合起来,让人的性爱和谐与大自然的和谐有机统一,把大自然的美景作为人发生性爱关系的背景,使男女间发生的性关系充满了诗情画意,引发的思绪和想象不是令人作呕的淫秽画面,而是让读者根据所观赏到的美的画面,发挥联想,去进行一种美的体验,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方面来感受人类性爱的和谐美。应该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所要确立的“男女两性关系和谐统一”的主导倾向,本是劳伦斯一生所有小说的中心或主导倾向(限于篇幅,在此不述)。正如笔者在本文开头所提及的,不少评论家在评论《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和劳伦斯的其他小说时,往往强调小说的批判性主题,突出劳伦斯作品的现实批判价值,仿佛不用传统的社会批判学说则不足以估量其小说的价值与地位;而常常把劳伦斯小说中的“立”的内容作为其缺陷性来谈,肯定前者,贬低后者,甚至根本不承认“立”的内容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中心主题,好像把“立”的问题当作小说的中心主题或主导倾向来谈,就贬低了劳伦斯小说的进步性,降低了劳伦斯小说的社会价值。主张男女性爱关系的和谐这是作家力图要表现的,也是小说文本直接呈现的主导倾向,不论我们读者、评论家能否接受它,它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从某种程度说,批判社会邪恶虽然是劳伦斯小说的主题之一,但还不是劳伦斯个人创作的独到特色。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像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远比劳伦斯的批判有力得多,深刻得多。恰恰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而劳伦斯另起炉灶,重新确立一个新的领域——考察人类社会男女两性性爱关系的和谐统一。这才真正是劳伦斯小说的个性特征。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劳伦斯才引来成千上万的读者与评论家的阅读和关注。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大家才看到一位对性爱、性体验、性心理那样真诚探讨的作家。
最后,笔者还要反复申述,不论劳伦斯的其他小说有没有对社会展开批判,但强调性与爱关系的和谐,必定是他所关注的中心话题。《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其一生这一创作主导倾向的总结,是其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扛鼎之作。《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又会因读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化素养不同、所属阶级集团不同,其社会意义与主导倾向自然发生新的变化。
[1]《译海》编辑部.审判《查特莱夫人的情人》[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6:190-239.
[2]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190-239.
[3]李银河.两性关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0.
[4]蒋家国.重建人类的伊甸园——劳伦斯长篇小说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350.
[5]劳伦斯.劳伦斯散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
[6]劳伦斯.劳伦斯散文随笔集[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424.
[7]劳伦斯.性与爱[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124.
责任编辑:卫 华
On the Dominant Tendency of Lady Chatterley’s Lover
DEN Nan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Yongzhou,Hunan,425100)
I106.4
A
1674-117X(2011)02-0083-04
2010-09-20
邓 楠(1962-),男,湖南安乡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