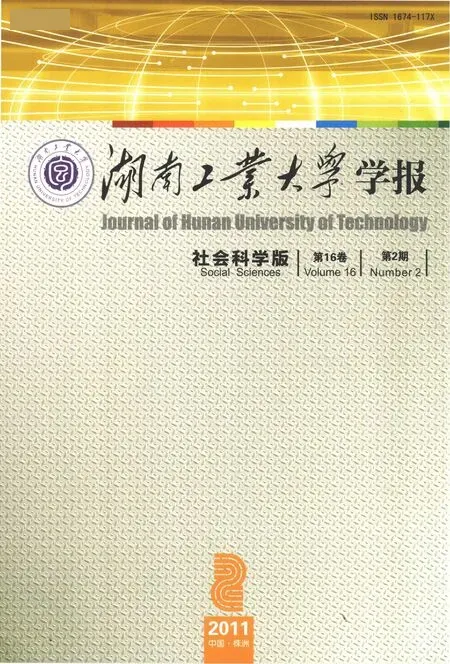唐代精怪小说谐趣的发生动因*
韩 瑜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唐代精怪小说谐趣的发生动因*
韩 瑜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精怪属于民间信仰范畴,进入唐代小说的精怪形象不仅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其富有戏谑的精怪形象描绘同时还丰富了唐代小说的艺术表现。唐代精怪类小说作品产生谐趣的动因有二:一是叙述者在文学表现手法上的刻意选择,一是心理因素上的双向认同。后世如《西游记》等作品,从唐代谐趣类精怪小说中撷取了一定灵感并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代小说;精怪形象;谐趣;谐隐
Abstract:Gremlins belong to folk belief.As Literature image,gremlins not only enriched the novel narrative space,but also enriched art style of Tang novle.There are two reasons can explain why those gremlin story produced humor:One is the narrator chose;the other is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The antient novle after Tang dynasty riped certain inspiration from gremlin story ,such as“journey to the west”,and developed it further more.
Key words:Tang novle;gremlin;humor;metaphor
民间信仰中的角色进入小说,极大丰富了小说的叙事空间。除了神、鬼之外,唐代小说中一个重要的民间信仰角色是怪。怪,即精怪。司马迁在《史记》中对精怪作了探讨:“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这里的“物”与魏晋以后小说中的精怪已较为靠近。精怪何来?精怪很早就出现在民间信仰中,刘仲宇先生在《中国精怪文化》中对精怪的定义是:“精怪就是老而成精的自然物,如山川土木、飞鸟潜鱼、走兽爬虫等,皆可因年岁久长而成为精怪”。[1]贾二强先生在《唐宋民间信仰》中则认为精怪是自然或人为之物幻化而成的怪物。[2]总之,物老为怪,具有幻化成人形等奇异本领,这应该是精怪的基本特点。民间信仰中,鬼有时令人畏惧,有时让人同情,但少有戏谑、诙谐的成分,这是人面对死亡、面对鬼魂的一种敬畏态度;神则更因为它是人们祈祷和求助的对象,因而也少有让人戏谑的可能;唐小说中,能给人提供一些喜剧色彩的,也就只有精怪故事了。小说作品产生谐趣意味有诸种原因,关键一点离不开叙述者、阅读者的双向交流。唐代精怪小说之所以产生了幽默戏谑的效果,一是因为作者叙述的主动,二是因为作者与读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双向互动。
一 唐代精怪小说谐趣的文学表现手法
根据所依附物种的不同,唐小说中的精怪大致可以分为动物精怪、植物精怪和物怪,物怪就是无生命的物品成精为怪。其中,植物精怪故事在唐小说中数量不多,且少有谐趣特点,因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动物精怪和物怪两类精怪故事,内容丰富,文学表现手法灵活,风格上也更多地呈现出谐趣特征。
(一)选材的日常性为谐趣的发生定下基调
谐趣类精怪故事一大特点就是在选材上表现出日常性和凡俗性的特点。通读唐小说中的谐趣类精怪故事就会发现,此类故事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常见或经常使用的物品,普普通通,一个木门闩,一只旧漆桶,或是一个陈年破旧的枕头,在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点,它们忽地具有了灵性,开始了一段奇妙的故事。
《华阴村正》讲述了破旧车轮为怪的故事:“华阴县七级赵村,村路因啮成谷,梁之以济往来。有村正常夜渡桥,见群小儿聚火为戏。村正知甚魅,射之,若中木声,火即灭。闻啾啾曰:‘射著我阿连头。’村正上县回,寻之,见破车轮六七片,有头杪尚衔其箭者。”[3]2943这则故事中,六七片破旧车轮幻身为群小儿,聚火而戏,其中一个被射中的破车轮片还啾啾而叫:“射著我阿连头”。把儿童的天真烂漫、喜爱玩耍赋予到精怪的身上,使得故事具有了幽默的效果。《独孤彦》则讲述了农具为怪的故事:“……俄有二丈夫来。一人身甚长,衣黑衣,称姓甲,名侵讦,第五。一人身广而短,衣青衣,称姓曾,名元。与彦揖而语,其吐论玄微,出于人表……”[3]2946这个叫独孤彦的人,深夜遇到两位谈古论今的高人,到了最后,才发现原来二人是甑和铁杵幻化而成。
作为唐小说精怪小说中的重要题材,植物精怪类故事因作品内容和主题多反映男女爱情,其选材显然更注意美感。《崔玄微》是一篇描写植物精怪和人间男子邂逅的情感类故事。同样是精怪,这里的精怪有梨树、桃树,化身为美女后,在园子里吟诗作赋,富有美感:
……色皆殊绝,满座芳香,馥馥袭人。诸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红裳人与白衣送酒,歌曰:“皎洁玉颜胜白雪,况乃当年对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风,自叹容华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绛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朵轻。自恨红颜留不住,莫怨春风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盏,性颇轻佻,翻酒汗阿措衣……[3]3112
这样的故事虽在写精怪,其主要目的却是在表现众花之美,美感和谐趣之间往往存在着一段距离,既然追求的是一份戏谑,以达到让人解颐的目的,美感就必然不在谐趣类精怪小说创作者的考虑范围之内。稀松平常之物,人所常见,感情上既没有神圣,也没有厌恶,这样的定位才容易出现谐趣的效果。
(二)模拟描写为谐趣的发生推波助澜
正如前文所言,谐趣类物怪故事不在乎形象之美,只在乎是否能否让人在谐趣中获得一丝愉悦。为了达到谐趣的效果,精怪故事通过对精怪形貌、服色和习性的模拟性描写,尽量逼真地描述精怪的形状或特征,尽量能够让读者在精怪与原形之间找到相似点或是联系,一方面达到对其原形加以暗示的目的,一方面也达到了幽默的效果。
《河东街吏》中出现的是一个由漆桶变身而来的怪物:“开成中,河东郡有吏,常中夜巡警街路。一夕天晴月朗,乃至景福寺前。见一人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吏惧,因叱之。其人俯而不顾。叱且久,即朴其首。忽举视,其面貌及异。长数尺,色白而瘦,状甚可惧,吏初惊仆于地,久之,稍能起。因视之,已亡见矣。吏由是惧益甚,即驰归,具语于人。其后因重构景福寺门,发地,得一漆桶,凡深数尺,上有白泥合其首,果街吏所见。”[3]2942对一个由漆桶变身的怪物作者这样描述:“俯而坐,交臂拥膝,身尽黑,居然不动”,这样的外形自然毫无美感可言,但当读者读到文末知道物怪的原形是漆桶后,转回头去想那个“交臂拥膝”模样的物怪,倒确实和原物有着十分的相似处,如此,文章的诙谐幽默感自然而出。再如《韦协律兄》描写了一个由古铁鼎变身而来的怪物:“……韦生以饮酒且热,袒衣而寝。夜半方寤,乃见一小儿,长可尺余,身短脚长,其色颇黑,自池中而出,冉冉前来,循阶而上,以至生前,生不为之动……”[3]2942身短脚长,冉冉前来,循阶而上,无论是从物体的长度和形态上,作者都尽量在做一种模拟,以求得逼真效果。《元佶》篇中则描写了这样一个猪怪:“唐长安中,豫州人元佶居汝阳县,养一牝猪,经十余年,一朝失之,乃向汝阳,变为妇人,年二十二三许,甚有资质,造一大家门云:‘新妇不知所适,闻此须人养蚕,故来求作。’主人悦之,遂延与女同居。其妇人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3]2948这则故事中,作者的叙述和其他故事有所不同,大多数精怪故事的叙述者在一开始并不交代物怪的来源,而是采用一种限知式叙述方式,直到最后才完成对精怪来源的揭秘。《元佶》则在一开始就以一种全知式叙述交代一牝猪变身为妇人,来至某家与人同居。正因为是全知的叙述角度,因此,猪怪的每一个行动举止就有了诙谐的特点,如“甚能梳妆结束,得钱辄沽酒,并买脂粉而已。”猪的习性是好吃懒做,此处的牝猪除好吃懒做外,多了一项女性爱美的特点,让读者捧腹。最为诙谐的一幕是“后与少年饮过,因入林醉卧,复是牝猪形耳,两颊犹有脂泽在焉。”[3]2948一个面颊上涂抹着胭脂的猪怪,让人读至此处,倍感可笑。
二 唐代精怪小说谐趣的发生心理
常人的心理特点是亲“近”疏“远”,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唐代的谐趣类精怪小说,此类故事恰多发生在与阅读者心理距离相对较近的动物或生活物品身上,反之则不然。
(一)精怪本体与人平等而非仰望或恐惧
谐趣类精怪故事通常发生在与人类彼此平等而非人类仰望的动物精怪身上。从唐小说中的物怪故事来看,物品本身就多是生活中常见的日用品,因此,人对物品谈不上什么平等或仰望的关系。所谓的平等或仰望,主要发生在人与动物之间。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从体力和杀伤力的角度来看,人对动物界的不少动物并没有多少绝对的优势,正因为如此,对不同的动物,人类的态度显然不同,而谐趣类精怪故事中的动物原型一般不会是让人类恐惧或仰望的一类动物。什么样的动物让唐人仰望膜拜?当然应该是具有超凡能力甚至有神异色彩的动物。民间信仰中某些让百姓仰望膜拜的动物乃自然界实有,如老虎;某些是人类加工想象出的非实有动物,如龙。这些具有神异色彩的动物,或是能够呼风唤雨,或是攻击力和杀伤力远超过一般人类,面对这些物种的时候,人类很难拥有与其平起平坐的从容态度,相应地,谐趣很难在此类故事中发生。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关于龙的故事还是虎的故事,出现在唐小说中更多的是追求喧奇效果,绝少谐趣成分,这也正好验证了笔者对谐趣精怪故事产生缘由的论述:人只有本着平等甚至是高高在上的态度的时候,精怪故事中谐趣的一面才有可能出现。
(二)精怪本体与人友好而非怖异
通读《太平广记》中有关精怪的篇章还会发现,唐人的谐趣往往针对那些与人类友好相处或是平常相处的动物,像畜兽类中的牛、马、驴、猪等,多成为谐趣类精怪故事主角;而类似狼、蛇、鼠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就令百姓胆寒或厌恶的动物,非但没有什么谐趣,相反还经常和一些令人惊悚、恐怖的内容关联在一起。
对虎崇敬,对狼斥拒,这是典型的汉族文化特点。同样对人类有较强伤害力,狼和虎在唐小说中的命运和面貌却迥然不同。体现在《太平广记》中,其区别在于:一是篇幅有很大悬殊,虎在《太平广记》中有专门的8卷,而狼仅在《太平广记》卷442中收有4篇故事;二是同样是精怪故事,虎故事内容丰富,有将虎神化的,有将虎视为朋友的,而关于狼的故事几乎都比较恐怖,且结局多伴随着死亡。
(三)文人游戏之笔的心态
广义而言,古典小说的创作本源于游戏之心态。小说自汉代渐兴,出于里巷,多琐屑之言,被孔子归入“小道”,小说家在创作的最初就不免有游戏戏谑的心理动因。小说如诗,“至唐代而一变”,[4]与六朝之前相比在于开始有意为小说,这里的有意,当然也包括有意的游戏之笔。正因为游戏的心态,小说呈现出一种文人风格化的谐趣。
文人风格化的谐趣之一乃吟诗作赋,互为传诵,表现在唐小说中,就是作者利用笔下人物吟诵出自本人的诗作,游戏之余,自有一种孤芳自赏的心态。《玄怪录》中《元无有》篇,故杵、灯台、水桶、破铛四种常用物品在月夜化作文人相与谈笑,吟咏甚畅,就是文人品性的一种写照。如《姚康成》篇中,一柄铁铫子、一管破笛和一秃扫帚在月夜饮乐诵诗,不无戏谑。此类小说,精怪所吟之诗大多是咏物诗,所咏之物,恰恰是自身。如《姚康成》篇中秃扫帚的吟咏:“又一人肥短,鬓发垂散,而吟曰:‘头焦鬓秃但心存,力尽尘埃不复论。莫笑今来同腐草,曾经终日扫朱门。’”[3]2948正是这样惟妙惟肖的状物,加上文人的曲意弄笔,作品的幽默感便产生了。文人游戏心态下所咏之物还离不开酒。酒是文人生活不可缺少的道具,酒具幻化为精怪当是文人风格化的另一种谐趣。《开天传信记》中《曲秀才》篇,曲秀才乃一坛美酒幻化而成的书生,来到文人的酒席上高谈阔论,被在座道士叶法善识破后灭之,结局处,众文人大笑不已。类似这样酒为精怪作乱的故事还有数十篇,由此我们不难想象唐代文人是怎样流连于酒宴氛围乃至不辨现实与幻化的朦胧醉态了。
三 谐趣与谐隐
谐和隐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两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学手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两种手法作了分别的阐述:“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隐者,隐也;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5]也就是说,谐辞是一种浅近通俗、追求喜剧效果的手法,隐则是一种曲折表达思想、追求微言大义效果的文学手段。综观上面对谐趣类精怪小说的论述,可以发现谐趣类精怪小说更多对应于《文心雕龙》中“谐”派风格,即手法的浅近通俗,追求喜剧效果。表现在唐代精怪小说中,谐趣与谐隐既有关联之处,也有显然的区别。关联之一是都要借助于“物”,不光是谐趣类精怪小说需要借助物品,谐隐类小说同样要借助动物或常用常见物品来演绎故事。如唐代谐隐类小说翘楚之作《南柯太守传》记述了淳于棼在槐树洞中的所经历的宦海浮沉,到了小说最后,读者才发现这不过是发生在蚂蚁王国的幻化故事。如果没有蚂蚁洞这个物源,谐趣就会失去大半。关联之二是文学手法运用上的相似,无论是谐隐还是谐趣,在文学表现手法上呈现出不少相似之处,比如物品和幻化之物的相似性,比如选材的通常性,比如文章结构的相似性——与异人相遇,发生故事,最后揭露异人的本来面目。当然,谐隐和谐趣两种手法的差异处也很明显。同样是游戏之笔,谐隐因为追求微言大义,社会批判性色彩较为浓厚。无论是《南柯太守传》还是《毛颖传》,作品中都承载了浓厚的社会批判内涵,在幻化故事的外表下掩藏着深刻的现实主义情怀。
相对于谐隐,谐趣追求的是喜剧性,是幽默滑稽,现实关怀比较微弱。随着文学关怀现实的要求越来越明确,作为纯粹谐趣式的小说创作逐渐式微,蕴含强烈社会批判色彩的谐隐类创作不断发展,到了吴承恩的《西游记》,作为精怪小说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好吃懒做的猪八戒,或是性急好斗的孙悟空,其身上的文学表现力已完全超越了唐代谐趣类小说中的同类精怪。
[1]刘仲宇.中国精怪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3.
[2]贾二强.唐宋民间信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253.
[3]李 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4]鲁 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1.
[5]刘 勰.文心雕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280.
责任编辑:黄声波
The occurrence of humor in Tang gremlins novle
HAN Yu
(Zhejiang police vocational academy,zhejiang hanzhou 310018)
I206.2
A
1674-117X(2011)02-0087-04
2011-03-20
韩 瑜(1970-),女,安徽滁州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